- +1
下一个季节正缓缓淡入,我想按下暂停键
“下一个季节正缓缓淡入。我想按下暂停键。”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在最新散文集《暂停键》中如此写道。2021年出版长篇小说《流俗地》之后,散文集《暂停键》于近日再版。
35岁时,黎紫书从工作了十三年的新闻机构辞职,开启全职写作之路。《暂停键》写于多年旅居之后,从北京到伦敦,从城市到乡间,她以文字重新整理此刻与过往。
时间流逝无声响,但生活需要“暂停”,需要我们“努力屏住呼吸,在这喧闹的世界尽量腾出一点空寂”。
下文摘编自散文集《暂停键》,收集了黎紫书对秋冬季节细腻入微的感受。不同于春夏的轻盈和秋的肆意,冬季的寒冷让一切变得缓慢,这或许是最适合按下“暂停键”的季节。
不妨试一试。
秋日症候群
只因为秋天朝我吹了一口气,从昨天起我便一直在打喷嚏。
这样的秋天实在酷呆了。光天化日,在人们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她像是在玩送奖游戏,一眼看中了走在法国梧桐树下的我。也许是因为我过早穿上了风衣吧。也许,是因为我在研究着行人道上的石砖,走得那样心不在焉,那样地魂不守舍而又不知身是客。
于是她迎面而来,朝我吹了一口气。多么调皮,有点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意思。于是我突然鼻子发痒,在街上狠狠地打了第一个喷嚏。
秋天为什么要选中我呢?她为什么要对我这个南国人嗤之以鼻?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路上抽鼻子、打喷嚏,又用光了一包纸巾去擤鼻涕。好厉害的秋天,好大的口气。可为什么她那样地不友好,偏要跟我过不去?
真不敢相信啊,去年的秋天明明是很友善的。直至回到住处,我看着镜子里那红了鼻子的女人,仍然以为是自己那沉睡经年的过敏症突然发作。然而一整日涕零,满脸秋风秋雨,感冒症状已溢于言表。唉,事实证明今年给秋季当值的是个不好相处的家伙。她没事怎么朝我吹气?凭什么呢?我和秋天其实也没什么交情,她凭什么这般轻佻又如此不客气?

《秋天的故事》
会是因为我岁数大了么?抑或是过去一年不小心多摄取了些化学品?什么时候我竟然变得如此孱弱,禁不起秋天的一次小偷袭。就这么一口气,便觉得秋天把她的魂魄吹进了我的身体。我哈气!哈气!哈气!
尽管遭受有生以来最具灾难性的一次感冒事故,但肉身的煎熬无损我沉迷于某些事物的意志。哈,不就伤风这点儿事吗。这整日,我一边努力抽鼻子,一边告诉自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中国古代哲人中,大概数孟子最懂得安慰人吧。可以想象他这一番话,曾经让无数寒窗苦读而怀才不遇的书生,自欺欺人地熬过多少春秋。
孟先生的好意只有心领了。可我每次站在窗前擤鼻子时,不知怎么老是生起《登高》之悲情:“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诗写得多么凄苦,几乎闻得出一种惨绝的味道。哀伤至此,灵气殆尽,便犹如《笑傲江湖》中莫大先生奏的《潇湘夜雨》,格调高不起来。可俗世凡尘,人的境界无非如此而已。英雄尚怕病来磨,想杜甫先生年老时以郁卒之心多病之躯跋涉登高,风中摇摇欲坠,自然满肚子苦水,诗意又怎么可能超脱!
老病之苦,由来最是磨人。生死无非只是两个点,老病却是两条延伸的线。想起老家一位前同事,记得过去共事时他还倜傥风流,总是一副得意扬扬的神色。近日却闻说他患病多事,在家中求妻儿将他敲晕送院而不果,竟以头撞墙求死。这种消息听得人背脊生寒,头皮发麻,毛骨悚然。尤其是在秋天吧,“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所谓伤春悲秋,秋季可正是忧郁症病发与传染的旺季。但凡文人写手,艺术细胞与音乐细胞过盛之士,双鱼座人,黏液质女子,产前或产后的初为人母者,切记要慎防叹逝、伤生、思乡、怀远等并发症。哈。

《秋天的故事》
为了对抗秋天的强大感染力,这些天我特别用心研究我的翻译。专注的程度接近沉迷,几乎达到年少时砌拼图那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境界。我砌过好些大型拼图,少则三千小块,多则五千小块。可每次砌成以后都毫无例外地把完成品解体,没有一点不舍或惋惜。这做法我自己年轻时也不甚了了,直至后来,当我已经年长到懂得以减法去数算自己的年月以后,我才逐渐了解——那最终的“摧毁”在我的潜意识中是一个完成。我赋予它意义,让它成为最后砌上去的一小块。它是一颗句号。或者说,在这潜意识的更深层,我以为这摧毁其实正是一种“还原”。它们,所有的小块,以最初的状态回到盒子里了。
写到这里,我已经不打喷嚏了。但秋天的魔法不容小觑,显然她已经在我的脑子里勾起了一些冷色调的回忆。我忽然想对谁说说自己后来怎么不再砌拼图了,尽管我现在想起来仍隐隐感到不痛快。那是因为最后一幅拼图,一幅五千小块的巨幅风景画,我最终只砌了四千九百九十九块。
最后那一小块,我怎么也找不着。
爱 别 离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仿佛候鸟,天冷了,便想飞向南国。
而天已经变冷。霜降已过,渐入冬。别以为我不知道,太阳神每天都在稍稍改变他的航道。每天清晨,我在梦中听到阿波罗的黄金车与彻夜赶路的载货卡车一起辘辘驶过;他下午五点钟准时下班,倒是未曾闻车辚辚马萧萧,而苍天却在目送红日西驰后,于顷刻间萎靡。常常是那样的,只要偷个懒闭目养神,再睁眼便看见白天已然落幕。这总会令我错愕,感觉像错失了一场电影的大结局:怎么可以就这样把黄昏省略掉呢?
这几日天色看来不很健康,老天爷的脸与经济局势一样暗沉。太阳神的黄金车改成铜制了,别以为我不知道。白天正被悄悄裁剪,人们身上的衣料却在与日俱增。叶枯草败,秋去冬来。唉。我听到了,北方以北,冬如愤世嫉俗偏又千年不死的白发魔女,正在某个山头散发扬鞭,生风虎虎。

《冬天的故事》
去年陪了我整个冬季的毛衣,终于又重见天日。这毛衣随我从老家过来,以前都没见识过真正的寒冷。就去年一个冬季,它好不容易才千帆过尽,而今其色已衰,其形亦残,有两枚扣子凋零着呢;萧萧其观,瑟瑟其状,似乎比我更畏寒。
可我说过不会把这毛衣扔掉。毕竟它曾经给过我相当于一头绵羊才能给予的温暖。我把记忆、希望和一些主观而私密的情愫编织其上,让它比皇帝的新衣更要神秘;本来无一物,偏会惹尘埃。倘若你仅仅是个聪明人,倘若你仅仅有点小智慧,你终究无法心领神会。而你若领会了又当如何?一切有为法,不过如此而已——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这是《六如偈》。它让我想起号六如居士的唐寅,或东坡之妾王朝云。朝云临去,诵《六如偈》以绝。可我每次想象这场面都觉得怪诞。朝云有情有义,相随被贬的东坡同去惠州,此后不离不弃,怎么想都像是个心有所执、志有所守的人。可她卅四岁香消玉殒时叹的是万法皆空,吟的是《六如偈》,梦幻泡影露电,而不是来两句“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这情诗读来总觉得过激,与《六如偈》适得其反。这样的句子或许更适合我心目中司冬风与怨恨的女神练霓裳。她爱得多么偏执而暴烈,不该给她一个季节吗?让她不死,长命无绝衰,如《荷马史诗》中受罚的西西弗斯,每年乘寒风而至,到哪个结冰的湖上明镜悲白发。
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很长吧?王朝云临终时只念了其中的《六如偈》,共二十字。这二十字自然不是她通往西天极乐的咒语或暗号,大概是念给守在病榻旁的人听的,诸法空相,勿念。若作如是观,便倍感王朝云的良善与体贴。时年东坡已花甲,算是送黑发人吧,尝的是八苦中的“爱别离”之苦,也许比死更难受。于是王朝云告诉他,自己这肉身与两人这些年的恩爱不过都是幻影,now you see it, now you don’t。
我是不懂佛经的,就像我也不懂得《圣经》、艺术或哲学一样,我总以为在它们面前,“懂”是一个肤浅而拮据的字眼。但我活着需要一些信念,好助我对抗厄运、诱惑、幻影、不如意事、死别、生离。于是我从这些圣贤先哲的文字上东抓一把西拈一些,自行组合与配搭,像在缝纫一床属于自己的百家被。而因为笃定与虔诚,不意竟让它成了一种超越人生观,却与宗教不太相干的信仰。
我们都是这样活着的。相信我们所相信的真理,追求我们所确立的价值。自然界的四季有序,人世的季节无常,冬天这厮总会不定时地强闯,想要统辖我们的岁月。所以我很庆幸能有那样的一床百家被,尽管它也许有点寒碜,正如此刻披在我身上的这一件毛衣。但它确曾被严冬验证过了,不是吗?我还好好地活着。

《冬天的故事》
冬天来了,黑夜也来了。我得打起精神呢。就凭这些宗教与哲学的碎片,与一件像干草编织的毛衣,我又得迎战白发的练霓裳,与黑衣的梅超风。
射手座人语
我回去,我回来。
终于,不论在这里抑或在那里,我都得对人说“待我回去”。回去怡保,回去北京。两边都是起点,也都是归宿;不管我身在何处,都意味着别离。“回”这个字依然无解,它那涟漪般的形象让我神迷,是要扩张呢,抑或在收缩?愈想愈觉得有那么点玄幻。
一回来气温骤降,仿佛过去一整个月,这儿的冬季都在苦苦隐忍,不等到我回来便不肯发作。于是她用四五级的北风与零下的温度拥抱我,而因为旅途劳顿,机上夜不成眠,在热切渴望着十楼小房子那一床凌乱而温暖的被窝时,我居然感觉到这冰冷的拥抱里有一座城市熟悉的体味,有欢迎的温度。(遂想到俗气之极的歌词之“我家大门常打开……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但此城依然不是我城,出租车司机的口音我终究不太听得懂。这不懂便也是一种熟悉和亲切,仿佛似懂非懂才是常态;这样若即若离,将信将疑,说不清是生分抑或是熟稔的状态,才能让我感到踏实与心安。因为这是座能收容我却不需要我付出爱,或给予太多关怀的城市。我像个借宿者或是个食客,行走其中却不会有太多的感情负担。这所谓祖国,所谓原乡,成了我岁月中的宾馆,生命长旅中的驿站。

《李米的猜想》
迁徙与赶路成了常事,漂泊感便随华发渐萌。我在一再转机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离散”这个词,它漂浮在我的脑海,一闪一闪地,像个求救信号,或一盏坠落海上的星星。
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里遇上一个老太太,因为太早抵达机场了,她有点过于热衷地对我这陌生人述说她此生的迁移,从桂林到天津,从中国到美国,然后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酌量分配自己的年月和余生。七十多岁了,老太太身体健朗,话说得不无炫耀的意思。可这于我有什么好羡慕呢?到了那年纪,我大概已不想再出远门。我会想要一个小庄园,努力把大岩桐和风信子种好,收养一两只愿意听我唠唠叨叨的狗儿。如果情况许可,也许我会想把庄园改建成小旅舍,然后像只蜘蛛守在网中,等待疲惫的旅者,好偷取他们的故事。我甚至拿不准自己是不是还需要一间书房,也许我宁愿选择一台手风琴或一个很好的烤箱。不管怎样,我知道我不会再向往迁徙了,我不会想坐在候机室里要陌生人猜测自己的岁数,并向她数算自己曾经的所到之处。
告别老太太时,我记得自己说了“希望有缘”。老太太一脸怅然,对我说,恐怕很难。“以后我坐的飞机不会在广州转机了。”也许我曾经回以一笑,也许我表以一脸抱歉,但我确知这样的机缘巧合与“飞机在何处转机”无关。真正的关键是:人海茫茫。正因为人海茫茫,大千世界的航线错综复杂千丝万缕,正是一个玩捉迷藏的好所在。我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借躲猫猫而遁迹,可以要来便来要去便去。真的,我们躲不过的唯缘分和命运而已。而除了它们,还有什么可以把人与人圈套在一起?

《李米的猜想》
回来后终于又可以惬意地写字读书。十楼够高了,仗着暖气,这几日我多半垂下窗帘,把灰蒙蒙的原乡和异乡都关在窗外,好让自己别再去意识我在这广大世界中的位置。可就在我安心地藏匿在连缘分也找不着我的角落时,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说的一句话却像圣诞树上的一长串小灯泡,总是在我幽暗的心灵秘境中忽明忽灭——“对待一个喜欢躲藏生活的生物,唯一适合的应对方式就是尽量去捕捉它。”
所幸这世上没有多少个像奥尔特加这样的猎人,因此我可以安心地、像随季候来去的燕子般伫立在横跨一座城市的某条电缆上。看看下面人头涌涌,城规划得如同蚁穴。四季更迭,流光暗换。城市从原乡变成异乡,或从家乡变成故乡。我指着密密麻麻涌动的人群,对倒挂着的自己的影子说:看吧,那些迷路的“朝圣者”。
二 月 雪
这是个平常不过的二月天。我站在窗前,怀疑你怎么在生命中经历过的许多个二月天里辨识它呢?我这儿初春了,气候正逐渐回暖,尽管站在落地窗前垂目下顾,仍然可以看见楼下的草坪有去年冬天最后一场雪的残迹与残雪上蜿蜒不知所终的足印。
我在这里。我曾经在这里。窗玻璃上留着我温热的鼻息与微凉的指印。
这里是十二楼,举头天上低头人间。城市在外头,在渐渐消去的鼻息与指印的另一边。行人只是些蝼蚁般缓缓移动的小黑点,大街上的车声多被摒绝于小区的围墙外。这意思,真似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我喜欢从描绘景致开始,喜欢用季节和天气这万能的钥匙打开一切话匣。它有一点预告地理位置的意图,像是不等我的朋友开口便抢先打发了他们已习惯得浑然天成的提问:你在哪里?你那边几点?天气可好?
事实上,如果不提这些变化的景致,我们或许再难找到其他什么更能表明岁月的动静。
而我以为朋友们的提问虽有“祝愿你生活平静,无险无惊”的意思,却也未尝不期望着用这些小问号去垂钓平湖深处可能隐藏的波澜。这些朋友多是我的同辈人,年龄相若,即便未必都经历过相似的生命情景,人生也已走到了相近的阶段;生活已层层胶着在现实的窠臼里,也都无可奈何地逐渐触知了人生的瓶颈。年轻时曾经让自己满心仿偟与满怀期待的未来,如今再没有多少未知的模糊地带。存在的状态已然落实,每个人都觉得现状既圆满又缺失。人生正在凝固,“未来”的不可预知性与憧憬的色彩在逐日减退;生活淤积了不能舍下的人与事与情与物;愈来愈多平常不过、难以记认的二月天或三月天或四月天堵塞在日子的档案柜里。

《本杰明·巴顿奇事》
在这些朋友眼中,我的壮年出走就像我少年时持续至今的写作一样,是件神秘、冒险而多少有点浪漫味道的事。每年回乡与故友聚首,我总会在友人们小心翼翼的探询口吻与闪烁不定的目光里察觉出他们的好奇、想象和怀疑。
那是个怎样的世界?你那是怎样的生活?
他们就像多年前在下课时吃着便当听我即场编造鬼故事的小学同学那样,如今仍然睁大眼睛,坐在餐厅里听我述说异乡的生活。说真的,这样的关注并未让我感到备受关怀或祝福,我只觉得人们需要我说出更多充满异国风情的细节好托起他们业已衰萎的想象之翼,借此让那一双快要麻痹的翅膀再去感受生活的流变、时光的速度,以及梦的动向——那些已被移植到孩子身上的一切。
却没有多少人想到,世界再怎么辽阔,生活本身实在只有车厢般大小。那上面的乘客不会有太多变动,也因为座位所限,我们不会与其中多少人发生故事。更多的时候,我们唯有靠着窗外不断涌现也随即流逝的风景去感知前进,或期待着与下一站上车的人相遇。
我心里也清楚,朋友们的坐乘已是停着的时候多,行进的时候少。窗外的风景停滞,车上的人物关系不变。因为缺乏可以目睹和感知的变化,时间作为记录运动与变化的参数,遂渐失意义。
而我因为畏惧停留,便频繁地下车、换乘、转站,屡试不爽地拿我的写手名片向陌生人换取故事。
有时候也掏出一点情感来,与路上相遇的人发生点纠葛,给这匮乏的世界创造一些可以托起想象之翼的故事。

《本杰明·巴顿奇事》
现在我说的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今天才有的想法。每一回我走在异乡城镇的大街上,尤其是在即将离开之际;有时候是看见自己的身影在每一家商店的橱窗玻璃上穿梭,有时候浏览着车窗外缓缓掠过的店铺招牌,或是听着司机压沉嗓子以我听不懂的语言对电话里的人叮咛什么,我都禁不住感慨自己竟又走过这些地方,遇见过好些人了。
我在这里。我曾经在这里。尽管印在窗玻璃上的热息与指印皆已消去。
这样就很好,我也不多求。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扮演着当年的说故事者,并且逐渐实现理想,拥有一扇能看见世界而世界无法看真切我的窗口。对我而言,“说故事者”本身就像穿插在这真实世界里的一个虚构的角色,她也像我随意编造的其他小说人物一样,几乎如同谎言——因为编造了她,从此我就得对她负责,让她圆满,使其有血有肉。
而此刻她在这里了,我们都站在这里,一起凝视热气与指印消去后的窗外的城市。把这个二月剪辑一下吧。咔嚓。去年华丽的冬雪已残,今年的第一场春雪悄悄落下。
本文节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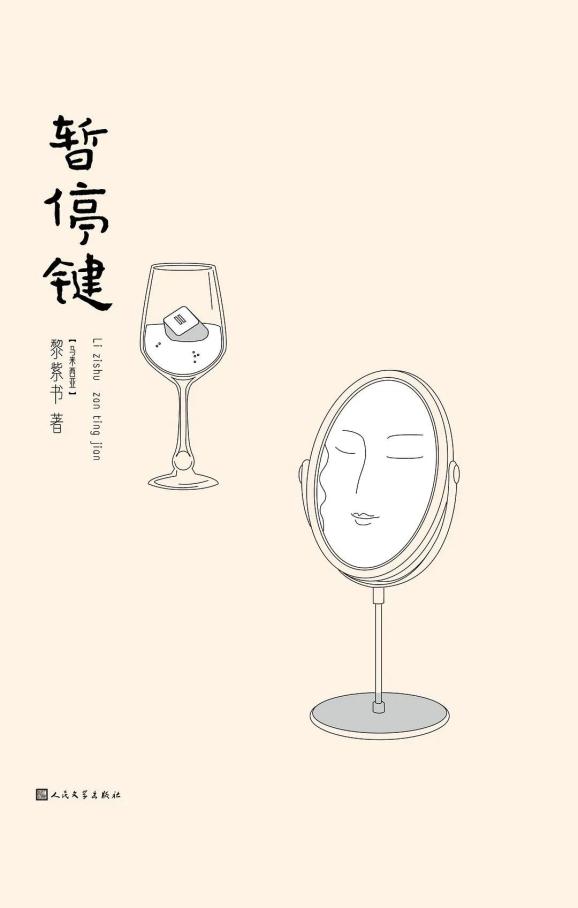
《暂停键》
作者: [马来西亚] 黎紫书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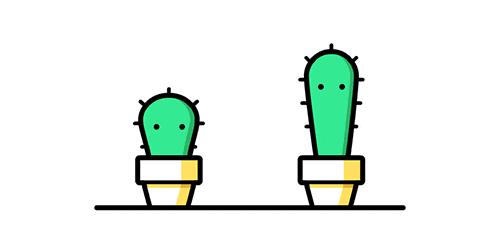
编辑 | 驼驼
主编 | 魏冰心
原标题:《下一个季节正缓缓淡入,我想按下暂停键》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