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宗白华:从哲学走向诗
2022年11月10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浪老师做客“朝内166文学讲座”,为广大读者做了《从文体追求看宗白华的散步美学》的主题讲座。金浪老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批评理论与批评史方面的研究,曾获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评奖一等奖、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美育学论坛优秀论文奖等。以下为讲座节选。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宗白华先生是以主编《学灯》著称,他与郭沫若、田汉的通信结集为《三叶集》出版,在新文学的发生阶段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他也是郭沫若的伯乐。郭沫若的诗,最早就是由宗白华先生在其主编的《学灯》上发表的。宗白华在文学创作上则以“小诗”闻名,他的《流云》小诗常常与冰心作品一起,被认为是新文学小诗创作上的重要收获。
但从散文角度来关注宗白华的视野却是罕见的。我想,但凡读过宗白华文章的人,恐怕对于这个认识又都能心领神会。因为宗白华的文章,哪怕是他那些在美学领域久负盛名的学术性论著,也都有着他自己独特的文体追求,打上了他个人浓厚的风格印记。这一点虽然我们都能感受到,却没有把它拿出来作为问题加以考察,这是很可惜的。这本《宗白华散文》的价值恐怕正在于此。
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很少从文体角度关注宗白华,他独具特色的文体追求与他的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恐怕就更是我们关注不够的问题。所以,下面我将从这个角度出发,和大家一起重新回望一下宗白华先生的美学。
一 从散步谈起
我们从什么地方讲起呢?就从宗白华最负盛名的“美学的散步”这个说法开始吧,因为这个说法早就已经成为了我们对宗白华美学的一个通行概括。
在通常我们的认识里,宗白华先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久负盛名的两大美学家之一,另一位是朱光潜先生。他们俩常常被推崇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双峰”。这个说法自叶朗主编的《美学的双峰》一书以后就成为了美学界的共识。不过,这两座高山上的风景又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各有独特的风光。

首先,在著述体量方面,两人就很不一样。朱光潜可以说著述鸿富,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光潜全集》就有二十卷,后来中华书局又重新出版了一个新版全集,达到了三十卷。而宗白华的论著就要少很多,由林同华主编的《宗白华全集》,著述加上译作,再加上一些未发表的笔记大纲,总共才四卷。
其次,朱光潜的著述以体系性著称,无论是他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早期著作《文艺心理学》,还是后来以一人之力完成的两大卷《西方美学史》,都属于对西方美学的体系性认识。宗白华的著述则是非体系的,甚至反体系。他的美学常常被称为“散步美学”,就跟这样的反体系追求有关系。
1981年5月,宗白华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一部文集《美学散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一年在台湾洪范书店也出版了一本宗白华文集,书名叫《美学的散步》。两个书名差别仅在于一个有“的”,一个没有“的”。可见,无论是大陆学界还是台湾学界,都不约而同摘出“美学散步”的说法来致敬这位美学大师。
“美学散步”这个说法其实来自宗白华本人,原为宗白华于1959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同名文章《美学的散步》。这篇文章是宗白华在美学大讨论背景下写出来的。当时的美学界主要围绕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对美学的解释,各家观点都不一样,有主张美在客观的,如蔡仪;有主张美在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如朱光潜;也有主张美在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如李泽厚。宗白华与他们都不太一样,这篇《美学的散步》放在当时的美学大讨论来看就显得与众不同。虽然这篇文章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它却传达出来了宗白华对于美学的理解,并且还是与其他诸派都不一样的理解。

文章的开篇就抛出了“散步”的说法:
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与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观看鹏鸟、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芬奇在米兰街头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戏画”,现在竟成为“画院的奇葩”。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
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是我们理解宗白华美学的一把钥匙。刚才提到,这个说法与美学大讨论中诸派都不同,他更像是一位旁观者,他打出的旗帜是“散步”。而“散步”不仅仅是审美的人生态度的表达,也是宗白华文章的文体追求。如果说朱光潜的著述更偏于体系性的构建,那么宗白华则更多采取了一种自由、随性、散漫、娓娓道来的方式来探讨深奥的美学原理。而要进一步了解这一文体追求的形成,还必须从宗白华先生的学思历程、生命成长过程中去寻找答案。
二 从哲学走向诗
宗白华很早就显示出了对哲学的浓厚兴趣。他十多岁在同济医科大学学德语的时候,就对德国哲学产生了兴趣。作为优秀毕业生毕业时,学校赠给他一本书,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虽然一度钟情于康德哲学,但宗白华的第一篇哲学论文的论述对象却不是康德,而是叔本华。这就是1917年6月发表在《丙辰》杂志第四期上的《萧彭浩哲学大义》。“萧彭浩”就是叔本华。后来他又发表了《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康德空间唯心说》。可见,宗白华的哲学兴趣是从德国哲学家康德、叔本华开始的。
不久后宗白华的哲学兴趣里又增加了一位,这就是柏格森。熟悉新文化运动的人都知道,柏格森哲学作为一战后的新思潮被引入中国,一度非常流行,很多人都受到过柏格森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宗白华也开始研读柏格森哲学,而且是把康德、叔本华、柏格森放到一起来理解。随后他便发表了《读柏格森创化论杂感》。这篇文章不仅接受柏格森的唯意志论哲学,而且还把康德哲学跟柏格森嫁接在了一起。在宗白华看来,柏格森和康德都反对机械的唯物质论的世界观,都带有唯意志论的特点,都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唯意志论哲学对宗白华影响很大,后来,他正是沿着这个唯意志论的道路,开始走向文学。宗白华担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编辑时,从来稿中发现了郭沫若。由于当时郭沫若远在日本,两人只能通过书信的方式交往,后来田汉也加入其中,三人的通信后来结集出版为《三叶集》。宗白华特别欣赏郭沫若的诗,甚至说“你的诗就是我的诗”,这话里带有浓厚的泛神论色彩。郭沫若则问为什么你自己不写诗呢?于是宗白华在回信里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答复:
你是由文学渐渐的入于哲学,我恐怕要从哲学渐渐的结束在文学了。因为已从哲学中觉得宇宙的真相最好是用艺术表现,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出的,所以我认将来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我将来的事业也就是尽力加入做这首诗的一部分罢了。(我看我们三人的道路都相同。)但我现在的心识总还便在理解的一方面。感觉情绪也有些,所缺少的就是艺术的能力和训练。因我从小就厌恶形式方面的艺术手段,明知形式的重要,但总不注意到它。所以我平日偶然有的“诗的冲动”,或你所说的Inspiration,都同那结晶界中的自然意志一样,虽有一刹那顷的向上冲动,想从无机入于有机,总还是被机械律所限制,不能得着有机的“形式”(亚里士多德的From)化成活动自由的有机生命,做成一个“个体生流”的表现。我正是因为“写”不出,所以不愿去“做”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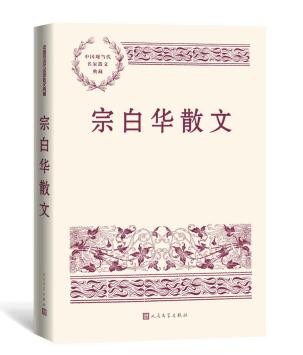
这段话对于理解宗白华太重要了。在那个时刻,他已然表达了想要投身于文学的冲动。当他认识到真理无法通过概念的、抽象的、机械的、逻辑论证的方式获得,而只能通过艺术的方式去获得时,诗歌、艺术、文学也就成为他的选择。但麻烦的是,尽管有冲动,有灵感,却无法将之行诸笔端。宗白华解释说我在这方面还缺乏训练,虽然有“诗的冲动”,却找不到“诗的形式”。最后一句“我正是因为‘写’不出,所以不愿意去‘做’它”也很重要。“写”是灵感的自由流露,而“做”属于为形式而形式。宗白华当时的苦恼正在于此,不愿意“做”,但又“写”不出。而或许,这个有关形式的苦恼,恰恰构成了宗白华文体追求的起点。
三 《流云》小诗的诞生
创作的契机很快就到来了。1920年5月,宗白华从上海出发赴德国留学。这为他接触西方艺术作品提供了机会。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参观各地的艺术馆、博物馆,那些过去只在文献中出现的艺术品,常常令他流连忘返。比如在路过巴黎的时候,他就和徐悲鸿一起参观了卢浮宫、罗丹雕塑展览馆,两人都对罗丹雕塑膜拜不已。其次,身处异国他乡也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独处时间。正是这种独处中的思绪连篇为他带来了写诗的契机。留德时期宗白华写下了大量小诗,这些诗作一开始被寄回国内在《学灯》上发表,1923年由亚东图书馆结集出版,这便是《流云》。
《流云》之所以被称为小诗,是因为它们篇幅都很短小,但同时又极具哲理性。这当然与宗白华的哲学兴趣有关,只不过,这时他的哲思已找到了自己的形式,不再是哲学家式的概念的、逻辑的运作,而是以诗的形式呈现于笔端。这是宗白华的重要时刻。因为有了这个时刻,他过去梦寐以求的形式渴求,终于实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流云》中很多诗作都标了“无题”,即没有题目。为什么没有题目?恰恰就在于无法提炼题目,因为这些诗作是宗白华生命体验的流出,是不自觉地带有半自动性地将自己的思绪付诸笔端,成于形式,诗兴难以捉摸,因此也难以概括。宗白华后来说他自己也概括不出来,他甚至自己都不清楚这首诗讲了什么。这是一种奇妙的创作体验,尽管如此,宗白华仍旧竭力地将之记录下来。后来他有一篇文章叫作《我与诗》,里面不仅回顾了他自己走上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更重要的是还记录下了他在异国他乡开始写诗的心理状态:
1921年的冬天,在一位景慕东方文明的教授夫妇的家里,过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夜晚;夜阑人散,踏着雪里的蓝光走回的时候,因着某一种柔情的萦绕,我开始了写诗的冲动,从那时以后,横亘约摸一年的时光,我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着。在黄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在大庭广众中的孤寂,时常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彷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仅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我的《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
这段文字写得实在太好了!虽然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的创作谈,但很少有像这段话这样能把自己创作的情绪、冲动细致入微地记录下来,让无形冲动转化为有形的文字。这段话描绘的情绪非常细腻,非诗人难为也!这时的宗白华已不仅仅是哲学青年,也成为了真正的诗人——能够将自己的诗兴转化为文字的诗人。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宗白华的诗歌创作非常重视体验,这除了他自己的创作经验外,也跟当时德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对体验的重视有关,比如狄尔泰的《体验与诗》便是这方面的著作。
宗白华留学德国时期,一方面是有了创作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当时德国的美学、艺术学相关理论,开始形成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这种思想上的渐趋成熟是在与创作的互动中完成的。强调生命,强调体验,同时赋予生命和体验以艺术的形式,成为宗白华文艺论述的理论模型。后来宗白华对中国绘画和中国艺术意境的理论探讨,其实仍是他自己创作经验和理论的延伸。比如写于40年代后期的《中国诗画中表现的空间意识》。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的创作经验再度投射于对中国诗人和画家创作过程的理解:
中国诗人、画家确是用“俯仰自得”的精神来欣赏宇宙,而跃入大自然的节奏里去“游心太玄”。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也有诗云:“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用心灵的俯仰的眼睛来看空间万象,我们的诗和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不是像那代表希腊空间感觉的有轮廓的立体雕像,不是像那表现埃及空间感的墓中的直线甬道,也不是那代表近代欧洲精神的伦勃朗的油画中渺茫无际追寻无着的深空,而是“俯仰自得”的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
这样一种对于中国艺术意境的表述,在源头上其实与宗先生在德国起步的诗歌创作体验是相通的。在很大程度上,他其实是把创作体验通过西方理论转化后,再度投射到对中国意境的理论建构中。
写诗的创作体验对于宗白华来说太重要了。有了这样的体验后,他不再是一个诗歌的外行、艺术的外行,不再是仅仅从理论概念来把握文学艺术的学者或批评家,而是成为了诗歌和艺术创作的内行人。他有了艺术创作的体验,明白了生命和形式的关系,理解了艺术创作的心理。而这和宗白华在德国的理论学习,又是相互建构、共同促进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宗白华美学论著中的文体追求。
原标题:《宗白华:从哲学走向诗》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