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史铁生:我走了,但我的灵魂依然在这个世界上
原创 '冰儿 民国女子

01
那一年,我13岁,住在一个乡村的大院子里。
野外的花儿开得蓬蓬勃勃,村口的小溪唱得叮叮当当,小院的中间有张小竹床,我就坐在那张小床上翻看各种厚厚薄薄的书——我有一个爱好文学的姐姐,邮递员总是骑着绿色的车子,送来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杂志。
记得那是一本《青年文学》,我翻到了那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那时候真的不懂什么是好的文笔,完全出于一个孩子的天性,我就是被文中那种舒缓亲切的调调吸引了,一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出几句知青与破老汉的孙女留小儿那些可爱的对话。
知青是从北京去黄土高原的,于是,留小儿就没完没了地冲他问北京的事儿。
“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

末了,这个北京知青感慨道: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就这些句子,我翻来覆去地看,第一次觉得,文字竟然可以这么有亲近感,或者换句话说,可以写得如此有趣儿。
我特意看了看作者的名字:史铁生。
事实证明,被一个孩子热爱的文笔就是有独特的魅力,这部小说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02
再次读到他的作品,是《我与地坛》。
这部作品享有的盛名无需赘述,我只想说说对我自己的震撼。
少年时候喜欢《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仅仅是对文字的一种天然的亲近,然后就丢开了,上学工作成家,其间读了很多很多的杂书,并没有因为喜欢这部小说而去特意关注他,就像童年熟悉的一个朋友,随着一次搬家离开便会逐渐忘却似的。
直到那年,已近中年的我,偶然看到。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
读完之后,我出了家门,沿着一条路走了很长时间,时值深秋,落叶飘了满地,夕阳欲落未落。我低着头,踢着落叶,脑海里反复只有一个念头:死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与这脚下的落叶一样吗?反正时节一到它就要落了;与这时候天边的夕阳一样吗?反正黑夜到来前它一定会告别……

甚至有一刹那,我又想掉头赶紧回到家里去,生怕某一刻的时光我会忽然失去。
在这反复缠绕的情绪中,其实另有一种笃定的声音在告诉我,你的情绪很正常。真的呢,这就是一个作家的伟大之处,他告诉你残酷的生活法则,无可更改的残忍现状,但他从不埋汰生活,他的豁达平静,是真豁达是真平静,是身处其中却又置乎其上的从容。
所以,他才可以平静地告诉你:“死亡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所以,每次翻《我与地坛》的时候我总会热泪盈眶,你一定不要以为我在矫情。
03
其实,我不喜欢提到他的残疾。真的,他的残疾,并不是励志的衍生词,我觉得这个词对于他几乎是多余的。
他的成名与他的天才,丝毫不需要这一项来加分。
只能说,命运总喜欢跟人开最残酷的玩笑。
他是个学霸,中学就读于清华附中,是不折不扣的尖子生,他最擅长的体育运动是80米跨栏,是学校的运动健将。18岁,他顺应潮流去插队,在那个有着他笔下的遥远清平湾的陕北高原放牛。20岁那年,在山里放牛的史铁生遭遇了暴雨,无处躲避的他因为这场雨落下了病根,发高烧大病一场后,下肢彻底瘫痪,他永远不会想到,21岁的他,从此只能生活在轮椅之上。
病痛的折磨远远没有结束。不到30岁,他又因肾病,常年需要在身上插一根排尿管,被确诊为尿毒症,需要每隔一日去透析。
2010年12月31日,饱受身体磨难的史铁生去世。
他用怎样强悍的内心来对抗这份来自身体的肆虐凌辱呢?
在《我与地坛》里,史铁生描述过当时的心境。可以用文字平静表达的时候,就代表他已经走过了最幽深黑暗的小径,所以,看他写这种感受,就更有一种隐隐的痛感,不是感同身受,而是对这份掩藏在淡淡文字里那份曾经炽烈的痛苦,有着天然的共情。

他说,“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他说:“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就这种笔触,你知道他一定为这个不能接受的残酷结果痛不欲生,崩溃失态,但他就是用文字漫出来的那束光拯救着自己。这份光里还有深沉的救赎自己的母爱。
也许,只有他有资格对这个世界说一声:精神才是永恒的,肉体算得了什么呢。记得有句评论说:“中国作家里,我只从史铁生先生那里看到一种态度。那就是:时时怀有将死的恳切。”
我理解为,这是一种经历过涅槃后的通透。
04
这样的一个人,注定要拥有世上最不落俗尘的爱情,他总会遇到一个相契合共节拍的灵魂的。
陈希米,1961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比史铁生小10岁,右腿有轻微残疾,就读于西北大学数学系。1978年底,史铁生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爱情的命运》,刊发在西北大学内部刊物《希望》杂志上,陈希米读了又读,被史铁生的文字深深打动。

那个年代流行“文学笔友”,陈希米先给史铁生写了一封信,与他探讨人生与爱情。于是,在文字的世界里,他们俩相见恨晚。
在那段时间里,史铁生先后创作出《秋天的怀念》《绿色的梦》《合欢树》《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等多部优秀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陈希米这个笔友的“功劳”。
至1989年,史铁生与陈希米整整通信10年,她见证了一个男人从文笔到精神上的蜕变,从青涩懵懂到成熟稳重,她是唯一的见证人。
1989年春天,孱弱的史铁生又患上了肾病,病情突然加重,需要人照料。得知消息,陈希米连夜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十年的“文学笔友”终于见面了,轮椅上的史铁生激动不已,他说了一句最动听的话:你,就是我想象中的模样。但他同样是理智的,他又说:若不是爱情,你可以离开,我绝不怪你;若是,请留下来,我们一起见证爱的荣耀。
就这样,陈希米留下了,与他相伴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陪着他去他爱吃的小饭馆,一起去看他们爱看的电影,俩人一起写喜欢的文字,用轮椅推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甚至,她还带他远赴美国,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她是他的腿,是他的拐杖,同时,也是彼此的仰仗。
史铁生写给陈希米的情诗这样写:
“希米,希米,见到你就像见到家乡,所有的神情我都熟悉,希米,希米,你来了黑夜才听懂了期待,你来了白昼才看破樊篱……”
陈希米写给史铁生的情话: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爱慕。”
05
最后,摘录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的结尾,愿这段句子,能抚慰世间的你我他: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
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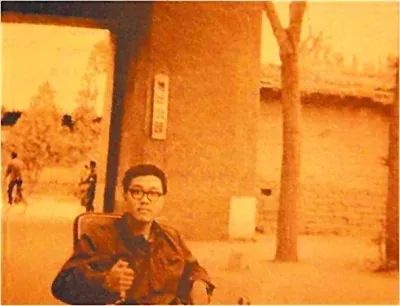
我总觉得啊,他的文章脉络里有一种自带的骨骼清奇,这是我少年时代就捕捉到的一种美;他的文字风格里更有一种深邃的诗意,栖息着他的旷达和灵魂自由;于他而言,文字是一种自然灵性的融入,而绝非一种乏味的冗长表达。
他的忧伤是一种亮晶晶的忧伤,不颓废也不萎靡,就是那种,来吧,生活,我们一起跳支舞的那种接地气的浪漫,有一种落叶簌簌雪花漫漫的闲适感,也有与命运对峙的尊严感,更似暗夜里的星光,闪闪而璀璨……
他怎么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呢?
他去世后贡献的眼角膜还在帮他看着这个美丽的世界。
他的轮椅,他的地坛,他留下的车辙,他的陈希米,热爱他的读者,也都还在呢。
原标题:《史铁生:我走了,但我的灵魂依然在这个世界上》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