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世界艾滋病日|凭啥为边缘人冒险?这些医生曾拒收艾滋病患者
•上世纪80年代,有位生物伦理学家写道,“很多医生似乎不只是在说‘我为何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是在说‘我为何要为这些同性恋者和吸毒者而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并非只有医生这样。有报道称,殡葬师拒绝对艾滋病患者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急救人员对同性恋社区的呼救置若罔闻。一些州的牙科协会建议推迟为艾滋病患者实施非常规手术,如搭桥和根管治疗。
一种毁灭性的新型疾病笼罩城市
1980 年11 月,一名男子因发热和气短来到贝尔维尤(即美国古老的公立医院纽约贝尔维尤医院)。他接受了胸部X射线检查,结果显示“有些模糊,无特异症状”,然后进行了肺部活检。“已无法单单用惊讶来形容。我们震惊得不知所措,”弗雷德·瓦伦丁医生回忆说,“这人得了肺孢子菌肺炎(PCP)。”
身为传染病专家,瓦伦丁近年来还治疗过一例肺孢子菌肺炎患者:一个营养不良的白血病患儿,其免疫系统已经崩溃。贝尔维尤的这名病人,是个34岁的同性恋者。他的肩胛骨附近很快出现了一个蓝紫色斑点,他的T细胞数——衡量身体对微观入侵者的防御能力——骤降。他陷入了昏迷。
瓦伦丁以自己见多识广为傲。从医学上讲,没有什么病是在贝尔维尤没见过的。但几天后,瓦伦丁在治疗一个有严重咳嗽和发热的瘾君子时,得到了同样的化验结果:“肺孢子菌肺炎,伴有严重的细胞免疫缺陷”。他觉得这不仅仅是巧合:两个明显素不相识的人,诊断结果却令人费解的一样。两人很快就死去了。
向北几个街区的纽约大学皮肤科诊所,也是国内最大的皮肤科诊所,在这里,另一谜团正在显现。一名男性到来时,脚上长了有色斑点。他最近因腺体肿胀和脾脏肿大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过治疗。值班的皮肤科医生阿尔文·弗里德曼–基恩做了一次活检。结果发现是卡波西肉瘤。
自然的反应是把这一病例视为反常。人体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卡波西肉瘤是一种皮肤癌,多见于地中海人种的老年男性,以及为防止器官排斥反应而服用免疫抑制药的移植患者。在癌症患者中间,这种病的发病率微乎其微。
但是,随后诊所又出现了第二起病例——一个30多岁的同性恋演员,鼻子上长了块紫斑。“我突然开始考虑病人的性史,医学院里从没有人教过我这些东西,”弗里德曼–基恩回忆说,“询问一个人的性生活?我的意思是,[我]从未问过任何人这种问题。没有人,连妓女都没有。”
在弗里德曼–基恩检查的病人中,有一人名叫盖尔坦·迪加,这位法裔加拿大空中乘务员,后来在旧金山记者兰迪·希尔茨的畅销书《世纪的哭泣》(以及HBO改编电影)中,被描述为“零号病人”,而他也将死于艾滋病。
后来证明,这一描述并不属实;把艾滋病带到北美的并不是迪加,尽管他吹嘘说自己曾在数十个城市与数百名毫无戒心的伴侣进行无保护性行为,而且他的这一说法很可能为真。“我曾碰到他从一个同性恋澡堂出来,我停下车,说:‘你在那里干什么?’”弗里德曼–基恩回忆说,“而他说:‘在黑暗中,没人看得见我的斑点。’他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者……[在那之后]我拒绝见他。我真的非常气愤。”
这是否只是冰山一角?弗里德曼–基恩认为是的。他与贝尔维尤的肿瘤学家琳达·劳宾斯坦等人合作,共同发表了一项涉及60名同性恋患者的研究结果:一组显示出卡波西肉瘤、肺孢子菌肺炎(或两者兼有)的明显症状,另一组无症状。“与[这些疾病]关系最密切的变量是每年男性性伴侣的数量”,这项研究的作者们得出结论:第一组平均有61个伴侣,对照组有26个。第一组还报告了疱疹、梅毒和肠道寄生虫病的较高发病率。
时间一周周过去,口腔、舌头、喉部、视网膜、结肠、阴茎和直肠患癌的男同性恋者开始来到贝尔维尤。所有临床指标都指向一种毁灭性的新型疾病。
起初,医学研究人员使用“与男同性恋者相关的免疫缺陷”(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 或简称GRID来描述这一系列症状,而媒体则称其为“同性恋癌症”。但随着异性恋病例的增多,其中有海地人、共用针头的吸毒者、接受输血的血友病患者,这一病症被重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或称艾滋病。
没人知道这些互不相干的群体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有联系的话。1982年,纽约市报告了543个新病例。此时此刻,唯一恒定的是死亡率。患者似乎都必死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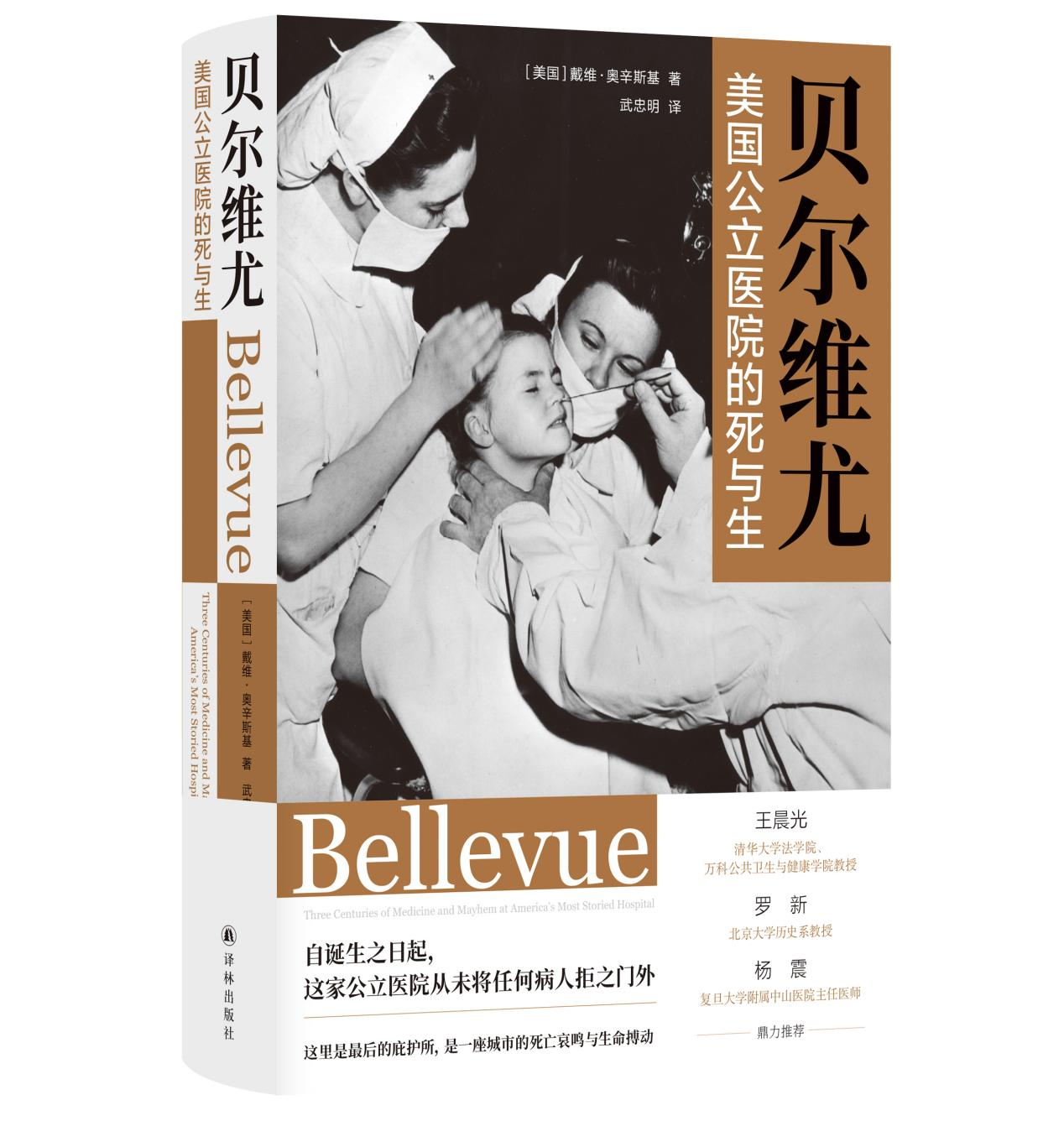
《贝尔维尤:美国公立医院的死与生》,[美]戴维·奥辛斯基 著,武忠明 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背负逃兵骂名还是与恐惧为伴?
美国医学会于1847年成立时,医生拒绝治疗流行病患者,更恶劣的是,甚至弃之而逃——这种令人遗憾的景象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丹尼尔·笛福在他写于18世纪的小说《瘟疫年纪事》中写道:“谴责的话语朝那些[伦敦]医生劈头盖脸扔过来,他们在这疫疾期间遗弃了自己的病人……他们被人叫作逃兵。”
为树立自身形象及原则,新成立的美国医学会采取强有力的立场,结果是制定了《医疗伦理守则》,要求其成员“直面[瘟疫]之危险,为救死扶伤不懈努力,甚至甘冒牺牲自己性命的风险”。
随着研究的进步,对传染病的担忧逐渐消失。疫苗、特效药和更好的卫生条件,抑制了过去那些传染病的严重暴发,使医学这一职业变得更安全。
为反映这一现实,美国医学会在20世纪50年代修订了《医疗伦理守则》,让医生“自由选择服务对象……以及提供医疗服务的环境”,不明“紧急情况”除外。之后,艾滋病降临了,不知源自何处。医疗防护这层安慰的泡沫,似乎一夜之间破灭了。旧的问题再次浮现。危险时代需要什么?是否应该恢复更严格的《医疗伦理守则》?
美国医学会认为不应该。在1986年的一份过度关注细节的声明中,其伦理和司法事务理事会用独具威胁性的话语描述艾滋病,这让犹豫不决的医生同行,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艾滋病患者。“从情感角度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照护艾滋病患者”,这份声明写道,尽管医学拥有“以同情和勇气”面对传染病的“悠久传统”,但不应强迫所有人这样做。该声明还补充说,如果医生选择退出,“必须对病人的护理另做安排”。
事实上,很少有医生面临这种困境,因为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会在城市的公立医院接受治疗,那里还有众多同性恋者和药物滥用者。迟至1990年,也就是艾滋病流行近10年的时候,新墨西哥州组织了一场关于艾滋病治疗策略的研讨会,1300名受邀者中仅有1名医生到场。即使在自由开放的纽约市,男同性恋者健康危机组织也仅能勉强找到50名私人执业医生愿将患病者的名字列入转诊名单。
金钱无疑起了一定作用。艾滋病患者往往很穷,而“私人医生不会接受没有医保和无法预付费用的人”,一位社会活动家抱怨道。但研究表明,对安全的担忧与个人偏见是更重要的原因。“将这类病人拒之门外时,”上世纪80年代,一位生物伦理学家写道,“很多医生似乎不只是在说‘我为何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是在说‘我为何要为这些同性恋者和吸毒者而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并非只有医生这样。有报道称,殡葬师拒绝对艾滋病患者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急救人员对同性恋社区的呼救置若罔闻。一些州的牙科协会建议推迟为艾滋病患者实施非常规手术,如搭桥和根管治疗。
对纽约市350名牙医的调查显示,“100%”的牙医反对治疗艾滋病患者——这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艾滋病的几个早期预警信号,包括鹅口疮、真菌性口腔感染和白斑(一种沿牙龈和舌头的病斑),在常规口腔检查中很容易被发现。牙医们声称,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危险病毒的侵害,如他们归咎于患者唾液的乙肝病毒。为什么要在致命得多的东西面前冒险呢?
在发表关于艾滋病的声明时,美国医学会设定了两种例外情况:
第一,在医疗紧急情况下,如车祸,决不能拒绝对艾滋病患者实施治疗;
第二,国家的公立医院将继续收治艾滋病患者,无论是否紧急。
这两种例外情况和纽约市的关联最为密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纽约市的艾滋病病例数占全国近三分之一,而且这种疾病将成为25岁至40岁之间的男性死亡的主要原因。
作为纽约公立医院的旗舰,贝尔维尤既服务于格林威治村的同性恋社区,也服务于包厘街和下东区毒品泛滥的街道,一时成了疫情的中心。早期面临的问题是信息匮乏。没人知道该采取什么预防措施,也没人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它没有名字,没有期刊提到它,也没有教科书描述它,”一名实习生回忆说,并补充道,“我们原以为它会消失。”
由于患者太多,真相不明,一种恐惧感席卷了整个医院。工作人员拒绝给艾滋病患者送食物、打扫房间和清理废物。一位护士长注意到,贝尔维尤的同事们受到了自己家人的压力。“他们会说‘你会染上艾滋病’,或‘回家前先洗个澡’,或‘你的制服要在医院里洗,不要带回家’。”只需拿起当地一张报纸,就能读到“致命病菌”逃离医院、让整座城市陷入危险的消息。“患艾滋病的吸毒者是贝尔维尤的勤杂工。”《纽约邮报》尖叫道。
然而,在所有潜在危险中,没有哪个能与被注满艾滋病患者血液的注射器的“针头扎到”相比,这样的事并不罕见。统计数据显示,以这种方式感染病毒的概率相当小——据疾控中心称,275起病例中约有1起。不过,那些不小心扎到自己的人,要经历数月的惶惶不安。“在那一瞬,”一名护士回忆说,“我所能感受到的只有一波又一波恐惧。”
报道“艾滋病浪潮”的记者,开始依赖纽约大学暨贝尔维尤的一线医生,寻找这一医学之谜的线索。每有重要文章发表,里面可能都会引用弗雷德·瓦伦丁、劳伦斯·弗里德曼–基恩或琳达·劳宾斯坦的话。劳宾斯坦的私人肿瘤诊所,收治了近百名艾滋病患者;而弗里德曼–基恩的皮肤科诊所,在1987年诊断出第1000个卡波西肉瘤病例。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劳宾斯坦承担的角色尤其苦乐参半。她是一名脊髓灰质炎幸存者,腰部以下瘫痪,从巴纳德学院和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贝尔维尤做住院医师,并于1983年接受了纽约大学的教职。分配回到心心念念的贝尔维尤后,劳宾斯坦时常开着电动踏板车在大厅里飕飕飞驰,威吓她怀疑“坑骗”病人的工作人员。
“从嗡鸣的速度可以判断琳达是否在大发雷霆,而[我们会]躲进壁橱里、桌子或柜台下面—只要能避开[她的]愤怒。”一位住院医师回忆说。劳宾斯坦深受哮喘和心脏病困扰,但她仍坚持上门问诊,虽然这一做法早已过时。朋友会在城市公交车上看到她,腿上放着医生的包,拄着拐杖,“身体状况还不如她的大多数病人”,但她总是为他们着想。
有时,劳宾斯坦会与同事发生冲突,他们认为她对艾滋病的处理方法“太过激进”。她毫无歉意地采用一切医疗手段,如化疗,这是一种治疗免疫系统遭严重损害的患者的方法,颇具争议。
“她对病人的照顾非常好,”弗里德曼–基恩说,“但我俩意见不合;我们屡屡争论,身为肿瘤学家,让每个人都接受化疗是否合理……我们观摩一次尸检的时候,她从轮椅上抬起头说:‘没有卡波西肉瘤。’我说:‘是的,但是琳达,他却死于各种机会性感染;是我们杀死了他。’”
两人达成一致的是,滥交、无保护性行为在传播这一疾病中的灾难性作用。劳宾斯坦不久即带头号召关闭本市的同性恋澡堂,此举遭到市长爱德华·科赫抵制,大部分同性恋社区也表示强烈不满。但也有人鼎力支持她,其中就有剧作家拉里·克莱默,他在1985年写了反映纽约市同性恋者生活的辛酸舞台剧《平常的心》,剧中有一个叫艾玛·布鲁克纳的角色,她是一名聪明的坐着轮椅的医生,专门研究男同性恋者的艾滋病治疗和安全性行为。
劳宾斯坦很欣赏克莱默的行动主义,但讨厌这个剧。“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纽约大学暨贝尔维尤]还有很多医生在照护[艾滋病]患者。单把她挑出来,她觉得我可能是在利用她,因为她坐着轮椅,所以更富戏剧性,”克莱默如是说,并补充道,“我承认自己因此而心中有愧。我想让这个角色和她有相似之处……以克服身体不利条件为标尺,让那些生病的人看看何谓真正的勇气。”
多年来,艾玛·布鲁克纳曾由朱莉·哈里斯、芭芭拉·贝尔·格德斯和埃伦·巴尔金(她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托尼奖最佳女主角奖)扮演。
听说芭芭拉·史翠珊买了电影版权,打算自己来演这个角色后,劳宾斯坦很不客气地对朋友说:“假如她要做直肠手术,最好剪掉她那该死的指甲。”1992年,劳宾斯坦死于心力衰竭,年仅45岁。她从未在百老汇看过《平常的心》,也未能在生前看到她的开创性工作带来的影响。
2014年,HBO终于出了电影版,主演是朱莉娅·罗伯茨,而不是史翠珊。克莱默对那些不了解纽约市艾滋病历史的人说,“艾玛·布鲁克纳医生这一角色是以琳达·劳宾斯坦医生为原型的”,“我希望这一角色能永葆她的遗产”。
谁来决定何时停止治疗?
考虑到贝尔维尤有大量与艾滋病相关的病例,令人不安的法律和伦理问题是必然会出现的。
“它与其他疾病不同”,一位医生解释说,每个病人都知道“自己将在两年内死亡,体重可能只剩65磅,大小便失禁,剧烈疼痛[且]经历精神上的变化”。迟早要做出停止治疗的决定,结束这个人的生命。但这个人的病情要发展到什么程度,由谁来决定?如果病人自己无法决定,能否指定一位朋友或家人来表达他的意愿?病人的嘱咐要写出来吗?如果要写出来,具体该如何写?医院能否参与进来,在不至引起诉讼和严重经济损失的情况下?
20世纪80年代,该领域还是一片处女地。纽约州对“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权拒绝医学治疗”不再有异议,但围绕“死亡权”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尤其是生前预嘱和医疗代理——才刚刚开始出现。早期针对此问题的一次关键抗争,今天已基本被人遗忘,涉及贝尔维尤的一名处于艾滋病晚期的病人。
1987年夏,托马斯·沃思,一名来自格林威治村的同性恋艺术家,因弓形虫病而被收治入院,这是一种脑部寄生虫感染。沃思曾目睹一位挚友在艾滋病最后阶段遭受的可怕痛苦,于是留下一份书面指示:倘若“无望治愈或恢复像样的生活质量”,不得进行“维持生命的程序”。如果沃思不再能为自己发声,这份文件赋予他的朋友约翰·埃文斯代理权。
送入贝尔维尤一周内,沃思陷入昏迷,埃文斯要求医院不得再做任何事。医院很自然地表示反对。医院避开艾滋病这个更大的问题,称弓形虫病是一种通常可以用抗生素成功治疗的疾病,因此并不意味着等死。通过药物治疗,沃思至少可以恢复意识,并告诉医生他希望如何治疗。若不如此,他就根本没有机会。“这种情况可以自行解决,”贝尔维尤的发言人解释说,“他可能下周就从[昏迷]中恢复过来,而后说‘我不想再接受任何治疗’,我们对此不会有任何问题。”
一场官司旋即而至。埃文斯声称,文件的内容和立嘱人的意愿并不难理解。托马斯·沃思此时正遭受着他力图避免的恐怖之事。“他想有尊严地死去,”埃文斯声称,“他希望避免的事情现在正发生着。”
医院回应说,这份文件并不适用,因为沃思“尚有希望”从目前威胁他生命的疾病中“康复”。贝尔维尤的几位医生出庭做证,坚称在医学研究飞速发展的世界里,让一名艾滋病患者尽可能长时间地活着是合情合理的。“治疗方法……每六个月就会改变一次,”其中一位医生表示,“新的疗法经常出现。”
法院判医院胜诉。法官杰恩·A.桑迪弗接受了沃思的脑部感染可能不会致命的说法,认定“没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病人“没有希望”——这无疑是一次沉痛的判决。“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珍贵的了。”这位法官命令贝尔维尤继续进行之前对弓形虫病的治疗时这样宣布。沃思于次月去世,未能恢复意识。
虽然埃文斯诉贝尔维尤案无法与那个时代更引人注目的死亡权案件相提并论,但其影响是巨大的。1985年,州长科莫成立了一个针对“生命与法律”的特别工作组,以帮助弥合病人和医院的分歧。两年后,在埃文斯案之后几周,特别工作组认可了“生前预嘱”和“指定代理”的理念——前者是为了给维持生命的治疗提供“详细指导”,后者是为了“保护无行为能力的病人的愿望和权益”。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思与贝尔维尤典型的艾滋病患者少有共同之处。他受过良好教育,出身中产阶级,用尽了医保和银行存款,深陷穷困潦倒的境地,只能去公立医院找一张病床。吸毒者通常不会提前计划医疗应急措施,那个时代的同性恋患者往往隐瞒病情,拒绝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也不愿告诉家人,因为害怕受到冷遇。结果是,结束生命的决定绝大部分落在了医院身上。
如今,艾滋病已不会再引发对生前预嘱、医疗代理、缓慢代码或“拒绝心肺复苏术”的争论。仅此一点就值得关注,它标志着艾滋病从一项死刑判决变成了一种可控制的疾病。
对引发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进行鉴定这一重要工作,由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的实验室完成了。包括纽约大学在内的一批医疗学术中心,在对该疾病的各种研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纽约大学的研究重点是卡波西肉瘤和其他癌症、病毒的母婴传播、测量血液中艾滋病病毒水平的数学模型,以及新药疗法的人体试验。
到1990年,纽约大学有两个小组在进行独立试验:一个在贝尔维尤,由弗雷德·瓦伦丁医生领衔;另一个在第一大道对面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由何大一医生领衔。
两个小组都与不同的制药公司合作,测试一种多药物疗法,旨在抑制已感染患者的艾滋病病毒。两组都得到了显著效果。被试的病毒载量几乎降到了无法检测的水平,而且只要忠实地按照常规治疗,病毒载量就会保持不变。该疗法产生了一些令人不适的副作用。它既昂贵又复杂,而且必须无限期进行下去,因为病毒只是被控制住,并未完全根除。不过,在遏制这种一度致命的疾病方面,已出现一道分水岭。
到2000年,贝尔维尤门诊里的艾滋病患者远远多于其病房里的,这些病人像其他人一样,患有各种常见病。2012年——30年后,这种疾病第一次不再是纽约市年轻男性的十大杀手之一——医院关闭了艾滋病(也称病毒学)科,此举在当初是不可想象的。
回想贝尔维尤被病患窒息的日子,“人人都在死亡,有的死得快,有的死得慢”,弗雷德·瓦伦丁称这一举动“令人震撼”。贝尔维尤历史上的重要一章已然结束——也许是永远结束了。
(本文节选自《贝尔维尤:美国公立医院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2022年10月版。作者戴维•奥辛斯基(David Oshinsky),系美国当代历史学家,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医学院医学人文部主任。他曾获普利策奖、罗伯特·F.肯尼迪图书奖、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奖章等。本书译者为武忠明。澎湃科技获授权刊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