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世界艾滋病日 | 翻开这本书,才了解他们为何而哭
文章来源:硬核读书会
作者 | 重木 编辑 | 程迟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是一个略显沉重,但是我们却必须面对的问题。可能没有哪种病毒,可以像“艾滋病病毒”那样搅动起如此复杂的个体和社会情绪。
从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到今日逐渐被大众认知,走过了漫长的一段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无知、恐惧与残忍,也看到了面对病毒时,科学以及社会所展现出来的善意。
今天,我们通过译文纪实推出的纪实作品《世纪的哭泣》,进入这段并不轻松的历程。
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 And the Band Played On,和中文译名刚好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追逐着个体解放、喧嚣沸腾的现代社会,像是一个演奏永不停息的乐队,而正在哭泣的人,却无人理会。


电影《平常的心》剧照
艾滋病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悄无声息的存在,它似乎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恐慌和喧嚣中尘埃落定。那些因感染艾滋而死于各种并发症的人们或许都还活在他们朋友和亲人的记忆里,而那些在药物维持下活下来的人,也早已经能够如普通人一样过日子,但他们却往往是带着旧日的噩梦与一次次面对亲爱之人死去的可怕回忆活下去的。
就如罗伯·爱泼斯坦2000年拍摄的纪录片名字,“活着为了证明”,那些侥幸活下来的艾滋携带者们,是一段关于瘟疫肆虐时残酷岁月的见证。在这其中,被考验的除了不幸的个体,还有各类政府机构与部门、科学群体以及社会主流,那些被当作正统的意识形态、关于性的迷思与恐慌,以及在面对病毒肆虐时,人类社会所展现出的无知、恐惧与残忍。
01
世纪的哭泣
这一切似乎就是兰迪·希尔茨这个见证者所写的那部《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一书的主题。
《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美]兰迪·希尔茨 著,傅洁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1
他按照时间发生顺序,向我们展现一个新型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获得性免疫综合征(AIDS)是如何在美国发现并扩散的,以及在这场发生于20世纪尾声的瘟疫是如何像一面镜子般照出人类社会各类不同机构和组织、群体与个人,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对艾滋病的利用而达到自身的目的。
似乎从一开始,艾滋就很快像其他世纪的瘟疫一样被隐喻和象征化,从而渐渐使得原本作为病毒传染的医学问题为各类政治、权力与文化包裹,而彻底忽略了在真实状况中,那些急切地需要被关注和救助的艾滋感染者们。
正是这些隐喻和象征,导致艾滋及其症状直到如今都承担着沉重的污名和刻板印象,从而直接影响到被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
当我们追溯这一污名的起源,一方面它必定与艾滋病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发现与命名的那一刻有关;另一方面,作为“疾病的隐喻”在人类社会文化中自有其漫长的历史,艾滋的隐喻只不过是这一谱系中的一部分。

对当时“零号病人”的报道:“给我们带来艾滋病的人”。/《纽约邮报》版面
无论是《世纪的哭泣》还是2012年的纪录片《瘟疫求生指南》,都指出当艾滋病毒被检测到,一个真相被隐藏:最初的艾滋病毒并非仅仅只在男同性恋身上被发现。但当媒体开始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聚焦在“零号病人”男同性恋者身上,由此导致艾滋病毒一开始就与男同性恋以及同性性行为联系在一起。
根据中国卫健委2019年数据,作为艾滋病主要的传播途径之一的性传播,73.3%是异性性传播,23.0%是男性同性性传播。恰恰是这23%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毒刚出现在美国社会时。当一些媒体以及政客发现病毒似乎与男同性恋群体存在紧密联系时,他们立刻通过对艾滋的隐喻和象征来攻击这个性少数群体,于是艾滋初期被称作“同性恋癌症”(Gay Cancer)和“同性恋瘟疫”。
02
憎恨、排斥和为时已晚
就如福柯在其《不正常的人》法兰西课程中所指出的,西方传统对待感染瘟疫人群往往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排斥作为主要手段的“麻风病模式”;另一种就是以容纳作为预防方法的“鼠疫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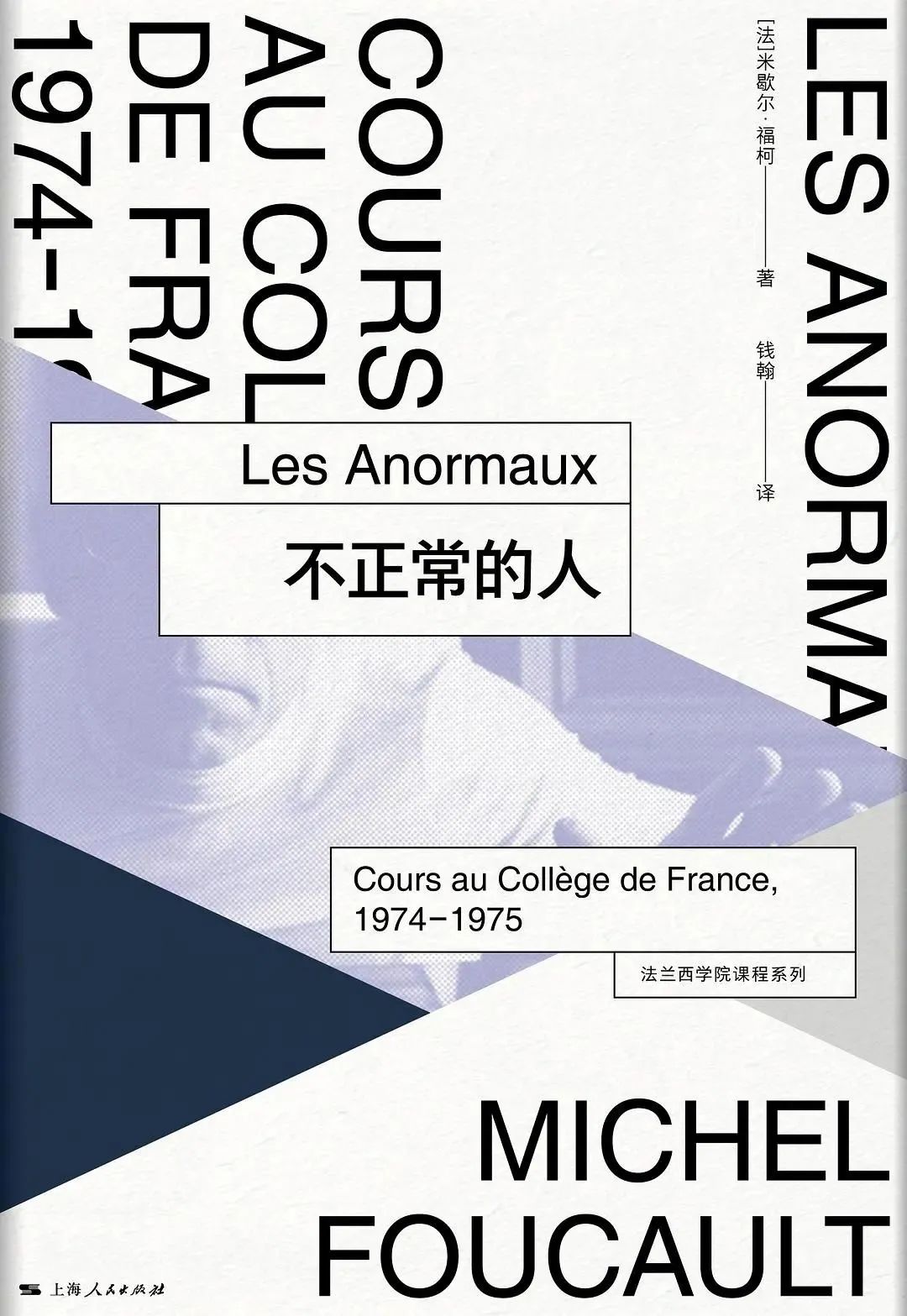
《不正常的人: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1974-1975》
[法]米歇尔·福柯 著,钱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1
这两种不同处理瘟疫感染者的方法暗示了不同的社会分类与权力运作模式。伴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排斥的行为(如把麻风病人丢到城市之外或孤岛上)渐渐被反思和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区分为手段的积极的权力运作机制。
由于媒体、政客和一些科学家的意识形态立场,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希望通过把艾滋与同性恋群体的绑定,达到排斥这一群体的目的。
也因为这一联系,导致美国当时的里根政府始终希望把艾滋病毒看作是一个特定群体问题,且因为这个群体本身是“令人憎恨的”(Abomination),所以他们不打算在政府预算上多花这笔钱。
加上西方传统基督教观念,更是让许多右翼宗教政客、媒体、教士与民众认为艾滋是上帝对“索多玛之罪”的惩罚,所以他们幸灾乐祸,隔岸观火地欣赏着艾滋在男同性恋群体里的肆虐。也恰恰因为这些被预设和想象的隐喻与象征,导致他们往往忽略或是有意地视而不见那些出现在异性恋男女身上的病毒感染,直到一切为时已晚。

1993年上映的《费城故事》就是根据1987年美国第一宗艾滋病歧视案件改编。
关于艾滋病毒初期的无知、恐慌和想象,我们或许会十分熟悉,只是人们已经从历史中学会了教训,而没有让这些毫无根据的隐喻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艾滋的特殊就在这里,一方面由于它最初与男同性恋群体绑定,另一方面由于它特殊的性传播途径,从而导致它比其他传染病多了一层更加暧昧的色彩。由于与性行为的密切联系,导致艾滋感染者也不得不面对诸如感染梅毒之人的道德审视与评判,似乎正是因为个体在私人生活上的放浪形骸才会导致病毒感染,由此它被看作是对这一不谨慎行为的惩罚,进而成为审核个体道德的标尺。
03
谁之过?
在莱里·克莱默根据自身经历创造的戏剧《平常心》(2014年瑞恩·墨菲拍摄了同名电影)中,他——男主角便是其化身——便在八十年代的艾滋肆虐时期警告其他人安全性行为的重要。但对于成长于六七十年代性解放的年轻人而言,这一警告无异于再次剥夺他们通过抗争而获得的性自主权,从而导致许多人未能意识到艾滋传染性的可怕。

80年代因为艾滋病所引发的社会争论。/Smithsonian Magazine
在希尔茨《世纪的哭泣》中,他毫不留情地指责群体领袖的不作为,以及他们希望利用艾滋作为筹码来达到和有关部门谈判的目的……
正是这些肆意的行为,为旁观者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印证自己关于艾滋病毒是那些个人性生活不检点之人的惩罚。病毒就是个体道德瑕疵的症状,是红字、是烙印。在这一传统涉及性的病毒或疾病的隐喻体系和文化中,艾滋感染者不得不开始承受更大的道德压力,而这一点直到如今都未能被真正清除。
在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她指出,传统社会时常围绕着疾病(尤其是流行病和传染病)建构出一整套复杂而精密的隐喻系统,以此作为某种用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打击和排除非正统人群、行为和思想观念的工具。
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中,桑塔格围绕着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艾滋恐慌,分析了政府、主流媒体和诸多保守势力通过对艾滋病这一疾病的隐喻化处理,使它成为曾在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同性恋群体的特有“疾病”,并且还通过对艾滋病的道德化处理,对该群体再次从道德层面进行贬低。由此就导致了:一旦感染艾滋病毒,便意味着感染者被塑造成一个道德有缺陷、性行为变态且遭到上帝惩罚、被遗弃的罪人。
因此如何清除污名以及正确地看待艾滋病毒及其感染几乎成为每一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保留项目。但在历史中被建构起的复杂且错误的隐喻却早已经根深蒂固地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中,从而导致它渐渐难以被察觉,却又始终鲜明地存在着。而这一道德亏损和个人生活问题的陈词滥调不仅仅影响因性传播而感染的艾滋病患者,也直接影响到那些或因医用针头污染而通过血液感染的病毒携带者,以及通过母婴传播而感染的群体。人们不会细问感染者自身是否“无辜”,而是毫无余地地自动调用这一系列隐喻和陈词滥调,做出颇具陈见的判断。
04
越过疾病的隐喻
在普遍的污名化中,导致艾滋病预防和防治变得更加困难。在2019年1月的《财新周刊》中,有一篇名为《变色的“淡蓝”》文章,对国内最大的同志交友软件blued与未成年人用户感染艾滋病的问题进行封面报道。这篇报道以张北川为期十个月对于blued相关用户的调查报告作为切入点,指出在当下国内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MSM(男男性行为者)群体中的未成年人感染率出现上升。
而在每年“世界艾滋病日”,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性传播中的未成年人比例大大增长,而在这背后隐藏的问题恰恰是由于性教育的匮乏和污名化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等所造成的悲剧。

为了避免同性恋和艾滋过于频繁地绑定出现,许多人开始提倡使用MSM来取代特定的群体称谓,从而希望人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一病毒。人们希望令其重新医学化,即把它限定在一个专业的、科学的范围内,剥除那些根据意淫、想象或别有目的而赋予其的隐喻与象征,让它仅仅被当作一种需要被医学探究和治疗的病毒与疾病。
疾病作为隐喻这一文化模式却不会轻而易举地消失。因为就如福柯或桑塔格所发现的,疾病本身之所以会被隐喻化,很多时候与病毒自身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它们往往只是被当做一个工具或容器,来实现社会、文化与权力的再分配或组织。
当人们对艾滋病毒所知甚少时,医院不愿意接收感染者,医生和护士不愿意照顾他们,而当他们去世,也往往被装进黑色的垃圾袋中进行消毒处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彻底保障人类的安全,而民主、尊严和自由的信念也依旧无法改变遭遇瘟疫时人类对人的轻视与散漫。
黑死病时,人们在露天烧死那些死去的人;在现代医院里,护工把死者装进垃圾袋……瑞典电视剧《戴上手套擦泪》便是当时一个典型的行为:医生为了预防感染会戴上手套给病患擦眼泪。在陌生病毒的入侵下,稳定的社会关系以及一系列规范都变得不堪一击,而作为人的尊严也彻底消散。一种自然的状态似乎重新归来,泄露了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地基下的可怕幽灵。

洛克·哈德森(左)1985年死于艾滋病。/《绝岭三雄》
真正让美国主流社会开始紧张的是好莱坞著名男星洛克·哈德森因艾滋病去世,一直以来隔岸观火的人们才意识到病毒本身的“盲目”和无区别性;与此同时,他们也才发现即使在大银幕上的形象“直男”如洛克·哈德森原来也可能是同性恋。
界线明确的区隔以及他者的形象最终都暧昧不清,现代麻风病人再也无法如古代那样,可以被清晰地诊断与界定,然后把他们丢出城市。恰恰相反,融合与模糊才是现代社会以及日常生活最典型的特征,而这也为病毒传播提供了一个无法避免的现代处境。
这或许就是关于艾滋病毒的现代谱系,对于每一个感染者来说,他们也都没有选择地必须继承这些阴影与污名。
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教育与再认知,围绕在艾滋上的迷思、无知、恐怖和陈词滥调也在渐渐地消失,但那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也在持续地运作着。
但这一切的象征和隐喻、背后牵涉的深刻危机,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忽略日常生活里那些真实地遭遇着污名和危机的个体的理由,就如希尔茨在《世纪的哭泣》中所指出的,我们常常会因为许许多多的教条或对观念的执迷而遗忘了活生生的个体。
原标题:《世界艾滋病日 | 翻开这本书,才了解他们为何而哭》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中方出手连环反制
- 中方连环反制,美指期货应声下跌
- 10位在韩志愿军烈士寻亲线索公布

- 乌外长:乌克兰代表团即将访美,就矿产协议进行磋商
- 多个美股热门中概股盘前跌幅扩大至10%

- 被誉为“活化石”的中国特有树种是
- 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南美洲亚马逊盆地的雨林是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