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英德对抗的兴起:“疲惫的巨人”与崛起中的强国
20世纪初,英国人谈起德国人时愈加紧张的口吻与早些年的满怀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彼时,英国在国际政治观察家们眼中的形象是一个“疲惫的巨人”,面临着来自多方的压力,而1896年之后的商贸扩张尤其使人更加坚信,德国是一个新兴的、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
客观来看,从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制造产量、国内贸易和国家财富这几项指标揭示了两个主要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尽管有些不平衡,但整个世界在生产、贸易和繁荣方面均出现了绝对增长。第二个趋势是英国作为头号工商业国家,呈现出相对衰退,而相应地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呈现上升状态。即便对那个时代的人而言,这两种趋势的迹象也都是极为明显的,而且在大萧条的结束消除了针对第一个结论的疑问之后,就没有什么人试图对这两点提出异议了。然而事实上,那些主张科布登式国际主义的人几乎全部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第一种趋势上,而贸易保护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总是强调第二种趋势的重要性。这一点尽管纯属意料之中,却十分重要。由此可见,这些有关全球经济变化之意义的争论是以有选择性的证据为基础的,尽管出现这样的情况颇为值得玩味。
对于英国的右翼势力而言,丧失经济至尊地位以及国家权势随之而来的减退,是十分可怕的:没有其他任何事情会比这种情况更让他们心烦意乱,或是激励他们采取行动了。正如加文(Garvin)指出的,基本问题在于“权势本身纯粹是一种相对概念”。 即便现在与皮特(Pitt)或帕默斯顿执政时代相比,国家财力更为雄厚,劳动者吃得更饱穿得更暖,这也不能带来丝毫的安慰:事实上,这对于19世纪末世界政治的基本趋势而言不仅是毫不相关的,而且也是一种危险的混淆——因为英国作为头号世界大国的地位已经彻底崩溃,不复存在了。随着横跨大陆式国家的迄今尚未利用的大量资源得到新技术的开发,以及美国、俄国和德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英国相对匮乏的物质基础第一次被凸现出来;正如麦金德(Mackinder)在一篇颇具先见之明的文章中解释的,如今“在较广的地理概括和较广的历史概括之间,存在一种相关性”,即在国际发展领域,数量和规模将得到更准确地反映。对于狭小的岛国而言,其结果将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塞尔伯恩对寇松所说的:“在不久的将来,联合王国单凭其自身的力量将很难与美国或俄国一争高下了,甚至都比不过德国。仅仅是体量就足以让他们把我们逼进角落。”“小国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保守党的一份《选战指南》(Campaign Guide)如是写道。张伯伦也坚信:“时代的大潮将把所有权势都送到更大帝国的手中。”为了吸引伍尔弗汉普顿东区的选民支持他进入议会,埃默里描绘了一幅更为耸人听闻的前景:
年复一年世界大国的权势竞争正变得日益激烈,除非我们能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的地位,除非我们能够保持战无不胜的海军,除非我们能够保证大英帝国的所有边界不受侵犯,否则我们的帝国和我们的贸易就会别人夺走,我们也会弹尽粮绝、被侵略、被践踏,甚至于被彻底毁灭。
然而从长远来看,英国这区区数岛如何才能和那些强大富裕的帝国匹敌呢?美国与德国正迅速变身为这样的国家,甚至一旦俄国从其当前(1905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也会成为其中之一。
我们仅仅依靠四千万人民如何能和这些两倍于我国规模的强国相竞争呢?
这种后世历史学家们有着诸多评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遍布于这些帝国主义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几乎所有作品当中;而经济高速发展的节奏和世界政治中无休止的纷扰碰撞,也表明了帝国的起起落落这一永不停息的变化过程。罗伯逊告诫英国的参谋军官:“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和帕默斯顿甚至迪斯累里时代自信的扩张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世纪之交许多英国人对于未来是否还会如此垂青英国已经越来越没有把握了。仿佛帝国边疆所面临的日益增加的挑战,频繁的海军“恐慌”和入侵“恐慌”,以及关于国家工业软肋的激烈辩论对英国自信心的打击还不够一样,布尔战争中的败仗又在帝国主义者的整个阵营中引起了极大反应。“我们面临的灾难接二连三,我们的将领普遍如此无能,我们无法取得任何进步,所有这些都是程度如此之深,让我们严重怀疑我们的体制必定是烂到根子里了。”寇松抱怨道。“哦,这实在让我感到恶心!”吉卜林愤怒地说道。“不是因为这是布勒([Buller]将军),而是因为这就是我们——英国自己。出现在一面肮脏的镜子当中的我们自己的脸,然而这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他在一首诗中问道,先辈们给予的千年遗产将会从这一代人手中开始断送吗?加文在1905年也不禁发问,“正在庆祝特拉法尔加海战胜利一百周年的大英帝国是否还能迎来下一个百年盛典呢?”对这一问题予以肯定的回答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米尔纳很担心“我们究竟能否成功挽救大英帝国”;他悲叹道:“要是我们拥有风头正盛的那些国家的特征该多好啊。”还有吉尔乐也曾颇为感伤地写道:“我的中国朋友曾评论说:‘英国和中国之间有一种奇妙的相似性。’我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意识到,这实在是一语中的。”
英国的帝国主义群体的这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在他们的私人通信和日记中反映得最为明显;而在公开演讲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们则总是倾向于展现出勇敢的一面,并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但值得强调的是,他们大多数人本质上还是对前景抱有悲观看法,他们坚信自己的立场是防御性的,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维持大英帝国的现有地位——而不是像后世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如果说有哪个国家颠覆了世界均势,那就是大不列颠。”要是在世纪之交时问一问各大强国的政府,如果要“冻结”当前的权力政治现状,它们将作何反应。可以有把握地推测,英国,或许还有奥匈帝国,将会给出积极答复。更加可以预测的是,诸如德国、俄国、美国和日本这样的新兴大国将会予以强烈反对,它们都正欣欣然于这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大潮,且都期盼着在20世纪的大幕拉开之时在世界舞台上占据更显赫的地位。
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们由于十分担心全球均势的这些变化,并且认为权力的“真空”很快就会被填满,新兴大国将不再有扩张的余地,因此推断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斯普林-赖斯认为,德国人对英国怀有憎恶情绪是相当好理解的:“我们处处阻碍了德国人的前进之路——我们占有最多的可获取物——从个人情感上而言我们是令人嫌恶的。”“ 如果他们可以做到的话,他们想要从我们手里夺走那些已经被我们占有,而他们的媒体声称我们正在滥用的东西。”斯特雷奇解释道。“他们的态度实际上和伊丽莎白时期我国人民对西班牙帝国的看法如出一辙。”除了历史的教训,还有达尔文的种种发现:
一旦有机会,强大而饥饿的物种将会吃掉弱小、臃肿且无法自卫的物种……无论绵羊如何伤感,对狼而言羊肉一直都是美味佳肴……我们已经拥有想要的一切,现在只希望能够置身事外;但欧洲大陆强大的军事帝国却并不这么想。如果我们想要保有已经拥有的一切,我们就必须保卫它。
当然,出于同样的考虑,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们曾经也担心沙俄帝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并且认为同沙俄的冲突无可避免;但是那种恐慌只是老派的托利党人的特有心理,而且尽管许多“新”右翼同张伯伦在19世纪90年代末设想的一样,认为和德国的结盟将会自然抵消俄国的威胁,但他们对柏林当局的期待很快就幻灭了,并对德国的居心充满了怀疑。早在俄国军队无坚不摧的神话在1905年被日本人打破之前,人们便开始将德国看作强大得多的竞争对手,其原因就在于德国技术上的先进优势以及工业上的竞争力。此外,一旦德国扩张至其现有疆域之外,将会成为距离英国更近的挑战者,这令英国感到十分不安。经济实力与领地扩张一次又一次地被联系在一起:正如格雷指出,德国的“实力已经到达危险的临界点,开始令其蠢蠢欲动,萌生谋取支配地位的念头了”。那种认为冲突不可避免的设想一次又一次地清晰出现,引起了后世历史学家的高度关注:《泰晤士报》驻欧洲大陆的通讯记者,比如驻巴黎的拉维诺(Lavino)和驻维也纳的斯蒂德(Steed),都相信“德国将阴谋摧毁哈布斯堡王朝,削弱意大利,并会对德国的舰队进行部署,使马耳他、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处于其攻击范围之内”;其他人则指出,泛德意志主义文学作品和德国对低地国家的经济渗透均预示着德国将对荷兰或瑞士进行合并,或者认为德国将借攻打法国来解决国内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假设同政府的计划制定者的想法并无太大差异,以免有人会误以为这些只是英国政治社会中非官方、非主流的危言耸听者的恐德心理在作怪。英军总参谋部在1906—1914年之所以提出“欧陆责任”方案,就是因为它认为仅靠法国不可能阻击人口和工业都在飞速增长的德国;1907年1月,艾尔·克劳在其著名备忘录中,首先重点关注的就是德国在工业和力量方面的巨大扩张将会带来的政治后果;而直接参与军事规划的伊舍则感到:
毫无疑问,德国和欧洲争夺主导权的重大战事正赫然耸现,离我们并不遥远。1793—1815年发生的历史即将重演,只不过这次将是德国而非法国试图夺取欧洲霸权。德国拥有七千万人民,并决心在经济上占据绝对优势。为此,它必须削弱英国,将低地国家纳入德意志帝国。
当英国海军部制定第一批战争计划(1907年)时,它认为“(德国的)进一步扩张将是必然之举”,扩张的方向或许是低地国家,或许是奥匈帝国,抑或是拉丁美洲:
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个别人的野心了。德国已经被引上了一条已带来巨大物质繁荣的道路,无论政策制定者们现在是否想要后退,他们都不再有回头的余地。除非遇到强于自身的敌手,或者除非主导德国的相关政策不再具有能刺激增长、鼓励繁荣的蓬勃本质,否则扩张势必会持续下去。
我们将会看到,事实上这些都是决定论的观点,并且这些观点绝没有被英国人普遍接受。然而,另一个事实是,诸如克劳、斯普林-赖斯、吉尔乐、加文、埃默里和斯蒂德这些人,都不可能是在对德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作或发言的,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通晓德语,并且对德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高度关注。明显的事实是,确实有大量证据证实,他们所有最糟糕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大批德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从长期经济趋势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且同样也是持决定论的口吻来谈及这些。1896年之后的商贸扩张尤其使人更加坚信,德国是一个新兴的、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正是德国的竞逐带来了这一点。”瑙曼(Naumann)欣喜地说道。“它为我们带来了陆军、海军、金钱和权力……这种巨型的现代化权力机器,只有全体民众都能在它的各部分中尝到甜头,才会成为可能。” 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预言道:“德国再次作为主要民族出现。如果有谁能鹤立鸡群的话,那将是德国,而不会是法国或英国。” 仅仅是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就使得德国社会不可能原地踏步。“我们需要土地、土地,还是土地。”带有泛德意志色彩的刊物《海姆达尔》(Heimdall)如是宣称。席曼指出,我们“迫于地理位置和贫瘠的土壤……迫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不得不向外拓展,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争取更多的空间”。工业化正在不断吸引着大批离开土地、即将成年的年轻人,但是这一趋势反过来又在更大程度上迫使德国拓展世界市场,并大量增加粮食和原材料的进口。一旦这一过程开始启动了,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就连年迈的霍恩洛厄,在向一位朋友哀叹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时,也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如此,“世界政策”的设计者们也持有与霍恩洛厄相同的观点,当然他们的态度要积极得多:瑟杰尼在描述威廉和他那些知名政治家时,将他们刻画成一群随着德国的扩张,期待为自己的国家着手准备辉煌未来的人;他的判断绝对是正确的。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的领导者们心里没有其他的动机(比如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只是说明他们确信工商业的发展会使得某种“世界政策”无法避免。“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想要殖民扩张,”比洛坚称,“而是我们必须殖民扩张,无论是否出于我们的意愿。”让德国中止其“世界政策”就好像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子说:“要是你长不大多好,你这个麻烦的小伙子,那样我就可以不用给你买更长的裤子了!我们只能实行‘世界政策’。”作为一位坚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蒂尔皮茨则更加武断,在回顾往事时,他认为:“我们拥有了全球贸易,这迫使我们只能成为世界强国。”他在1899年9月于罗明顿(Rominten)觐见皇帝时试图表明,德国的工业化和海外扩张都是“像自然法则般无法抗拒”。至于威廉,他自1896年以后的所有私人谈话和公开发言都体现出他满怀着对德国的使命感,他告诉瑟杰尼,“德国在旧欧洲的狭窄边界之外有要完成的任务”;她的未来“更多的不是在欧洲,而是在整个世界”。
然而,就算巨大的经济增长推动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是当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都已被老牌帝国们瓜分为正式或非正式的领地时,德国又能如何作为呢?在这一点上,德国的统治集团实际上意见是一致的:特赖奇克的说教,黑格尔和达尔文的思想中有关国家发展与自我实现的论述,来自俾斯麦的“现实政治”传统,使这个答案成为必然。
为彰显德国力量,发出德国声音,
地球上必需还有空间!
这是海军协会中广为流传的打油诗,而比洛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将这首诗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我们不能让任何外部大国,任何外国的主神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世界已经被划分完毕……。’”德国要么成为铁锤,要么成为铁砧。马克斯·伦茨·森登(Max Lenz Senden)坚信,“要知道,只要足够强大,什么时候提出要求都不算晚!”这指的就是下个世纪全球范围的势力重新划分。对任何特定地区的权利主张,相比于兴衰起落的基本规律来说,只是法理意义上的旁枝末节罢了。“事实上起决定性作用的,”阿道夫·瓦格纳指出,“是实力和武力的原则,是使用武力与进行征服的权利,而且这必定仍将是决定性的因素。”《民族自由党手册》(National Liberal Party’s Handbook)解释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完全不能考虑任何限制军备的主张:作为世界大国中的后起之秀,“她还得努力赶上其他国家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取得的成就”。
然而,如果说德国不可避免的扩张将使它挑战既有的世界秩序,那么,受其影响最深的是哪个国家则是显而易见的。显然,有许多德国人在它的东方积极参与了同波兰人的争斗,或是盼望能碾压他们的宿敌法国人;但是如果话题涉及世界政策和殖民地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强大得多的对手进入视野。归根到底,是哪一股势力在一直不停地阻挠德国在安格拉佩克纳、新几内亚、东非、中国,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海外扩张?“从桑给巴尔到萨摩亚!这条不间断的给人带来无尽失望的海岸线!”《西里西亚日报》(Schlesische Zeitung)在回顾19世纪90年代时发出这样的呼鸣:“德国人逐渐意识到英国才是德国最大的敌人。”他们的导师特赖奇克不是早就坚持认为“最后的清算”将是对英国展开的吗?英国充满敌意的真实原因在于经济,是小店主民族(krämervolk)对德国商业取得的成就抱有的嫉妒心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因此,必然的结果是,“德国制造”引发了焦虑和骚动,《星期六评论》还凶恶地提出“德国必须被摧毁”(Germania esse delendam)——对此,蒂尔皮茨每次获得些证据时都会津津乐道一番。在被反复提醒存在于他们自己的“理想主义”和英国人现实的冷酷无情之间的不同后,德国的帝国主义者采用的是甚于所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和决定论。“英国人对我们的愤怒,”施托施告诉蒂尔皮茨,“其真正的原因是德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既然英国的外交政策完全由商业利益所决定,我们因此必须小心对付那些岛民的对立情绪。”他的门徒表示赞同:“强大的老牌公司都会在新兴公司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将它们扼杀。” 不足为奇的是,这一观点在威廉二世的新海军中非常普遍,于是在有关针对英国的行动计划或英德总体关系的所有备忘录中,作为一种政治开场白或辩护,都会提到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将我们看成是最危险的贸易对手。”
俾斯麦阵营的媒体将英国描绘成因格莱斯顿的所作所为和科布登的教义而陷入衰败,内政混乱、外政无能,人们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德国的历史学家解释说,那段时期受经济趋势影响仅仅是暂时的:在17和18世纪的战争中将商业对手都粉碎之后,英国,正如李斯特所指出的,狡猾地抛弃了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以削弱欧陆新生的产业。这个计划在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因德国和其他地方重新采纳贸易保护主义而遭遇滑铁卢,因此英国工业在此时是一百年来首次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竞争;也因此,英国在当前的“新重商主义”时代下所采取的行动颇为类似于克伦威尔和皮特时期。法绍达事件和布尔战争就是不祥之兆。在英国政界,格莱斯顿和坎贝尔-班纳曼的支持者们已经被时代所抛弃;而约瑟夫·张伯伦则是明日之星,是20世纪的“克伦威尔”。“ 张伯伦先生的演讲,”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上将认为,“给我们提示了英国未来的打算,就像当年胡德(Hood)领军包围土伦一样,英国在哥本哈根的行为说明,为了打垮一个潜在的未来对手,它是没有道德底线的。”蒂尔皮茨告诉比洛,英国现在对德国的敌对,“同它之前先后打败西班牙、荷兰和法国都是出于类似的原因。总是伦敦金融城在起作用”。卡尔·彼得斯(Karl Peters)一想到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德国受到的羞辱就心有余悸,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伦敦金融城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兽,将一个个外部国家吞噬殆尽;唐宁街就是为思罗格莫顿街(Throgmorton Street)服务的。而它健康勤劳的对手,比如德国,与这些势力格格不入。德国在一般英国人的眼里,就如同16世纪的西班牙,19世纪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俄国。(威廉二世:“对极了。”)德国人必须理解他们与英国之间这一最深刻的利益冲突。
进入新世纪之后,德国人谈起英国人时愈加紧张的口吻与早些年的满怀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也容易理解。19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在国际政治观察家们眼中的形象是一个“疲惫的巨人”,面临着来自多方的压力。尤其是在布尔战争的早期阶段,德国的评论家——与英国的评论家一样——都对英帝国的未来提出了质疑,并谈到了即将到来的“英国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English Succession)。然而,在陷入谷底没过几年,英国实现了惊人的复苏:扩张、重整海上力量;陆军改革;成功通过外交手段与法国、美国达成谅解,与此同时其盟友日本将俄国打得在十年内一蹶不振。由于他们相信大国间存在着对于世界财富和土地的根本性争斗,因此德国民族主义者认为伦敦与华盛顿、东京以及圣彼得堡建立友好关系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至少在接下来的十年,这些冲突将会暂时平息,这也意味着只有德国似乎还在挑战英国的商业及权力政治地位。然而,无论这个岛国是被看作(用比洛的冒犯言语来说)一头太胖而无法自我防御的公牛,还是“重新振作想再次成为斗牛的公牛”,基本局面始终是不变的:有另外一只动物想在英国公牛的地盘上分一杯羹。
蒂尔皮茨和比洛认为德国必须穿越“危险地带”。这一理论也体现了他们对未来的假设。他们之所以多次表示担心英国可能会发起攻击,是因为当时海上力量的不平衡;然而,只要能够避免战争,形势就会转向对德国有利。也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的文章中充斥着自然发展这样的说法。在1899年春天的萨摩亚危机中,蒂尔皮茨对很多人表示,英国对德国这个商业对手怀有很深的恨意,并“想要在我们的战舰破壳而出之前就摧毁它们”;比洛则写道,要“像毛毛虫还未破茧成蝶时那样小心行动”。根据世纪之交时海军参谋部的详细估算,从长远看英国很难在战列舰数量上保持现阶段领先于德国的优势;而即便是1908年之后蒂尔皮茨迫于压力放慢了海军军备竞赛的速度,他也始终坚持认为英国在财政上很快就会面临很大压力,从而愿意主动放弃独霸海权的企图。
(本文选自《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英]保罗·M.肯尼迪著,王萍、李高峰、胡二杰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转载时注释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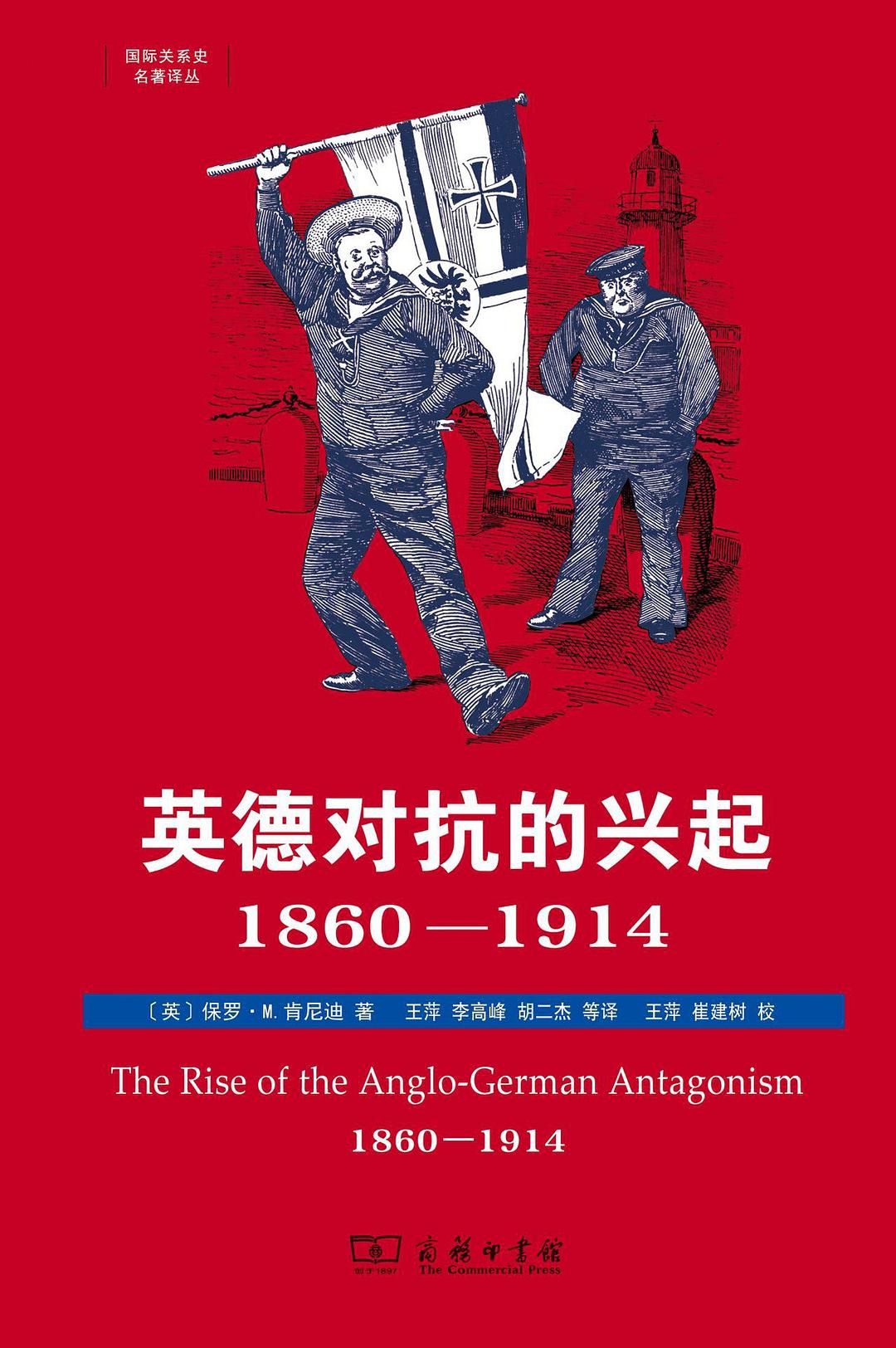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