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妈在北京做了20年清洁工 | 三明治


从我记事起,妈妈的工作一直是清洁工。
记忆的起点在一座北京城南的家属院小区。整整齐齐的几排六层老楼,楼与楼之间栽着柿子树,秋天的时候叶子落得很快,几个大风的夜晚就匆匆凋零,留下满树黄澄澄的果子。
跟随父亲来到北京打工的妈妈,找到了这份小区保洁的工作。幸运的是,我们一家可以住在小区的地下室,平日妈妈上下班非常方便。
妈妈的任务就是打扫小区。她和另一位四川来的阿姨,两个人一人一半,负责起整个小区的清扫,除了路面,还包括居民楼里的楼道和台阶。
妈妈个子高,体型灵活,干起活来勤快麻利。扫户外的大路时,她会用沉甸甸的竹子大扫帚,抡起来,落下,竹枝扑在柏油路面或者石砖地上,富有节奏地哗哗作响。而打扫楼道用的是小笤帚和一只墩布,先把明面上的大块垃圾扫走,再用半干的拖布一阶一阶地卷走尘土。偶尔在放学早的时候,我会掐着时间去固定的楼栋里找妈妈,背着书包跟她聊天,跟着她清扫的节奏,顺着台阶一阶一阶地往下蹦。
待她扫完最后一级时,我们再一起回家。我们的屋子很小,却被妈妈打理得井井有条,杂物柜、衣柜、上下铺、电视柜....…东拼西凑来的家具们如俄罗斯方块一般完美地嵌合在一起,最后留出几平米的空余,用来摆桌子吃饭。厨具们被摆放在楼道,回家之后,我们先一起坐一会儿,随后妈妈去做饭,我撑开折叠桌,铺上报纸写作业。等爸爸骑着电动车从另一个区下班回来之后,也差不多就到了晚饭时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饭菜的热气缓缓向上升腾,一如家乡悠悠的炊烟——在离乡几百公里的城市一隅,我们在这座小小的麻雀之巢,经营起流动的生活。
在周六日的早上,妈妈虽然不用像工作日那样忙一整天,但还是需要做简单的清扫,保持大体上的整洁。妈妈常常会在早上出门完成这些工作,在扫到我们楼附近的时候从窗户外面瞧瞧我。于是我常在半睡半醒间听到慢慢接近的、哗啦哗啦的竹枝扫帚声,那是妈妈正在走近地下室浅浅露出地面的小窗户边。她弯身下来喊我“丫头——睡醒了吗?”,我就赶忙坐起来扭着身子应声,美好的周末从这样的一声呼喊开始。
在工作的时候,妈妈要穿着工作服。一件类似于车间制服似的大褂,黑漆漆的深蓝色,罩住妈妈1米7多的窈窕身材,但盖不住妈妈身上浑身散发的活力——她爱笑,一口整齐的牙齿露出来,说话声音清脆爽朗,普通话讲得也特别好,几乎听不到什么口音。久而久之,她便和小区里不少老人们都熟悉了。
“小秦——”院子里的人们爱这样叫她。
妈妈的好人缘,让她得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在每周1、3、5、7的晚上,去一户人家做小时工,打扫家庭卫生。夫妻俩算是我们的老乡,在北京读了名牌大学,就此扎根下来。妈妈回来的时候会向我们描述他们的生活,比如不想做饭的时候就点麦当劳必胜客、不想洗碗的时候就堆在水池等着妈妈来清洗、吃不完的东西会随便扔掉不用心疼、女主人的衣柜里有很多名牌衣服和名牌包包…...他们是妈妈心中的榜样,她在教导我好好学习时,常用他们来做例子。

妈妈自己没有读过书,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受尽了没文化的苦“,于是便格外重视我的学习。当时我们住的小区旁边就紧挨着一所很好的小学,小区里几乎所有孩子都在这里读书。但因为我是外地的孩子,入学要额外交很多钱,叫做“借读费”——我忘记了具体的数目,但我想一定是到了我家难以承担的地步,才让父母很快便放弃。
于是妈妈开始四处带我去别的学校考试,以争取入学名额,但过程并不顺利。临近九月开学的日期,学校却还没有着落,妈妈愈发焦急起来。好在小区一户特别善良热心的老两口,也是妈妈平时用笑容、热心的问候结识下来的人,在跟妈妈闲聊时知道了这个苦恼,帮我们介绍到了我后来入学的小学,那所学校会招收不少外地的孩子。妈妈万分感激,连忙骑着车带我来学校报名。
假期的校园空荡安静,采光不好的楼道显得黝黑深邃。在办公室,我们见到了老师。但离入学的时间实在是近了,学校的招生时间已经过去了,老师对妈妈恳切的请求显得为难。妈妈教我出门等,她和老师单独说说话,然后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很多年过去了,但那扇门还存在在我的记忆里。那不是一般办公室的木门,而是一扇高大的防盗门,冷峻,森严,手指放上去冷冰冰的。我在外面紧张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妈妈出来了,我仰头看见她的眼眶,红彤彤的,是刚哭过的神情,但冲我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我获得了入学的机会。
之后我慢慢地理解这件事,在我等候在门外的那段时间,妈妈在办公室里面完成的那件事情叫做求情。不知道她究竟讲了什么,做了什么,为了我从容而无奈地狼狈。
小时候妈妈对我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我能通过读书,可以走上有别于她的更宽阔的路。冬天的时候,我们裹着棉袄,拎着澡篮和换洗的衣物去职工楼里洗澡。热腾腾的水汽蒸腾起来,浴室里闷热潮湿,我们赤条条地站在一起,轮流用一个花洒洗澡。妈妈耐心地给我搓澡,给我讲她小时候不能上学的事,反复告诉我要认真读书、认真读书。
我心里谨记着她的话,为了妈妈能在看到成绩时露出舒展的笑容而乖乖地努力。所幸儿时的我成绩还不错,一个学期下来,可以把能拿到的奖状七七八八拿个差不多。妈妈总会很开心,我能感受到我的存在于她是个重要的慰藉。姥姥姥爷去世得很早,妈妈一直也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加上爸爸年轻得时候冷硬、沉默,这段因为相亲而促成的婚事,也鲜少流露出过什么幸福的时刻。感性的妈妈满腔柔情,于是把很多的爱都投射在我身上。

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妈妈怀孕了。当时我就已经知道,这是父母有计划的备孕,他们想要一个男孩。到九月份快临产的时候,妈妈辞去了小区的保洁工作,一头长发也剪成了短短的齐耳发。在辞去工作的同时,地下室也不能再继续租住给我们了。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曾因为地下室房租的上涨搬过两次家,但是后来都又兜兜转转得搬回来。而在妈妈辞去工作的情况下,或许这间地下室真的要住到头了。
我们开始找新家。第一处找到的房子是临近铁道的平房,那片房屋快要拆迁了,周围已经有些快拆完的房子,断壁残垣堆在碎砖之上。我挺喜欢那里的,房子的面积是我们地下室小屋的两倍大。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离铁路实在是太近了,火车呼啸而过时,整个地面都随之微微震动起来。妈妈怕担心影响到肚子里即将出世的弟弟,又转而去找小区的物业商量,希望可以多租一段时间地下室。
就这样,一段并不安稳的预产期与月子就开始了。妈妈临产那几天,我住在了小区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好朋友、大我一岁的一个姐姐家,他们一家人都待我很好。记得下午五六点多,在医院的父母给这边打来电话,阿姨转述给我,一切平安,你妈妈生了个男孩——我舒了一口气。我庆幸他们可以如愿获得一个男孩,我弟弟,这样妈妈就可以不用像老家村子里那些母亲一样,继续生三胎甚至四胎,不用再多承受一个生命为家庭带来的辛劳。
从医院回来之后,我们又回到地下室短短地住了一小段时间。但事情谈得不算顺利,物业要求我们尽快搬走,爸爸只得继续去找新住处。需要不分昼夜地点着灯的地下室,并非照顾新生儿的好地方。妈妈就这样一点点熬着,日夜颠倒地照顾着弟弟,整夜地靠在墙上、被子上抱着他,哄他入睡。我看着自己的妈妈又从零开始成为母亲,想不起来当时有什么其他的感受了,只觉得她辛苦。
临近冬天的时候,我们找好了新住处,正式同住了六七年的地下室永久地道别,搬进了一栋居民楼里被隔音很差的简易墙分割成的一间小小的格子间,十平米左右。爸爸把奶奶接来了北京照顾妈妈月子,于是那间小小的屋子里,一张双人床,一张上下铺,奇迹般地住进了算上我弟弟在内的五个人。
妈妈因为此前辞工作的事情动了气,奶水变得稀少。她身上生产的伤口也还没有完全愈合,爸爸会为她定期抹药。每当这时,我坐在旁边的床上,看着眼前的一切,紧张地屏住呼吸。为了“下奶”,家里给她煮猪蹄汤、排骨汤、鲫鱼汤。浓浓的汤,汤汁发白,不会放太多的调料,咕嘟咕嘟地在锅里翻滚着。我掀开盖子凑过去闻,都是肉质原生的味道,撇撇嘴巴把盖子又合上。
为了让身体快点恢复好,让奶水再次充足起来,妈妈很努力地、超出自己原本的食量地,吃。当我长大之后看到《天下无贼》里刘若英含泪拼命往嘴里塞烤鸭时,总能想到那时的妈妈。但很残忍的是,即便费力气地进补,妈妈的奶水却没有恢复。原本窈窕的身材,也从那个冬天开始,吹气球一般臃肿了起来,此后再难瘦下来了,留下一团肥大的腰腹。
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妈妈全身心地照顾着弟弟。原本小小的,皱成一团的弟弟,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变成了白白胖胖惹人喜爱的样子。妈妈的状态也好转起来,在北京暖烘烘的室内暖气里逐渐有了红润的脸色,哄着弟弟玩时,眼睛里有化不开的温柔笑意。
我的初潮也在这段时间来临了,妈妈给我准备了卫生巾,告诉我网面和棉面的区别。两个生命在她的手上,这样前赴后继地生长起来。
快过年的时候,奶奶记挂着独自在家的爷爷,没有呆到过年就回去了。为了给弟弟拍些照片,妈妈从同在北京的亲戚那里借来了数码相机,给弟弟穿上红彤彤的新衣服,抱着他坐在床上,靠在贴着大张装饰画的墙边上,让爸爸拍照。之后妈妈又招呼我过来,让爸爸再给我们娘仨儿拍。我凑过去,靠在妈妈的怀里。
妈妈的怀抱永远那么温暖柔软。我想起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生病发烧,不小心拖成了肺炎。妈妈火急火燎地把我送到儿童医院,带着浑身烫呼呼的我打了退烧针。那一针可太疼了,我窝在妈妈怀里疼得直哭。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她紧紧地抱着我,低声呢喃着自责的话:“都怪妈妈没有早点带你来医院,早点治好就不用受这个罪了.....”带着变形的哭腔,泪水随之掉落下来,滴在我的脸上。
我始终记得那一瞬间的触觉。妈妈的泪,温热的泪,湿湿的泪,仿若一条暖暖的溪流,带着最深切的爱意,永久地蜿蜒进我的生命,成为滋养我长大的、最宝贵的养分。
如今,她有了另一个孩子,重新投入浑身的爱来呵护。但从一开始,我就从来没有害怕过偏心的事情。我知道对于妈妈来说,当有一个孩子,她会给出一百分的爱;而当第二个孩子出现之后,她不会将那一百分的爱平分成两份,而是尽她所能得,再拿出一百分的爱。
那个冬天的午后,二层楼的格子间里,采光比地下室不知道好多少倍。阳光暖烘烘地晒进来,我们既简陋又庄重地靠着墙拍照留念。妈妈一手搂着我,一手抱着弟弟,我们一齐冲着镜头笑。
我们三个同一个属相。这一年,妈妈36岁,我12岁,弟弟0岁。

等我读完了六年级下学期,为了让我早点适应老家的教学体系,也为了能降低照顾弟弟的成本、同时还能得到奶奶的帮衬,秋天开学之前,爸爸把我们仨送回了老家。我去了镇上的寄宿中学读书,一周回来一次;而妈妈则短暂地回归到了农妇的身份,在照顾弟弟长大的同时,在来年开春的时候,勤劳地经营起了我家那片闲置已久的田地。
水稻、青菜、玉米、豆角.....田里的作物一茬一茬地轮换,时间缓慢地进入夏天。妈妈耕种的技艺似乎也没有生疏,打理起田地来也得心应手。弟弟已经会走了,咿咿呀呀地学着讲话。周五放学回家的我,在小院子里陪着弟弟玩,听着妈妈在厨房叮叮当当地切菜。院子里支起小灶,木柴燃烧的炊烟味同蔬菜下锅的香气一同冒出来,令人倍感幸福。
于我来说,在老家生活的那几年是回归桃花源一般的美好日子,但是对妈妈来说,却无法同老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那样平静闲适。虽然此前清洁工的工作薪水不高,但是好在定期发送,月有所得。而回到老家之后,差不多是断了收入的状态。
让我切实体会到妈妈心中的不安,是那一年她种的玉米:从田辛苦地运回来,满满当当地码了整个月台,在秋日的阳光下金灿灿得好看——但最后只卖了不到三千块钱。于是在我读完初三,升上高中的暑假,妈妈决定再次离开家乡,像当年带着我一样带着弟弟,回到北京,去找一直留在北京打工的爸爸。
我不想让妈妈走,虽然我知道这是一件不需要我的意见的事情。多多少少有些不理解,留守在村子里的女人们,大都不是这样吗?丈夫在外打工赚钱,自己带着孩子在家,农忙时打理田地,剩下的时间操持些家务,打打牌,坐在树荫下一起聊聊闲天儿,生活平淡、安宁。尽管在家收入有限,可生活开销也随之降低——不是非去打工不可的。再说了,去外面有什么好的呢?狭小的住房、难以融入的城市,与此在那里做一名被视为底层的清洁工,不如安心留在农村,当平凡的普通人。当时的我这样想。

回到北京之后,妈妈带着弟弟住到了爸爸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后新找的住处,位于一个规模不小的城中村。妈妈把弟弟送去幼儿园,自己找到了附近一家公司的保洁工作。不仅如此,趁着中午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妈妈又在附近写字楼里的一家麻辣烫找到了一份小时工的兼职,在中午生意最忙的时候帮着煮食材。妈妈之后向我形容起这份工作时,有些骄傲地说,她煮出来的食材,总能掌握最恰当的火候。
生活重新紧锣密鼓地运转起来,妈妈所负荷的工作与劳动,比我儿时在北京时要重得多。高二升高三之前,家里在老家所在的市里买了一栋面积不大的房子,除了生活开销与攒钱之外,又多了一笔房贷的支出。再加上我和弟弟一个马上要上大学,一个马上要上小学,现在想想或许那正是父母压力最大的时候吧。
于是快入夏的时候,妈妈又去找到了她的第二份兼职,在一家水果店帮着卖水果,工作时间是晚上7点多,一直到11点往后——妈妈一天的工作时长,延长到了可怕的13小时。还好白天正式工作比较轻松,让妈妈有休息的时间。但那家水果店位置好,十字路口的旁边,又挨着一家超市,加上临近夏日,生意好得不得了,这让妈妈这几个小时的兼职,比白天一天的工作还忙。
放暑假的时候我会从老家过来北京住。吃过晚饭之后 ,妈妈去水果店忙,我则带着弟弟去公园遛弯。有时候会去水果店看妈妈,隔着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抬眼就看到她站在那家狭长的小店的门口,一边切西瓜,一边招呼客人。
妈妈干得很卖力,整个人精神抖擞,像是有着用不完的精气神。
她从货架上搂过一个西瓜,麻利地切开,用旁边的抹布擦去瓜皮上切瓜时淌下的汁水,一边笑着问客人要哪一半。给客人包好之后,还不忘记再推荐推荐旁边架子上摆放的桃子、葡萄、羊角蜜等等进货最多的夏时令水果。
夏夜躁动,晚归的上班族们、去遛弯的大爷大妈、上街觅食采购的人们......一如空气当中久不消散的燥热,让这条街可以热闹到快十点——店里的客人终于慢慢稀少下来,而妈妈的工作还远未结束,她整理货架,清扫店铺。快11点的时候,运西瓜的车开到店门前,妈妈上前,配合着店主,把圆滚滚的西瓜们挨个抱进店里。一切都打理妥当之后,整条街早已沉静下来,妈妈这才沿着路灯,踩着影子,拖着满身的疲倦回到家中。
尽管辛苦,妈妈却显得动力十足。多干一点活,意味着可以多一份的收入,让家里的花销不再那么紧张。然而,对于当时的妈妈来说,体力上的劳累倒是其次,家中的琐事、争吵、相互埋怨,却严重地消耗着心力。因为妈妈晚上的工作,弟弟需要爸爸来照顾,家里干不完的家务也得爸爸来承担。而对此,爸爸显得不满。工作一天的他只想歇着,常常在饭后丢给弟弟手机让他玩,而不是带着他出去遛弯、运动,让弟弟的体重在那段时间一下子涨了上去;对于家务也显得敷衍,常常需要妈妈从提醒到吼叫,才勉强收拾一下。
于是在那几年,一到暑假,回到家里的我,常常要面对在窄小的出租屋里乱作一团的争吵与指责。生气时的妈妈会用她嘹亮的嗓音大声地嚷,情绪臌胀在身体里,神情里带着愤怒和委屈。我才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妈妈已经有了苍老的神色,眼角的皱纹多了不少,面容显得沉重而疲惫。再后来,妈妈换了一份晚间兼职,给一家小公司打扫办公室,但时间仍在夜间的三个多小时。
爸爸会断断续续地表达对妈妈找兼职的阻挠。妈妈不悦,不做什么犹豫地就拒绝了他,继续同往常一样,陀螺一般奋力地旋转在正式工作、晚间兼职和家之间。他们会继续争吵,虽然多数时候是妈妈单方面的责骂,爸爸显得沉默、厌烦。弟弟从上了三年级成绩就开始下降,爸爸还是漫不经心地管教是妈妈焦虑却难以花太多时间顾及。
日子一直这样紧紧地绷着,而这其中,妈妈是最大的压力承受者。
在那几年,尽管我和妈妈一样厌恶爸爸的态度,但我却和爸爸一样,希望妈妈可以停下来。我希望妈妈不要那么辛苦,不止是因为她受累,而且我不想面对道德上的负罪感;我希望妈妈晚上可以陪弟弟、带弟弟玩,不要把照顾孩子的任务推到我头上,也希望她可以耐心地教育他,不要用那种急躁焦虑的态度;我希望妈妈在时间宽裕了之后,可以不用每天那么火急火燎跟爸爸生气,对她身体不好,而且我也不想要这鸡飞狗跳的家庭生活。而且我在那时,面对父母经常的对峙,不知道如何和爸爸交流,怯懦的我只会在争吵过后安慰妈妈,根本没有意识到潜藏其中的最重要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妈妈惯常地责备爸爸对家务置之不理,爸爸闷声闷气地反驳道:你就每天在家做好饭,收拾好家务带好孩子不行吗?整天瞎折腾什么?
这句话像是像是一道闪电,突然让我意识到,我们,父亲、我、弟弟,都施加给了妈妈什么呢?她如此尽她所能地分担家庭的经济压力(并且因为爸爸挣得多,我觉得他并不能认同妈妈辛苦劳作的意义,在他看来“去挣那两块钱不如照顾好家”),但与此同时,还要承受我们所有人对她在家务事上的期望、在养育子女上的期望,希望她可以做一个更完美的母亲。
就连我也是一样的,即便在父亲应该操持家务这件事的态度上和妈妈站在同一阵线,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难道不也认为着:反正爸爸也干不好家务,要是妈妈辞职来干的话,大家都省力嘛;反正爸爸也带不好弟弟,又死板,不如妈妈来带嘛。
连我也在给爸爸开脱。
所幸妈妈如此坚定,她气势汹汹地骂回去:“什么都等着我干,要你这个当爹的是摆设吗?!”

随着妈妈辛劳的努力,加上爸爸在工厂也凭着多年的经验和积攒的技术小小地升了职,家里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妈妈对于她的新兼职非常满意,不仅工资上跟水果店比起来可观不少,公司的领导人很不错,见妈妈工作得勤快、细致,陆陆续续给妈妈涨过几次工资;平时节假日发月饼、粽子的时候,也少不了妈妈的份,过年时还有几千块钱的年终奖。妈妈会在那几天等待那“嗡”的一声短信提示,看着红火的数字打进工资卡里,妈妈眉头舒展,露出满足的笑容,眼角的皱纹密密地堆叠。
“秦姐——”公司的人常这样叫她。一位女领导待她向来都很尊重、礼貌,妈妈打心底敬爱她,有时候会买盆栽、鲜花,放在那位领导的办公桌上。那么爱花的妈妈,家里的花还经常是我买的呢,但是她买的鲜花,总会给那位她喜爱的女领导。
日子缓慢地拉扯。在妈妈的不懈的“训导”之下,爸爸虽然也免不了抱怨两声,但作风也终于有所好转,近来勤快了不少,性情上比年轻时柔和很多,也给予了妈妈更多的关心。而在工作之外,妈妈还做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独自搞定了我家新房子的装修设计。我爸想完全甩手扔给施工队,但妈妈决心要装得满意。于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妈妈在工作休息的间隙,一点点在抖音上刷,在海浪一般的信息碎片里挖,硬是在上面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装修风格,从墙面的乳胶漆配色、电视墙的风格、瓷砖花式的选择....…挨个去钻研,和装修队“斗争”,最终在今年夏天,基本完工。让我惊讶的是,妈妈把新家弄得非常棒,洁净、大方、温馨——那是她了不起的作品。
明年,就是我弟六年级毕业的时候了。12年过去了,就像轮回一般,我们的生活转动到了相同的境遇——他需要像当年的我一样,为了高考返乡读书。因为新房子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所以回去的话,大概率会回到新住处,而非老家的村庄。我对此显得兴奋,揽着妈妈的肩膀笑嘻嘻地说,太好了,这样你可以好好歇一歇了呀!养个小狗,拍拍视频,多舒服呀。
妈妈喜欢拍视频。我超级喜欢她拍视频的样子,喜欢她盯着屏幕中的自己仔细瞧,给自己选好看的特效,配着音乐认真唱。我喜欢她关照自己的样子。
但让我意外的是,对于回新家这件事,妈妈却显得有些低落。
我刚开始权当她的低落是因为一直以来的挣钱上的压力,就凑上去献宝,“诶呀妈,我明年毕业马上就工作了,也开始挣钱了,你就安心歇歇呗,这几年过得也够辛苦的了。”妈妈没理我,有些无奈地叹口气。
妈妈说,她舍不得放下这份工作。
我一愣。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将来会进入家庭、我是生育后的母亲,当我需要为了我的孩子的学业,放弃我原本的工作,我会是什么心情呀?我因为妈妈的工作是清洁工,就忽略掉她自己对工作的追求吗?这好傲慢。
我开始觉得,我向来对于妈妈的理解都有偏差。从前我是怎样理解她的呢?我觉得她孤单,父母早逝,没有什么亲密的女性朋友,喜好浪漫却从来不曾恋爱过,在数十年的撮合当中才终于同父亲的关系磨合成了亲情;我觉得她太辛苦,跟随我爸来京打拼,在贫穷与辛劳中告别青春;我觉得她勤劳而强大,为了家庭勤勤恳恳。
此前她在我心中似乎从来都只是——含辛茹苦的,奉献牺牲的——中国式母亲的形象。我有理解过她在一位母亲之外,那个“小秦”、“秦姐”的身份吗?妈妈喜爱她的新兼职,不光因为挣得钱多了,同样重要的是她在其中获得尊重,用自己漂亮的工作成果换来认可;没怎么读过书、网络技能也不太好的她,完成了很棒的房子装修规划.....
我的心里像是加了热的肥皂水,饱胀的泡泡咕嘟嘟地翻滚了出来。我突然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要不让我弟去念寄宿中学,周末的时候过来住?”我为自己的主意兴奋了一下,然后补充道,“但是你只干晚上你喜欢的那个工作好不好,把白天的辞掉。”
妈妈抬头有点惊讶地看着我。她想了想,半开玩笑地说:“再说吧!万一你弟弟要是还不认真学习,就让他在北京念中专得了,这样就不走了......”
或许大概率她还是会回家老吧,但我想,妈妈还会把她那时的新生活,再次经营得热闹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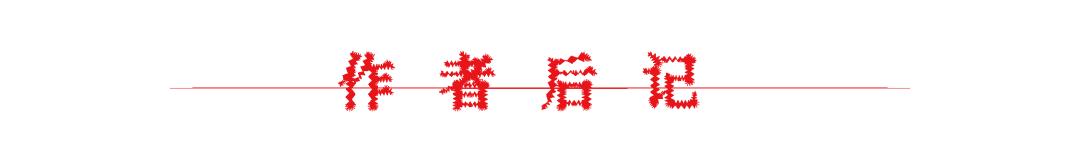
一边写一边慢慢回忆同妈妈这20年来一起走过的这些日子,温馨也惆怅。但很开心我终于长大了,能够并肩站在妈妈身旁,更好地理解她、爱她。
在完成的过程中,读到了一篇文章《流动中妇女的母职实践和主体重塑》,完全写出了我在妈妈身上所感受到的城市务工女性面临的困境(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微信搜一搜里就有全文~)。妈妈不仅在养家与母职的双重压力之间奋力周旋,还了不起地在体力劳动当中渐渐唤醒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与肯定,真希望这篇作品能够把这些坚韧而闪闪发光的特质传达出来些许。
最后谢谢旁立老师!半个多月来一直耐心地鼓励我、等待我,用心阅读我的表达,从不吝言夸奖,真的是帮我坚持下来写完的很大很大的动力,表白旁立老师~!
原标题:《我妈在北京做了20年清洁工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