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卡夫卡的情书集比他任何一本小说都长丨此刻夜读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
Love
Letter
”
情书就像人类情感的研究标本,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美学意义。这些私密的情感让我们领略到爱的千姿百态……工科男丈夫向居里夫人求婚的“素颜”情书,济慈大吐吃醋、嫉妒苦水的“撒娇”情书,“恐婚狂魔”卡夫卡不断撤回的“誓言”情书……名人们的情书里有他们对爱的理解。
作家张天翼在其译编的新书《81种爱的写法》里直率地解读这些情书中爱的千万种面目,带领读者一观爱情在各种人生中的不同模样。

弗朗茨·卡夫卡致菲利斯·鲍尔
菲利斯:
我现在写信是想请你帮个忙,这事听起来很疯狂,如果收信的是我,我也会觉得不可理喻。
即使对脾气最好的人,它可能也是一项极大的考验。
那就是:一星期只给我写一次信,那样你的信便可在周日送抵——因为我受不了每天收到你的信,我实在受不住了。
例如,我给你写了回信,然后躺倒在床上,貌似平静,但心脏狂跳,浑身战栗,满脑子都是你。
我属于你,除了这话,我实在没有别的方式能表达,而这表达也仍不够充分。我不想知道你的穿着,它让我心烦意乱,简直再无余力生活,也因为这个,我无法去想你对我的爱意。但凡一想,像我这样的傻瓜,还怎么能呆坐在办公室或家里?我只能闭着眼,跳上火车,直等到见了你再睁开眼睛。
哦,我不能那样做,还有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简言之,我的健康状况只允许我过单身生活,无法为人夫,更休提为人父。但每当读你的来信,我都有种错觉,觉得我能忽略那些实际上无法被忽略的事。
若是现在我手中就拿着你的回信,那该多美!我竟然这样折磨你,逼你在安静的房间里,阅读桌上这封最讨厌的信!老实讲,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幽灵似的,四处捕捉你的芳名。如果周六我把那封信寄出去就好了,信里我恳求你别再给我写信,我也保证再不写了。
哦,天哪,我到底为什么没把它寄出去呢?真寄了,一切都好了。那现在还有没有和平解决的方案呢?如果我们一周只通信一次,能不能管用?
不,如果这么容易就能解脱痛苦,那说明它并不严重。我已预料到,即使只在周日收一封信,我也很难承受。在这封信的末尾,为了弥补周六那个失去的机会,我用仅余的力量请求你:如果我们还珍视生命,就彻底断绝通信吧。
我是否考虑过娶你?不,那将是大错特错。不,我已经永远被自己束缚住了。这就是我,我只能这样活下去。
弗朗茨
1912年11月11日
最亲爱的:
……你周六寄出的信,我今天收到了,晚些时候周一的信也已送达。昨天下午,运送柏林邮件的邮车起火了,导致今天整个上午我都笼罩在愁云惨雾中,心情沉重,一直想着那辆被烧毁的车,很可能你周一发出的那封描述外出经历的信已随之化为灰烬。不过迟些信还是来了,并没有被烧掉……
1916年10月18日
于布拉格

凡见过弗朗茨·卡夫卡照片的人,一定对那张脸印象深刻。
他无疑是英俊的:发际线很低,前额清秀,双耳从头颅两侧警觉地支出去,薄嘴唇抿在一起,眼睛亮得令人不安,目光好像能把凝视的空气烧出个洞。看一眼就知道那躯壳底下有一个敏感、忧郁的灵魂。

卡夫卡
他大可早早开始恋爱生涯,但实际上他直到29岁才交往第一位女友,即上面那封信的收信人菲利斯·鲍尔。1912 年他在评论家马克斯·勃罗德(此人是卡夫卡的挚友,卡夫卡弥留之际, 嘱托他烧掉自己的手稿,然而勃罗德权衡再三,选择把遗稿公之于众,为文学界立了大功)家中见到菲利斯,立即心生爱意。菲利斯比卡夫卡小 4 岁,虽然相貌平平,“瘦削而无表情的脸庞……光着脖子,披着衬衣,穿着打扮像在自己家里一般……几乎像是被打坏的鼻子,有点儿僵硬的、毫无光彩的金色头发,厚实的下巴”,但精神强健,是个活泼能干的姑娘。
相恋不久,他写了短篇小说《判决》,副标题为“献给菲利斯·鲍尔小姐的故事”,从9月22日晚上 10 点一直写到第二天清晨6点,用了8个小时。
他们订过两次婚,两次解除婚约。1913年他写信向菲利斯求婚,然而几周后就分手了。在这期间,卡夫卡完成了短篇小说《判决》,接着他开始创作《变形记》。第二次订婚后,卡夫卡开始写长篇小说《审判》。
然而菲利斯并不支持卡夫卡的写作,卡夫卡试图通过写信的形式,掏心掏肺地说服菲利斯。交往 5 年,卡夫卡写给菲利斯的信多达500多封,大部分是深夜写出来的。他去世后,这些信结成集子出版,取名《致菲利斯的情书》,其德语版厚达800页, 比卡夫卡任何一部长篇小说都长。
读他的信能充分感受到,他那种令人窒息的自我意识,谈起恋爱来是多么纠结,精神又是多么脆弱,明明极度渴望收到女友的信,却禁受不住天天收信。后面又是一大串颠来倒去的话,把每周一封信的说法又推翻,“如果周六我把那封信寄出去就好了,信里我恳求你别再给我写信,我也保证再不写了……我到底为什么没把它寄出去呢?真寄了,一切都好了……如果我们一周只通信一次,能不能管用?不……我已预料到,即使只在周日收一封信,我也很难承受……如果我们还珍视生命,就彻底断绝通信吧”。磨磨叽叽,磨磨叽叽,我翻译的时候都生气了。他是在往后撤退,以一种真爱至上、造化弄人的姿态后退,总结一下就是 “不要太爱我,咱俩没结果”嘛。
第二封关于邮车起火的信,写于他们第二次订婚之后。几个月后,他再次主动结束了婚约。
卡夫卡渴望得到爱情,他也不是不爱菲利斯,“没有她我活不下去,和她在一起我仍然活不下去”。但他对婚姻的恐惧感太强烈了,导致他每次把恋爱谈到深处就推进不下去,反复订婚、取消婚约。他常用的逃避理由是身体不行,“我的健康状况只允许我过单身生活,无法为人夫,更休提为人父”。他甚至以“睾丸大小决定性能力”等露骨的话暗示菲利斯,他在性方面无法满足她。
在另一封给菲利斯的信中他写到自己“是文学的一部分”。他怕婚姻会挤占他用于写作的精力。
后来卡夫卡又投入地恋爱过至少三次:与布拉格的鞋帽女工尤莉叶、有夫之妇密伦娜(他写给她的信,被她在潦倒困顿时高价卖掉了),以及他生命最后11个月遇到的朵拉。当年未能被菲利斯点燃的承诺,在面对朵拉时他终于有勇气说了出来,他们计划到巴勒斯坦定居,开餐厅。去世前一个月,他最后一次求婚, 但这次订婚也没能走到婚礼。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在朵拉怀中停止呼吸。

皮埃尔·居里致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
亲爱的玛丽:
得到你的消息,是世上最让我快乐的事,然念及未来两个月无法收到你的信,又让我非常难过。也就是说,你的小纸条对我越发重要。
盼你多多注意健康,10月便可回到我们这里。至于我,我就待在乡间,哪儿都不去,成日消磨在敞开的窗前或花园里。
我们已经互许了承诺,是不是?至少做最好的朋友。但愿你不要改变主意!因为承诺并无约束力,它不能给意志强加什么命令。我想和你并肩携手,沉醉在梦想中:你报效祖国的梦想,我为人类谋福利的梦想,我们的科学之梦。如果能度过这样的一生那该多好,我简直不敢相信它会成真。
我想,以上所有梦想只有最后一个切合实际。因为你我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秩序,即使有能力,也不知怎样做。若要诉诸行动, 不管哪个方向,我们永远无法确定,阻碍必然发生的社会演化进程是否损多于益。从科学角度来看则恰恰相反,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因为科学的土壤更为坚实,不管我们做出多么微小的发现, 都必将留存下来,成为切实的收获。
关于做朋友,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但如果你一年后离开法国,此后再不相见,我们的关系就只剩柏拉图式的友谊。留下来跟我在一起,不是更好吗?我知道这种问题会惹你生气,你也不想再聊这事。我由衷感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配不上你。
我希望你允许我某天到弗里堡见你,可你只在那里住一天——也许我搞错了——而那天你肯定会被我们的朋友科瓦尔斯基夫妇占为己有。
你可信任的、忠诚的
皮埃尔·居里
1894年8月10日

1894年春天,27岁的波兰姑娘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正在巴黎大学准备学位考试,见到了比她大10岁的大学教师皮埃尔。为他俩引见的,是同在巴黎大学的波兰裔教师科瓦尔斯基夫妇——上面那封情书末尾提到的二位,他们当时就隐隐有一点儿“做媒”的心态。
转年7月,玛丽与皮埃尔以最简单的仪式,结成了科学史上最了不起的一对伴侣。
多年后,玛丽在自传里讲到皮埃尔的情书:“1894年夏天,皮埃尔·居里给我写的一些信很有文采,热情洋溢。信都不长, 因为他习惯了言简意赅,但他每一封信都在诚心诚意地表达着他对我的一片深情,希望我能成为他的终身伴侣。我对他的文字功底十分钦佩。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三言两语就把一种精神状态或境况表达出来,而且是用一种十分简朴的方式讲出事情的本质,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接着她引用了上面这封“他殷切希望我能成为他妻子的信”, “根据这封信,我们可以明白,对于皮埃尔·居里来说,他的未来就只有一条路。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的科学梦。他需要一位与他一起去实现这一梦想的伴侣。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他之所以直到36岁都还没有结婚,是因为他不相信会有符合他这一绝对条件的婚姻存在……
从所引述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皮埃尔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对人类有着无穷的力量,这种信念是坚定不移的”。这真是一封十分“工科生”(或者说,符合“大众对工科生的刻板印象”)的情书,先列出理想的一二三四,然后分析论证哪种人生路径最切合实际、最有可能实现。没有什么浪漫的句子,但这种简约、脚踏实地和以理服人的风格,比不着边际的大话 、梦话更具动人之处。
在这封简洁的情书里,皮埃尔说他将“成日消磨在敞开的窗前”,那也是玛丽对他的第一印象:他们初见时,皮埃尔站在一扇朝着阳台的落地窗旁,就像窗户里镶的一幅画。
令人略感讶异的是,皮埃尔认为自己“在各个方面都配不上”玛丽。实际上,当时他已经是取得过巨大成功、蜚声业界的物理学家了。他与其兄长雅克一起发现了压电的新现象,确定某些晶体的绝对量,发明了后来广为应用的“居里静电计”……而玛丽当时只是个还没取得硕士学位的青年学生。他是否那时就发现了她身上像镭元素一样不为人知的光芒?
婚后他们的确过上了他所憧憬的、“沉醉在科学之梦”里的生活,只是这生活结束得太早、太凄厉。1906年4月19日,皮埃尔在街上被马车撞倒,头骨破裂而死。那天他离家时最后一句话是问玛丽“去不去实验室”。
玛丽在日记里写道:“我的皮埃尔,我们生来就是要一起生活的,我们的结合是必然的。唉,这生活本该更长一些。”
她亲吻他那沾着血和脑浆的衣服,将之剪成碎布,投入火中。他们11年婚姻所共创的“留存下来,成为切实收获”的,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和两个女儿(长女于1935年与其丈夫共获诺贝尔化学奖)。
内容选自
张天翼/译编
中信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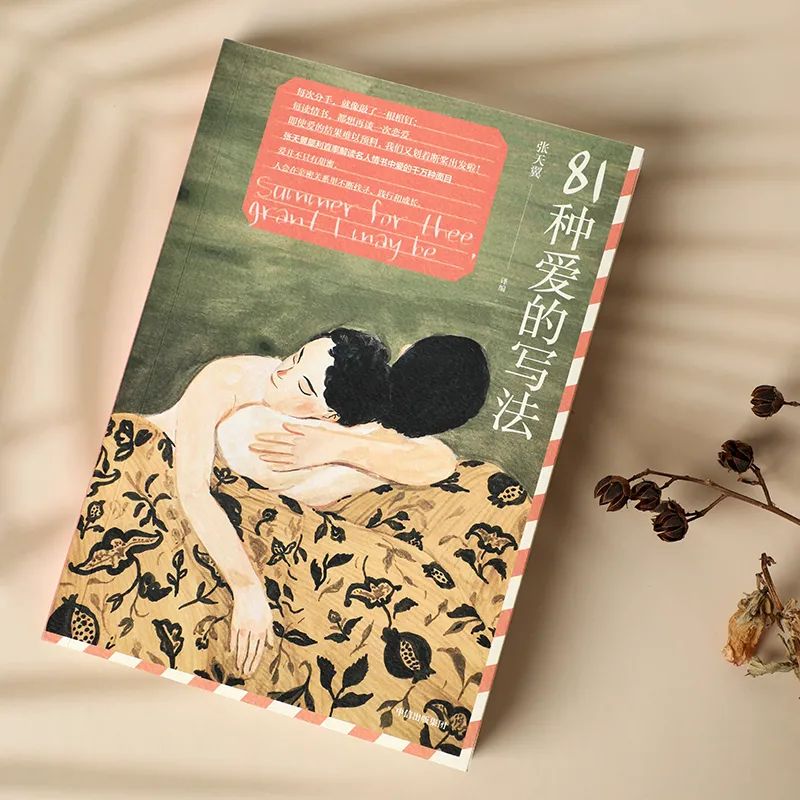
原标题:《卡夫卡的情书集比他任何一本小说都长丨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