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匿名十三年 | 流动中的世代
Sixth Tone(第六声)此前举办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以“世代”为主题向全球写作者征稿,最终12篇稿件从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近450篇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项。获奖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间的华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热衷观察世界的中国学生……他们以扣人心弦的笔触写下历史潮流下的个体命运、对家庭传承的复杂情感、国际交流中的碰撞和收获,展现出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结的多元样貌。
(本文获第六声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一等奖)
本文图片来自于许鞍华电影《投奔怒海》
作者:段文昕
英文翻译:Wang Jiyuan
一
坐在隔离酒店的床上,电视播放综艺节目的背景音,欢笑吵闹,永兰俯下身去,按了按自己的小腿肚,尽管已经出狱一个月,腿上仍然有镣铐的印记,她试着拍一张照,觉得很丑,又将照片删掉。
她记得那天判决完毕,走出新加坡法院,狱警将镣铐扣在自己的手脚上,沉重的铁环让她往下坠,就像电视上看过的情节。恐惧和忧伤涌出眼眶,这是她决定自首以来,第一次没有忍住,哭了。
判决书上,永兰的罪名是逾期逗留。2009年,永兰花一万中介费,办理了新加坡的旅游签证。抵达新加坡,她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期限:不回国,一直工作到被警察抓住的那天。一开始,她住在福州老乡的群租房里,屋内最多时挤过二十个人,大多和她一样,是没有身份的黑户。

永兰的家乡福清——一个临近低矮青山和内海的小镇,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掀起出国打工潮。因受教育程度有限,又不甘于县城低廉的薪水,不少人选择用偷渡、假结婚、换人头(指借用别人的护照)等非法方式出国,他们将华人超市开进阿根廷,把按摩店扩张至唐人街,足迹遍布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
与永兰同屋的福建男人,一赚到钱便爱去喝酒,就像她曾经的丈夫。半夜回来,酒瓶砸在地上,哐哐作响。玻璃碎渣令永兰恐慌,她听到邻居报警了,于是赶紧收拾东西,赶在警察来之前离开。她按照过来人的经验,把别人的工作准证复印,再贴上自己的照片,试着去租本地人放出的房子。房东不放心,核实出身份是假的,永兰再次搬了出来。如此折腾三四趟,后来,她认识了一个胆大且缺钱的马来西亚人,他的女朋友和永兰是同乡,大家互不说破,便住下了。
因为没有工作准证,永兰选择做钟点工,不用查验证件,用手机沟通,现金结算,工资可观,危险更小。十三年来,永兰的日程几乎没有变化。她一周做十户人家,清晨六点起床,八点抵达雇主家开始工作,午饭是打包的三新币的海南鸡饭,她常坐在楼道间,在十五分钟内匆忙吃完,才能在下午一点准时到达另一户人家。
永兰的第一任雇主是一对中国夫妇,在新加坡从事科技工作,待人和善。他们的儿子也在新加坡长大、成家,待儿媳怀孕后,永兰便转到他们的新家,继续旧日的工作。
为了不暴露黑户的身份,大多时候,她会说自己是陪读妈妈或单亲妈妈,辛苦劳动是为了孩子的学费。到了年轻女孩家,永兰就强调自己是随丈夫来的,男人在身边。她称之为“善意的谎言”,说多了便习惯,但有时也容易混淆,有一回,她忘了自己是单亲妈妈还是陪读,在雇主前说错了话,回去后,她告诫同伴,谎话不要编太多,认准一个就好。雇主常常会被她们骗倒,直至警察打电话来通知,他们才恍惚地问:“谎言讲得那么美,怎么会是假的?”
新加坡的热浪如海,缠绕不绝,人同被单一样晒着。从三十岁迈进四十岁,永兰发现自己变得更怕热,尤其在扫厕所时,白净的瓷砖映出她被汗打湿的影子,像云投下的阴影。朋友笑永兰笨,为什么不开电扇,一直对着马桶吹。她连说不行,这是在别人家干活,开电扇不就成了享受。到了春节,永兰还会把女儿寄来的家乡特产——鱼丸和紫菜送给雇主,再给小孩塞一封红包。
找她的人渐渐多起来。永兰曾给一户印尼人家做清洁,只去一次就拒绝了。她走进厨房,看见墙壁上粘附厚重的油污——他们爱炸东西的痕迹,气味很重,永兰擦起来太累。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有许多繁琐的讲究,雇主警告她:小心家里的地板,是大理石的;别摸柜子上的包包,很名贵的。永兰的手连忙停在空中,心里默念一句:“去你的”。有一回,她在熨衣服时烫出一个洞,女主人拉住她,说衣服是在香港买的,真丝材质,得赔两百新币。永兰上门,每回只收一百,她干脆搭上这次工钱,再也不来了。她很怀念在新加坡当老师的英国夫妻,总和她保留礼貌、合适的距离。每当工作开始,夫妇二人就会把孩子带到室外骑脚踏车,到结束时间再回来。有需要叮嘱的,他们便写张英文纸条放在柜台,永兰半蒙半猜,实在看不懂的,就带回去让男友杰哥翻译。
永兰和杰哥是在一场卡拉OK上认识的,刚到新加坡,女伴把认识的朋友叫出来一块玩。摇晃的彩灯下,男男女女,永兰显得比较沉默。第二天,她接到了杰哥的电话。杰哥是新加坡本地人,比永兰大12岁,他的妻子早年过世,留下两个女儿。杰哥有一家汽车修理厂,雇了一位马来西亚工人。杰哥在电话那头,问道:“我要养你,可以吗?”她愣了一下。
永兰知道身边两个女伴,都找了本地人作男朋友,这也是她们的生活支柱。她们备着两个手机,可以不留痕迹地和多个男人保持联系。曾经留学新加坡的女作家九丹,在小说《乌鸦》中写过被新加坡人称作“小龙女”的中国女人,她们的天地在夜总会、酒店、床单和浴室内。来钱快,也更容易被警察觉察。
二

永兰同意了两人搭伙过日子的请求,杰哥又问她需要多少钱,永兰算过国内家人的开销,提出要五千人民币。听到后,女伴笑她笨,说没有人像永兰这样,“一棵树上吊死”,来新加坡还过安稳日子,直至2019年末,新冠肺炎席卷,大家又羡慕起她的安稳。
没有身份无法进出医院、打疫苗,领口罩,她们的生存空间在不断收紧。永兰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打完疫苗之后的感受,并尽可能讲得真实细致。“打完没什么反应”,她这样对雇主说,“就是有点犯困”。
一条短信在她们间流传,那是有工作准证的人的疫苗记录,上面具体有接种的时间、地点,种类,她们保存好,将姓名换成自己的,展示给雇主看。永兰还会把紧缺的口罩送给雇主,以表示自己也能从政府处领到。
2020年的早春,因为房东欠债卖房,永兰不得不搬离居住了十年的屋子。生活好像自那一日开始滑坡,变得剧烈而危险。
四月,新加坡颁布封城令,人们进入公共场合需要追踪码。商店、菜市场、百货公司门前立着保安和检测仪器,永兰无法进去。两个月来,她的餐桌上几乎没有荤菜,只有吃素,以及杂货店里卖的干粮、马铃薯、地瓜。她偶尔会去杰哥家住,让杰哥多买一些食物,顺便给独居的朋友送去。
街上巡逻的警察更多了,她将习惯的夜跑改成一周一次,晚上几乎不出门。
唯一不变的是做工,将口罩系紧,永兰仍旧是一家一户地跑。没想到连公寓也开始检查证件。她索性坐在门外边,看见推儿童车的人家开门,趁机跑进去。进入家中,永兰和雇主抱怨几句:“今天又查我,好严格啊。”
杰哥的小女儿是护士,偶尔会回杰哥家住。2020年9月29日晚上,永兰做了三菜一汤,三人围坐着吃饭,永兰发现杰哥的女儿有些咳嗽。睡前,她敲开杰哥女儿的房门,提醒她注意身体,还递去一杯热水,就像往常平淡的夜晚。
次日清晨4点,杰哥的女儿打来电话,说自己确诊了,按新加坡的政策,永兰和杰哥需要居家隔离。
家,这个词对永兰而言很模糊。永兰考虑了四小时,觉得无处可去,决定要自首。同时,她清晰地感到,无论是回去还是留下,自己都会后悔。
假如,永兰想过许多可能。假如她在杰哥家隔离,即便感染了也无法进医院治疗。假如她去移民厅自首,或许有接种疫苗的机会。疫情爆发以来,白天的警力也在加强,她们建的许多微信群,不断因为共同好友入狱而解散、彼此删除。有个朋友被抓到遣返回国后,劝永兰去自首。
“去自首,起码还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朋友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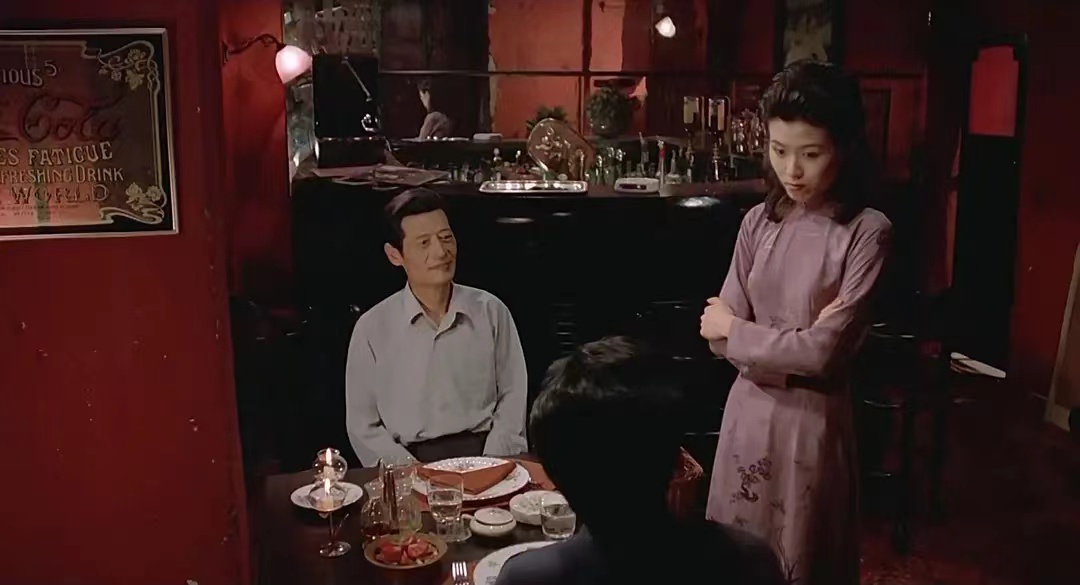
九月的新加坡,偶尔飘来很短暂的凉意。下午,永兰挑了一件黑白条纹衫换上,横竖看了看,也没觉得多漂亮。她的衣服都是儿子从国内淘宝转寄来的,整理过后,又扔掉不少,最后只剩下一个行李箱,再加上一个背包,像一名简单、轻松的游客。
在进移民厅前,永兰和家人拨了一通视频电话,母亲、女儿、儿子,浓缩在屏幕的四方格里,永兰简述自己的决定和安排。女儿从她尽量保持的冷静语气中,听出一丝死亡的寒意。女儿哭了,让她拍一张自己的照片。永兰打开了美颜相机。
她的身形清瘦,大概是坚持跑步的原因,眉毛理得很纤细,双颊饱满。黑色口罩上方一双眼睛明亮,仿佛被水洗过,安静地看向家人。
被送进樟宜女子监狱前,移民厅的长官向永兰抛来一个机会。一男一女站在审讯室,严肃地问道,永兰认不认识像她“这样的人”。他们早查过永兰的手机,还有几个没来得及完全删除的回信。长官问她,要不要来当警方的线人。只要以工作为名,把这些人叫出来就可以了。
永兰摇了摇头,说自己做不来。女长官换过温和的语气,说假如给她线人准证,能让她在新加坡正常打工,做不做线人?
男长官用英文窃窃问道:“有这样的准证吗?”
永兰接着问:“有吗?有假如的吗?”
男长官很惊讶:“你会讲英语?”
永兰说:“我不会,但你们就是这个意思。”
女长官只好承认,确实没有这样的准证,不得已让永兰出门去了。
她知道做线人的诱惑力,有人拿到十年的工作准证,不必再为身份发愁。有人拿了八千新币,附加一张回国的机票。但她也知道,自己的好朋友就是被线人举报才抓进去的,在监狱内感染了疫情,至今仍没有治好。
三
做完核酸检测,永兰需要先隔离十四天。她领到一个箱子,里面装有牙刷牙膏、一块香皂,两卷厕纸,这是一周的用量。狱警还给每人分发一张草席,两床被子。每日清晨5:30,她们起来整理床铺,轮流洗澡,穿戴整齐,等待长官巡房。到了晚上九点将被褥铺好,再等待检查。盒饭按点从门下的窗口递进来,大家席地而坐,吃完再递出去。后方用隔板挡住,形成一方卫生间。
监狱里,永兰认识了林姐,她们有共同的好友,共同的家乡。隔离间内,有新加坡阿姨,印尼女孩、印度女生,五人语言不通,都显得有些沮丧。
唯有林姐是快乐的。逾期逗留的十四年零六个月,林姐通过放贷款,攒下两百五十万人民币,她待够了,很轻快地到移民厅自首,随身行李多得让打包的长官发愁。林姐手一挥,大气地说,回国之后,要请全村人吃自助餐,再买几件好的大衣。
看印尼女孩长得美,林姐想让她当儿媳妇,拉永兰来作翻译。她用仅会的几个英文单词问女孩:“林姐有很多money,你要不要嫁给她的son?”不知道怎么表达金额,永兰写了个二,加上许多零,五人笑成一团。
林姐又问,印尼女孩怎么会到这里来,犯了什么事。女孩不语,林姐再去问别人,众人沉默。
永兰拦住林姐,说:“林姐,每个人到这里来都有他们的心结,不要再问了。”

约莫到了第十天,印尼女孩才开口,说自己做女佣,在雇主家遭到虐待,所以想去报复小孩,结果被摄像头拍到,于是被关进来。
隔离期满,永兰发现自己没有感染的症状。随即,她被换到监狱的四人间,她惊喜地看见,林姐和自己在同一个房间,她刚想庆祝两人的重逢,一位坐在旁边的老太太,做出缝住嘴巴的动作,又一个人开口了,用英语解释道:“少说话,不要问”。
永兰看出来了,那位老太太,应该就是监狱里的“大姐”。
大姐是一位娘惹毒枭,在狱中已经待了四十年,狱警很照顾六十八岁的大姐,常常会来她们房间问候,有事情一叫就到。大姐身旁是一位马来人,身形很胖,信奉回教,常窝在一角念词、做礼拜。
永兰私下和林姐商量,她们初来乍到,不如承担打扫的责任。由林姐拿饭,抹地,永兰打扫厕所。永兰还会顺便把大姐的拖鞋从门外拿进来,再替她拿出去。被林姐看见了,很生气地说,永兰太积极了,搞得自己也要这样做。
永兰耐着性子和林姐解释,算了,大姐年纪老,我们让着她。林姐没有擦干净的地板,永兰就拿出自己洗澡的肥皂,重新擦一遍。
让一点,再忍忍,永兰总抱持这样的态度。在新加坡的十三年,她看见太多破碎的生活,混乱的感情。永兰的同乡阿敏,因为没有钱,不敢离开酒后施暴的新加坡男友。陪读妈妈阿芬,在新加坡待了23年,在工作的菜场感染了新冠疫情,一天下午回到家,阿芬发现房东把她所有的衣服都丢在门口。她只好自首回国。永兰也有快要忍不下去的时候,尤其当她和孩子吵架,隔着手机,怒气就快突破那层束缚的,名为母亲和长女的道德薄膜,她说自己明天就要拎着东西回国, 永兰话音一落,电话两头的人都安静下来。
十三年过去,永兰坚持在新加坡工作,直至为家人买下一套商品房,供女儿出国留学,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日子似乎有了希望,就像她擦过的地面,变得更加明朗。她正打算再攒一些钱,却走到告别的时刻。
高中辍学的永兰,在监狱里读了四本书,她印象最深的是九把刀的爱情小说,情节起伏,里面的人物一会爱一会恨。每天,大家能出门活动一小时,那是她们唯一不用戴镣铐的时刻。监狱两层的铁门都被打开,永兰看见女人们身穿白色囚衣从铁门内走出来,一间间、一排排,又融成一团,淡绿色的墙壁上,影子重叠,又分开。公共电视上轮流播放马来和印度的影视剧,听起来很陌生。永兰还瞥见一个很像男生的囚犯,常常与另一女孩贴得很近,每当此时,狱警就大声斥责两人分开,身边传来奚落的笑声。永兰渐渐明白,随后和大家一起笑起来。
查房开灯,睡前关灯,时间就在一明一暗中流走。十四天满,狱警叫她们收拾东西,准备出去。没想到,娘惹大姐忽然起身,送给永兰一个拥抱。大姐指指地板,比出称赞的手势。
在狱中二十八日,永兰学会说几句英语,例如向长官问候早午晚安,读手腕上的四位编号,喊到时要大声说Yes。直到她在移民厅听见别人字正腔圆地喊“到”,很响亮,她才醒悟过来。她小声问林姐:“我们要讲中文吧?”反倒是林姐,摆出轻松的表情,让她直接讲yes。
林姐说:“现在学了不用,以后什么时候用?”永兰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户籍问题,永兰的护照始终办不下来,她在移民厅住了几天后,被暂时放出去,等待消息。林姐则在出狱两天后,踏上了回国的飞机。走之前,林姐问永兰回国的安排。
她想了想,说:“我两手空空的,推个三轮车,去卖肉骨茶算了。”
永兰又想到,自己还不会骑三轮车,变得更沮丧了。
林姐很诧异地问:“怎么从新加坡回来,还要推三轮车?当然是开小车。”
“你开小车吧,我骑三轮车就好。”永兰笑着回嘴。
“她们这种人”,没有身份的人,那么相似,又那么不一样。
从樟宜女子监狱出来之后,永兰觉得自己仿佛失忆了,变得很笨,很多东西都不会。阿芬女儿告诉她:“没关系,我妈妈也是这样。”阿芬的指标已经转阴,回国隔离,留在新加坡的女儿,则尽力帮助母亲身边的朋友。回国的手续变得更为繁琐,直至11月16日,永兰的护照才批下来,她留在杰哥家,进行十四天居家自我监测,两次核酸通过后,她便可以申请绿码,登机回国。
这也是永兰在新加坡最后的十四天。倒数的日子里,杰哥变得很焦虑,凌晨四点便醒来。他拒绝了来修车的客人,收入几乎停滞。胃口也在减缩,打包回家的面吃不下,只能用吞的。永兰听移民厅的长官说,新加坡的政策变了,她还有机会重回新加坡,只要有人担保,给移民局写信。她决心回国后办离婚手续,迁出孩子的户口,把房子转到自己名下,再申请到新加坡的签证。但她始终无法对杰哥做出承诺,像他曾经那样。她不知道自己多久才能再到新加坡,三年,五年?她能抓住的太少。
临走前,她对杰哥说:“我们来谈一场异地恋吧。”

2021年11月底,永兰返航,跨越海峡,落地厦门,她是第一个下飞机的人。入境的小黑屋内,海关问了她不少问题,她请求海关不要在笔录上写“非法”。
永兰说:“大家都用逾期逗留,好听一点。”
“好吧好吧”,海关人员答应了。
直至12月,永兰结束隔离,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她看见自己买的商品房,小区崭新,一幢幢高楼从绿化带中长出来,围住天空。厨房的窗格中露出远方的山影,接近黄昏,灯光从山顶的寺庙倾泻下来,她曾在庙里祈福、祭拜。
似乎不太适应福建的冬季,回来后她几番感冒,变得很爱睡觉。家里添了一只叫春春的狗,瞥见生人会迅速地跑来。母亲的饭菜较她在新加坡吃的厚重,她们坐在沙发上,于新年当晚拍了一张合照。永兰没有去卖肉骨茶,也没有急着去工作,她想休息了。
她还想到,该给十年前逝去的父亲上一炷香。不料母亲拒绝了,说要问问别人,合不合适。依镇上风俗,只有长男才能祭拜先祖。她愣了一下,两人的距离在光线中无限延长。
作者简介:段文昕是一名小说和非虚构写作者,就读于复旦大学学习创意写作。2022年她关于移民的小说获得了广州青年文学奖。
英文译者Wang Jiyuan是一名口译员,立志从事文学翻译。他在英国华威大学获得文学翻译研究硕士学位。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