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望百年|专访施郁:“爱因斯坦热”是中国人拥抱科学寻求真理的范例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访问上海,距今已是百年。关于这段历史,很多细节众说纷纭,甚至扑朔迷离。为让更多人知道更多真实的细节,澎湃科技专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和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施郁,以此纪念爱因斯坦和他所代表的科学精神。
·澎湃新闻记者和施郁教授一道走访了爱因斯坦在沪足迹,当年的亭台楼阁有的业已破败或湮灭,爱因斯坦对中国青年的期许却言犹在耳,“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

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施郁与上海汇山码头旧址的爱因斯坦塑像合影。澎湃新闻记者 陈竹沁 摄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乘坐日本邮轮“北野丸”,在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汇山码头登陆,准备在上海逗留两日后赴日讲学。下船后,他得知自己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奖。然而,受到当时“反相对论浪潮”的影响,诺奖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却是“光电效应定律”。
1916年,爱因斯坦基于广义相对论,提出引力波的预言。整整一百年后,科学家宣布首次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并获得201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该奖项宣布当天,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施郁发表了相关介绍文章《爱因斯坦的奇葩诺奖》,而这年11月12日,他又碰巧受邀在位于汇山码头旧址的建投书局进行引力波主题科普讲座。百年时空仿佛交汇于此,施郁指了指窗外,“当年爱因斯坦就站在那里,向我们这里走来。”
一天后的11月13日,施郁撰写的《1922年的今天,爱因斯坦在上海滩做了些什么?》在科学媒体“知识分子”发表,文章详细考证了爱因斯坦的两次上海之行(分别是去程的11月13至14日以及返程的12月31日至1月2日)。前前后后的系列文章还有《98年前的今天,谁一夜成名》和《爱因斯坦访华计划为何流产》,也都围绕着这段历史展开。
施郁对爱因斯坦访沪历史研究的兴趣,萌生于这年夏天——约瑟夫•艾辛格(Josef Eisinger)所著的《爱因斯坦在路上》中文版首发。他留意到,该书英文原版是2011年出版,当时《爱因斯坦文集》还没有出到13卷(爱因斯坦1922至1923年的文章和通信),而艾辛格依据的主要是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爱因斯坦1922至1933年的旅行日记的复本。
查阅手头的英文版文集,施郁发现,艾辛格书中的有些细节描写偏离了爱因斯坦日记的意思。而比对不同资料,关于“爱因斯坦在上海”的情况,也多有不准确或失误之处。例如上海学生在南京路街头托举起爱因斯坦庆贺其获得诺奖的故事,就谣传甚广,“这种虚构应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在真实的历史人物传记中,每件事情都应该标明出处。”施郁说。这也是他一贯的治学态度。
虽然对爱因斯坦访沪的典故和细节了如指掌,五年来施郁一直没能抽出功夫,系统重访爱因斯坦在上海的足迹。这个愿望在“百年纪念日”前夕终于达成。澎湃新闻记者陪同施郁一起探访了健在的几个地标——
上海汇山码头的现址,仍然有货客船迎来送往,爱因斯坦两次从这里下船。滨江沿岸露天的“老上海码头文化博物馆”,竖有爱因斯坦的铜像,提着旅行包的他,慈爱地看着长凳上不谙世事的幼童。作品命名为“相对”,背后的雕刻壁画,还有一段爱因斯坦访沪的简介。
爱因斯坦第二次访沪短暂下榻的礼查饭店,现名浦江饭店,内部已改建为中国证券博物馆。几年前墙壁上悬挂的爱因斯坦相片和介绍,已不见影踪,被其他展陈所取代。向工作人员打听据称是爱因斯坦入住的304房间,得到的是模棱两可的回答。4楼房间对外关闭,也无法让人一探究竟。
爱因斯坦从这里前往犹太富商加登的豪宅用晚餐,并参加除夕晚会。早在30年代末,这处花园住宅(东湖路9号),已改建为戏院,如今则成了办公大厦。只有一旁青年报社所在的小洋楼,还能从中一窥上世纪20年代的西洋建筑风情。
福州路上的工部局礼堂,是“重头戏”所在。1923年元旦下午,爱因斯坦在这里参加了相对论讨论会。我们循着旧路牌号找错了地方,离开时才恍然大悟,沿路穿过的施工通道,就是正在改造中的工部局大楼外围,预计明年年底会完成保护性修缮与更新。而根据规划,一座新建筑将取代原礼堂的功能,用于活动和表演。
梓园的变化令人唏嘘。这处位于乔家路113号的旧宅,曾在爱因斯坦抵沪的第一天招待晚宴。房子的主人王一亭是著名书画家和实业家(中国证券博物馆的展览恰好展示了他的一段事迹和照片),参与宴会的有于右任、张季鸾等社会名流。2019年起乔家路地块开始旧改,如今居民均已迁出。梓园大门上锁,曾经的一块“梓园遗址”铭牌也已移除。一位路过的老人向我们指点了北边的一个弄堂,居民平房的墙面上,赫然画着爱因斯坦和徐光启的卡通肖像,仿佛是民间记忆的另一种遗存。
“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个人作品。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所见。”这是一百年前,爱因斯坦在梓园晚宴中所作的答谢辞。
“如果穿越回1922年,你想在哪段旅途中陪同爱因斯坦?如果可以问他一个问题的话,你会选择问什么?”施郁没有细想,便抛出一个学术问题,“考虑1955年后物理学的进展,你是否还认为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对统一场论又有何新见解?”
不过,和1922年的爱因斯坦对话,还是轻松一些吧。施郁最后“决定”,去梓园赴晚宴前,带爱因斯坦去附近的徐光启故居(“九间楼”,乔家路 234~244 号),“谈谈徐光启和利玛窦对《几何原本》的翻译,以及中国古代的文明,问他:‘如何看近代科学在西方、而非中国出现?’”

梓园北部的面筋弄里,社区绘制的徐光启与爱因斯坦头像。澎湃新闻记者 陈竹沁 摄
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更突出革命性和哲学意义
澎湃科技: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学说是怎么进入中国的,有哪些社会背景?
施郁:爱因斯坦是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1917年,留日学生许崇清和留日归国的李芳柏初步介绍了相对论,但是影响有限。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呼唤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和民主,各种报刊书籍和社团如雨后春笋成长起来,给相对论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这时国际上恰好又发生了一件重大科学事件。11月7日,英国皇家学会宣布,天文学家在日全食期间,观测到了恒星发来的光在太阳附近弯曲,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泰晤士报报道:科学革命,牛顿思想被推翻。这使得爱因斯坦“出圈”,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的名人,堪称科学新闻传播的一个极端案例。
当时一次大战结束不久,人们充分感受到了世界的振荡。爱因斯坦带来的科学革命强化了人们的不安心理。动荡的社会气氛、人们对于宇宙的敬畏和好奇、爱因斯坦理论的抽象和神秘却又得到证实,以及媒体、收音机和照相机的兴起,乃至爱因斯坦本人某种程度上的配合,都是爱因斯坦声名鹊起的因素。从此,在世界上,爱因斯坦所到之处,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激动的人群狂热欢迎。
3个月后,这个“传播热”也到达中国,逐步升温。这是相对论也在中国引起强烈兴趣的一个国际背景,而且我觉得,当时中国也具有动荡这一社会心理因素。而且出于对赛先生和德先生的追求、对救国救民道路的寻求,当时中国人对世界上的各种理论感兴趣。
澎湃科技:民国报刊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介绍,似乎在人文知识界影响更广,原因是什么?
施郁: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英国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访问中国,主要在北大讲学。罗素演讲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相对论,特别是其哲学意义。此前,1920年5到6月,他访问苏联,会见了列宁,然后回到英国。离开中国后,他顺访了日本两周,在日本期间, 将列宁和爱因斯坦并列为思想革命的伟人。因此,罗素演讲急剧升高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热”。所以,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中,革命性因素和哲学意义较突出,所以在人文知识界影响很广。
当时在中国,物理学教学和科研还处于初创阶段。相对论被当作一个革命性思想,受众面很广。推介相对论的学者有科学工作者夏元瑮、周昌寿、魏嗣銮、郑贞文、高鲁、王崇植、任鸿隽、文元模、张贻惠等,也有其他学者,如张崧年(申府)、王光祈、杨杏佛、徐志摩、陶孟和等等。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也关注相对论。1920年初,张崧年以“科学中的革命”撰文介绍了相对论。当年8月,周恩来将相对论这一科学革命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作类比。哲学学者张君劢是“科玄论战”的玄学方,主张科学并非万能,却也多次引用相对论,并将之介绍给徐志摩。
1921年4月,《改造》杂志出版“相对论号”,其中有夏元瑮翻译的爱因斯坦的通俗著作《相对论浅释》,徐志摩的文章,王崇植的两篇译作。1922年2月,《少年中国》杂志也出版“相对论号”,包含三篇文章,其中魏嗣銮写了两篇。
澎湃科技:“科玄论战”的持续发酵,也与西方世界“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辩”相呼应。你怎么看当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施郁:爱因斯坦的理论是物理学基本理论。因为涉及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基本概念,所以也引起广大知识界的兴趣。哲学家柏格森挑战相对论,还引起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注意。1922年4月,法国哲学会在巴黎召集了一个关于相对论的讨论会,会上柏格森先表达对爱因斯坦工作的仰慕,说“这不仅是新物理,某个方面,也是新的思考方式。”但是他和爱因斯坦发生了争论。 这一年柏格森还写过一本关于相对论小册子。他离世后,别人编的一部柏格森文集没有收进这本书。一般认为柏格森错了,虽然他自己不承认。
不过爱因斯坦对柏格森一直是尊重的。相对论中的时间是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而柏格森涉及到时间的其他方面,比如宏观不可逆性和时间箭头,他的定性思想也许是有启发性的。科学越来越复杂,哲学工作者越来越难跟进。柏格森与爱因斯坦之争算是一个典型例子。现代科学启发了很多哲学上的发展,虽然很多哲学工作者并未真正理解掌握所论述的科学概念。
澎湃科技:1922年至今,爱因斯坦的中国传播经历了哪些阶段?探究和还原百年前爱因斯坦访沪的历史,对今天的我们为何仍然重要?
施郁:虽然爱因斯坦因故取消了正式访华,但是他在11月中旬和年底两次乘邮轮途经上海,分别活动了两三天。为了迎接爱因斯坦而准备的演讲和报刊文章,仍然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热”推向高潮。
比如,1922年11月到12月13日,北京大学举办了7次相对论演讲。1922年12月25日,《东方杂志》出版“爱因斯坦号”,发表了10篇文章以及爱因斯坦小传和著作目录以及爱因斯坦夫妇的合影,其中有李润章编译的郎之万的演讲,郑贞文编译的石原纯的演讲,周昌寿的文章,郑贞文的科学短剧。《申报》在岁末和年初的星期增刊中分别刊登相对论方面的演讲记录。《科学》和《大陆报》介绍再次检验光线弯曲的天文观测。《申报》1923年元旦刊登相对论书籍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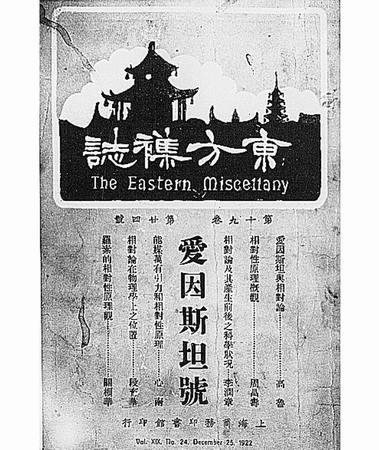
《东方杂志》“爱因斯坦号”。
胡大年的《爱因斯坦在中国》记载了1950到1970年代的情况。1950年代早期,苏联对相对论的哲学批判影响了中国。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周培源在人民日报和物理学报各发表一篇纪念文章。此后直到1960年代前半期,人民日报对爱因斯坦作正面宣传,包括胡宁和周培源的科普文章。1960年代末,北京有过短暂的“批评相对论学习班”,但很快就结束了,大多数成员由批判转为学习研究相对论,有的成员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比北京稍迟成立的“上海理科批判组”继续维持了几年。复旦大学有的教师抵制这个批判,但也有教师成为骨干,还欲以“复旦大学编译组”名义出版许良英和李宝恒的译作,遭到原译者抵制。这个译作后来扩充出版为商务印书馆3卷本的绿封面《爱因斯坦文集》。 1979年,中国召开了盛大的庆祝爱因斯坦诞辰百年的大会。
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中国“传播热”是中国人拥抱科学、寻求真理的典型事例,因此探究和还原百年前的这段历史也是有意义和有趣的。
“强调人类的共同财富,首先是科学”
澎湃科技: 中国遗憾错过爱因斯坦正式访问已成为一段公案,如何评价蔡元培先生的初衷和作为?如果这次访问得以促成,你觉得它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施郁:忧国忧民的蔡元培先生表现出拳拳之心。爱因斯坦在日本时,他还在为欢迎爱因斯坦来访而征集签名。(“我们合各种学术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团体电复,发出稍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踪无定,寄到稍迟;我们那里会想到他正在日本候我们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我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怎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什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磅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安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诚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吧!——蔡元培《跋爱因斯坦来信》,《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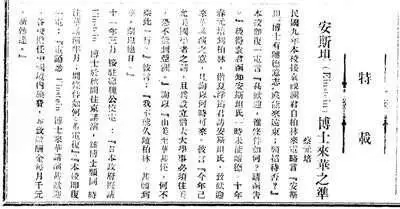
1922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蔡元培《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
爱因斯坦爽约了。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他突然要去巴勒斯坦,加上与北大缺少沟通。爱因斯坦第一次逗留上海时,有一位德国人斐司德和他的美国朋友罗勃生和他接触,他们也曾经试图邀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误以为他们与蔡元培有关。但事实上蔡元培与爱因斯坦没有做任何接触。
如果蔡先生与爱因斯坦保持联系,情况也许会不一样。最近我留意到,爱因斯坦访日的邀请者与一年前罗素离开中国后访日的邀请者一样,都是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蔡先生如果与日方邀请人做好协调,效果也许也会好些。
如果这次访问得以完成,会对相对论和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澎湃科技:对比中日双方的邀约过程,两国科学知识界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施郁:中国的邀请最早是在1920年,由在德国访问的前教育部次长袁观澜代表北大校长蔡元培发出,爱因斯坦没有接受。但是1921年3月蔡元培访德期间,由北大物理教授夏元瑮陪同拜访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表示,目前即将去美国,但乐意将来访问中国。当时在柏林的北大教师朱家骅继续与爱因斯坦商讨,希望爱因斯坦去北大访问一年。
统观中日的邀请,可见,同行朋友引荐的邀请,似乎更容易打动爱因斯坦。夏元瑮先在美国求学,1908年又到柏林大学学习,听过普朗克和鲁本斯的好几门课。1919年,他又回到柏林大学访学两年,与爱因斯坦有不少交流。他还曾介绍梁启超与爱因斯坦夫妇共进晚餐。爱因斯坦1919年信中提到过“和几位高雅的中国人在一起”,估计是指夏和梁。
前面提到的1921年罗素对日本的访问是由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邀请的。他问罗素世界上哪三位人物最重要,以便邀请。罗素说了列宁和爱因斯坦两个名字,正如他在演讲中将他们列为思想伟人。山本通过理论物理学家石原纯与爱因斯坦初步接洽。
石原纯在日本获博士学位,但曾在欧洲访学,求教于索莫非、普朗克和爱因斯坦,成为日本最重要的相对论专家。如前所述,他的科普文章也被翻译为中文。他是爱因斯坦访日期间的翻译和陪同。离开日本前,爱因斯坦给他写了感谢信。
澎湃科技:爱因斯坦统筹安排访日和访华时,主要考虑了哪些因素?
施郁:1922年1月,山本给爱因斯坦明确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3月,爱因斯坦通过中国领事馆告诉中方,可以顺访中国半个月,询问条件。这时朱家骅还坚持爱因斯坦先去中国一年,再去日本。爱因斯坦回信说,先前中方预备提供的资助不够,现在日本提供了合适的资助,所以顺访中国两周,他本人考虑到中国的冬天比日本温暖,所以希望先访问日本。而且日本先给出了合适条件,所以有优先权,即使中国的邀请在先。蔡元培回复,提供食宿和每月1000中国元的报酬。爱因斯坦再次表示只能顺访两周,报酬1000美元,承担东京至北京,再去香港的旅费以及旅馆费。因为北京大学财政困难,在梁启超承诺支持后,蔡元培接受条件。爱因斯坦表示将于新年前后到达北京。
看上去,这个达成协议的过程不很顺利,爱因斯坦当时是在乎报酬的,但是意见公平中肯。当时,日本已经比较发达,财力雄厚,而中国还很贫困,大学也处于财政困难。蔡元培和朱家骅本来希望爱因斯坦来一年,最好在日本之前,但是不容易提供爱因斯坦满意的资助。最后能达成协议,中方已很不容易。
爱因斯坦期望的报酬确实是天价。我查了一下,按同等时间算,蔡元培最初打算给爱因斯坦的报酬已经是罗素的近双倍(而罗素的报酬已经算很高了),但只是爱因斯坦所要求的1/4,是日本报酬的1/16。但是爱因斯坦在日本的公众演讲,日本东道主是卖票的。爱因斯坦也在东京大学做了专业讲课。

1922年在东京帝国饭店逗留期间,爱因斯坦给当地邮递员手写的一张便条,在2017年拍出了156万美元天价。纸上写着,“安静而有节制的生活能比始终在不安困扰下追求成功带来更多的喜悦”。
澎湃科技:爱因斯坦对访日的邀请方观感如何?
施郁:日本人的接待工作从上海就开始了,向导稻桓守克夫妇到上海来接,又全程陪同爱因斯坦夫妇在日本的旅程和活动。日本方面对爱因斯坦安排照顾得很仔细周到,爱因斯坦非常满意,也很喜欢东道主山本实彦。12月30日,爱因斯坦登上离开日本的船后,给山本夫妇每人专门写了封赞美信,说山本先生出自自身的动力,将精力贡献给改善社会,还说他致力于建立一个阻止战争的国际组织,又说“为此,首先需要各国人们的相互理解,强调人类的共同财富,首先是科学。我是这样理解你对我的邀请。”
山本实彦是日本的名人,是鲁迅的朋友,曾经引进中国作家的作品,还最早出版过鲁迅全集。正如爱因斯坦的印象,山本有政治追求,而且当时算左派。不过山本后来右转,有机会主义的意思。他战后在日本的政治影响大起来。
“孤持”是科学创造的必要因素
澎湃科技:在爱因斯坦访沪活动中,学者张君谋出现了两次。在1923年1月1日下午工部局礼堂的相对论讨论会上,他为何会问爱因斯坦对洛奇心灵学的看法,这股思潮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和影响?当时许多科学家曾对心灵学感兴趣,爱因斯坦的态度是什么?
施郁:1840年代到1920年代,西方流行过心灵学。洛奇是一位有爵位的英国物理学家,成就主要在电磁波和电磁学方面,也做过伯明翰大学的校长。他年轻时就开始相信心灵学。他儿子在一战中战死后,他写了一本书,关于他和他死去儿子的交流。洛奇相信以太是存在的,所以认为死后灵魂在以太中。似乎英国对心灵学感兴趣的科学家相对较多,一方面与这些科学家的个人经历有关,也因为他们不能坚持科学方法,而且还因为不少现象当时还不能从科学上解释。他们被其他科学家批评。爱因斯坦从来不对这些感兴趣。

爱因斯坦在梓园合影,张君谋也在宾客之列。
君谋是张乃燕的字。他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侄子,1913年赴欧洲留学,在伯明翰大学、帝国理工和日内瓦大学学化学,1919年在日内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先在北大等很多学校当过教授,1923到1926年又在上海、浙江、广州、上海频繁换过很多职位。不清楚他参加爱因斯坦晚宴以及出席相对论讨论会时,是何职位。1927年,张君谋任由东南大学合并其他学校而成的第四中山大学(旋即相继改名为江苏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3年后辞职。他的名字刻在中央大学大礼堂的奠基石上。我查了一下,张在伯明翰大学学习时,校长就是洛奇(1900年至1920年任职),想必这是张关注洛奇的一个原因。
爱因斯坦当场说洛奇心灵学不足道,后来张也遭到新闻报道的批评。在这次讨论会上,除了张的问题,我觉得前面提到的问题都还不错。比如有人问,迈克耳孙-莫雷实验是否足够精确,可据以假定真空光速为一恒量;主办方探索社主席、土木工程师查特莱(Herbert Chatley)问,最近澳洲日食期间的观测结果;工部局电气处的安东尼问,能否用木卫掩星现象证明相对论。对于各种问题,爱因斯坦都能立刻抓住要点,微笑着走向黑板说明或用口头阐释,回答简要而直截了当。
至于他为什么在日记中把这次讨论会称作“愚蠢问题的滑稽戏”,也许是因为有些问题没有被报纸报道吧,另外,爱因斯坦是性情中人,日记行文幽默讽刺意味较浓。从我阅读到的材料,我的印象是他对待媒体或访问者很友好。
澎湃科技:如何综合看待爱因斯坦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人的印象?周培源先生1936年赴美,和爱因斯坦曾共事一年,据说爱因斯坦还曾向他特地回忆了1922年在上海的见闻。
施郁: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爱因斯坦1922-1923年的旅行日记,引起一些评论,认为爱因斯坦歧视中国人。其实,这些旅行日记早先已经包含在《爱因斯坦文集》第13卷。我在我的3篇文章中,已经翻译了其中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字。现在很多关于爱因斯坦的上海逗留和他的日记的文字,来自我的文章。我不觉得有歧视。爱因斯坦是性情中人,日记行文直率,笔调幽默讽刺,除了直陈对中国人的印象,也不乏对欧洲人和日本人的讽刺。
爱因斯坦尊重中国的文明,而对当时被西方压迫的中国人的印象可概括为:同情、好感、好奇。之前提到过,爱因斯坦1919年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朋友贝索将回到专利局。可怜的家伙与动物差距太远——只有概念、没有欲望,佛的理想的化身。他会更适合在东方。这让我想起前天夜里和几位高雅的中国人在一起;他们丝毫没有我们的目的和实用主义。对于他们和长城来说,这太不好了!” 1921年,他给一位在中国教书的前同事的信中说:“我想象在中国人当中生活其实挺好、很吸引人。我遇到的几个例子就特别有吸引力。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身材匀称的人实际上似乎比我们优越得多。”
爱因斯坦对当时中国人的悲惨状况铭记在心,所以1936年,向在他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一年的周培源谈起时,还深有感触。1938年,周培源也曾于西南联大写信给爱因斯坦,介绍抗日情况。爱因斯坦曾与罗素和杜威联名要求释放陈独秀,还曾联名杜威等人要求释放七君子。

梓园现貌。澎湃新闻记者 陈竹沁 摄
澎湃科技:1949年后,年轻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先生也与爱因斯坦有过短暂的直接交流互动,这些私人交往是否影响他对中国的看法呢?
施郁:爱因斯坦访沪时,杨振宁刚在合肥出生44天,4年后的11月李政道出生在上海。1949年杨振宁成为爱因斯坦的同事,在这个研究所一直工作到1966年,1951年李政道也来到这里。除了派斯,研究所的年轻人与爱因斯坦的接触都很少。但是195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的两篇论文引起爱因斯坦的兴趣,与他们做了讨论。杨先生也曾经拍了大儿子与爱因斯坦的合影。
1966年,美国发布爱因斯坦纪念邮票时,杨先生在发行仪式上做了演讲。1979年,纪念爱因斯坦诞辰百年时,杨先生在世界上4个大会上做了演讲。2005年,李先生在北京的爱因斯坦纪念会上做演讲《在祖国纪念爱因斯坦》,杨先生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科学史大会上做演讲《爱因斯坦:机遇和眼光》。
最近我专门向杨先生求证,爱因斯坦有没有向他提起过当年的旅行中对中国人的印象,杨先生回答:从来没有(never)。
澎湃科技:你曾用“孤持”(apartness)一词形容爱因斯坦个性的重要成分,并将其归结为他喜欢频繁的国际航行的原因。你认为,哪些因素造就了他的这种个性?你从中得到哪些感悟?
施郁:apartness最初是爱因斯坦专家派斯对爱因斯坦的描写,后来杨振宁先生曾经引用并翻译成“孤持”。杨先生提到,派斯还引用了牛津辞典对孤持的解释:与其他人保持距离;单独地、孤立地、独自地。杨先生写道:“的确,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的一个必要因素。”
我觉得,这首先是爱因斯坦的性格,因为他小时候就这样。后来这又成为他的风格,他的科学研究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在对待其他事物上他也是如此。这时,为了独立性,他需要保持孤持。独立思考是我从这位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身上得到的首要启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