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经典重读 | 陀思妥耶夫斯基口中的“俄罗斯语言的巨匠”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俄罗斯文学三巨头”之一,主要作品有《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屠格涅夫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他的语言简洁、质朴、精确、优美,为俄罗斯语言的规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列宁誉为“俄国的语言大师”。
屠格涅夫是俄罗斯语言的巨匠,是第一个拥有全欧乃至全世界影响的俄国小说家。他以自己的创作和丰富的艺术经验,扩大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为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称,未来的文学史专家谈及俄罗斯语言发展时,一定会说,这种语言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创造的。
孤狼
屠格涅夫
傍晚,我一个人坐着赛跑用的马车回家。离家还有七八俄里。我那匹跑得很快的好马精神抖擞地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跑着,只是偶尔打两声响鼻,摇晃几下耳朵。我那只跑累了的狗一步也不离开后轮,好像拴在上面似的。暴风雨要来了。前面有老大的一片淡紫色阴云,慢慢地从树林后面升起来。在我头顶疾驰和迎面而来的是一条条长长的灰云。爆竹柳惊慌不安地晃动起来,簌簌地响着。闷热一下子变成湿冷,阴影很快地浓起来。我用缰绳抽了一下马,马车就下了河谷,过了一条长满柳树棵子的干河,上了坡,就进了树林。
我面前有一条路,弯弯曲曲地在已经笼罩着暮色的茂密的榛树棵子中穿过。我的马车艰难地向前行进着。百年老橡树和老椴树的一条条树根横穿过老深的旧车辙,我的马车在坚硬的树根上蹦跳着,我的马打起趔趄。狂风突然在上空怒吼起来,树木呼啸起来,大颗大颗的雨点猛烈地敲打着树叶,电光一闪,雷雨大作。雨像泉涌般倾注下来。我的车子慢慢走起来,走不多久,不得不停下来:我的马陷在泥水里了,而且这时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好不容易钻到一丛老大的树棵子底下躲雨。我弯下身子,蒙住脸,耐心地等待雷雨的终止,却忽然在闪光中恍惚看到一个高高的人影。我就凝神朝那个方向注视起来——那个人好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一下子出现在我的马车旁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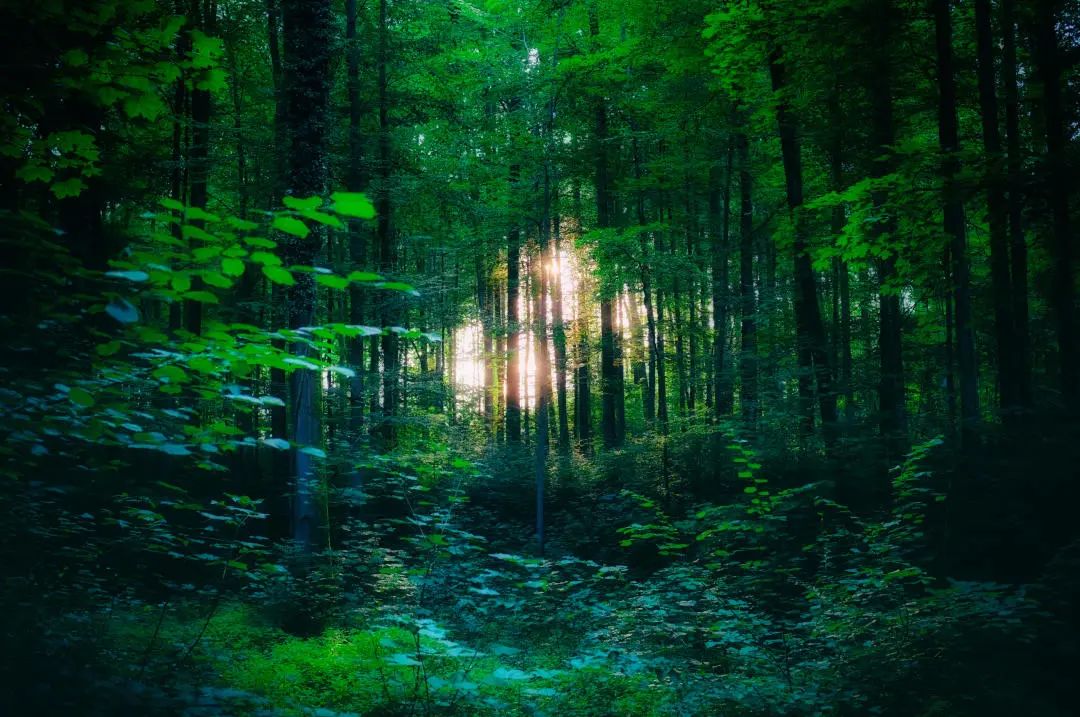
“什么人?”一个洪亮的声音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在这儿看林子的。”
我自报了姓名。
“啊,我知道!您这是回家去吗?”
“是回家,可是你瞧,多么大的风雨……”
“是啊,暴风雨。”那声音回答说。
一道白亮的电光把守林人从头到脚照得清清楚楚,紧接着霹雳一声,响了一个炸雷。雨更猛烈地泼下来。
“不会很快就停的。”守林人又说。
“怎么办呀!”
“我是不是可以把您领到我的小屋里去?”他断断续续地说。
“那就麻烦你了。”
“请您坐好吧。”
他走到马头前,抓住笼头,把马拉动了。我们的马车就走起来。马车像“大海里的独木舟”一般颠簸着。我紧紧抓着马车的坐垫,一面呼唤着狗。我那可怜的母马吃力地在泥水中吧唧吧唧走着,又打滑,又打趔趄。守林人在辕杆前面左右摇晃着,像一个幽灵。我们走了很久,我的领路人终于站了下来。“咱们到家了,先生。”他用平静的语调说。篱笆门咯吱一声开了,几条小狗一齐叫起来。我抬起头来,借着电光,看见围了篱笆的宽大的院子中央有一座小屋,从一个小小的窗子里透出幽暗的灯光。守林人把马拉到台阶旁,便敲起门来。“就来,就来!”说话的是一个尖细的声音,接着是光脚板的走动声,门闩吧嗒一声开了,于是一个穿着小褂、腰系布条的十二岁光景的小姑娘带着提灯出现在门口。
“给这位先生照着路,”他对她说,“我把马车赶到敞棚里。”
小姑娘朝我看了看,就往屋里走去。我跟在她后面。
守林人的屋子只有一间,熏得黑乎乎的,又矮,又空空荡荡,没有高板床,也没有间壁。墙上挂着一件破皮袄,长板凳上放着一支单筒猎枪,屋角堆着一堆破布,炉边摆着两个大瓦罐。桌上点着松明(供点燃照明的松木条或松树枝),一会儿可怜巴巴地亮一下,一会儿暗下去。在屋子正中央,一根长竿的一端吊着一个摇篮。小姑娘把提灯捻灭了,坐到一个小凳子上,就用右手摇起摇篮,用左手摆弄松明。我朝四下里看了看——心里非常难受:夜晚走进农家的屋子是不会愉快的。摇篮里的婴儿又沉重又急促地呼吸着。

“你就一个人在这儿吗?”我问小姑娘。
“一个人。”她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回答。
“你是守林人的女儿吗?”
“是守林人的女儿。”她小声说。
门吱扭一声响了,守林人弯下头,跨进门来。他拿起地上的提灯,走到桌子跟前,把提灯又点着了。
“点松明恐怕您不习惯吧?”他说着,摇晃了几下他的鬈发。我望了望他。我很少见到这样的好汉。他高个子,宽肩膀,身材好极了。那强壮的肌肉在湿透的麻布衬衫底下凸得高高的;那黑黑的卷曲的大胡子把他那刚毅而严肃的脸遮住一半;在紧挨着的两道阔眉毛底下,一双不大的栗色眼睛流露着刚勇之气。他一双手轻轻地叉着腰,在我面前站着。
我向他道过谢,就问起他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福玛,”他回答说,“外号就叫‘孤狼’(在奥廖尔省,常常把孤单而阴沉的人称为“孤狼”)。”
“哦,你就是孤狼?”
我更好奇地朝他望了望。我常常听到我的叶尔莫莱和别的一些人谈守林人孤狼的一些事,附近的庄稼人都像怕火一样怕他。据他们说,能够像他这样恪尽职守的人,天下还没有,“他连一捆树枝都不让人拿走。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在半夜,他也会一下子来到,你休想反抗,因为他力气又大,又像魔鬼一样灵活……而且你对他毫无办法:请他喝酒,给他钱,都没有用;不管用什么收买他,都不行。有些人不止一次想把他弄死,不行,办不到。”
附近的庄稼人就是这样议论孤狼的。
“原来你就是孤狼,”我又说一遍,“伙计,我听人家说起过你。都说你是什么人也不肯放过的。”
“我要尽我的职,”他阴沉地回答说,“不能白吃主人家的饭。”
他从腰里抽出板斧,蹲在地上,劈起松明。
“怎么,你没有老婆吗?”我问他。
“没有。”他回答说,并且使劲儿劈了一斧头。
“就是说,是死了吗?”
“不……是的……死了。”他说过,便转过脸去。
我没有再说什么。他抬起眼睛,朝我望了望。
“跟一个过路的城里人跑了。”他带着苦笑说。小姑娘垂下了头。婴儿醒了,哭起来,小姑娘走到摇篮边。“喂,给他这个。”孤狼说着,把一个肮脏的奶瓶塞到小姑娘手里。“就把他丢下了。”
他指着婴儿又小声说。他走到门口,站下来,并转过身来。
“先生,您恐怕,”他说,“不会吃我们的面包吧,可是我这儿除了面包……”
“我不饿。”
“哦,那就算了。我倒是可以给您生个茶炊,可是我没有茶叶……我去看看您的马怎么样。”
他走出去,把门掩上。我又朝四面打量了一下。我觉得这屋子比先前更加凄凉了。已经冷了的烟气有一种苦味,非常难闻,使我连气都不敢喘。小姑娘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连眼睛也不抬;她只是偶尔地推推摇篮,怯生生地把老往下溜的小褂往肩上拉一拉;她那一双光着的脚一动不动地耷拉着。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乌丽妲。”她把她那悲伤的小脸又往下垂了垂,说。
守林人走进来,坐到板凳上。
“风雨小些了,”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他说,“您要是想走,我把您送出树林。”
我站起身来。孤狼拿起枪,检查了一下火药池。
“拿枪干什么?”我问。
“树林里有人捣鬼……在砍母马沟的树。”他说后面一句,是为回答我疑问的目光。
“在这儿能听得见吗?”
“在院子里能听得见。”
我们一同走出来。雨已经停了。远处还聚集着一团团浓浓的乌云,偶尔还划过长长的闪电,但是我们头顶上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暗蓝色的天空,星星透过疾驰的稀薄的行云闪着亮光。黑暗中显露出一棵棵沾满雨水、被风吹得摇来摆去的树木的轮廓。我们倾听起来。守林人摘下帽子,低下头。“就是……就是的,”他忽然说,并且伸出一只手,“瞧,就挑选这样的夜晚。”除了树叶的响声,我什么也没听见。孤狼从敞棚底下把马牵出来。“要是这样去,”他又小声说,“恐怕会让他跑掉的。”
“我和你一起走着去……行吗?”

“好吧,”他说着,又把马牵回去,“咱们一下子把他抓住,然后我再送您。咱们走吧。”
我们就走。孤狼在前面,我跟在他后面。天知道他是怎样认得路的,但他只是偶尔停一停,为的是听一听斧头的声音。
“喏,”他小声说,“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在哪儿呀?”
孤狼耸耸肩膀。我们进了沟,风停息了一小会儿,一下一下的斧声清清楚楚地进入我的耳朵。孤狼朝我看了看,点了点头。我们蹚着水漉漉的野草和荨麻继续朝前走去,听到了一阵低沉的、长长的轰隆声……
“砍倒了……”孤狼嘟哝道。
这时天空越来越晴朗,树林里有点儿亮了。我们终于从沟里爬出来。“请您在这儿等一下。”守林人小声对我说。他弯下身子,举起枪,消失在灌木丛中。我聚精会神地倾听起来。在不肯停息的风声中我隐约听到远处有轻微的声音:斧头小心地砍树枝的声音,车轮轧轧声,马打响鼻的声音……“哪儿去?站住!”突然响起孤狼那钢铁般的声音。另一个声音像兔子似的可怜巴巴地叫起来……厮打起来。“胡说……胡说……”孤狼喘着粗气说,“你跑不掉……”我朝打闹的方向奔去,一步一趔趄地跑到厮打的地方。守林人在砍倒的树旁的地上蠕动着。他把那个贼按在地上,在用腰带反绑他的两手。我走到跟前。孤狼站起来,也把那人拉起来。我看到那个庄稼人浑身湿漉漉的,穿得破破烂烂,老长的大胡子乱蓬蓬的。
一辆货车旁边站着一匹很瘦弱的马,马身上有一半披着疙疙瘩瘩的草席。守林人一句话也不说。那人也不作声,只是摇晃着脑袋。
“把他放了吧,”我对着孤狼的耳朵小声说,“这棵树我来赔。”
孤狼一声不响地用左手抓住马鬃,他的右手一直抓着那个贼的腰带。“哼,你这笨东西,看你有多狡猾!”他厉声说。
“您把斧子拿着。”那庄稼人嘟哝说。
“斧子怎么会丢掉呢?”守林人说着,捡起斧头。我们就走了。我走在最后面……又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很快就转为瓢泼大雨。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那座小屋。孤狼把抓来的那匹马放在院里,把那个庄稼人带进屋里,把腰带的结松了松,就叫他坐到角落里。那小姑娘本来已经在炉边睡着了,这时一下子跳起来,带着惊恐的神气一声不响地打量起我们。我在板凳上坐下来。
“啊,这雨好大呀,”守林人说,“只好再等一会儿了。您要不要躺一下?”
“谢谢。”
“您在这儿,我本该把他关进贮藏室里,”他又指着那人说,“可是那门闩……”
“就让他在这儿吧,不要难为他。”我打断孤狼的话说。
那人皱着眉头看着我。我在心里发誓,要想方设法把这个可怜的人放了。他坐在板凳上一动也不动。在灯光下,我能看清楚他那憔悴的皱皱巴巴的脸、耷拉着的黄眉毛、惶惶不安的眼睛、干瘦的肢体……小姑娘躺在他脚下的地板上,又睡着了。孤狼坐在桌旁,两手托着头。蟋蟀在屋角叫着……
雨敲打着屋顶,顺着窗子哗哗往下流。我们都不说话。
“福玛·库兹米奇,”那人忽然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说,“福玛·库兹米奇呀!”
“你要怎样?”
“放了我吧。”
孤狼没有回答。
“放了我吧……因为实在饿得没办法呀……放了我吧。”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守林人阴沉地反驳说,“你们全村都是这样,除了贼,还是贼。”

“放了我吧,”那人一再要求说,“管家……我家完了……放了我吧!”
“完了呢!……不管怎样都不应该做贼。”
“放了我吧,福玛·库兹米奇……不要把我毁了。你也知道,你那东家会要我的命的。”
孤狼转过脸去。那人浑身抽搐起来,好像是热病发作了。他的头直晃荡,喘气也不均匀了。
“放了我吧,”他带着灰心绝望的神情一再地恳求说,“放了我吧,真的,放了我吧!我来赔钱,真的。实在是饿得没法子呀……孩子们饿得直哭呀,真是走投无路呀。”
“可是你总不应该做贼。”
“就把那匹马……”那人又说,“就把那匹马留下吧……我只有这匹牲口了……放了我吧!”
“我说过了,不行。我也是不能做主的人。东家要追问我。再说也不能由着你们。”
“放了我吧!穷得没办法呀,福玛·库兹米奇,实在是穷得没办法呀……放了我吧!”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
“放了我吧!”
“哼,跟你有什么好说的。你老老实实坐着,不然我可要……明白吗?怎么,你没看见这位先生在这儿吗?”
那可怜的人垂下了头……孤狼打了一个呵欠,把头放到桌子上。雨一直没有停。我等着看事情怎样了结。
那人突然挺直身子,一双眼睛冒出火来,一张脸也红了。“哼,来,你把我吃了吧,哼,噎死你,来吧,”他眯起眼睛,挂下嘴角,说了起来,“来吧,你这该死的凶手,你来喝基督徒的血吧,喝吧……”
守林人转过脸去。
“我对你说话呢,你这蛮子、吸血鬼,对你说话呢!”
“你醉了吗,怎么骂起人来啦?”守林人惊愕地说,“怎么,你疯了吗?”
“喝醉了呢!……那还不是你让我醉了的,你这该死的凶手,畜生,畜生,畜生!”
“哼……我来收拾你!……”
“我怕什么?反正一样是死。没有了马,我能上哪儿去?你杀我,我也是死;饿死,也是死——都是一样。全完蛋吧:老婆,孩子……什么都死光吧……可是你呀,你等着吧,总有一天会跟你算账的!”
孤狼站起身来。
“你打吧,打吧,”那人用发狂的声音说,“打吧,来,来,打吧……(小姑娘腾地跳起来,用眼睛盯住他。)打吧!打吧!”
“住嘴!”守林人大喝一声,向前跨了两步。
“算了,算了,福玛,”我喊起来,“饶了他……由他去吧。”
“我就是要说说,”那个倒霉的人继续说,“反正是一个死。你这凶手、畜生,怎么不死呀……不过等着吧,你威风不了多久啦!会有人把你绞死的,你等着吧!”
孤狼抓住他的肩膀……我冲过去解救他……
“您别动,先生!”守林人朝我吆喝。
我并不怕他吓唬,而且已经伸出了手,但是,使我万分惊讶的是,他一下子把那人胳膊上的腰带扯掉,抓住他的衣领,把帽子扣到他的眼睛上,拉开门,一把把他推了出去。
“带着你的马滚蛋吧!”他在他后面叫道,“可是你要小心,下次我可要……”
他回到屋里,在角落里摸索起来。
“哦,孤狼,”我终于说,“你真使我感到惊讶。我看出来,你真是一个极好的人。”
“唉,得了吧,先生,”他烦恼地打断我的话说,“只是请您不要说出去。我还是送您走吧,”他又说,“看来,您一时是等不到这点小雨停息的……”
院子里响起那人的马车的轧轧声。
“听,他走了!”他小声说,“下次我要好好收拾他!……”
半小时以后,他就在树林边上同我分手了。
(选自《猎人笔记》,花城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经典重读 | 陀思妥耶夫斯基口中的“俄罗斯语言的巨匠”》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