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叶攀︱排斥的代价:从普鲁士到魏玛德国的自由主义

德国是欧洲的重要国家,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关于纳粹的崛起,以及德国反犹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研究。比如有关学者的研究已经揭示,在纳粹崛起的过程中,正是魏玛德国的右翼民族主义(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以及两个自由主义政党(德国民主党DDP和德国人民党DVP)的选民转向使得纳粹占有了大量议会席位,为纳粹上台,或者说,以兴登堡为代表的普鲁士权贵铺平了道路。赋予希特勒无限权力的《授权法》上,也有魏玛议会中仅存的七名自由主义议员的签字。那么,这些自由主义者政党及其选民的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呢?埃里克·库尔兰德(Eric Kurlander)在《排斥的代价》一书中,通过讨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下西里西亚,以及阿尔萨斯(这是作者设置的“对照组”)三个地区的自由主义从十九世纪后期到魏玛德国终结这个时代的历史,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初步探讨。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地区,是因为在普鲁士德国期间,这三个地区都是自由主义力量强的地区,而到了魏玛德国,尤其上世纪三十年代,还处于德国领土范围的前两个地区都成了纳粹重镇。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首先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德国自由主义,尤其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普鲁士自由主义。大家都知道,1848年德国与其它欧洲国家一样都发生了革命,这次革命不幸失败,但是革命之后的普鲁士德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继续昂首阔步前进。这个时候的普鲁士自由主义者则日益放弃了他们早先的立场,逐步和普鲁士政权结合起来。双方首先在普鲁士德国的帝国主义措施,特别是海军事务上结合了起来,马修·菲茨帕特里克(Matthew Fitzpatrick)在其著作《德国的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 in Germany)中已经对这一点做了详细的探讨。同时,双方在一系列内部事务上也合作愉快,达成了“共同的底线”。至于德国自由主义在国内事务上的表现,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例如本杰明·拉普(Benjamin Lapp)在《来自右翼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一书中就对萨克森地区的状况进行了研究,指出当地中产阶级从反对社民党及其改良主义措施到支持纳粹的演变过程。那么,魏玛德国的其他地区又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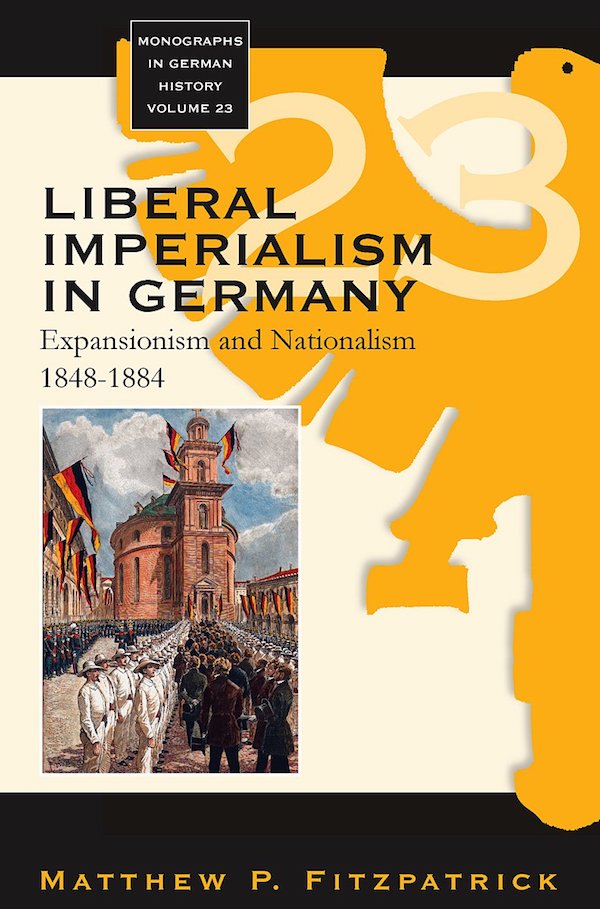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位于日德兰半岛,和丹麦接壤。在普鲁士和丹麦战争之后,从1867年起,这个地区正式成为普鲁士的一个省。从这时开始,当地流行的就是一种民粹主义式的民族主义(voelkisch nationalism),这种思潮强调的自然也是当地的德国种族,强调种族纯洁与尚武价值。换言之,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向种族主义迈出了一大步。这个地区的自由主义也就成了“民粹主义式的自由主义”(voelkisch liberalism)。有趣的是,当地的自由主义甚至认为普鲁士太“斯拉夫化”了,换言之,他们的民族主义比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更加“激进”,他们和第二帝国时期的“全国性”自由主义党派也颇为格格不入。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这个地区也就成了德国民族主义(毫无疑问,这种民族主义的重心就是对外侵略扩张)最强大的地区。
这种民粹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确也有一些冲突,但是这个地区的自由主义大佬试图对之加以调和。该地区进步党人士弗里德里希·霍夫曼(Friedrich Hoffman)就认为,为了促进“社会平等”,国家干预是必须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自由主义者认同了改良主义,相反,他们始终视社会民主党如寇仇。1903年德国大选期间,该地区的民族自由主义政党领袖直接认为,所有自由主义团体都应该成为普鲁士政权在所有重大民族政策和世界政策上的负责任的支柱。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是普鲁士通过战争从丹麦手里夺得的,因此生活着不少丹麦裔居民。后者也就成了上述自由主义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过,这些自由主义者还是出于种族理由承认了丹麦裔居民的自决权——这也是他们否认斯拉夫裔居民,尤其波兰裔居民的自决权的同一理由。
毫不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也吸收了反犹主义。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自由主义者也发现,他们和犹太裔居民或者犹太人议题的结盟,使得他们的选民背离了自己。于是,该地区的自由主义报纸对犹太裔激进左翼人士展开了凶狠的攻击,例如,《伊策霍尔新闻报》(Itzehoer Nachrichten)直接指控所有犹太人都是“红色和黄金”(Red and Gold)国际阴谋的盟友,该报甚至“鼓励”当地的犹太人和犹太裔政治家离开自由主义,进入社会民主党。熟悉历史的人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个指控在日后的回响。虽然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对东欧例如沙俄的反犹主义提出批评,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这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指责一样,是照别人而不照德国自己的手电筒。虽然个别进步党人也想倾向社民党,但是他们仍然抱怨社民党对“军国主义和海军主义”的无条件反对。
这个地区还是德国新教的传统重镇,不过,新教在种族主义问题上的表现并不良好。不用说,当地的自由主义选民对一部分自由主义政党吸纳德国工人的企图也反应冷淡。虽然进步党人在名义上的政策和社民党不无接近之处,但是,如果前者在民族问题和少数族裔问题上对后者做出让步,他们的选民就将离开他们。1903年该地区的自由主义政党在选举中惨败,他们的反应则是进一步转向右翼,转向民族主义。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通常熔社会改良和帝国主义于一炉。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中,无论是进步党,还是民族自由主义者,都和比洛(Buelow)集团达成了“共同底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自由主义也在民族主义、反对社民党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该州的选举中,几个自由主义者甚至对保守派候选人礼让三分。瑙曼(Friedrich Naumann)调和自由派和社民党的企图在其集团内应者寥寥。转向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也如愿以偿地在1907年选举中收复了部分失地。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这样,1908年,巴特(Barth)、布莱特希尔德(Breitschield)等人士就与该地区的自由主义者分道扬镳,洛塔尔·许京( Lothar Schueking)则写了一本书批判农业联盟、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这本书激怒了德国各地的自由主义者,不过没能改变普鲁士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瓦尔德斯坦(Waldstein)等持普遍主义立场的人士也被其政党要求降低调门。自由主义者继续攻击社民党。不奇怪,在一战前日益激化的欧洲列强矛盾中,普鲁士自由主义者也是火上浇油;战争爆发之后,普鲁士自由主义者,例如特劳布(Gottfried Traub)、赫克舍尔(Heckscher)等则企图吞并中东欧广大地区,并和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等携手同行。
一战以普鲁士德国的土崩瓦解而告终,不过,德国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同魏玛共和国。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的眼里,魏玛共和国是虚伪、浅薄,而且“非德国”的,他们追求的是一个能够培育并且捍卫德国民族特性(Volkstum)的国家。1918年之后,魏玛境内工人起义不断,右翼民粹主义青年组织和准军事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个地区的独立思潮也在战后初期甚嚣尘上,石荷地区也不例外。魏玛德国的两个自由主义政党德国民主党(DDP)和德国人民党(DVP)在这个地区也和一战前他们的先辈那样,继续诉诸民族主义。在这种气氛下,犹太裔人士日益从该地区自由主义政党高层中被排除掉。例如,德国民主党就是因为其犹太人身份而拒绝前述的瓦尔德斯坦成为该党在其选区乃至该省成为议员候选人。虽然个别自由派例如保罗·纳坦(Paul Nathan)对此颇为不满,但是该地区的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安之若素。当地的自由主义政党采取的是既尽可能排斥犹太裔人士,又指望别人对此不予理会的掩耳盗铃手法。德国民主党人、石荷地区这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之一,未来的纳粹经济事务负责人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公开批判“犹太民主党人”为世界主义的和平主义者。该党的多数也赞成沙赫特。
一战之后,石荷地区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社会基础之间的裂痕相比战前也有所缓和,该地区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对抗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的底线”也因此更加坚实。这种对抗既针对社会民主党在该地区的社会基础亦即农业工人,也针对社会民主党的外交和民族政策。这个地区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选择德国民主党,也是因为该党把下列主张结合了起来: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反对普鲁士的特殊论、强调族群特性的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魏玛共和国的中央政府里,德国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以及社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但正是这个联合政府,使得石荷地区的中产阶级和德国民主党离心离德。在反犹主义方面更加暧昧、反对社民党也更加坚决的德国人民党,也就取代了德国民主党,成了石荷地区最强大的自由主义政党。德国人民党在卡普-吕特维茨(Kapp-Luettwitz)政变、重建君主制、犹太人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也就口是心非、摇摆不定。如前所述,石荷地区本身是普鲁士通过战争攫取的,那么在一战之后这个地区尤其是石荷北部的归属就成了争议焦点之一。石荷地区的德国居民组织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协会,这个组织的几乎所有出挑成员也是该地区自由主义政党的领袖。不过,这个联合会鼓吹的并不是自由主义民主,而是通过自决权实现民粹主义的扩张。和前述的魏玛其它地区一样,石荷地区也涌现了大量右翼民粹主义的准军事组织。而且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这个地区自由主义者对待魏玛的态度和该地区激进右翼,如“青年日耳曼人”(Young German)对待魏玛的态度几乎毫无二致。他们只是因为魏玛能够暂时完成他们设定的各项任务暂时与之妥协。
1924年后,虽然魏玛德国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但是石荷地区的自由主义进一步朝着民族主义方向进行。这个地区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力量也随之不断加强。德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同的底线”最终成型了。每当魏玛自由主义者在选举中表现不佳,他们也以进一步转向右翼应对。到了1928至1929年,这个地区的德国人民党和德国民主党已经大大方方地提出右翼民粹主义主张了。毛伦布雷歇(Maurenbrecher)等自由主义者也最终成了纳粹。1933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民粹主义式民族主义,以及民粹式自由主义走到了终点,这个地区也就成了魏玛境内仅有的一个纳粹通过选举上台的地区。以沙赫特为代表的该地区不少自由主义者们也对之欢呼雀跃,并咸与维新。
下西里西亚地区与石荷地区殊途同归。这个地区和波兰接壤,也有不少波兰裔居民,因此,这个地区的民粹主义式民族主义不仅针对犹太人,也针对这个地区的波兰裔居民。如果说这个地区的自由主义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个地区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自由主义政党高层中有不少犹太人,这些人当然不会接受反犹主义。这个地区的自由主义者转向纳粹的程度和他们的石荷地区同侪相比也有所不同。当然,他们的“日耳曼”自由主义同道就不会如此了。当普鲁士保守主义以“犹太人”攻击自由主义时,这个地区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反对反犹主义本身,而是认为其观点知识等级不够,换言之,这里的“日耳曼”自由主义者和其石荷地区同道一样,并不支持民族平等。这些自由主义者在犹太人问题上往好里说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的反犹主义不仅针对东欧犹太人,也针对已归化的犹太人。早在一次大战中,尽管德国犹太人“踊跃参战”,但是这个时候犹太人已经成了德国右翼设定的替罪羊,德国自由主义者也加入了这股大合唱。尽管这个地区犹太裔自由主义者创立的《犹太人民报》(Juedische Volkszeitung)持归化派立场,并主张一次大战表明“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万众一心”,他们仍然被自己的自由主义同侪攻击为太智慧、太成功,而且太民主了。
如前所述,这个地区有不少波兰裔居民,虽然当地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石荷地区的丹麦裔居民和德国人种族地位相当,因而拥有自决权,但是他们同样认为,波兰人的种族地位比德国人低,因而不享有自决权。这个地区的自由主义者也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化身与象征,因而有义务反对斯拉夫蛮子。他们甚至反对天主教政党和社民党的存在本身,他们支持的是普鲁士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at),而不是自由主义民主。尽管这个地区的自由主义政党在这个时期对普鲁士右翼多有反对,但是这并没有使得他们支持社民党,他们始终视社民党为敌人。
不过,这个党的党首欧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1906年去世之后,再也没有强有力的人物阻止这个党朝着民族主义方向前进了。但即使是该党内对民族主义有所保留的领袖也得承认,这个时期普鲁士农村和小城市中产阶级中的帝国主义倾向相当强烈。1907年1月的选举中,这个地区的进步党人、民族自由主义者、保守派和反犹主义者正式达成了联盟。对付社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因为刊登了一个犹太商人呼吁该地区自由主义政党支持社民党的个人广告,该地区的《布雷斯劳晨报》(Breslauer Morgen-Zeitung)甚至公开致歉。和前述石荷地区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也结合了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并成了比洛集团的支柱。当然,这个地区反对上述联盟的声音更大一些。前述的巴特、布莱特希尔德,以及戈泰因(Gothein)等人士也在这个地区活动。不过,这个地区的保守派中产阶级也日益结合社会改良和帝国主义。虽然该地区的部分自由主义者探讨过他们和社民党结盟的可能性,但是1913年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扎本事件”(Zabern Affair)使得这个动议胎死腹中。这次事件中驻扎当地的德军少尉(second lieutenant)冯·福斯特纳(von Forstner)公开煽动扎本市居民使用暴力手段对付阿尔萨斯本地人士。社民党对此事猛烈批判,石荷地区的自由主义者站在军方一边,下西里西亚的自由主义者则首鼠两端。这些自由主义者也始终不愿意对普鲁士德国政府进行坚决批判。在一次大战初期,下西里西亚的自由主义者就对普鲁士德国的侵略行径轻描淡写,力图洗白。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是前述的戈泰因也站在了第二帝国当局的立场上,在他设定的一战后秩序里,比利时失去了拥有常备军的权利,其他“和平主义者”的立场也包括了维持德国在一战前拥有的殖民地、德国-奥地利地区的自决权(这实际上意味着德国与奥地利合并)以及德国“自由”使用海洋等主张。
在一战后,这些自由主义者也指望通过威尔逊的自决权主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开路,具体地说就是支持生活在当时的德国境外的德裔居民。德国民主党的厄尔克(Oehlke)则通过《布雷斯劳晨报》的1919年新年祝词,要求该地区的自由主义者放弃对社民党的幻想。该地区的德国人民党在支持反犹主义方面更加赤裸裸,他们直接宣称自己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德国国家人民党一致。德国民主党则和包括德国国家人民党在内的激进反犹主义组织共同发起集会。当然,他们也对魏玛外交的“消极”提出了批评。该地区自由主义者支持的保卫德国协会要求积极在国外“扶持日耳曼种族”“夺回一切可能夺回的德国东部地区”;另一个得到当地德国自由主义者支持的组织德国东方协会也鼓吹向中东欧地区进行扩张。诸如席弗(Schiffer)这样的犹太裔自由主义者对这类组织则颇为暧昧。该地区的德国民主党也不甘落后,建立了“三月协会”,其目标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把德国资产阶级的左翼和右翼统一起来。这个党也因为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rnau)的犹太人身份拒绝让他成为该党的议员候选人。
这个地区的不少自由主义者也像德国保守派一样,认为犹太人对一战中德国战败起了作用、组织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并污染了德国文化。隐藏在德国自由主义自决权背后的反犹主义和公开的反犹主义之间的区别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奥托·菲什贝克(Otto Fischbeck)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手法和希特勒早期的手法颇为相似。此人的手法在当时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内也远非个例。有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反犹主义或许有助于把下层中产阶级等远离右翼政党的阶级阶层吸引过来。虽然德国人民党的官方原则是反对反犹主义,但是这在实际中意味着,与德国激进右翼所采取的那一种形式的反犹主义切割。正如另一位学者拉里·琼斯(Larry Jones)指出的,德国人民党自己把一战后魏玛反犹主义的猖獗归咎于犹太人在德国国内外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态度是否真诚,笔者以为不难得出结论。而无论德国民主党还是德国人民党,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魏玛全境内蔓延的反犹主义,只采取了装点门面的抵抗。这两个政党尽可能地对犹太人问题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期望犹太人问题有朝一日像魔术一样自行烟消云散。该地区的犹太裔自由主义者倒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强调犹太人和日耳曼人的团结。一些犹太裔自由主义者建议成立一个犹太人——日耳曼人政党。不过,前述的菲什贝克,以及莫尔登豪尔(Moldenhauer)等民粹派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自由主义政党,以“反驳”魏玛右翼对德国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的指控。
毫不奇怪,在这样一种状况中,下西里西亚的自由主义最终分崩离析。上述犹太裔自由主义者被他们的自由主义同道们无情地抛弃了,再也无法阻止这两个自由主义政党内的反犹主义公开化,并成为这两个政党的主导政策。批评民粹派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卡尔多夫(Kardoff),也被他那些青睐德国人民党的民粹主义腔调的自由主义同道抛诸脑后。早在二十年代初期,第二帝国时期的进步党领袖考夫曼(Kaufmann)就因为德国民主党太和平主义,在社会问题上太激进而转投德国国家人民党了。事实上,一大批德国民族主义者认为德国国家人民党才是德国自由主义的真正代表。这个地区的新一代自由主义者,例如博伊默(Gertrud Baeumer)和奥布斯特( Erich Obst)都更加青睐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柏林(犹太裔)自由主义者”的共和派主张。德国自由主义再也不主张普遍性了,下西里西亚的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同道一样,提出了结合社会改良和民粹派民族主义的纲领。经过上述铺垫之后,当1929年的经济危机来到,当纳粹这个更加“彻底”的反犹主义政党出现的时候,德国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的选民的大规模离去就不难理解了。总的来说,纳粹的成员和普鲁士统治阶级重合的程度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双方大异其趣的。

阿尔萨斯地区的故事则有所不同。虽然这个地区的多数居民们说的是德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的主流政治是德国民族主义。恰恰相反,这个地区传统上更加认同法国的政治制度与思潮,而不认同普鲁士德国的政治制度。一战之前,这个地区流行的“特殊论”也是共和派的;一战之中,这个地区的民族主义也不如德国其余地区强烈。当然,这不是说法国就是世外桃源。事实上,根据其他学者,比如凯文·帕斯莫尔(Kevin Passmore)的研究,自由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转向在法国也发生了(From Liberalism to Fascism)。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说明阿尔萨斯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纳粹支持者,也有一些纳粹组织。那么阿尔萨斯地区,以及法国整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为什么没有像其德国同侪那样上台,执掌大权呢?或者说,为什么法国的人民阵线就能阻止法国法西斯主义执政呢?这显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也期待有学者早日完成这个研究。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