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洞穴岩画、星座传说与宇宙狩猎故事
【编者按】
从古至今,人类都在通过观察星空理解宇宙,这段历史漫长而艰辛。《人类仰望星空时:繁星、宇宙与人类文明的进程》一书回顾了人类的宇宙观如何定义现实的本质与生命的意义,看看我们业已摈弃的神祇与魂灵、神话与魔兽、天上宫阙与恒星天球是什么样子,了解科学宇宙观是如何最终确立地位并塑造了今天的你我。本文摘编自该书,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
为什么在分布于世界各地、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化中,会流传着相似的神话呢?这是一个长期未解的谜题。例如,世界各地的宇宙狩猎(Cosmic Hunt)故事大同小异,不外乎是讲动物在猎人的追赶下奔向天空,变成星座,只不过故事的主角——星座、猎人和猎物——各不相同而已。
在希腊神话中,宙斯诱骗女神阿耳忒弥斯的同伴卡利斯托公主放弃贞洁,为他生下阿卡斯,愤怒的阿耳忒弥斯把卡利斯托变成了熊。阿卡斯长大后成了猎人,险些用长矛刺死自己的母亲。后来宙斯介入,把卡利斯托变成大熊座,又把阿卡斯变成小熊座陪伴在母亲身旁。
美国东北部的易洛魁族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三个猎人弄伤了一头熊,他们循着秋叶上的血渍一路追到天上,最后跟熊一起变成了大熊座。在西伯利亚楚科奇,猎户座是追逐驯鹿(即仙后座)的猎人,而对邻近的芬兰-乌戈尔(Finno-Ugric)族来说,猎物是一只麋鹿。
法国考古学家和统计学家朱利安·迪伊(Julien d’Huy)借用系统发育学原理探索宇宙狩猎故事的起源。系统发育学可以比较物种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从而得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生物学家使用计算机软件分析 DNA 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构建家谱以显示物种之间最可能的亲缘关系。迪伊研究神话的方法与此类似。
迪伊分析了世界各地47个宇宙狩猎故事,从中抽出93个独立单元,称为“神话素”,比如“这是一只草食动物”“神把这只动物变成了星座”等。他对每个神话是否含有某个神话素进行编码,含有记作“1”,不含记作“0”,如此得出一个由0和1组成的字符串,然后用系统发育学软件进行比较,构建出最可能的家谱。2016年,他发表了研究结果:宇宙狩猎故事起源于欧亚大陆北部,之后其中一支扩散到西欧,另一支随人类经由俄罗斯东端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陆桥传到北美。这意味着故事的源头必定要追溯到距今约1.5万年之前,因为白令陆桥在那之后没入了海底。
迪伊总结说,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版本可能讲述了一个孤独的猎人追逐一只麋鹿的故事。猎人穷追不舍,追到天上,麋鹿在临死之际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北斗七星(大熊座的尾巴和胁腹)。在旧石器时代,麋鹿是欧亚大陆北方森林中占支配地位的哺乳动物,对人类狩猎至关重要,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它们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2017年,一项以爱沙尼亚出土的数百个动物牙齿垂饰为对象的研究发现,麋鹿是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8900 — 前1800年)最常见的哺乳动物,之后才慢慢让位给熊。宇宙狩猎故事扩散到世界各地,世代相传,不同民族将故事的主角换成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动物和星座。
迪伊分析的其他神话故事似乎可以追溯到更早的4万多年前,也就是第一批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候。他编撰了“原始神话”的内核(所谓原始神话,是他认定早期人类向北、向东迁移时带走的神话故事),但这些故事并非都涉及恒星,例如有的故事里有龙,也就是会飞的有角巨蛇,能变成彩虹,还能呼风唤雨。有些故事确实提到了昴星团,通常是一个女人或一群女人,与猎户座的男人对应。银河在故事里要么是一条河流,要么是一条亡者之路。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讲述的群星神话不仅是故事,也是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迪伊将群星神话称为“对人类祖先的精神世界的窥视”。这些神话并没有将昴星团和原牛直接联系起来,但与拉斯科洞穴岩画一样,它们生动地描述了那些铭刻于天空的生灵。
在1998年出版的《史前萨满》(The Shamans of Prehistory)一书中,南非岩画专家大卫·刘易斯-威廉姆斯(David Lewis-Williams)和法国洞穴专家让·克洛泰(Jean Clottes)将萨满教的思想运用到对拉斯科洞穴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研究中。刘易斯-威廉姆斯研究过19世纪和20世纪南非游牧民族桑族(San)的岩画,画上的萨满都是以动物形态或精神指引者的形象出现,这显然是在描绘萨满教的异象追寻。
随后,刘易斯-威廉姆斯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洞穴中的心灵》(The Mind in the Cave)。他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在解剖学意义上与我们属同一物种,具有相同的神经系统,所以很可能也会经历与我们同样的幻觉。他指出,现代西方社会注重逻辑和理性思考,往往将恍惚状态和异象视为反常的或可疑的,但对萨满教的研究表明,在全世界几乎所有传统社会中,改变意识状态的做法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被视为一种珍贵的体验。仅从我们死板的视角看待洞穴艺术,这或许令我们漏掉了关键点。沿着法国和西班牙那些幽深狭窄的洞穴行进,人们好似进入了地下的精神王国,所以与两万年后的楚玛什萨满一样,史前萨满深入洞穴也是为了追寻异象,并且将他们的所见所感画在岩壁上。
这一理论有助于解开拉斯科洞穴和其他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岩画的几个谜团。首先,它能解释一些常见的抽象几何图形,比如点、网格、之字形和波浪线。刘易斯-威廉姆斯指出,这些视觉印象通常出现在恍惚状态的第一阶段,偏头痛患者也经常看到。南美洲的图卡诺(Tukano)人用一种对精神有影响的藤蔓饮料“雅姬”(yajé)催眠,把他们在异象追寻中看到的几何符号画在房屋或树皮上。
这一理论还可以解释旧石器时代艺术中古怪的半人半兽。法国东南部肖韦(Chauvet)洞穴岩画中有野牛人,法国西南部特鲁瓦-弗雷尔(Trois-Frères)洞穴岩画中有造型奇特的巫师,长着雄鹿的耳朵和角、健壮的人腿和臀部、马的尾巴和巫师的胡须。此外,经常有人报告说,他们在深度恍惚状态中看到了动物、人和怪物,并且感觉它们与自己融为一体。
最后,刘易斯-威廉姆斯的理论可以解释岩画中那些融合了洞壁特征的形象,以及洞穴艺术家触碰和处理洞壁的方式,比如在洞壁上留下手印和指痕,或者用泥土填洞,再用手指或棍子刺穿。如果洞穴被视为通往地下精神世界的门户,那么洞壁就是两个世界的界线,或者说是一层可以让灵魂穿透并显现的薄膜。“这些洞壁不是毫无意义的支撑物,”他说,“而是这些形象的一部分。”
从本质上说,在萨满的精神之旅中,洞穴的物质现实与萨满头脑中的精神世界交织缠结,彼此影响。萨满走进洞穴,把他们见到的异象刻画在洞壁上,从而改变了洞壁的物理样貌。而与此同时,过往到访者留下的岩画也会激发和塑造后来人眼中的异象。换句话说,过往到访者在看到异世界的同时也在塑造它今后的模样。
刘易斯-威廉姆斯很少讨论天空,他主要关注洞穴作为地下精神王国的隐喻。但是,一些年代更近的部落的证据表明,上界之旅也很关键,这一点在岩画中亦有体现。楚玛什祭司定期将太阳、月亮等天空特征刻画在洞壁上,图卡诺人用平行的点链代表银河。拉彭格吕克认为,有些人把拉斯科洞穴和与之类似的洞穴中的符号看作纯粹的幻觉,这种看法其实遗漏了一些东西,因为这些符号是整个“宇宙异象”的一部分,洞穴不仅代表下界,也代表整个宇宙。
我们无法直接问史前萨满,宇宙在他们眼中到底是什么样子,但特拉维斯·赫德森研究了楚玛什人的天文学并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宇宙“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充满着影响万物的巨大能量源”,在无休止的转世轮回中,“物质既不产生也不消逝,而是转化为生与死”。
现代西方萨满的信仰似乎与这种解释是契合的。桑德拉·因格曼(Sandra Ingerman)是新墨西哥州的一名萨满和作家,据她描述,萨满教的意识状态变化揭示了一种另类的现实观,它将其他生命视作“一张相互联结的生命之网”,其中不仅有动植物,还有太阳、月亮和群星。
让我们回到1940年9月12日。那天,马塞尔·拉维达和他的朋友们在拉斯科洞穴取得了惊人的发现。他们没有声张,而是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13日,找来更亮的灯和更结实的绳子,一步三回头地回到洞穴,生怕被人跟踪。他们把洞口又拓宽了一些,爬进去把洞穴里的地道走了个遍。走过洞穴深处雕刻密布的后堂,他们来到一口深不可测的竖井前头。怎么办?谁先下去?
拉维达再次挺身而出。他顺着绳子往下爬,紧张得心跳加速,他不怕自己抓不住绳子,而是怕同伴们会撒手。下行八米,触底了。他举灯四望,看到了最奇怪的洞穴艺术。
洞穴墙壁上只有一个人类形象。那是一个火柴人,常被称为 “亡者”,长着鸟头,阴茎勃起,45度仰躺,双臂和手指大张。一只毛发竖立的野牛低头从他的上方逼近,牛角前伸,肩上有个黑点,腹下挂着一串圆环,看起来像掉出来的肠子。他的正下方有一只鸟,站在一根直立的木棍上。
这个奇特的画面令几代学者困惑不已,但迪伊和拉彭格吕克都认为,答案要在天空中寻找。如果稍微改换角度,让画中的火柴人立起来看向天空,那么小鸟和野牛就变作与他一齐飞升的同伴。迪伊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宇宙狩猎场景,也就是猎人追逐野兽,最后飞到天上变成了星座。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处在攻击位置的野牛看起来并没有进攻,而它肩上的黑点可能是一颗恒星,下方地面上的黑印可能是带有猎物血迹的叶子,标志着秋天的来临。
迪伊承认,这只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是,这个场景酷似西伯利亚迈亚(Maia)河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人们认为,迈亚河岩画表现的是一个早期版本的宇宙狩猎故事,画中猎人瞄准一只腹部挂着太阳的麋鹿。或许,在拉斯科洞穴深处的那幅岩画中,那只野牛腹下的圆环不是肠子,而是太阳。
我们无法证明远古艺术家的真实创作意图,但不同的证据似乎都指向同一个解释——拉斯科洞穴最深处的这个场景展现了一次星空之旅。同样,本章所描述的《18号公牛》、亡者、宇宙狩猎等各种线索,在我看来虽然存在种种不确定性,但综合起来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压倒性的结论:如果想了解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从何而来,找到人类原初信仰和身份的源头,就必须将旋转的夜空纳入我们的思考。
夜复一夜,季节更迭,天空周期循环往复,这些必定激发了古人类对“我们是谁”和现实本质的最初思考。在今天的狩猎采集社会,这些思考依然存在。“他们提出过同样的问题,”拉彭格吕克说,“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太阳去哪儿了?世界的背后是什么?”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人类宇宙,它既是对天空景象的再现,也是人脑另类意识状态的产物。当意识状态转换时,生命与非生命、人类与自然、地球与群星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人类和宇宙彼此造就,内心体验和外部现实纠缠不清,难以分割。但从此以后,人类开始图谋与宇宙一刀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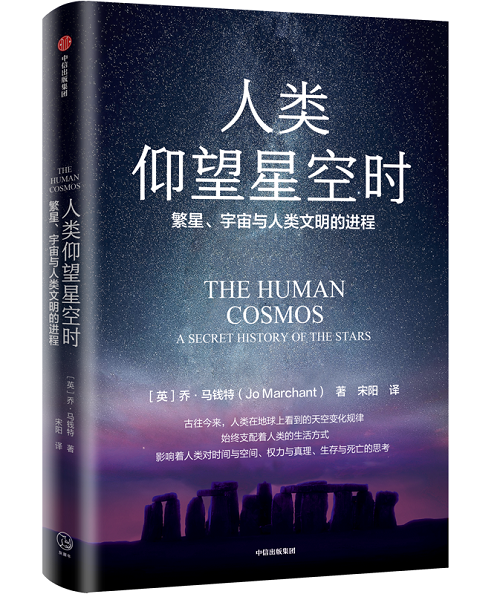
《人类仰望星空时:繁星、宇宙与人类文明的进程》,[英]乔·马钱特(Jo Marchant)著,宋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8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