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块“朽木”的还击

万岭的童年始终伴随着一个令人绝望的预言:他将在18岁之前死去。这是他一岁多的时候,一个医生看着他无法坐立的双腿,叹息着说的。医生推断,这个孩子“没有用”。
万岭的母亲不明白“没有用”是什么意思,医生说:“你听过朽木吗?正常的木头可以做成桌子、椅子,但是朽木就没有用。你这个小孩就是朽木。”
如今,“朽木”27岁了,是一名走路歪斜、说话含糊不清的脑瘫患者,也是一名管理着25名员工、年收入超过300万元的创业者。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残疾人数约有8500万人,其中就业人数仅为881.6万人。
万岭想证明自己是十分之一的分子,更希望证明自己“有用”。由于小脑受损,他无法灵活控制自己的双手,小时候,他总会把拳头重重地砸向那些嘲笑声。
因为打架,万岭的额头曾被缝了三针。后来,为了通过CCIE高级网络工程师认证考试,他把一本600多页的教材抄了一遍,曾经用来打架的手一下下有节奏地戳向键盘,他试图努力控制屏幕里代码的方向,也控制手指不断袭来的疼痛。
27年来,万岭把所有的力气从拳头挪到键盘,再到屏幕上的一行行代码,只是为了让自己距离“正常”更近一点。
文 | 刘欣
编辑 | 卓然
用拳头击败“正常人”
6岁之前,万岭几乎住在医院里。他熟悉许多地方的医院:老家高邮的、扬州的、南京的、上海的、北京的,有时是打吊瓶,有时是做手术。
为了照顾万岭,母亲谢芹辞掉了工作,家里人天天带着万岭去运河边爬台阶,慢慢教他走路,教他用勺子吃饭,哄他喝极苦的药。他们带着万岭去北京做理疗,去长春矫正发音,一个月的学费就要五万多元。这个家里的眼泪多得快要溢出来。
曾经有人让谢芹扔掉这块“朽木”,“你如果下不了手,带到这边来,我帮你把他掐死。”
可这个说“已经流尽了一辈子眼泪”的母亲还是舍不得,她甚至没想过再要一个孩子。她怕,怕自己有了“正常”的孩子,“一定会偏心忽略了万岭”。万岭有时会好奇自己从哪里来,谢芹就会拖长了声音说,万岭是个小天使,在天上是他选择了谢芹当自己的妈妈,“趁我喝水的时候,你就钻到我肚子里去了”。
由于小脑受损影响了平衡感,万岭骑车总是摔跤,他常常连人带车从河堤上滚下来,但第二天又骑着车去上学了。母亲鼓励他:“人家能骑你也可以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母亲总会多花两千块钱,让万岭上“补习班”。她告诉万岭:“不好好上学就没有工作,你要努力自力更生。”不管是什么饭局,母亲总会带着万岭一起去,“把他当成正常的孩子”。万岭七八岁的时候,谢芹还半夜带着万岭去招待所安顿亲戚,因为她觉得“万岭是男子汉了,可以保护我”。
母亲像一朵柔软的棉花包裹着万岭。但吃药、手术以及这些连绵不绝的爱都没能让万岭变得“正常”,只要离开这个家,万岭还是会因为说话含混不清、走路歪歪扭扭被人嘲笑是“傻子”。早读课,同学跟他借书,万岭说他也要用,同学很生气:“你用了干嘛?反正你又不学。”后来,万岭胖得厉害,同学们当着他的面讨论“是吃多了冬虫夏草”,还叫他“胖子”。
毫无意外地,拳头替代眼泪,“对抗”成了万岭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日常。他经常鼻青脸肿地回到家,有时门牙掉了,有时衣服破了,有时脸上挂着口子。
母亲从不因为打架骂万岭,只会问:“打赢了没有?”
“打赢了。”
“赢了就行。”她知道“赢”对儿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万岭的拳头几乎没输过。他希望自己的人生也能像拳头一样,直接、干脆,“打垮”所有不好听的声音。他曾经叫了一帮同学,坐着面包车从高邮到扬州打架,那是他学生时代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他想让对方知道,自己能够轻易击败这些“正常人”。
可坚硬的拳头背后,是更坚硬的现实。小学三年级之后,因为无法灵活控制自己的手,一笔一划对万岭来说无比艰难,他的作业总是写不完,学习慢慢跟不上了。尽管万岭的智力没有问题,但初中的学校还是不想收他。母亲跟校长写了保证书,低声下气地承诺,万岭如果出了什么意外都跟学校无关。
上了初中之后,作业更多了,别的孩子写到晚上八九点钟,万岭要写到凌晨一点。考试的时候他经常答不完题,成绩倒数。有的时候,他离开家会骑车到河边坐一整天,等到傍晚,再装作放学回家。
这个少年第一次发现,有些困境是用拳头也解决不了的。
从脑瘫患者到网络工程师
一块屏幕成了万岭的“避难所”。
小时候,万岭躲在邻居背后看他们在这块屏幕上玩纸牌、扫雷。后来,母亲给他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他爱看《电脑爱好者》杂志,每一期都买,每次电脑坏了,万岭就按照杂志上学的知识自己拆开修。甚至还帮同学组装电脑、安装系统。
只有0和1的代码世界不会投射出鄙夷的眼神。一开始,万岭只是沉默地跟这块屏幕用代码对话。渐渐地,他觉得代码或许能代替拳头,用“更高端”的方式帮他向这个世界还击。
读大专的时候,万岭选择了计算机专业。但毕业后他发现,许多书本上的知识在实践中并不实用,他甚至分不清内存的规格。同事觉得他话都说不利索,能力也不够,就安排他去做“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打字或者整理资料。那时,万岭暗暗在心里想:“等哪天有机会我肯定要‘搞死’你。”
为了“搞死”对方,万岭通过了专升本考试,还参加了当地残联举办的技能大赛,获得了高邮市“数据处理”项目的第一名。他满城找培训机构上课,那个时候,他每天的路程都在扬州的地图里画“三角形”,从借住的亲戚家到公司再到培训机构,一天要骑两三个小时的自行车。可他看到,即便是如此费力地学习,也不能让他在职场上获得更多尊重,培训机构的教学内容离产业一线距离很远,学完的万岭甚至找不到一份对口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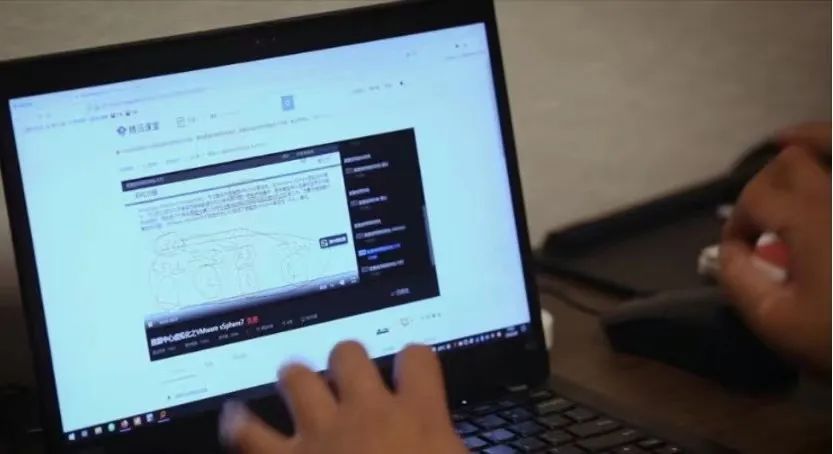
他默默作了一个决定——考CCIE高级网络工程师认证证书。
CCIE被称为IT行业的终极认证,目前全球仅有66200人通过考试取得认证,持证者的平均考试次数为3.98次。腾讯课堂平台上的数字人才培育机构——“熊猫同学(思博网络)”创始人胡明回忆,自己刚毕业的时候月薪2500元,考完CCIE的证书后,年薪涨到了20万元。在他的学员中,许多都是30岁以上的工程师,因为“只有拥有很丰富的行业经验,才有可能通过这场考试”。
所以当万岭联系他、想报名“熊猫同学”的CCIE考试培训课程的时候,胡明很是犹豫。他的学员中有塔吊工人、开挖掘机的,却从没有像万岭这样的残疾人。
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疑虑。为了让学员们看到自己的成长,胡明在班里发起了一个跑步群,邀请大家一起“云跑步”。万岭每天都会在群里更新自己的跑步动态,风雨无阻,尽管,他连走路都有些困难。
因为白天上班,万岭只能晚上上课,刚开始,他像学生时代一样,跟不上班里的进度。但是与上学时不同的是,他可以随时打开屏幕,每天无论多晚到家,万岭总要一遍遍看课程回放,他的鼠标在进度条里反复拖动,没有人会怪他耽误了教学进度。
那块屏幕隔绝了一张张神色异样的脸庞,也过滤了与学习无关的嘈杂声音,有时凌晨两点,有时清晨六点,老师的邮箱和微信里塞满了万岭的作业和问题,万岭在自己的“时区”里开始一步步攀登那座看似遥不可及的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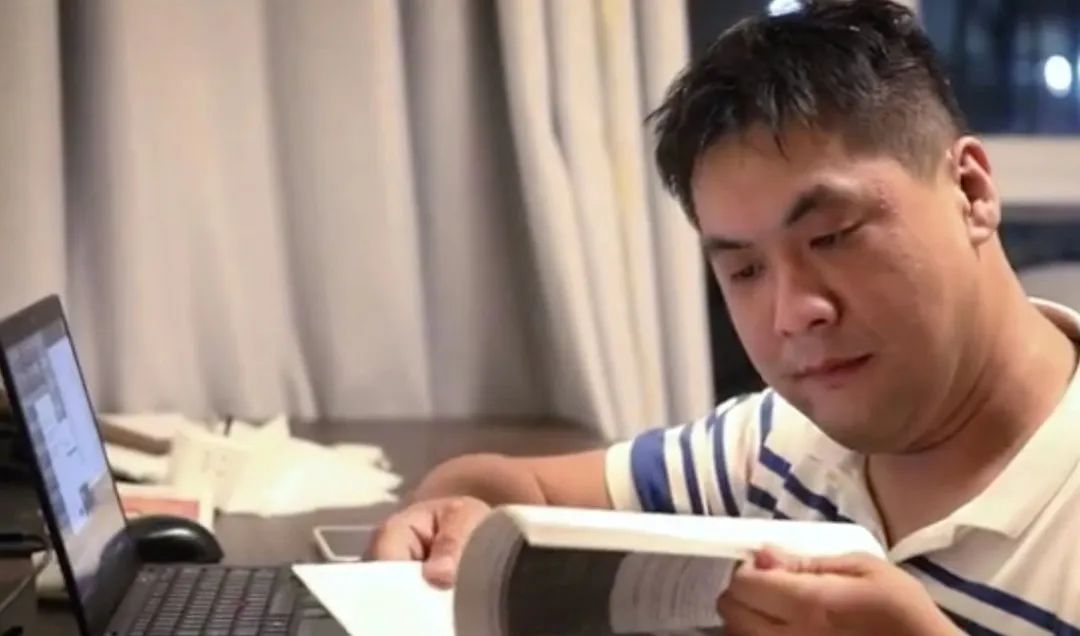
图 | 对照书学习编码的万岭
对普通人而言只是随时随地能学习的在线职业教育,却让万岭人生第一次拿回了学习的主动权。
在屏幕前学习了几个月后,经过两次考试,他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获得CCIE证书的脑瘫患者,拥有了一个新的、无形的“拳头”。拿到证书后,父亲逢人就说,有时还会把证书带出去给别人展示。
这一次,万岭觉得自己或许不会再被人叫“朽木”了。
“我不是中国阿甘”
现实很快又把这个青年摁回原地。
那段时间,万岭常常“白天很亢奋,晚上很低落”。CCIE的证书给他带来了无数面试邀约,但机会往往也结束在面试。由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万岭还去干过两个月的网管。
好不容易,万岭找到一份匹配的工作,工资也翻了一倍多。他很珍惜这个机会,为了一个项目,他和同事在现场值守了三天,“吃喝拉撒都在机房”,工作完刚出机房就晕倒了。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可以用“证书”这种更体面的方式回击这个世界,但人生为他设置的程序是“地狱模式”,一个客户在他完成项目后指指点点,说了一些“很不友好的话”,万岭气得再次伸出了拳头。

图 | 万岭正在调试
他再次回到了那块屏幕前,在腾讯课堂上更多的课,和老师讨论更多的实操案例,考更多的证书。屏幕像他最忠诚的朋友,“学习是最简单的事儿,只要努力就可以学好。”后来,有个公司需要在6小时内完成核心网络升级和改造,高邮的本地团队没人敢接,万岭就拉着几个朋友接下了这个项目,从此在当地“一战成名”。企业的老板们开始点名让“小万”负责某个项目。
这块脆弱、纤薄的屏幕,成了他还击这个世界的新武器。
万岭依然不想止步,他已经明白,“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件事、一个瞬间,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是一个又一个挑战。
母亲谢芹只希望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觉得他创业是“爱折腾”,更多的人说他“励志”,但只有他知道,自己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生存”。他必须更努力、更“成功”,才有可能让自己含混的口音和歪斜的身体变得模糊,才有可能获得应有的“尊严”。
万岭想创业。他不想一辈子只和计算机、技术、代码打交道,他想走出那块屏幕,回归到社交生活里,因为“与人斗,其乐无穷”。合作伙伴李俊杰劝他,这两年行情不好,创业压力会很大,但万岭说:“我就要干。”
26岁的时候,万岭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刚开始,公司只有3个人,但他从不强行挽留任何一个客户,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客户最终还会回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抬高自己的地位了。”李俊杰说,在高邮乃至扬州,万岭是网络安全技术的“天花板”,每次出现网络安全的问题,大家总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口齿不伶俐但技术过硬的“小万”。“小万”的出现,填补了当地乡镇网络安全服务的业务空白。
万岭知道,创业对他来说最困难的不是资金、技术,而是“如何让别人信任”。
这是一个伴随了他27年的问题,而现在似乎正在得到解答。去年一年,万岭公司的收入就有300多万元。如今,公司已经有25个员工,还是华为、深信服在当地的合作伙伴。他的手机铃声总是无间隙排着队地响起,大大小小的客户打来电话,耐心等待着一个个字从万岭嘴里缓慢地、含糊地蹦出,那是“小万”对业务的判断和结论。
万岭终于变得松弛。他不再时刻攥紧拳头,也不再成天躲在屏幕后头。只是每次深夜回家的时候,他总会换下湿透的衣服,重新坐到屏幕前学习。他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而那块屏幕能让他的“系统”永远保持更新。
有人说,万岭像“中国的阿甘”。但万岭觉得:“阿甘比较老实,他一直在跑步,他只知道跑步,从战场跑到运动场。我很不一样,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想办法走近路,找到更短的路径。”
对于万岭来说,那块屏幕就是这条捷径。他认真地想过,如果没有当初腾讯课堂那块屏幕,只会用拳头还击这个世界的自己,也许此刻在福利院,也许成为了一名按摩师。

图 | 计算机前编码的万岭
在更大的一张图纸上,根据中国残联实名制数据统计,当前通过网络实现就业的残疾人每年约6.8万人次,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和软件服务、电商服务等行业,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成倍的速度增长。
现在,距离那个18岁的“魔咒”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没人再说万岭是“朽木”。他新的愿望是,让另外8500万块“朽木”,可以活得不这么用力。


原标题:《一块“朽木”的还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