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访谈︱罗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做一个学者
【编者按】在我的印象中,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罗新教授上一次受到读书人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他那册薄薄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而最近一次“火”起来,是因为他去年年底出版了《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本访谈大体围绕“学术旅程”和“读书献疑”两个主题展开。“学术旅程”期望借此增进对其人的认识,“读书献疑”则基本上由《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引申开来。

澎湃新闻:您在《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前言里说,“我能够较多地使用魏晋南北朝史料,全拜近二十年田余庆先生和祝总斌先生两位恩师的教诲。”很想请您谈一谈田先生和祝先生在教书育人和治学风格上分别有什么特点,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
罗新:两个人性格很不一样。田先生年纪大一些,资格老一些,我(在北大)入学的时候,平时也见不着他,一年大概见上一面、两面的。经常能见到的是祝先生,我们几乎每周跟祝先生在一起,一是在他家里读《通鉴》,一是上他制度史的课。在研究生头一两年跟祝先生的接触是很多的,到三年级的时候准备写硕士论文了,我和另一位同学就要分开,各选一位导师,祝先生对我说,田先生让我跟他,另外一位同学就跟祝先生。从那以后,我和祝先生的接触就慢慢少了,好多都是礼貌场合那种见面。但是,我觉得祝先生对我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第一个是他怎么对学生,他对学生(的态度),用田先生的话,就是“菩萨心肠”,总是为学生着想。要是按照田先生那种严格的标准,有些学生不能招,有些学生不能毕业,有些学生中途就应该淘汰了。可是祝先生总是会替学生想,这是特别难得的。要是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连我们做学生的都觉得,这个人就算了,中期考试让他不过关,就让他回家了,可是祝先生会觉得人家是真的愿意学习,一个人想学习,那一定要想办法帮他。他是这种性格和心肠的人。这点对我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另外,要说学历史,入门,那是祝先生带的路。我中文系毕业的,原来也读历史书,毕业之后好几年都是在读历史书,读笔记啊,读正史啊,读杂七杂八的著作啊,可是不大了解(文学和历史)有什么不一样。自从跟他读了制度史,我才真的领悟了,哦,这才叫读得懂历史。上了他的制度史的课,再读《通鉴》这种书,读法不一样了——过去都是从里面找故事而已。祝先生的课我都听过,史学史、法制史、官制史,在我读硕士和博士期间,他开的课我都听过。这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读硕士时每周到他家里读《通鉴》,真是很有收获的。
祝先生今年88岁了,据说现在身体很不好,师母身体也不好。前不久张帆代表历史系去看望祝先生,我看到照片,感觉很苍老,跟我记忆中能量无限的,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的,在未名湖边不停跑步的,每天拉单杠的祝先生,那个记忆完全不同了。他现在真是老人了。
我认识祝先生比认识田先生的时间要长得多,因为我本科就上他的课——本科时中文系、图书馆系和历史系的通史课是一起上的,他给我们上通史。我是因为他才进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的,因为我不认识别的历史系老师——当然祝先生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所以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问您招什么(方向的)研究生。他说我招魏晋南北朝。那我就考魏晋南北朝。

祝先生在回信的时候说,我呢,是跟田余庆先生一起招生。我当时还想,田余庆什么人呢?这个名字肯定在哪见过,在报纸上、在杂志上看到过,但没有任何印象,也没有读过他任何东西。入学之后才读他的文章,那时候《东晋门阀政治》也出来了,就读(他的)书读文章,才了解他。当然田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用说了。在我一生当中,我接触最密切最多的、情感和思想上联系最深的人,应该就是田先生了。我现在五十多岁了,我一生主要的时间在北大,我在北大期间主要是跟田先生在一起。而田先生也不仅仅把我当学生对待,我也不把他只当一个老师对待,所以,无论是在学业上、个人感情上、个人生活上,(田先生)对我都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每个人读书都是希望学老师的,像我从读硕士开始,崇拜田先生,我的硕士论文简直就是模仿田先生那一套来写的。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很早就会意识到,自己学不到(田先生)那一套东西。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治学风格。田先生常说“泥我者死”,机械地学是学不好的。事实上,我们这么多学生跟着田先生,都崇拜他,都想学习他,但没有一个学得比较像。我也学不像。这一点,我早就意识到了。所以,老早就放弃了,就做自己能做的一点事情。这点田先生也是赞成的,他觉得不能机械地模仿别人,不然会失去自己的风格。当然,一个人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即使没有风格,也不需要去模仿别人。
我觉得,田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另外一些方面的,不是直接(反映在)学术上、写作上、读文献上的,这些当然都是应该跟着老师学习,但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方面——比如说,对待学术的态度,对待人生的态度,在对人生和学术关系的处理上,这些方面(田先生)对我影响是最大的。在我认识田先生之后,我少年的那些想法都抛弃了。我猜想,如果没有碰到田先生,我的人生会非常不同——我不敢说更好或更糟,但肯定会非常不同。因为,看着他,会觉得这样的人生就是美好的,就应该过这样的人生,就是做一个学者,不必做任何别的事情,不求别的东西。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觉得挺美好的,至少挺适合我的最基本的价值观。所以我心甘情愿过这样的人生。

澎湃新闻: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北族名号这个专题进行研究?这里面涉及比较语言学这个很难啃的骨头(当然这只是中古史研究的困难之一)。
罗新:我最早写这类文章的时候,国外有些专家就跟我说:这些问题都是几十年来人们拒绝再讨论的,因为讨论这些问题很危险,差不多都是在胡思乱想。但是,我是出于两个原因走上这条路:第一,这些都是五六十年前学者们的工作,但五六十年来都不做了,不做自然有学术内部的道理,学科自身的逻辑,这个我们今天都能理解。我们当然反对名词解释那样的研究,又是语言,又是历史,东扯西拉写一篇文章。但是呢,这是一大片应该开垦却没有开垦的荒原,特别是中古史料里有大量这方面的材料,契丹以后、元以后通过语言的比勘,用科学的方法去还原,是做得到的。但是在唐以前,相当部分会是众说纷纭,如果有十个人研究,可能会有五六种、七八种说法,甚至各有一种说法,莫衷一是。在百十种说法的基础上,又增添一种说法,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片应该利用的资源,不能因为前人的教训就不敢触碰它,就不敢用它。中古史资料那么少,而现有材料中有这么一个矿藏不开发,实在说不过去。这是第一个原因,使得我不舍得不去动它。
第二个原因,如果我想离开传统的以中原史为中心的视角,换一种视角看那个时代的历史,就必须处理这些材料,我的博士论文写十六国,写得很失败,毕业之后好多年我一直在反省。田先生也认为我的博士论文写得不好,他觉得我的硕士论文做得很好,那个路子他能接受,是因为跟着他那个路子走的,他的意思是我应该做点别的研究。这样,就有点做不下去了。我就是有点不服,想了好多年,在去哈佛燕京之前跟张广达先生聊过,张先生对我起了很大作用,他说这些问题应该做,但你的做法不对,因为你的做法,几百年来传统中国学者都是这样做的,清代学者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读的书比你多,他们积累的材料比你丰富,还是照原来的方式,你超不过他们,说不出更多的话来。这一说对我触动很大。的确如此,钱大昕都这么做了,我还能怎么做呢?你想比他们了解更多,就得具备和他们不一样的能力和视野。这个视野,就应该是现代学术的视野。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暂时放下了中古史,开始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比如中亚的研究啊、蒙古啊,读突厥以下的东西。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发现因为语言资料的宽阔,一下子视野就变了。这一变,你对北方的感受是不同的,你会发现传统学者对这个是隔膜的,他们很信赖中文史料里的说法,你只要站在另一角度,就会深刻地怀疑这些说法。而且你一怀疑,背后的漏洞就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学习语言。虽然我们不知道鲜卑是什么语言,但我们知道古代阿尔泰语的基本规则,而突厥时代跟鲜卑时代有很强的继承性。比如说在名号方面就有强烈的继承性,突厥人把那一套东西都拿来用。而且,整个阿尔泰文化的继承性都很强。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突然发现这个字原来是这个意思,这样一来就做了不少工作。我和传统的以语言来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同,我是这个时代的学者,具备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和追求,就是说,我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还原语言,我其实不在乎这个东西,而是希望借此恢复历史面貌,发掘史料背后的政治构造和文化特征。即使我的一些具体解释是错误的或不可靠的,或者说是永远无法证实的,但没有关系,我模模糊糊意识到那背后的道理,而那个道理是非常靠得住的,或者说,是有启发的。这一点,使得我愿意做下去,但也没有做多少年,因为我渐渐意识到这背后的关怀是有限的。如果只做技术性的工作,做多了也烦,我关怀的其实是(语言、名词)后面的东西。后来我觉得可以跳出语言了,就做了《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类的东西。

罗新:我们翻译的那些论文都是历史方面的,而丹尼斯·塞诺的厉害在语言方面。我们没有选语言方面的论文,是担心翻译难度太大。当然接触丹尼斯·塞诺本人,看他别的东西,对我影响很大。不过,那时候我在这条路上走得挺远了,有点儿回不了头了。
阿尔泰学主要是关注语言的,当然也会涉及广义的文化,甚至政治,也会讨论历史问题,但国际上的主要参与者主要是做语言研究的,可以说是一门以语言学为中心的学问。我没有资格去讨论阿尔泰学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就这一部分来说,我们还是做得很不够。内亚研究跟阿尔泰学这两个概念所指固然有所不同,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好像阿尔泰学是更早的东西,是东方研究、东方学的一部分,内亚研究是现代学术的一部分。就像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关系,说它重合,确实是大重合,内亚研究本身不包含学科规范、方法,可是阿尔泰学是包含这些内容的,它的门槛很高。
澎湃新闻:国内有哪些学者涉足这个领域呢?
罗新:国内还是有挺多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过主要是做突厥以后的,我们还有国际顶级专家,比如做蒙古的,过去有亦邻真先生,现在有乌兰、乌云毕力格等,在突厥学领域我们过去有耿世民先生,都是成就卓越、在国际上很有地位的学者,很了不起的。但是,用阿尔泰学的积累、规范与方法做唐代之前的研究的,好像还没有。所以,我做这个研究,有点孤掌难鸣,没有人说你好,也没有人说你坏,确实是一个糟糕的事。大概是因为熟悉阿尔泰学的人对中古史不太了解,而熟悉魏晋南北朝史的人对阿尔泰学的方法也挺隔膜。希望今后会有较多年轻人勇敢面对。

罗新:我是参加过走马楼吴简早期的整理工作,这方面的论文写得不多,大概有三四篇吧。做魏晋南北朝研究的人,学科上最大的焦虑就是史料太少了,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史料你在读研究生期间可以全部读完。当然不是说读完了就可以不再读了,吃透它当然需要一辈子。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所谓拓宽史料的说法。要拓宽史料,出土史料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做的工作比较多,名号研究是一种,同时我也做墓志,还有就是当时出现了吴简,我也很积极地参与了。当然简牍整理的技术性很强,但是对于努力的学者来说这个困难还是能克服。而更重要的是看自己能不能利用这些史料。对我来说,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能力不够。怎么说呢?我感觉我对吴简的材料很隔膜——材料本身我很熟啊,因为是我参与整理的,可是要我把这些材料写成文章,我不大会写。当然我那时候也是把精力放在北方这些研究了。这样,就很快主动放弃了。
澎湃新闻:读这些材料,应该会刺激您阅读文献材料。
罗新:那当然。绝对的。因为很多文献你根本就不读,或者读了根本视而不见。比如说,竹简里面常见“屯田司马”,这是我自己整理的,老遇到“屯田司马”。很久以后读《三国志》才发现曹魏那边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屯田民都带有一定的依附性,就是半奴隶身份的人,罪犯或俘虏,曹魏把这种人每五百人设一屯,屯长官是司马。当年做吴简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有可能孙吴学了曹魏的制度,就有了同样类型的“屯田司马”。也许长沙郡下的临湘侯国规模不大,设一个屯就可以了。当然我没写过任何文章,也没看到别人提这个事。我读书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当你读了出土的文献,再去读正史文献,过去可能不注意,现在明白了。
澎湃新闻:迄今为止您自己比较满意的论文有哪几篇?
罗新:没有特别满意的。如果说写得比较有意义的,文章本身写得并不好,但是文章写了之后对我后来的研究,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有意义的,大概有两三篇这样的文章。
一篇是《可汗号之性质》,通过讨论可汗号,我突然明白了名号内部的结构是什么,而且对我来说是一个发现,因为过去没有人这样讨论。我把名号区分成两个部分,它们各有功能。而且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通例,在任何级别的政治领导名号身上都有类似的结构。这个功能与结构的突破,使我后来所有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可能。
另一篇是《王化与山险》,也是由一对概念所结构起来的,把它简化为“王化与山险”这样相对立的一对观念之后,我就明白了,对于南方土著人群,一个大型帝国是怎样采取政策的,以及这个历史进程经过怎样的阶段性发展。如果回过头来重写,会写得好得多,但当时写得很草率,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想明白了,已经来不及了,前面写了一大堆废话了,但也舍不得扔。写完之后的收获,要比论文本身的收获大。
其他的(论文),就没有这种理论性的、方法论的意义。

罗新: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并不是往复,而是天涯上有一个关天茶舍,那是我创办的。
往复最大的收获,是陆扬老师的加入。我们这些人说的话,即使不算坏,对大家都不那么陌生,只有陆扬的参与,他说的话,他带来的信息,他带来的想法,是当年的中国学术界很陌生的,所以他的意义非常大。2000年左右的中国学者,对海外学界的了解,和现在相比,不是一回事。现在陆扬说个什么,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但那个时候陆扬说的话,都是新鲜的,都没见过。云中君的出现,是网络学术生态的一个新现象。如果说往复(对中国学术)有贡献,这就是一个贡献。
因为我本家姓冷,我父亲本来姓冷,但我奶奶带着我父亲嫁到罗家,这样我们家都姓罗了。这个在传统社会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传统社会根本没有所谓纯正的姓氏。姓氏的文化意义要远远高于姓氏的血缘意义。认同反映的是文化意义。谁养我,我就姓什么,对不对?
澎湃新闻:您是个电影谜,一年大概要看多少电影?最喜欢哪种类型的片子?电影对您的史学研究有何影响?
罗新:我过去狂追电影和美剧。时间合适的话,我能没完没了地看。
我年轻时是爱文学的,也曾想当作家,更多的是看小说。但看小说需要时间,看电影,像看美剧一样,比较省事。所以,看电影可以说是一种偷懒,你进入虚拟世界,它迅速就结束了,两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不像看小说,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真正看小说的收获比看电影的收获会大得多。
我经常在想历史和虚构文学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们写的历史跟那些文学作品没什么大的不同,只是游戏规则不一样,历史学要遵照一套自己的学理、研究和写作规范。历史和文学最大的不同是,文学从构想开始,就是有主人公的,有中心思想、故事主线,而历史没有,历史哪有什么主人公啊,只有写出来以后才有主人公,比如你把伟大领袖写出来,他才是主人公,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主人公随时都在死啊,随时都有新的主人公出现。真正意义的历史是没有主人公的,是一团混沌,没有主线,也没有故事,——故事是写作的时候,被历史学家特意找出来的,围绕一个主人公写出来,放在有限的时空里讲述。但是这样做就抹杀了很多别的主人公,抹杀了很多别的主线。我觉得,对历史学的这个叙事特征进行反思,可能对我们认识历史有意义。我们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我们会觉得我很重要,其实对历史来说,只不过是万万千千的线索之一,你把这个线索单独拿出来的时候,强调它的时候,意味着抹掉了很多其他的线索,而其他的线索也都是真实的东西,你抹掉了他们,是因为你认为他们在你的研究中不重要,当然也可能是你对他们认识的不够多。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要经常这样想,经常反思自己的工作,别把你写的东西看得多么神圣、多么重要、多么不可动摇。
澎湃新闻:您无疑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很好奇,您从大都到上都的路上还带着什么书?
罗新:如果从背包客的角度说,不带帐篷,不带睡袋,不带吃的、喝的,所以带的东西不多。十来公斤,不到十五公斤。不重。露营的人,一般都得带二十公斤以上。十五到二十公斤是一个跳跃,到二十公斤就很难受,走一步都很难受。十五公斤以下,多一点、少一点,差别不大。背负增重到近二十公斤,我去年经历过,每一步都不是好惹的。我走之前,请社科院历史所的罗玮,他是张帆的学生,我请他帮我准备了相关史料的电子版,当然我还带了几本闲书,因为我还是喜欢看纸本。其实后来看不了。前一个礼拜还能看,后一个礼拜就看不动了。

罗新:文章的最后部分,我是把草原官号和古代华夏制度联系起来讨论。我那时候受了人类学的影响,在几篇文章里都暴露出这一点,不愿意只说北方是这样的,非常想说我做的这个研究具有一般性,也可以用来反观其他文化,包括华夏早期文化。我那时候有一种这样的观念,后来我放弃了——认为北方的发展只不过是反映了华夏早期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让北方的政治继续成熟发展,将来它会走到南边的华夏这条路上来。这种预设,很可能是受到普遍历史观的影响,我们这代人都受这种历史观的影响,就是进步史观那套东西。虽然嘴上不说,但始终想把北方和华夏搭上,碰到谥号这个东西,觉得好奇怪,生前有谥号,为什么改为身后有谥号。我想对这个问题给一个解释,对这个解释,有人说很有启发,有的人没有感觉。时间长了,我也想不清自己是怎么想的了。后来我就沉迷在名号的功能分析上了,不太敢跟华夏搭边了。除了《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这篇文章,我后来再也不敢把北族名号和华夏传统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种解释还是很冒险。当然做先秦的人也不从这个角度想问题,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启发。
澎湃新闻:在史料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您对史籍中有关南匈奴的零星记载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在《匈奴单于号研究》一文中,您认为:“南匈奴历任单于的单于号,都是死后获得的。”这“是匈奴单于号传统的重大改变,推动这一变化的力量,一定来自东汉王朝”。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直接证据,我对这个论断仍不免有所怀疑,毕竟内亚草原民族的名号传统根深蒂固。我想请教的是,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已有十几年,您是否有更多证据(包括旁证)进一步证明您的观点。或者,您是否改变了原先的观点?
罗新:这个就是普遍历史观的影响,既然到了中国文化环境下,匈奴慢慢就接触汉朝文化这一套,所以匈奴名号就从生前变成死后获得的了。如果能说明这一点,我当时所信奉的那一套历史观就起作用了,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这套东西就不是中国独有的了,而是在某个社会、某个政治发展阶段必然经历的,是普遍的。北方之所以没有,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这个历史阶段。后来这套我就不提了,我感觉这背后的预设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有问题的。
相关材料就这么几句,后来也没有新的出土材料。别人要反驳也很难,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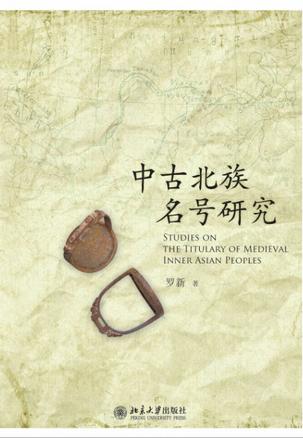
罗新:我当时推测赐名几百个人,应该是有一个机构的,有一个赐名的班子,这个班子是秘密的。里面的成员级别可能不高,都是一些文人,让他们弄清楚,然后以皇帝的名义去颁布。
我的一个学生写论文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赐名是不是被受赐者家庭接受,接受程度如何,使用范围如何,这还是不一定的。有些人家里可能没有行用赐名,当然在正始场合是用的。近年所出的“元苌墓志”,元昶不见于史。苌不像是赐名,苌就是长,长命、长安,都可以换用苌这个字。元苌的苌,可能是长命一名的缩略。那时候“长命”是一个常见的名字,这个名字作为一个汉语词早就连音带义进入代北鲜卑语了,所以代北集团的人取长命做名字并不奇怪。书写时按照汉语书写习惯,简写为元苌。按照元苌墓志,知道他官居高位,是个重要人物,但正史里却看不见。我的学生潘敦在他的硕士论文里考证,原来这个元苌就是《魏书》里的元俨。正史记他的赐名,家里安葬他时还是用他的本名,两不相干。这样,我们就知道,赐名不一定为家人所遵用。
澎湃新闻:您在《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一文中提出,唐代的皇帝尊号制度根本上渊源于内亚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而武则天恰好借此自封“天后”,而后临朝称制。我的问题是,可汗号传统诱发了皇帝加尊号,并且形成一套制度,但皇帝尊号本身(所谓“允文允武,乃圣乃神”)是否包含了宗教因素,比如说武则天的尊号是否有佛教的因素?
罗新:武则天的尊号里面带有佛教的内容,有的可能带有道教的内容,更不用说到了元代,那里面有太多宗教的内容。称号就是美名嘛,才不分什么道教佛教,只要觉得是好东西,都可以拿来用。
澎湃新闻:唐太宗时期完成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的修纂,高宗时期完成了《南史》和《北史》,有学者指出初期的唐朝政权是个具有异常高度历史意识的政权。今人研究南北朝史,必然要利用唐初编纂的这些历史文献,您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陷阱或值得时刻警惕的地方?
罗新:步步陷阱。但这几乎是唯一的材料。除了现在出土的一些墓志,文学有些诗文,几乎没有别的。南北朝时代的文献丧失,太严重了。
所以历史观很重要,得建立一套批判的历史观。你有了自己的问题,不要被这些材料迷惑住。学会从材料中读出材料背后的意图。我们的老师,周(一良)先生、田先生,最喜欢说的一个词叫“读书得间”,就是在字里行间去找背后的意思,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老师经常说这个词。现在人们说的少了。那时候见面就说,要读书得间、读书得间。

罗新:我们任何时候都在说某些时期变动特别大,当然有可能,但我们不能忘记一点,历史本身一直在变动的。所有重大的变动都是前面的小变化积累的结果。有时候我们只注意到那个重大变化发生的瞬间,比如只注意到辛亥革命的那一场暴动,可能没有注意到将近一百年来各方面的条件在往这方面指引。如果只注意到那场暴动,那是严重不够的。拿魏晋南北朝来说,至少有些变化在东汉的时候就开始了,不能只看到五胡十六国、北朝发生的动荡。归根结底,历史是写出来的,发生的历史跟写出来的历史不一样。刚才说过,历史没有主人公,没有线索。但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有线索,都有主人公,都有“问题”——历史自身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说的是,历史上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历史学家的说法问题。他说这些的时候,是要表达某个目的。我们要注意他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
古代历史的特点是只记载重大的政治变动,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事件和人物,就写得很多,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熟悉的人物,应该超过两汉。我们大概只记得汉高祖时代、汉武帝时代、两汉之际、东汉末的人物和事件,东汉中期一百多年的历史,就不大管了。就此而言,做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是幸运的,因为这些政治变动都记录下来了。但是,这也容易造成错觉,你会觉得这个时候的历史变化特别多,其实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变动。很多重大的文化上的变动,如果不是因为有考古发掘和其他传世材料,我们几乎看不到。比如佛教,如果不是因为有石窟,有大量的造像碑,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最大的变化可能是文化上的,民众生活、社会形态的变化,可能出现了新的结社方式,人们有了新的交往方式,女性因为宗教而获得了一定的解放,她们有了自己的生活、精神和价值空间,是过去所没有的。而史料在乎的是谁和谁打了战,谁赢了,并不关注更重大的变化其实是发生在另外一些方面。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日本的北族史、内亚史研究有什么值得中国学界关注的地方?
罗新:我觉得日本学术挺有意思的,一方面日本学者跟西方学界关系非常紧密,另一方面它自有传统,它自己的研究传统非常深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问题、方法、资料整理等方面,它自有传统,甚至有一些东西比西方要强得多,比方说他们的蒙古研究和满文研究,特别是满文研究,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好。就这一点来说,姚大力老师开过一个玩笑,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玩笑当真,他说,你用满文材料,不需要懂英文,不需要懂满文,只需要懂日文就可以了,因为日本学者整理得很好,很可靠。
当然他们的传统也在变动发展中,比如早先比较重视与中国对立的游牧世界,把这个叫作朴素主义、文明主义,相当于罗马文明世界与蛮族世界的对立,这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是,现在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不再把蛮族世界、游牧世界看成是跟中国历史相对立而存在的,他们是跟中国历史发生了关系,但更大程度上它们是自我存在的,而它们的自我存在是跟后面更大的内亚世界、甚至欧亚世界相联系,我觉得这是学术的新发展,不是什么分裂中国的政治阴谋。这个发展值得关注,因为阿尔泰语言和芬乌语言在空间上的确是连续分布的,因此它是一个广大的世界,过去我们只注意到中国周边,只注意蒙古高原,以为已经看得够远了。日本学者是一直往西,看到乌拉尔以西,一直到波罗的海,这样一个广大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所以他们再也不把内亚史看成是东洋史的一部分了。这在学理上有它的道理。
澎湃新闻:您在《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前言中指出,一切历史视野中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另外还提到文化体的概念。那么,文化体和政治体之间是否会有矛盾和冲突?如果有,一般会有怎样的措施予以调解?
罗新:我觉得文化体和政治体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对某种结构进行描述的时候,因为观察的东西不一样,就有不同的区分。政治体(这个概念)强调的是用政治关系塑造出来的,文化体强调的是用文化关系塑造出来的,或者说是通过文化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汉字文化可以构成一个文化体,包括整个东亚,甚至越南,但它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体,相对来说文化体的连续性比较强,空间比较大,而政治体的连续性很不强,可能几十年就换一个王朝,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时有发生。所以,政治体、文化体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危险的是,政治体比较喜欢把自己描述成文化体。过去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对两者不加区分。当我们讨论一个王朝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这个王朝代表了某种文化,其实它只是这个文化中的一部分,它有政治边界,它想把边界之外的说成跟它在文化上也没关系,甚至是敌对关系,而事实是,那个是它所属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它不能在政治上征服人家,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边,就把人家推出去。另一方面,有的政治体无视别的政治体,人家明明是一个政治体,但你总是声称那是你的一部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至少我的研究倾向是,我们始终要重视政治体,因为政治体有不同的利益,虽然文化体、社会体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政治体有它特别的利益,它的利益是王朝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只有明白它的利益,才能理解它的政策、手段和统治方式。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