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周理乾评《蛇、日出与莎士比亚》︱爱与恐惧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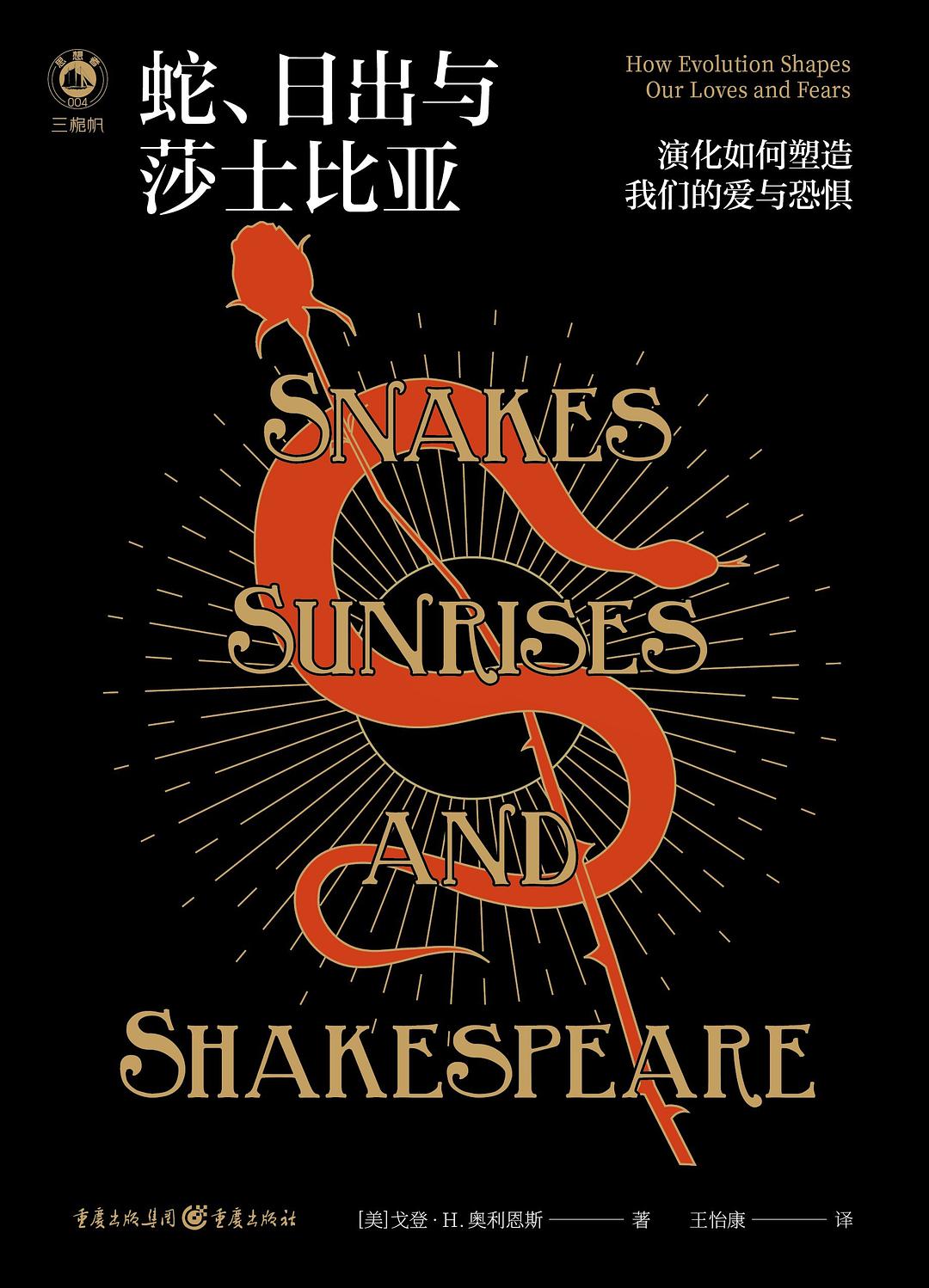
《蛇、日出与莎士比亚:演化如何塑造我们的爱与恐惧》,[美]戈登·H.奥利恩斯著,王怡康译,重庆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288页,6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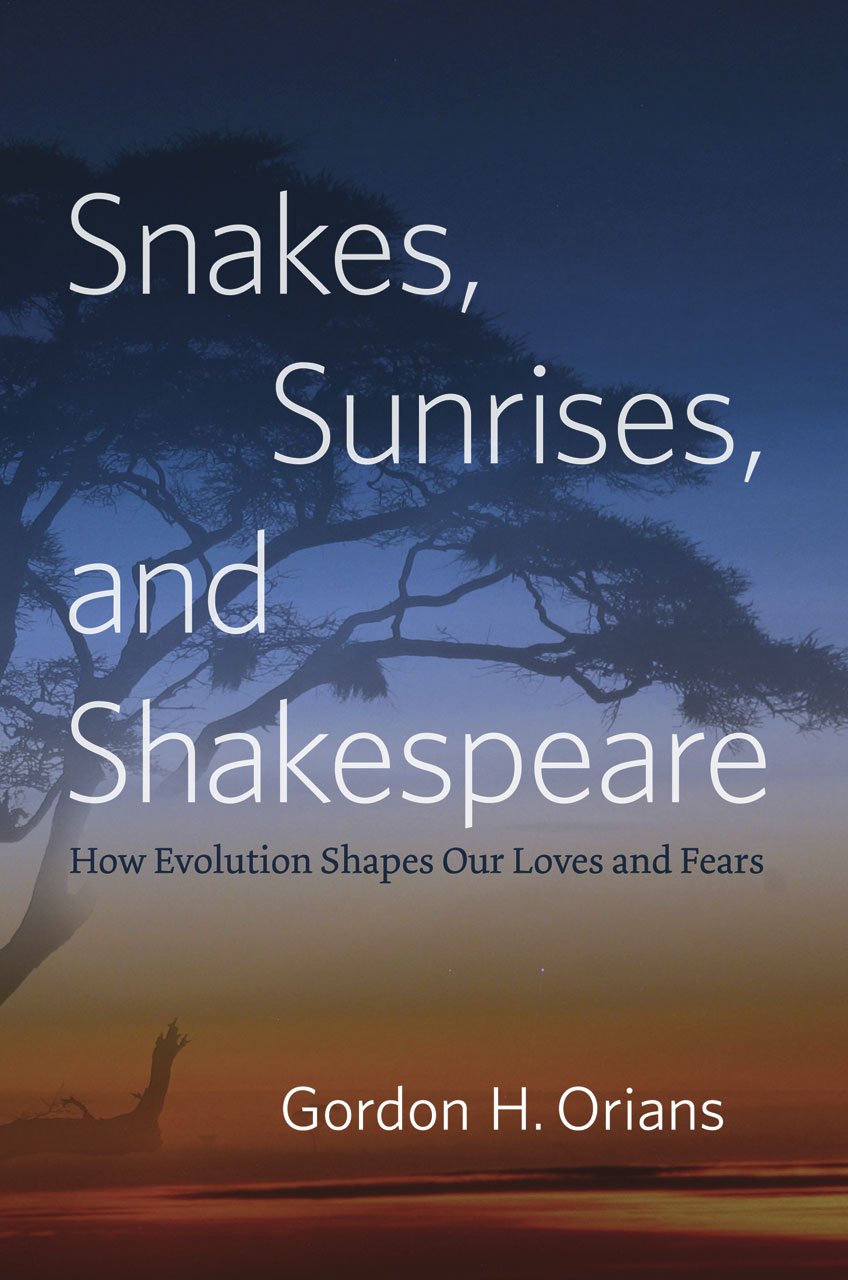
Snakes, Sunrises, and Shakespeare: How Evolution Shapes Our Loves and Fears
一个东西之所以是美的,因为能够激发起我们强烈的愉悦情感,例如黄山日出;一个东西之所以是丑的,因为会让我们感觉不适、恶心或者恐惧,比如野外树枝间慢慢移动的棒络新妇蜘蛛。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这般的审美偏好?为什么我们会对周围环境中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情感反应?对于第一个问题,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我们的审美偏好深受文化的影响,更多是后天习得的。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对周围事物直接的情感反应很可能是先天本能的,对有利于我们的,我们有正面的情感反应;对于可能损害我们的,我们感觉厌恶。不过这两个看起来可靠的回答却都面临严重的问题。如果第二个回答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激发我们强烈情感反应的审美偏好不是本能的,而是文化塑造的呢?如果情感反应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为何我们对实际上几乎不对人产生伤害的蜘蛛感到恐惧,而对枪支、超速等等对我们人身安全有严重威胁的却不会感觉那么害怕?
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著名动物行为学家戈登·H.奥利恩斯(Gordon H. Orians)在其新书《蛇、日出与莎士比亚——演化如何塑造我们的爱与恐惧》中尝试从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上面的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环境美学的观点: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爱与恐惧实际上是我们对人类故乡——非洲热带稀树草原——的“乡愁”。就像我们每个人无法忘记家乡饭菜的味道,智人(Homo Sapiens)对非洲热带稀树草原环境的适应已经刻在了我们的基因里。也就是说,与其他生物性状一样,对周围事物的情感反应、审美偏好等等习性(habits)也是自然选择、性选择的产物;我们的情感、审美偏好是非洲祖先长期适应热带稀树草原环境的产物。

戈登·H.奥利恩斯(Gordon H. Orians)
当奥利恩斯说情感和审美偏好刻在我们的基因里时,他对心理学中一个长久存在的争论——人类行为究竟是先天本能还是后天习得的——给出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的情感和审美偏好是先天本能的,是我们的内在知识。在第三章开头,他引用康德的话,“除非我们进入了我们已经理解了其中关系的世界,否则就无法理解环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站在先天本能的一边。在一篇访谈中,他认为我们的行为当然既受先天因素的影响,又受后天环境的塑造。就像我的母语是中文,是因为我在中文环境中出生、成长;但我的语言能力是先天就有的。他也用同样的思路来理解园林设计。虽然中国的苏州园林、日本传统园林、欧洲皇家园林在风格特色上各有不同,但基本的结构元素却是同构的,都会潜移默化地构建成与热带稀树草原同样结构的模式。无论是树木的选择,空地空间的设计以及水的应用,都蕴含着资源丰富的非洲热带稀树草原构成的关键元素。不过,不像自然选择理论诞生之前康德所认为的那样,人的认知范畴是先天固有的,奥利恩斯认为这些情感并不是“神圣造物主赠送的礼物,而是我们动物起源的馈赠”,“美与丑也不是对象的内在性质。相反,美与丑来自于对象特征与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我们人类情感和审美偏好的内在知识是我们的祖先在热带稀树草原适应的结果。
既然情感和审美偏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它们与早期人类的生存和繁殖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提高我们的适应度。我们对一个事物感觉到恐惧,是因为这一事物对我们的生存或者繁殖会产生潜在的威胁。恐惧这种情感反应可以让我们避免这些潜在威胁。而一个事物让我们感到愉悦,是因为该事物可能会提升我们的适应度。这种解释看起来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这是奥利恩斯在第五章解释恐惧的方式,即我们之所以对一事物感到恐惧,是因为该事物在人类演化史上对人类的生存可能造成伤亡,比如毒蛇、尖形物体等等。而枪、超速行驶等等虽然对人类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但在人类史上是很晚近才出现的,因此不足以让我们产生本能的情绪反应,所以我们并不会感到很恐惧。然而,作为科学解释,这还不够。作为一流的科学家,奥利恩斯深谙此道。因此,他在书中对情感和审美偏好的解释做了大胆的假设,但在具体求证上却极为小心。
如果没有严格仔细的经验证据和实证研究,基于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演化论解释很容易流于空泛,变成无法证伪、只能自圆其说、自说自话的理论。因此,要用演化论来解释人类的情感和审美偏好,需要更具体的理论假说。而一个好的理论假说不仅仅能够解释现象,还能够做出预测。因为,同一现象可以由不同且不相容的理论进行解释。如果能够做出预测,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操作、干预,进而判断这个理论假说适用与否。
奥利恩斯在书中主要使用了两个演化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情感和审美偏好的起源:热带稀树草原假说(Savanna Hypothesis)和了望-庇护理论(prospect-refuge theory)。热带稀树草原假说认为,人类情感的根源植根于非洲热带稀树草原之中,因为资源丰富的非洲热带稀树草原是古猿到智人(Homo Sapiens)演化发生的环境。也就是说,这一地理环境的特征特别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繁殖,因此热带稀树草原的独特特征对人类尤其有吸引力,即人类在审美上偏好相关的特征。了望-庇护理论认为,“我们通过寻找安全探索的方法,进而决定如何对陌生的地形景观进行评估”。这意味着,“在将自身暴露于最小风险之下的同时,我们应该选择能够让我们获取关于环境最多信息量的途径”。奥利恩斯根据这两个具体的理论假说做出来了具体的预测:首先,如果热带稀树草原假说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应该在审美上偏好这一地理环境的独特特征,比如这一环境中具有独特宽树冠的树;其次,如果了望-庇护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创作风景画的艺术家会偏好这样的风景,应该描绘一条确保人类安全地抵达庇护所的路径。这条路径还需要视野开阔,风景优美。
对于第一个预测,奥利恩斯一方面实地考察非洲热带稀树草原以金合欢为代表的树木的特征,另一方面依据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来做出预测,然后测试现代人对树干高低度、树冠分层以及树冠宽广度的审美偏好。对于第二个预测,奥利恩斯则搜集了大量中西方的园林资料、风景画进行深入的量化、质性分析。这样严谨、深入且大量的实证研究为他的理论假设,进而为他对情感和审美偏好的解释提供了坚实的经验证据。同样对于食物口味的偏好,他和他的合作者搜集了全世界上百份来自不同地区的基本菜谱,进行深入分析。
不过,他的这种实证研究似乎没有贯彻到所有的话题之中。例如在第八章对音乐的起源讨论中,他认为性选择在音乐起源中起了重要作用。讲到音乐表演时,为了支持现代社会的音乐创作活动支持人类音乐性选择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音乐表演主要是男性进行的,而女性是观众。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早期现代音乐表演的确是男性为主,但观众也是男性为主。而在中国湘西,山歌是男女互动的重要方式,在性别比例上并没有差别。而且,现在进行音乐表演的男女比例上趋于均等,这似乎反驳了他一开始所支持的观点,即就像恐惧一样,音乐这样看起来是后天习得、深受文化传统影响的活动实际上是人类祖先在非洲热带稀树草原上适应的结果。文化的发展不应该过于影响从事音乐表演人员的性别比例。在讨论发声能力可以为繁殖带来优势时,竟然只是引用了美国摇滚明星吉米·亨德里克斯这个个例来说明。这样的证据对于他想支持的理论来说,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在演化生物学中,适应度是指种群平均后代的数量,而不是某个个别个体所繁殖后代的数量。
即便有这样稍微显得不严谨的地方,奥利恩斯的研究仍然为我们熟悉的现象提供了新颖且更符合直觉的解释。无论是对不同风格的园林共同模式的深入分析,还是对食物口味偏好、对香料偏好的分析,抑或对嗅觉的解释,都富有洞见,竟然让我们感觉耳目一新。大的方面,奥利恩斯对审美偏好的分析直接冲击了我们传统对美的理解。一般认为,美是深深置身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的;美是带来了纯粹的愉悦,与兴趣、利益无关。而奥利恩斯的研究则表明,在演化史上,审美偏好与人类的生存、繁殖的成功紧密相关。审美偏好与适应度协同演化。此外,在很多具体现象的重新解释上,也让我们获得了新的理解。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在第七章对食物口味偏好的讨论中,奥利恩斯用一小节重新理解了孕吐。传统认为孕吐是病理性疾病,因此人们想方设法来压制这种反应。不过,从演化生物学上来看,孕吐是一种适应性反应,可以提高人类的适应度。孕吐仅仅停留在怀孕的前三个月,因为在这段时间,发育中的胚胎最容易受毒素的影响,也是主要器官形成的时期。因此,孕吐可以保护胚胎受到可能毒素的影响。而且孕吐与食物中荤素的比例有密切相关性。
虽然这本书是以解释情感与审美偏好为主,但奥利恩斯并不是纯粹“为了研究而研究”,仍然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他在书的最后一章着重论述了理解我们情感与审美偏好的演化起源,对于重新理解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城市环境设计、人类行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任何对演化心理学、行为生态学、环境美学或者园林、食物、音乐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有所收获。
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收获是指读者去读英文原著可以获得的,而不是中译本。由于不好的翻译和编辑,这让原本集科普和专业研究为一体的原著有变成廉价畅销书的风险。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这本书的中译本存在的问题在译著中相当普遍。首先是翻译的文字表达。该书英文原著的一大特点是,文风朴实直白,通俗易懂。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阅读这本书就好像我们悠闲地在博物馆或者公园散步,让人心情舒畅。但中译本前半部分的翻译却过多地使用成语或者四字词语进行意译,朴实直白的文风夹杂着华丽的四字词语,就像熟米饭中夹杂了很多生腊肉。虽然是肉,但硌牙。或者,就像我一个朋友所说的,太多的成语把书变得啰里啰嗦了。这种对科学著作意译的做法实际上在中文译作中并不罕见。我仍然记得大学时读到的一本科学著作,与英文原版对照时便发现很多专业知识点中译本全都以文学化的语言进行了意译。这样做,不仅丧失了原意,也让科学原本的严谨消失不见。对于科学著作的翻译,我一直认为,不借助炫技式的意译,忠于原文的朴实直白翻译同样也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美感。此外,有关键词汇前后翻译不一致。作者引用吉布森的生态心灵理论中的关键词“可供性”(affordance)来作为他理论假说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该书在前文将该词翻译成“给养”,在最后才将之翻译为学界通用的译法——“可供性”。如果读者不熟悉这一背景,会不理解“给养”的含义,也无法把前后联想起来。
其次,中译本的《蛇、日出与莎士比亚》并不能说是全译本,只是删节本。中译本大量删除了原文中用于配合理解文字的插图、注释,把参考文献和索引全部删除。插图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可以帮助读者直接理解文字的内容,比如园林部分、涉及非洲土著文化的部分、不同文化传统的部分。一旦删掉,会让读者理解的难度增加很多。本书对注释的处理更让人费解。如中译本的前两章,译者还细心地将注释和参考文献都翻译成中文。注释中的说明确实有必要翻译,但参考文献中是标题不但没必要翻译,而且翻译后会严重损害参考文献的功能。参考文献的目的是让读者按图索骥,找到相关参考文献。一旦翻译后,这就让读者很难找到参考文献的准确题目,导致读者很难定位这些参考文献。当然,更不能让人接受的做法,是把所有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删除。一本专门著作,不是孤零零地存在着的一个文本,而是处于一定学术生态之中的产物。我们要想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它,就要理解它所处的生态位及生态环境,而参考文献和注释就是重要线索。另一方面,这让想更深入了解这一领域或话题的读者也无法直接找到进一步阅读材料的线索。一本著作本身也是一个小生态系统,而关键词索引就是一幅精确地图,可以帮我们快速确定关键概念在著作中所处的位置。删掉了索引,同样让想要快速定位相关概念位置的读者抓狂。删除注释、参考文献和索引的做法在国内中译本的出版中相当盛行,这严重损害了我们引进西方高质量著作的工作。翻译非易事,但要想做好翻译,这个“懒”还是不能偷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