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王宏图:写小说是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确认
今年8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的最新长篇小说《无所动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无所动心》聚焦都市男女的俗世情欲。
这是王宏图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教学和研究才是他的主业,但他一直将小说创作视为自己的爱好,或者说一种内心需求的表达,以及自我意义的确认。
“写《无所动心》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内心盘桓的焦虑情绪的一次宣泄。”王宏图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当今物质产品空前丰富的消费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众多的诱惑,内心原有的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此时此刻,如何保持内心的平衡,不让自己的生活滑入不可控的弯道,便成了每个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我觉得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面临这一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叙写的不仅仅是我个人一己的情感,也折射出许多人共同的心声。”
在新书出版之际,王宏图就小说创作、“教小说”“评小说”“写小说”之间的关系、阅读对写作的影响、高校创意写作专业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
【对话】
创作和研究,好似渐行渐远的孪生兄弟
澎湃新闻:《无所动心》是你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这么多年,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小说创作?
王宏图:最初的动力恐怕还是幼年时的文学梦。和许多报考中文系的学生一样,我在读中学时便想当一名作家,曾起愿这辈子要写部长篇小说。我倒并不是觉得能做一个作家比做一个学者高明,而是内心的情感意绪无法在学术著作和评论文字中得到释放,无法获得圆满的自我价值确认。
因此,在长年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期间,我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创作的念想。开始是写中短篇小说,2004年起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起先我对自己能否顺利完成一部长篇作品并没有充足的信心,但写作过程很顺畅,远远超出了我先前的预想。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十余年间又写了《风华正茂》《别了,日尔曼尼亚》《迷阳》,还有就是《无所动心》这部新作。

《无所动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新近出版
澎湃新闻:包括你在内的不少大学中文系教授、批评家写起了小说。从你自己的经验来说,大学教授与批评家的身份,会对小说创作带来哪些影响?
王宏图:大学中文系老师或批评家创作小说,其实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在中国新文学初期,不少人兼有作家、批评家和教师多重身份。这类小说在人们眼里常常或多或少地带有书卷气,很多以知识者的生活作为叙述对象,在语言更为考究,有时还会渗入哲理的思索。它们为小说园地增添了新的变种,有利于小说艺术拓展自身的疆界。
文学研究和创作毗邻而立,仿佛没有比它们关系更紧密、更亲近的。但实际上,它们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在起跑线上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在日后便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轨道前行,渐行渐远,难以找到交集点。
这种情形其实并不奇怪,文学创作依恃的是丰沛、敏锐的感受力,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对语言别具一格的运用,以及在虚无中创造一个坚实的世界图景的综合能力,这主要体现在虚构作品的创作中。而文学研究则走的另一条路径,它当然也需要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但并不是运用到自身的创作中,而是作为研究的前提条件之一,理论分析的目光,文学史的视野,以及其他相关历史、哲学知识素养对一个合格的研究者来说同样必不可少。
澎湃新闻:那么,“教小说”“评小说”会与“写小说”发生冲突吗?
王宏图:要在你说的“教小说”“评小说”会与“写小说”间游刃有余,有很大的难度,这涉及到复杂的角色转换。教师面对的是学生,批评者面对的是同行和广大读者,而“写小说”更多是独自一人,尽管有设定的潜在读者,但在创作过程中还是孤独一人在不懈地探索。这种角色有时并不成功,但我会努力适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无法评论自己写的小说。
当代都市生活中某一类人的写照
澎湃新闻:你之前的不少小说都格外关注人的欲望,还有专著《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这次怎么想到要写《无所动心》这样一个故事?
王宏图:我的学术专著《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成,它选取了20世纪中国一些都市叙事文本,对隐匿其间的欲望运行的轨迹作一番探索。至于说创作《无所动心》的灵感契机,那还是在快完成前一部小说《迷阳》时产生的。《迷阳》也是聚集都市人的欲望,对父与子间的代际冲突花费了大量笔墨。一次,望着快完成的《迷阳》,我忽然想到还可以写一部新的小说,写一个人罹患了癌症后的种种情状。
这似乎成了常态,我常常在写作一部小说后半部时,便不知不觉地在构想一部新的小说。或许每部作品都是不完美的,因而总有新的东西可以表述。在写《无所动心》下半部分时,我也萌发了新小说的构想。它如新生命的胚芽,在你体内随着时光推移日长夜大,等成熟之日悄然分娩。
澎湃新闻:当你又一次聚集都市人的欲望,为何取名“无所动心”?
王宏图:如何能超越在众多欲望的诱惑之上,这是一个棘手的伦理学问题。书名“无所动心”(ataraxy)源自古希腊语,原本是医学名词,意为心气平和,心神安定。后来斯多噶派哲学家借用了这一词语,标示一种不受外界环境干扰的宁静心境。这当然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境界,人活在世上,只要一息尚存,很难不受各种外界因素的刺激而生出纷繁的思虑,所以欧阳修在《秋声赋》感叹道:“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
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徐生白也是这样,作为一名作家他在文学界拥有盛名,却自感江郎才尽,心绪颇为烦乱。他在《庄子》等书中寻求精神慰藉,力求在纷乱的世界中达到无所动心的境界。在查出患上了癌症后,徐生白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与妻子、父母间的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女儿不顺心的婚事也让他不安。此后他又在癌症康复俱乐部中与病友陈玫君生出情感上的火花,过后又与画家朋友俞日新的模特刘娅玲陷入情感漩涡。这一切都没给他的心灵带来安宁,最后他还因集资案受牵连,历经沧桑。到全书结尾,他也没能达到无所动心的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无所动心”成了对徐生白个人生活的巨大反讽。
澎湃新闻:徐生白有人物原型吗?你对这个小说人物充满了怎样的情感?
王宏图:徐生白这个人物是我倾全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对他有几分偏爱也是常情。他的名字也来自《庄子·人间世》,原文如下,“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大意如下:如能把眼前万物视为空无,就能让自己心境空明而发出纯白之光,吉祥就能会集于虚明之心。“生白”作为人物的名字,与书名“无所动心”恰好对称,它是人们有幸臻于无动动心的超凡之境后的状态,心无尘染而衍射出洁白的光焰。徐生白最后并没能发出他孜孜以求的纯白之光。
尽管有偏爱,徐生白这个人物并不是完美的,他身上有许多弱点,令人叹息扼腕,我对他被欲望裹挟而不可自拔怀着一种悲悯之情,我们和他一样,在生活中同样不完美、脆弱不堪。在一定程度上,他成了当代大都市生活中某一类人的写照,他们功名成就,衣食无忧,但时常为欲望所困,无法迈入澄明的超凡脱俗之境。
他并没有以通常所说的生活中的原型人物为蓝本。好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一位著名作家去加拿大探望在那边留学的女儿。这启发了我构思出了小说的情节轮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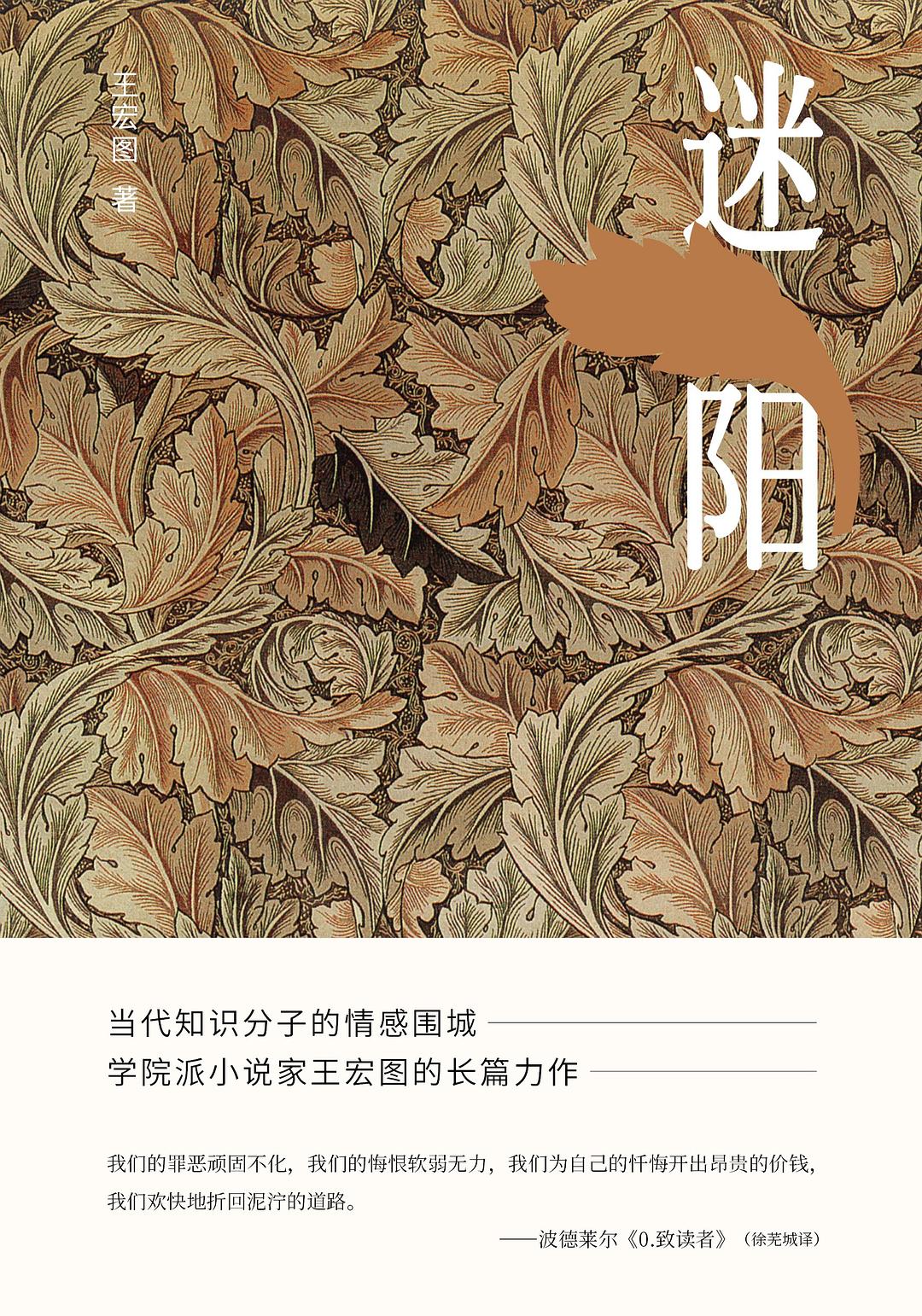
《迷阳》
贯穿全书的“副文本”
澎湃新闻:包括你自己的作品在内,此前已有不少小说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你希望《无所动心》在哪些方面写出新意?
王宏图:的确,自20世纪以降,有关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可以列出一长串,从鲁迅的《孤独者》郁达夫的《沉沦》叶圣陶的《倪焕之》到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还有前几年问世的李洱的《应物兄》。我自己希望徐生白这一形象能鲜明地展示出当代知识者的精神世界,更富有时代气息,不加伪饰地袒露内心复杂多变的矛盾冲突。同时,我并不是将他置于一尘不染的真空环境中,而是在他与家人、朋友与情侣的关系中多侧面地塑造这一人物。
澎湃新闻:具体到《无所动心》的写法,全书二十多章,每章以《易经》中的卦象冠名,各个卦象间联结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怎么设计出这样的小说结构?
王宏图:我有一个时期曾花时间研读过《易经》,最终并没有入门,仅得几丝皮毛。但它在我眼前展现出一种与近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科学观全然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在现代人眼里它无疑带有迷信的成分,但也那么神秘莫测,远远超出了人们现有的知识领域。
我在这部小说中以《易经》中的卦象为章节命名,很大程度上有游戏的成分。每个卦象与所属章节间的情节有着模糊含混的对应关系,形成一种“似花还似非花”的朦胧效果。20多个卦象间联结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交错缠绕,相互映射。读者可以感受到卦象指示的情节推展的趋势,但无法精确框定。
从文本效果看,这数十个卦象其实组成了一个贯穿全书的副文本系统,它借用了远古的卦象卦辞,自成一体,与正文叙写的繁复多彩的当代生活,与运用的诸多西方文学技法如意识流、有限视角等形成一个对照,增加了文本层次的丰富性。
澎湃新闻:小说也采用了“书中书”,将徐生白正在写的一部民国小说《大江东去》“嵌套”在这部当代作品里。有意思的是,《大江东去》充满了叙事雄心,希望能“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尽收其间”,它所追求的宏大和《无所动心》对特定时期人内心世界的幽微探寻似乎正好是相反的。“书中书”的设计背后有着哪些用心?
王宏图:因为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徐生白是一个作家,描绘一个作家的生活常常绕不开他的创作。“书中书”的套嵌手法在当今的小说创作中其实并不新鲜,你可以在很多作品中发现。和使用卦象作为章节的标题一样,这一套嵌手法也是为整部作品增加了一个副文本。而且这个副文本和正文的视野和旨趣大不相同。小说正文聚集的是当下的生活,缺乏厚重的历史感和纵深的视野。加入了徐生白创作的《大江东去》这一副文本作为“书中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正文的一种补充:它力图涉及20世纪中国几代人在历史风云变幻中的曲折命运,地理空间上也不再局限于上海或那不勒斯,而是从中国到北美,横跨太平洋。此外,它也是徐生白创作生涯中的一次自我超越,从纯情、浪漫主义的创作转向更为宏阔的史诗性追求。
现实经验与阅读经验的平衡
澎湃新闻:从《无所动心》也可以看到你丰富的阅读积累。能谈谈你的阅读偏好吗?
王宏图:我的阅读,它分两类,一是较为正统的阅读,它与我的小说写作有着密切的关联。早在上大学期间,在接触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后,我心中便萌生了这样一种理想,想将细腻逼真的写实手法和以展示人们内心无意识奥秘的意识流技法相结合,熔铸出一种新型的写作风格:它既栩栩如生地表现外部世界,又不滞留于表象,而能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中探幽烛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设想太过幼稚,也太理想化了,有想把一切好事占全的贪心。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在创作追求上的折中倾向:即便在刻意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时,我也没有忘记为他们安置一个现实的背景,一个有着相对清晰轮廓的舞台。这一切创作的构想和实践是建立在大量作品阅读的基础上的。
从个人趣味而言,我偏爱法国文学。就学期间修读过法语,我可以较为顺畅地阅读法语作品的原文,蒙田、帕斯卡尔、福楼拜、普鲁斯特、莫里亚克、萨特等人的作品我都读得津津有味,而且不知不觉间在我自己的写作中烙上了难以抹去的印记。按照辜鸿铭的说法,法国的语言文化有一点与中国很相像,那就是那种精美雅致(delicate)的情趣,这是英、德等民族所匮乏的。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李商隐,最钟爱的小说是《金瓶梅》。从文学史看,没有《金瓶梅》就没有后出的《红楼梦》。人们初读《红楼梦》,除了宝黛的爱情外,会对作者对日常生活不厌其烦的精细描写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它并不是《红楼梦》的独创的,很多手法在《金瓶梅》中已初试牛刀。此外,《金瓶梅》虽然从总体色调和氛围上不如《红楼梦》高雅,但它对社会各阶层人物和人的欲望的展示深度超过了《红楼梦》,洋溢着一股蛮野的生命力。
除了文学,我还喜欢读一些哲学类著作,德国的叔本华、尼采等人我一度都很入迷。还有就是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书。
我也会看一些闲书,主要是外国的侦探推理小说。阿伽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读了有20多种,日本的东野圭吾也很让我入迷,在今年上半年疫情封控在家时断断续续读了不少,加上前些年读过的《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也有20来种。东野圭吾的写作受松本清张的影响很大,我接着又读了松本的十余种小说。他的作品社会性很强,在侦探故事的框架内栩栩如生展现了一幅二战后数十年间的社会风俗画。而以“证明三部曲”享誉文坛的森村诚一将松本的传统光大发扬,为社会派推理小说拓展出新的境界。
澎湃新闻:你的写作和你的阅读有着怎样的关系?在写作中,有的作家更偏重现实经验,有的作家更偏重阅读经验,你理想中的写作是怎样呢?
王宏图:应该说我的写作与阅读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没有阅读就没有我的文学写作。这种情形不是孤例,很多作家都是这样。但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在写作中偏重写作经验。很多写作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窘境:写作的素材有了,各种技法也是现成的,但就是写不出来,欠缺了一点火候。实际上那是因为写作激情的匮乏造成的。而写作的激情难以从单纯的阅读经验中获得,它更多是从现实经验中孵化、衍生而出。
我的写作不少地方有书卷气,但这并不能说我就是一个偏重阅读经验的写作者。或许和很多作家相比,我作品中世俗生活的气息不浓厚,人物和场景不够丰富多样,但我更多地关注的是人物内在的精神生活和感受。对人们内在世界的感悟也是现实经验的一部分,不能把现实经验狭隘地局限于外部的有形世界,它包括内与外两个维度。
我理想中的写作应该是写作者有着丰富的现实经验,同时有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手段将它们展示出来,而后者大多来自于先前的阅读经验。这两者之间要保持某种平衡,偏执于一端会导致作品文本出现醒目的缺陷。
澎湃新闻:写小说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王宏图:写作小说对我而言,是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确认。人生如白云苍狗,倏忽而逝。能将短暂的生命中遭遇的或宏大或细琐的影像,涌现的色泽各异的体悟,深陷其间的情感困局一一落到纸页上,凝固为文字,构筑起一座声色俱全的艺术品,不失为一种升华。发生的一切都会逝去,化为烟尘,而纸面上结晶化了的文字超越了个体的生命而长存,给人以启迪与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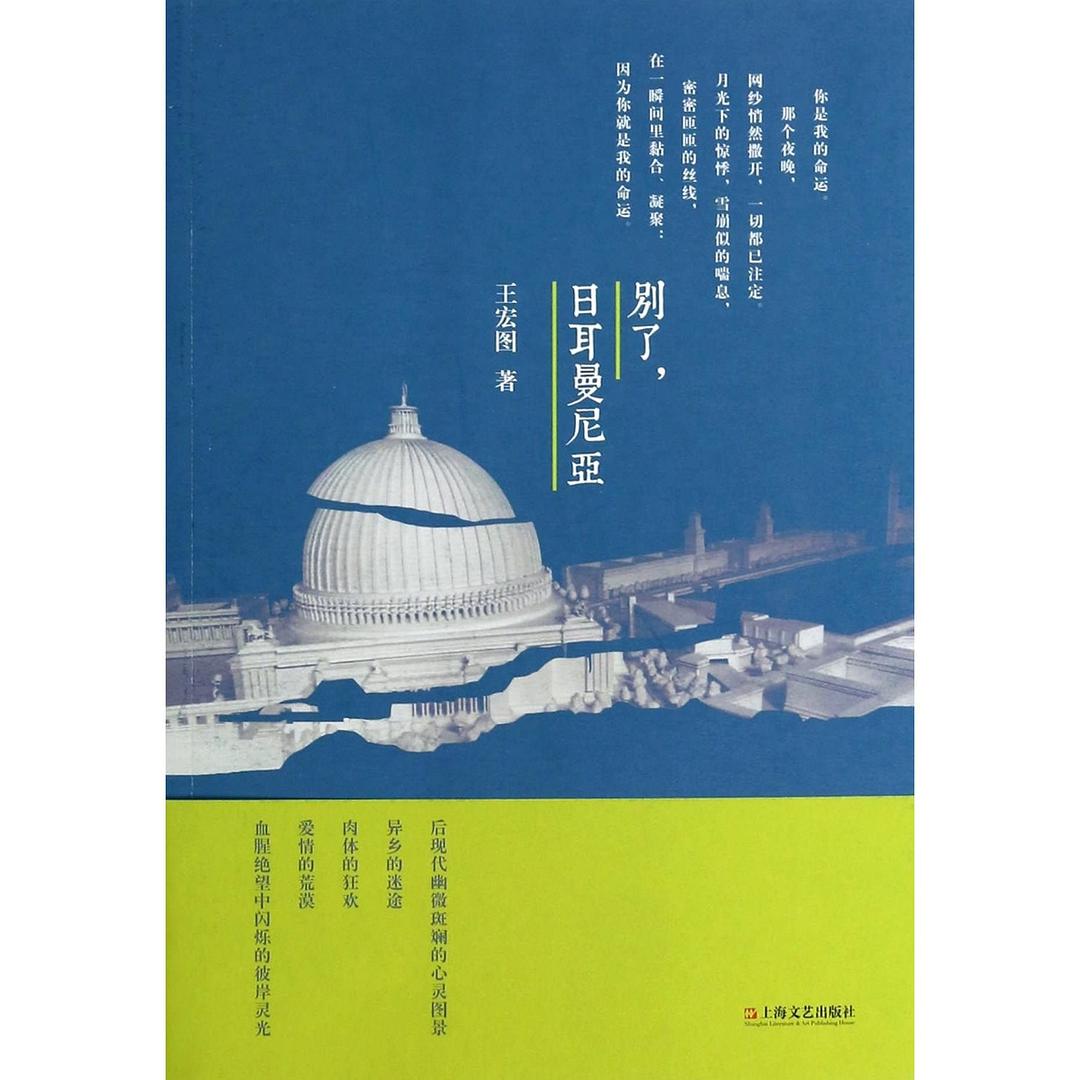
《别了,日尔曼尼亚》
文学写作部分可教
澎湃新闻:你目前的主业是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老师。“创意写作”作为一个专业在国内落地生根也有十多年了,但业界关于这个专业依然有很多争议,比如它是培养作家还是培养“写作产业工人”?它是让文学更专业化还是更大众化?你认为开设这门学科最重要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
王宏图: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MFA)经教育部批准于2009年成立,2010年正式开始招生,迄今已有十年之久。其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也开始招收创意写作专业的研究生,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北大学在更早的时候便在本科阶段设立了写作方向。十余年来,创意写作专业在国内高校中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据我所知更多的学校在积极筹备成立这一专业。
“写作能不能教”是一个老问题,从创意写作专业设立起便是不绝于声。现在创意写作专业主要在英语国家和东南亚地区、中国港台地区生根发芽,而在欧陆国家大学中还难以找到发展的空间。恐怕人们也是觉得写作无法真正有效地教授。这一问题我只能说文学写作部分可教,譬如语言运用的能力,情节设置和结构安排,对以往作品的借鉴,这些大多是技术性元素,但创作的内在心理动力和灵感,敏锐的感受力,这些的确没法教,其实也不用教。
澎湃新闻:在录选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新生时,什么样的学生会让你们感到眼前一亮?
王宏图: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大多是那些富于艺术家气质的考生,他们的言谈举止神情充满了灵气。或许他们先前的学习积点不够高,或许他们还没有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但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们内在的创作潜力,这反映在他们是否对世界有独到的理解和态度,语言表达是否真实地传达了内心的体悟。和这些灵气满满的考生相比,有的写过一些甚至发表过作品的考生,如果他们的文本显得平庸,缺乏让人耳目一新的出彩之处,我们就不太看好他们的发展潜力。
澎湃新闻:你认为要成为一名好小说家,哪些能力是最重要的?
王宏图:要成为一名好小说家,首先得有对生活细腻的感受力和观察力;同时他还得能将这种艺术的形式赋予从生活中汲取的杂多素材,将它塑造成一件完整的艺术品。这些要求也适用于诗人和写作非虚构散文的作家,而小说家在此之外,还需要设置人物和情节展开叙述,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此外,语言表达的新颖与个性化,进而形成可辨识的独特风格,对一名好小说家也不可缺少。

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MFA)课堂之一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