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谈|金雯×赵松:“我们都是马克洛尔”
【编者按】
9月24日,第二届“西葡语文学月”的活动之一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金雯与作家、评论家赵松,围绕哥伦比亚作家阿尔瓦罗·穆蒂斯的长篇小说《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一书进行了主题为“我们都是马克洛尔:用不断失败将人生过得波澜壮阔”的线上对谈。
长篇小说《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由七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人物叫马克洛尔,他是一个瞭望员,在整个小说里从出场到最后,都像是一个没有来处也没有归处的人,常年漂泊在海上。该书作者哥伦比亚作家穆蒂斯,早年写诗,19岁就以诗人的身份成名。马尔克斯对他的评价很高。

《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
本文为该活动对谈内容精编,澎湃新闻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稿整理摘编,并经主办方授权发布,以飨读者。
金雯:本书是由七个小说组成的小说群,也可以认为是一个长篇小说,这七个部分是有内在关系的。马克洛尔这个人物贯穿始终,随着时间演变有所成长,而不是非常随机地出现在七个不相关的故事里。因此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比较松散的“虚构的传记”。作为传记式的小说,它又非常不传统,因为对这个人物的传达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有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但是没有那种对来龙去脉非常仔细的铺陈。七个部分虽有时间上的关联,却不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的。比如说马克洛尔之死在整个长篇的中途就揭示了,好像是同自己在最后时刻相爱的女人死在航行途中的船上,这可以说是对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结尾的重写,践行的是《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所出现的非常诗意的一幕,在船上飘荡到最后一刻。
我感觉当一个读者初次进入这个书的时候,可能会感到一些疏离感,因为毕竟里面的情节线条不是那么清晰,马克洛尔也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物,一开始进入肯定会有一些阻力,我本人也是。但是对这个作品了解多了,沉下心来看了一部分之后,就会发现七部作品还是能够组成一条若隐若现的线条的。
更有意思的是,马克洛尔这个人物虽然很难概括,他的经历也好像是包裹在一层迷雾当中,但他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魅力,就像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最神秘、最难以进入他内心、却非常有魅力的人那样。他时时刻刻把你挡在他的世界之外,可大家还是对他有些兴趣。这是我对这个作品的一种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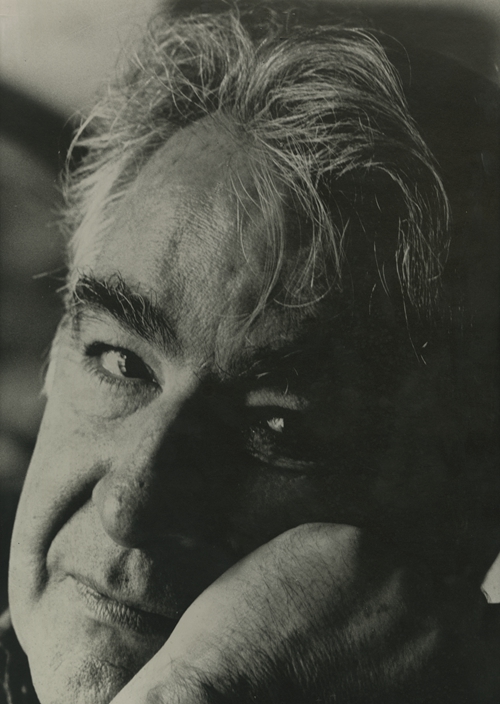
阿尔瓦罗·穆蒂斯©摄影师LM Palomares
而且这个人物跟作者穆蒂斯之间,既有相似的经历,又有非常鲜明的反差。这也是作家创作当中非常独特的一面,就是怎么样把自己隐藏的一面投射在他的人物当中,但同时又映照到自己在事实层面的、表面的经历。所以我觉得马克罗尔跟作家的关系也挺有趣的。
赵松:我对穆蒂斯有一个很奇怪的记忆错位。看到《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译稿时,我才忽然意识到,这个穆蒂斯,就是当初马尔克斯在回忆胡安·鲁尔福时提到的那个穆蒂斯。为了表达鲁尔福对他的重要性,马尔克斯讲到自己那时候寄居在墨西哥城,已经出了四本小说了,在圈内小有名气,但是圈外则没什么反响,其实很迷茫。有一天,穆蒂斯去他家,塞给他一本书,说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吧。这本书就是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马尔克斯说他后来几乎能整段地背诵这本书的内容,并且在它强烈的震撼下真的开窍了。实际上在之前的几本小说里,他尝试过很多写法,但一直都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式——那种在西班牙语拉丁美洲的语境下,有着浓郁哥伦比亚本土气息同时又能很好地转化欧美现代小说技艺的方式。所以那时候,我就记住了穆蒂斯,但是我完全没记住穆蒂斯是做什么的,甚至以为是个编辑、记者之类的。直到在《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的译稿里,看到了马尔克斯为穆蒂斯七十大寿写的那篇致辞,我才把这个穆蒂斯同“那个穆蒂斯”对上了号。穆蒂斯跟马尔克斯是终身好友,这个关系里肯定包含了对文学的共同热爱和相近的价值观和彼此的长期认同。穆蒂斯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也是非常奇特,就是直到他退休后开始写《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之前,他都不是职业作家。
金雯:他是一个有职业的作家,但不是一个职业作家。
赵松:对,他一直在上班,不是在一些跨国公司就是在什么机构,经常在海上,要去出差或者旅行。说白了,他就是一个要忙忙碌碌去上班的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跟他那些以写作为生的穷朋友比起来,可能算是活得比较好的。
但我完全可以想象,穆蒂斯看着他的朋友们冉冉升起,成为著名作家,这对他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能持续专注于写作的状态,对他来说肯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马尔克斯一直在追问他,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你想写的书写出来呢?他说退休以后吧。人们会以为他就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退休以后,真的花了6年,把这个《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写出来了。包括马尔克斯在内的朋友们都很震惊,在马尔克斯看来,这就好像是从飞机上跳下来直接平稳落地一样。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到了退休后,按理说应该到创作的晚期了,很少还会在创作上有这么强大的爆发力的。
真的把这部《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从头到尾读起来,我还是挺意外的。因为穆蒂斯和同时代的马尔克斯、略萨这样的作家很不同。那些作家面对欧美强大的现代主义和19世纪小说传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与变化,穆蒂斯的回应显然要晚很多,当年那种激进的、追求创新的拉美爆炸文学已经慢慢消退了,不再以追求新奇或者去抗衡什么为目的了。
我也在想,为什么马尔克斯会说“我们都是马克洛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看完以后,发现《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是一部拼贴画般的作品,七部的手法都不太一样。穆蒂斯会根据人物的经历做出写作手法上的相应变化,这些变化细细比较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在拉美文学语境里,穆蒂斯首先是个著名诗人。在《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里其实不难看出,尽管经过翻译,但仍然能感觉到他很注重诗意气氛的营造。看他的叙事过程会发现,事件本身的推进并不快,也没有发生很多复杂的情节变化,但这个充满诗意的气氛一直弥漫着,从头到尾你会觉得有一种气息在你脑子里停留,马克洛尔就像一个声音一样,就在徘徊萦绕着你。所以我觉得,阅读这种小说,更像是一种体验的过程,而不是仅仅要解读人物的命运或者故事情节,这种体验是有某种强烈的代入感的。我也觉得马克洛尔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他没有背景,更像是一种缺乏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为什么马尔克斯会说“我们都是马克洛尔”呢?马尔克斯在晚年说出这句话,我觉得是有某种指向性的,指向了他们那代人。在获得写作上的成功之前,他们在年轻时都吃了很多苦,经历过很多波折,但是在老年时回头看,会觉得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可能正是他们人生中最快乐难忘的时段——那种充满未知感的青春燃烧的年代,那些梦想、幻想、奇怪的想法和经历都是非常可贵的。反倒是成名之后,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被很多东西框住了。马尔克斯就很典型,再也不能随便乱跑了,再也不能乱讲话了,随便批评谁了。总会有记者来采访你,你得小心翼翼,以免被别人断章取义地攻击你,你的政治立场也会被人反复地强调,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为此甚至原来是好朋友的也会反目,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了。
我觉得马尔克斯看到穆蒂斯的这本书时,一眼就看明白了穆蒂斯要干什么。穆蒂斯就是要写一个永远不带有任何目的性的四处游荡的人,充满了不确定,生活不确定,感情也不确定,家庭也不确定,因为一确定就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固化。
穆蒂斯写的是一个无目的性的人物。之前的很多作品,无论是康拉德的还是麦尔维尔的《白鲸》,都是有很多大场面和冒险经历的,都在某种目的牵引下推进并贯穿起经历和命运的。但是你在马克洛尔这里看不到这些,他没有什么目的,就那样出发了,至于说会发生什么,他也不知道,就是不断地面对偶然和意外。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很强烈的特点,避免可以计划、可以预设的有逻辑性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结果是某种死亡,他其实就是要避免死亡,避免那种把人固定在某个地方、某个确切的身份上、一切都很清楚的可能性。或许在马尔克洛看来,只有这样,人才是不死的。这部小说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运行的,马克洛尔不断地出发,没有目的,没有家,也没有亲人,直到最后他好朋友巴舒尔的私生子出现时,他有了一点变化,对那个孩子有了一种温情。所以我称《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为体验型的小说。
金雯:对,这是一种比较神奇的体验,一种悬空式的体验。在阅读的时候就像马克洛尔一样,能感到没有根的、在海上漂着的状态。这本书跟之前的那些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代的小说有很多的关联,而且它是很明显地在向之前的作家致敬。
就像他这里面的第一部《阿尔米兰特之雪》,最初是以散文诗的形式出现,后来经过修改扩充成为这部小说,是很明显地在重写康拉德的《黑暗之心》,讲马克洛尔是怎么样沿着一条河流往上,要找到一个神秘的木材厂,就像在《黑暗之心》里面马洛要找到库尔茨那样。就像马洛有一个目的地,要去揭开黑暗之心——殖民地经济运行的中心——的秘密,找到是谁在掌管着殖民地的经济,产生着利润和价值。但马克洛尔比起《黑暗之心》中的马洛的确是少了很多目的性,也就是他不是专门要去寻找一个秘密,他也没有肩负一个任务,只是去谋生,是被所谓生命最基本的需求推动着的,他就是一个漂泊在世界上的打工人。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19世纪的《白鲸》,麦尔维尔的小说和马克洛尔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捕鲸船上有各种不同的种族,有白人、有黑人,也有印第安本土人,他们构成一个水手团队。他们是那些背叛了自己所谓的民族或文化之根的人,也是那种被遗弃的人,很边缘的人。他们是美国在进行帝国扩张时期所需要的经济引擎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洛尔就是这样一个人,就像《白鲸》中的那些人,没有任何社会网络,是被孤立、被遗弃的人,是流浪的、在整个全球化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底层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的确是没有目的性的,是被所谓的全球化的经济浪潮所裹挟,哪里有一点生存机会,他就到哪里去。在七个故事里,他都是被动地被招募去做跨国公司的公关,或者去运输木材,他总是在四处流散,去任何有雇佣工作机会的地方。
这部小说里,殖民时代的痕迹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看到的,虽然已经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全球经济仍然被某些强势的经济中心或力量所垄断。书中写到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要去摧毁所谓全球资本主义在全球各地散布的触角。书中有对全球资本主义有很多非常模糊的指涉,同时也有反抗这些资本主义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有要运输炸药去摧毁资本主义堡垒的那些革命者,这也是他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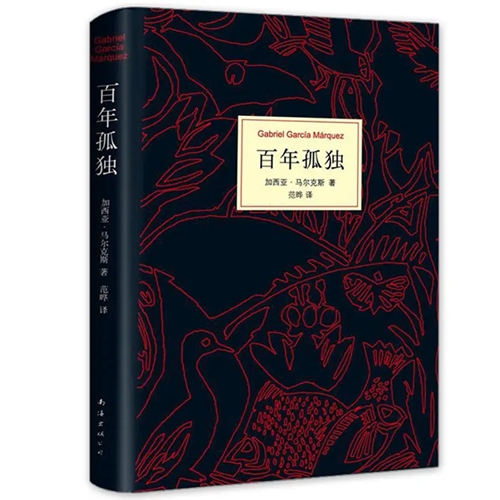
这里面无根的马克洛尔实际上就是《百年孤独》里被困在了马孔多村庄里,但始终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孤独的人物的镜像。马尔克斯讲的是完全孤立的南美村庄,相反,孤独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虽然不会被限制在一个地域中,却无法停留在一个地方,建筑起比较稳固的社会结构。就像在马尔克斯小说里那些不断流浪的吉普赛人,他们的足迹是遍布世界各地,被全球化经济的浪花所携带。这种孤独就使得这个人物始终处于迷雾当中,在一个气泡里面,周围的人——我们读者——很难参透他的内心。因此,马克洛尔的孤独也和《百年孤独》当中人物的孤独非常相近。
他在七个故事里不停地更替女伴,短暂的情感联系之后就进入下一段关系,就像《百年孤独》里的人物,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事情,用这样的方式来持守孤独。马克洛尔并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他同第一个女伴分离的时候,也会感到非常痛苦,他不断同这种可以称为人之常情的感情作斗争。所以这个作品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可以联动起来看的,他们都是关于人在不得不孤独的时候,在受迫于历史境遇的压力下不得不孤独的时候,如何想象一种面对孤独能够坦然生活的方式。这实际上挺悲情的,因为即使是像马尔克斯和穆蒂斯这个年代的作家,在欧洲似乎找到了自由的时候,也有一种极度的虚空感,一种虚无感,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什么地方,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文学传统。
这种强烈的不属于任何地方的孤独感,是一种诅咒,但它可能也会变成一种财富。马克洛尔并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但他可能比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现实的人更加具有一种神秘的可塑性,可以把自己抽离,抽离出那些痛苦,让自己与情感之间的勾连不显得那么牢不可破。所以他在经历了不同的女伴之后,还是不断地投入到新的情感交流当中去,没有因此而放弃情感,但是也没有追逐一种比较稳定的情感。他学会了一种适合自己的同其他人发生勾连的方式。
他是一个在卑微处境下谋求生计的人物,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变成了我们可以想象的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人物。最最确切的一个类比就是堂吉诃德。纳博科夫对堂吉诃德有一个很经典的诠释,说他“从一种戏仿变成了一个典范”。的确是这样,这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戏仿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所勾勒的拉美人普遍的困境,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历史记忆的一种极致的孤独。但是马克洛尔从中升华出了一种新的生存态度,可以摆脱所有社会网络的羁绊,对所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些稳定的价值都不屑一顾的、近乎于神话般的新的生存态度和方式。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