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 +114
倪妮唱到哭的老歌,早该火了

这周广东的气温终于从30℃降了下来,一秒入秋。早晨打开窗户,仿佛能听到整个城市苏醒的声音,在秋天几近透明的空气中穿梭回荡,脑海中不禁响起了一首秋天的歌谣:
堤边柳,到秋天,叶乱飘
叶落尽,只剩得,细枝条
想当日,绿荫荫,春光好
今日里,冷清清,秋色老
这首歌名叫《秋柳》,在不久前上映的电影《漫长的告白》中,倪妮饰演的女主角阿川在异国的小酒馆里唱起了它,略带忧伤的曲调令人怅然若失。
倪妮演唱的《秋柳》
同为学堂乐歌,《秋柳》不比《送别》广为人知,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存在于老人的记忆中(他们当年在学堂学到了这首歌),没能被现代的信息技术记录、传播。而如今,有一群人正在进行着歌谣的活化,致力于将即将失传的童谣记录保存下来。
上个月,我们发布了一篇讲述的文章,从《秋柳》聊起,谈到对老人的关怀、音乐的凝聚力、线下人与人连接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日渐不确定的日常下去抵御非常——从艺术出发,最后落到了非常具体的生活提案。
在这个信息爆炸、线上生活甚至比线下生活更丰富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聚在一起唱歌呢?
这次访谈的四位嘉宾,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和生活经验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分别是寻谣计划的发起人小河,寻谣计划的设计师、97年出生的宇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寻谣计划志愿者的陆晔,以及寻谣计划的制片统筹美香。
以下,是我们的talk实录。

Q:寻谣计划的初衷是什么?
小河:从2016年到2019年,我们做了一个叫“回响行动”的艺术项目,想试着让音乐走出livehouse,走出唱片的模式,和观众以及音乐人们一起在自然环境中完成音乐会。
“寻谣计划”的一些形式是由“回响行动”延展开来的,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回到四合院,去寻找老北京以前的童谣。

"胡同童谣“音乐现场,老人和听众一起唱歌。
开始时我们只是觉得,音乐有更大的力量连接城市的各个角落、社会上不同身份的人,人们能在音乐的怀抱中更深刻地体验到彼此之间共振的美好。
实际行动起来才发现,老人,特别是城市里的老人,是一个特别应该被关注的群体。我们的志愿者都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从事的职业也不一样,但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交互是寻谣计划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年轻人和老人能有一个机会去连接,彼此收获不同的理解。
Q :寻谣是怎么进行的?
宇威:城市中的寻谣经常在公园中进行。公园里的老人很多,喜欢唱歌的、喜欢乐器的、喜欢跳舞的,都能很直观地看到;你很容易通过一个老人知道有另一个爱唱歌的大爷,深入老人的关系网络里去做记录。我们还会联系当地的文化机构和民间已有的收集者。

寻谣计划小队在公园。
美香:每个地点和不同的主办方们,都有各自希望达到的目标。比如古伦村,当地有很多侗族的老人会唱童谣,但一直没能有系统、有条理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当寻谣团队来到村庄,他们会分为几支小队,每一组会有一个寻谣前哨,搭配一位摄影师,志愿者则会带着笔记本和录音设备,挨家挨户登门去寻找。寻谣不仅是记录声音,我们会了解歌曲的故事,有时候也需要当地的志愿者来进行翻译。
Q:在众多音乐类型中,为什么选择童谣?
小河:最初是想做一个由声音线索串起来的城市记忆,当时就琢磨,关于老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记忆有哪些,除了红歌和戏曲之外,还有什么声音素材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能够记得,并且值得深挖的?渐渐地就想到了童谣。
本来胡同童谣是一个半年的项目,但越做越深后我们发现,不管是在现场还是通过视频传播,当老人记忆中的歌谣被再次唱响时,它们有着超出人们想象的凝聚力,能激发非常特别的情感互动。每个人都有童年,童谣这个主题能让不同年龄的人更快地连接起来,老人小孩都能产生共鸣。
宇威:我从小是缺失童谣的那一类人,家里的老人没有传家宝一样的歌谣唱给我听。我现在接触童谣,就像在获得一种新的视角。童谣提供了一种看星星、看月亮、看万物的新的方式,在听的时候,我可以对万物的形状进行再想象。
在童谣中,儿童的、大人的、老人的生长形态重叠了,所以我觉得童谣是很容易传播、很容易产生变体的一种媒介。它所承载和表达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副本,它是不同人、不同视角凝聚成的一个时光机器。
Q:记忆深刻的和老人之间的连接?
小河:每一个童谣背后都有一个老人,寻谣也是和一位老人发生连接。我们在北京找到的第一首符合条件的童谣《卢沟桥》,是由何大爷回忆起来的。何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我们后来处成了很好的朋友,时不时会联系,如果要离开北京了,还会专门去见一见这位大爷。

何大爷(左)和小河(右)。
在浙江金华我们认识了一位周奶奶,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好,走路都费劲,得坐轮椅。但我们执着地邀请她从金华来杭州参加音乐会,这背后也有一段故事。
原来周奶奶在年轻时是一位特别好的民歌手,一九六几年她来杭州参加民歌赛,还获得了二等奖。本来她要被推送到北京参加全国的一个民歌赛,但因为家里人的不支持而未能成行。这一晃就是60年,金华离杭州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但奶奶再也没有去过。
我们想着,60年前奶奶因为唱歌去了杭州,即使现在身体不如从前了,如果能帮助她去杭州再唱一次歌,那就太好了。于是我们就一直在努力,最后接奶奶去了杭州,圆了这个跨越半个世纪的遗憾。

周奶奶时隔60年再到杭州唱歌。
不久前到大元社寻谣,我们认识了一位瑶族奶奶,也让我倍受感动。
这位奶奶有些离群索居,住在离村民聚集地稍高的位置,平时村里老人井口边围坐聊天,都见不到奶奶的身影。村里人告诉我们,可以试试去找她寻谣,但奶奶能下来的概率很小。
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奶奶不愿意给我们唱歌,直到有一次,我和宇威死缠烂打地跟着奶奶去放牛,奶奶牵着牛走到了森林深处,突然开始唱歌了,那个场景让我特别感动。
她在村子里也许很难开口,但她会走到林子里,在一个特别放松、很美、很自然、很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她才愿意唱。后来我经常去“骚扰”这位奶奶,假装帮她干活,每天死缠硬磨,最后把奶奶和女儿都请了下来。
在最后的音乐会上,她们俩都特别害羞,但是又特别美,不管是歌声还是人。
跟随纪录片走进寻谣大元的故事吧!
Q:怎么对童谣进行筛选,哪些童谣适合被“活化”?
小河:被挑选出来进行“活化”的童谣值得被更多人听见,也有必要让未来的孩子听见。
我们在选择童谣进行活化时,通常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歌词的美感,一个是它体现了一些本地的文化,是对文化符号的连接和传承。
筛选童谣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听录音,一起讨论,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对这首童谣的感受和理解,为什么这首歌值得做活化。最后会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就去做。
在大元村,我们找到一首瑶族歌曲,孩子们根据村落的地理位置、村民的生活状况和他们之间的连接创作了歌词,填进曲子里。最后看见孩子们围坐在村里的空地上,合着曲子唱着自己写的词,唱着这首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歌谣时,我觉得非常非常美。
老人和孩子一起在田间地头歌唱。/寻谣大元音乐会为上海睿远公益基金会与寻谣计划联合出品。
Q:现在很多孩子都唱着大人的流行歌,童谣是不是消失了?什么样的歌谣是适合孩子唱的?
小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缺少音乐,音乐类型和数量都太多了,很多家长听抖音、快手上的歌,孩子们自然而然也就跟着听,但孩子们真正能喜欢的、实际能唱的的儿歌其实并不多。
童谣没有消失,但童谣中的诗意和美消失了。孩子是天真无邪的,他们的嘴里能唱很多大人觉得汗颜的东西。
比如《秋柳》。这首歌听上去有点忧伤,表达者似乎是属于大人的那种比较复杂的情绪。但对于孩子,他知道秋天的意象可以代表一种心境。给孩子听的歌,不应该全是傻白甜,全是幸福小花什么的,童谣可以探讨的话题可以有很多种,它可以带着一些启示。
童声版《秋柳》
我们教育孩子,总是想让他们回避失败,或是回避一些被认为不好的体验,但我觉得,当然要让孩子们知道,失败或是忧伤的感觉是正常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困苦、一些坎坷、一些挫折,要适当地体验这些,才是正常的。

Q:在这个流行文化快速更新迭代的当下,什么才算是好的音乐?
小河:这个时代不缺音乐,但音乐里最原始的或者说最好的那部分,是通过音乐的发生,使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消除、理解增进,有很多现实当中没办法沟通或是互相认同的障碍,可能会在音乐发生的那一刻改变。
在当下,很多东西有了功利性,音乐变成了职业,你需要靠它去赚钱,音乐变成了一个商品,它的社会功能性正在减弱。现在你要听音乐,不用去看音乐会,手机里就有很多唱片,你可以打开网络看任何东西。但它们是音乐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音乐的全部。如果我们在现场,有一个真正的人在演奏,或者哪怕你不会演奏,也能和表演者有一个音乐上的互动,那是音乐非常可贵的一部分。

寻谣计划上海站,大家一起唱歌。
音乐其实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行为,它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商品。“回响行动”也好,“寻谣计划”也好,我们把音乐当成了一个身体力行的行为,当我们参与到这个行为当中,那个通道就展开了,就像魔法一样。一旦寻找童谣的行为开始,一旦音乐发生,人与人之间连接的通道就已经建立,已经打开了。所以说音乐不只是听一下歌或是看一下视频,它是整个身体力行的过程。
Q:“寻谣计划”被定义为公共艺术项目,怎么看待这个“公共性”?艺术家怎么进入公共生活?好的公共艺术是什么样的?
陆晔:大部分艺术家在创作时都会追求社会性,但很多作品和公众之间是隔着一个东西的,你是通过观看展览,或者聆听作品来感受艺术家与社会现场的表达。但是小河从《音乐肖像》开始,就有意识地把艺术家的创作和普通人连接起来。音乐肖像就是邀请好几位艺术家,和一位普通人相处几天,然后为ta写一首歌。到了“回响行动”就更不一样了,普通歌迷直接参与到了整个过程中。
小河的作品有往自己内心走的一部分,同时也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比如我很喜欢的(“美好药店”时期的)《老刘》,就直接是从社会现场来的。到了回响行动,小河进一步把自己放到了公众当中,放到了一个现实的社会空间里面,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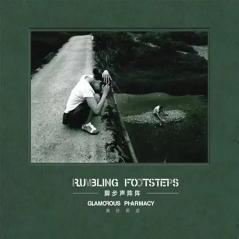

美好药店的《脚步声阵阵》(左)、“音乐肖像“中五条人的创作(右)。
在现场,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他们带来了各自生活世界当中的历史,老人和孩子连接在了一起,这非常动人。原本我是安于做观众的,但这两年我意识到,要进入一个社会空间,和其他人一起唱歌这件事不再那么容易发生了。我就有了一种紧迫感,觉得应该更进一步,对于那些我喜欢的东西,应该更多地加入进去、表达出来。
我过去二三十年的研究场域都是新闻编辑部,但在当下这个社会场景里,公众有了更多的渠道去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内容。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抵达很远的地方,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但是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小时候所习惯的那种附近,那种邻里关系,童年时和玩伴、青年时代和好朋友在一起,一群年轻人勾肩搭背、喝酒聊天的场景似乎正在消失。
在2000年前后,我们关注年轻人的生活更多地是去看大众媒体中的言论以及信息的传播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但在当下这个自媒体带来的多样化表达成为日常的时代,审美公共领域对青年人的思想和生活发生的影响正在提升。
当我们不再那么容易能面对面地一起拍手唱歌,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看着对方的微笑,当互联网让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有了新的连接方式,我们作为个体,还要不要有一个“附近”,能不能把这个“附近”作为在面对社会的变动和风险时内心的一个支持系统,就显得格外重要。

陆晔在古劳村寻谣。
长期以来,我的生活都在高度紧张中,我特别注重效率,希望一切都按计划完成,但在古劳村的一次寻谣经历,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那一次我们去到一对老夫妻家里,老人给我们看孩子们给买的智能手机,说他太太很喜欢拍天上的云。老太太很不好意思,说自己只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普通农村妇女,但看着相册里的照片,我只有惊讶,觉得怎么拍得这么好看。小河当时忽然说了一句话,说我们读了那么多书,走过那么多路,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看云吗。
这个场景对我的触动很大。回到上海后,一位朋友写了“看云”两个字送给我,它们现在就放在我的电脑旁边,当我对生活不那么肯定的时候,我看到这两个字,想起那天的那个场景,就觉得特别美。

作为一个学者我会反思,在过去的研究中我时常忽略了审美公共领域。它虽然不那么有冲击力,但它是潜移默化的,在不断地塑造我们的心灵和人格,有着非常重要的情感价值。
我们可以用日常的情感和审美,去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情感支持系统。我们的祖辈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那些声音、那些童谣,孩子们能在今天通过音乐再次唤醒,这是非常具有社会公共价值的。
Q:寻找和记录老童谣有怎样的公共意义?
陆晔:文化像水一样,它是流淌的,是会传承的。当我们一起歌唱,把那个声音永远地保留下来时,这些歌所承载的我们与这块土地的、文化的血脉的联系就不会丢。
在当下,老人和孩子是社会中相当不重视的一部分。大多数年轻人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形成自己的虚拟社群,但对于老人来说,村庄已经凋敝,他们的生活仿佛还停在远处。
我记得小河说过一句话,老人不是活在过去的老人,他们就是今天的老人,他们跟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时代。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让他们能有一种连接?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寻谣计划提出了一种让老人和孩子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的一种聚合可能性。
我们需要架起一些桥梁,让孩子们听到爷爷奶奶所唱过的那些歌,去发现孩子们到底喜欢什么,到底愿意唱什么样的歌,我们可以给他们更多的东西,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然后把那些歌变成自己的。

陆晔在古劳村和老人交谈。
把被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抛下的东西打捞出来,给它们一个机会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和文化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Q:怎么看待现在大众流行文化的碎片化和“低俗化”(例如短视频的流行)?我们可以怎样建设一个更好的公共艺术氛围?
陆晔:我觉得这个事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就是在没有短视频的时代,整个社会普通老百姓的教育素养和文化品位有多高,那他们所喜欢和接受的东西大约就是那个样子。
知识分子比较容易从高处往下看,会觉得说,哎,这怎么这么低俗啊,其实因为互联网,因为移动短视频,多少人、多少年轻人有了做自我表达的可能。这种自我的表达其实还挺多元的。
比如前两天,寻谣团队的钢片琴手,同时也是微信的编辑四旬推荐我看一个东西,特别好玩,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南美的乐器,和这些做世界音乐的人。如果没有短视频这个平台,我们普通人更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元的东西。所以说在今天因为有了互联网,那些更小众的东西变得可见了。
所以互联网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和可能性的,并不能把整个社会文化的这种低俗一概都算到短视频的头上。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像老四、手工耿这些从快手上出来的网红,我真的觉得民间的力量是无穷的,创意是无穷的,特别有趣。
公共文化建设应该是社会多种力量介入的,寻谣计划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这还是音乐人自觉的一种努力。要说到今天整个社会的文化状态,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一个社会有没有内驱力可以让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做这样的事情。

Q:“寻谣计划”开展5年,有实质性的进展吗?怎样去传播这个相对小众的艺术项目?
小河:“寻谣计划“的初衷一直没有变,从一开始起,它就是一个公共艺术项目,当寻谣的行为发生的时候,通道就建立起来了。我们一旦行动起来,公共效益就已经产生了,所以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包袱。
我们还有很多想去的地方,比如广东的粤语区、闽南、东北,这几个地方肯定有非常好的东西值得挖掘。但目前“寻谣计划”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自己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美香:现在的我们也在一步步尝试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音乐会直播,有的人看到了,觉得很喜欢,我们就保持这样的小规模人际传播。比起突然火爆,我们更想让寻谣计划慢慢渗透,比如我们把它带到校园里,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它可能无法一下子触及到非常多人,但它有一个循序渐进、慢慢在成长的过程。

走进课堂的“回响儿童节”。
宇威:我们找到的童谣本身,不论是美感、底蕴,还是背后的故事,都给了我极大的感染,它们已经很好了。如果说用什么方式让它们被更多人感受到,我只能尽量去还原,然后把感染我的部分适当地放大。它们本身已经非常美好了。
小河:寻谣这件事有双重意义,一个是公共艺术性,一个是它的产出是否有社会价值,比如在孩子的音乐教育方面。我更看重前者,这也是我们没有包袱的原因。民间有很多自发的民谣收集者,我们和他们的一大区别,在于我们更看重音乐身体力行的那部分。
音乐是身体力行的事儿,听者在理解中也是身体力行的,我们在一起让音乐发生。
最近大家都在探讨环境危机问题,大家好像觉得,气候危机就应该是国家层面去商量的事,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责任,我倾向于相信人的自觉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留那些好的、值得被留下的东西,或者对于老人这个群体有沟通的意愿,都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和改变。
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分子,你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因为有你这个人而不一样了,就是这样。
陆晔:好的公共生活应该是多个层级、多个主体、多元的行动。在公共审美领域来说,人们参与进来,真正在里头看见美的东西,大家一起发出声音、相互聆听,让旋律和自己的生活关联,或者就感受当下的愉悦、感受童谣的美,我觉得就足够了。

寻谣计划在杭州的音乐现场,老人孩子一起歌唱。
我觉得寻谣计划特别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它会打破很多固化的东西。它告诉你在田间地头、在村口的老榕树下,在一个下雨天的弄堂里,有猫、有跑来跑去的孩子,你开口和大家一起唱歌,这件事本身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
对于职业音乐人来说,自己的作品留下来,就像一颗石头扔进了水里,可能在某个时刻产生更大的涟漪。这颗石头不一定是你的那个作品,而是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去身体力行的一些东西,它带来的影响可能比你留名的那首歌更重要,这是艺术家对于社会非常有价值的一种介入。
反过来对于社会来说,我们希望有更多不同维度的、各种各样的公共艺术活动。它可以是声音的,可以是空间的,可以是时间的,可以是互联网线上线下结合的。
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传统的边界,比如社群的边界,在被打破和重组,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原始的传统或是乡村,一切都被编织到了一个更大的,全球化、数字化的当代生活中。对于普通人来讲,你在生活中能参与的艺术实践越多,生活可拓展的面相就越多。对于一个大时代来讲,我觉得个人的幸福感的来源和审美维度的这种弹性有关。我想这个就是“寻谣计划”可以带给社会的一个启示吧。
宇威:最后我想说说《秋柳》这首歌的故事。
它最初是一首宗教赞美歌,叫In the Sweet by and by,后来在20世纪初,有个叫Joe Hill的工人重新填词,作了一首新歌,叫《传教士和奴隶》,内容和原本的宗教精神是针锋相对的。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调发生了一些变化,词配合着曲也构建着一个更抒情的意境。
我们确实能感受到秋天万物凋零的环境,因为我们看过、听过,有解码能力,所以我们能捕捉到歌曲里的伤感。但今天,我们的生存环境在发生变化,温度升高、冰川融化,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棵柳树在未来会不会成为濒危的东西,《秋柳》这首歌还会在哪里呢?

撰稿 桑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祖国统一必将实现
- 福建福耀科技大学迎来多个考察团
- 清明假期流行“下县”赏花

- 短途游主导清明假期出行市场,“2小时高铁圈”成热门选择
- 南向资金净买入额超130亿港元

- 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又名
- 文艺复兴时期名画《维纳斯的诞生》是谁的代表作

- 18当“黑户”27年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