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跨过海峡的台湾新创客:大陆不再只是“淘金场”,也是定居地
“起风了”
25岁的廖子瑄在台北苦苦经营一间农产品小店。台湾市场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小,价格上又打不过东南亚进口产品。有好几次,火龙果滞销,果农们接二连三地给她打电话,苦苦追问,我们的火龙果甜度高,水分好,为什么人们还是吃越南火龙果呢。她也给不出答案。
这种情形让她想起小时候。她是台商二代,童年时期,家里曾经营过一家体育用品贸易公司。每年,她都跟随家人去东南亚参加亚洲区域的行业展会。一开始,展厅全被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参展商所垄断,大陆来的参展商只有零星的展位。慢慢的,局面扭转了。大陆厂商的展位从一个两个到三个四个,直到占领大半个展馆。那时的她,就像这些卖不掉火龙果的农民一样,怎么也想不通。
焦虑的时候,她喜欢抱着手机,紧盯每一条创业资讯,期望从中找到点什么,可以改变自己目前艰难的处境。当刷到那则上海市金山区创业基地落成的消息时,一种不妨试试的念头忽然蹦出脑中,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订了飞上海的机票。她性格中有一种说走就走的果敢,“我朋友都说只有我才能干出这种事”。
唯纶是在一年后来大陆的。2016年6月,43岁的台湾人唯纶离开台北,独自空降到东莞,开始创业之路。
她来是为了推广一种能治理汽车尾气的石油清洁剂。
在台湾,唯纶的长兄是此项专利的持有者,也负责生产,她跑销售。三四年的时间,全台湾已经有一千三百多辆汽车使用这种减排清洁剂,但市面上还有其它类型的清洁装置同在,竞争格局难以突破。
“但如果不是双创,可能真的不会来”,种种利好通过媒体传到台湾,她感到有点不可置信。同时,在大陆,每年新增燃油车数量在2000万左右。她和哥哥一商量,笃定这里才是一片更广阔的蓝海。
很快,唯纶住进松山湖台湾高科技园区配备的创业宿舍——一套两室两厅的公寓,装有空调、冰箱、热水器,房租为零,水电月开销在200元左右。她喜欢这个住处,干净方便,周围聚集着一帮热气腾腾的创业者,门口小卖部的老板娘认定她是第一位台湾朋友,请她品尝自己煲的鸡汤,生病时送药给她吃。
专为支持台湾创业者而设的创业孵化器遍布全国多个城市,以上海、东莞和昆山居多,很大一部分是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的热浪而落地的,其中既包括各地台办挂牌成立的服务机构,也有大型台企自发搭建的公益性平台。
根据国台办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大陆共有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53家,入驻或服务台资企业近1200家。孵化器为台湾创业者提供资源对接、创业培训甚至启动资金等服务。“我们这一代比较幸福”,唯纶不好意思再用“艰苦”两个字形容自己的创业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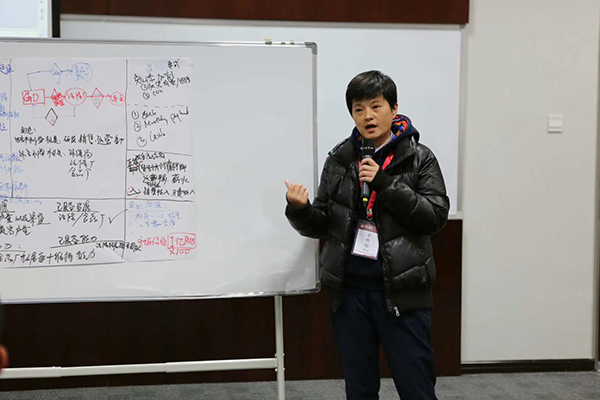
“双创”的风一起,带动了一批像廖子瑄、唯纶一样的台湾创业者流向大陆。和他们的前辈,那些十几年前跨过海峡前来的老台商不一样,多年前的大陆还是等着被拓荒的热土,商机俯拾皆是,凭借台湾的先发优势,台商们很容易在这里收割财富。而现在,这片土地已经孕育出成熟的商业社会,很多跨过海峡的新新创客不再只是把大陆看作是淘金场,而是理想的定居之地。但同时,这里的机会被贴上价签,规则明暗交错。谁都说不清他们将在哪里觅得良机,又在何时铩羽折返。
初来乍到
头三个月,唯纶被巨大的陌生感围困。
这并非是她第一次来大陆,相反,她记不清自己来过多少次了。在台北创业之前,唯纶曾经做过模特经纪人,隔三差五地,她就带着手下的艺人到大陆赶通告。然而仅此而已,那时候总是工作完立刻就走,“睡遍了数不清的饭店”。除了饭店,她哪也没去过,更不知道这里人们的日常是怎样的。
现在不同了,她住在东莞,但为了拓展业务,南北到处跑。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复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领略到的。
“就拿汽油来说,北方的是乙醇汽油,南方的就是汽油”,在此之前,她以为大陆和台湾一样,烧的都是无铅汽油,也只用一套标准。她想把产品认证为“低碳”,百度上众说纷纭,她一条条看下来,依旧一头雾水,搞不清楚应该准备些什么。事实上,配方不一样,各地政府对“低碳产品”的认证标准就不一样,这是她后来才得知的。
产品包装上,她本来用的塑料,北方客户告诉她不行,会结冰。“还有这种状况?”,于是立即告诉工厂,改成铝罐。
还有一些不成文的心得,比如北方人更关心天气,碰上一次蓝天总是兴奋地对着她抒发一通;南方人不在乎这个,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吃喝玩乐。“当然,赚钱是大家共同的兴趣”,她正经地补充道。
有一次,她向一位检测线老板介绍产品,原本准备了讲解资料和一系列证书,面前的老板露出质疑的神色,表示并不想听,直接提议让唯纶用产品试车,三分钟后,排放检测仪显示指标下降,对方立马表示买账。
为了认识客户,她在各种名义的沙龙和论坛上和人交换名片。通过社交网络,她执着地向每一位可能认识的大陆人发出好友邀请。利用公司还没注册下来这段时间,她必须恶补不同城市关于节能减排的政策法规。她学会使用微信,学会拉群,也被人拉入不同的群。
在一个名叫“起风了”的创业群里,天天都有群主汇总当日资讯,分门别类扔进群里,“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差点吐血,这怎么消化得完”,她对着整屏的简体字,一条一条地念,因为有的字词语法跟台湾不一样,“我感觉自己像个文盲一样”。
从食物到形容词,从生活到工作,生词接二连三地冒出来。“马铃薯”变成了“土豆”,“修路车”变成了“SUV”。在台湾叫“延长线”的,大陆叫“排插”,她背了三天,然后发现叫“插排”也可以。还有一些机械用语,比如大陆习惯称的“三元催化器”,台湾叫“触媒转化器”。
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或朋友,心爱的车也留在台湾。以后出门不能开车了,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件事其实很要命。
想家的时候,她躲在房间大声唱歌。2017年的春节,她不知道需要提前订票,临近了一查,回台北的机票已经卖光了。除夕那一天,她中午和隔壁的四川小伙吃了一顿团年饭,晚上,她一个人在房间,嚎啕大哭。这个教训之后,她索性买了航空公司的年票。
2017年3月,唯纶去大连,还在为第一次见到北方街道而兴奋不已时,这里干燥粗粝的水土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当时她等公交,即将与一位重要客户见面,鼻血就那么毫无征兆地淌了下来,白衬衣立马遭殃了,一大片血迹滴到胸前,突兀而刺眼,想遮都遮不了。“如果我在台湾,我早就去看医生了,我才不管什么客户咧”,而现在,她没有这个底气。下一班公交一刻钟后才到,她迟到不起,只能硬着头皮上车,然后以平生最狼狈的形象出现在客户面前。
这一年多,她去了不少地方。记忆深刻的一次是乘高铁到辽宁丹东,站在鸭绿江畔,远远望着江那边的朝鲜,课本中的历史与现实在此刻重叠,她心中升起一种无可言说的复杂情感。
唯纶迎来真正的心安是在到东莞后的第三个月,2016年9月3日,中国宣布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唯纶听到这则新闻,好像接到了一份厚礼。“下面一定会有治理汽车尾气的政策出台”,她坚信自己赶上了风口。
风口之后

吴宗鑫显然没赶上风口。
2014年7月,Facebook收购虚拟现实硬件制造商Oculus。听到这则新闻,他内心有些躁动,隐隐感觉到VR游戏的前景变得清晰起来。他本是游戏研发出身,后来转做美术外包,但一直对游戏保持着强烈的兴趣。
不久后,他买了一台Oculus Rift DK2。这款VR设备在全球几乎断货,他花了原价的三倍,才辗转从一个黄牛手中订了货,托人在北京检验后再送到上海。
“现在回头看,DK2的画面跟现在的比,差的太远了”,但当时,他戴上的刹那,感受是“太神奇了”。
他快四十岁了,这时候忽然发觉内心对游戏的热情一下子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他想,必须要做。于是一头扎下去,开始组团队,做VR游戏开发。
2014年被称为是“VR元年”,而吴宗鑫是从2015年年底才开始从事VR游戏开发。仅仅晚了一年,他就没赶上VR在资本市场上的大热,当他进场时,曾经的热闹已经偃旗息鼓了。
2017年11月,他带领团队开发的一款游戏从三百名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在一个颇有分量的行业大赛中获奖。在之后的交流会上,一群得奖者聚在一起,丝毫没有在领奖台上那种喜悦。“大家都在说,寒冬还是寒冬嘛”,在台上开开心心地领完奖,散场之后每个人都得各寻办法过冬。
风口说变就变,留下的是一个看似庞大但百废待兴的市场。
手机从笨重的大哥大发展为iphone用了二十年,吴宗鑫觉得VR游戏也一样,“要熬的年份还很长”。他有些沮丧,已经半年多没听说国内VR游戏开发公司的融资新闻了。
他逐渐意识到,在很多困境面前,仅凭游戏开发者一己之力很难让整个行业的天花板抬高一寸。
他开发的第一款VR游戏叫《正妹真爱打篮球》,支持双人对战模式,首先在台湾推出。当时台北市长科文哲走访三创科技园区一个VR展馆,正好体验了一把,在名人效应的作用下,这款游戏一下子名声大噪。

在这款游戏成功的基础上,他一度想开发更多的连线对战模式。理由很简单,如果一群朋友在商场看到一家VR馆,可只能一个人玩,其它人在旁边傻站着,这群人多半会掉头就走。
但现实是,目前国内建成的VR体验馆大多只能提供单机游戏设备。短期内,很多商家不愿意更新。他当然没办法,他设想的场景难以落地,反过来只能修改自己的创意思路。
他考察了国内很多线下体验馆,发现维护人员的专业水准参差不齐,有的连玩家的疑问都解答不了。一台设备坏了,商家没有维修能力,就那么晾着,因为厂家的维修点可能在别的城市,要过很久才能送修。这些状况看似跟他离得远,但往回一捋,大家都在一个生态圈里,一损俱损。
问他,有没有碰到过同行竞争的情况,吴宗鑫苦笑一声,“远远谈不上,连抱团取暖都做不到”。他只想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撑到这个寒冬的结束。
文化创客

袁亮天生于台湾,但成长于大陆。念研究生期间,有次回台北,他骑着自行车满大街转悠,看到遍布街头的自助洗衣店,心想,这种模式能不能搬到大陆呢。为此他研究了好久,琢磨出好几个创新点。不过一算,一间店至少需要四五百万的投入,他只能不甘心地放弃这个想法。
2017年夏天,临近研究生毕业,他和朋友聊天,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两年国内流行什么,有人提到《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的走红,说起“匠人精神”变成一个热门词汇,感觉那些回归质朴与本真的风格重新得到人们的珍视。这么一说,袁亮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手捏一张绝佳的创业入场券。
他的母亲是一名画家,他一直帮母亲做着策展联络等工作,对艺术市场还算有点门道。母亲的朋友圈子他从小就熟知,其中有很多台湾本土的手工艺人。因此他想,何不把台湾的手艺人介绍到大陆,帮他们对接展览、讲座或授课机会呢——这是他目前的主要创业方向。

来大陆十几年,袁亮天还是说一口台湾腔,音调抑扬顿挫,语速慢慢悠悠。他说,他的大陆合伙人总是很急迫地推销团队,“我不会,我会先交朋友嘛”。
他知道,很多时候同行竞争过于激烈,大家都差不多,“讲来讲去讲不出什么点”。他天生会聊天,还懂幽默,别人一问,“你是台湾来的?”,他马上就能接过话头,从成长经历漫不经心地聊起,最后再绕回业务。这样一来,就帮自己在客户面前增加了一个记忆点。他相信,再拿出台湾服务业的水准来对待客户,谈一桩生意应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台湾的艺术家更会表达,也更愿意表达。从一件作品的构思到选材、制作到价值,可以说得头头是道,而大陆的艺术家不会讲解得那么深入,有待学习者自行体悟。
他非常欣赏这种讲解——不管是对于艺术家的自我包装也好,或是对整个创意行业而言。现在人们的消费热情起来了,但是艺术知识储备还没有跟不上,这个领域的从业者可以不那么“高冷”。
不仅是袁亮天,因为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早,从文创切入大陆市场,也是很多台湾创业者的首选。
谢国梁在台湾曾是有名的政坛明星,曾任基隆市国民党三届“立法委员”。2014年,从政转商、成立华联国际以后,主营业务之一是将台湾电影引入大陆。
之所以选择内容产业,是因为他认为“内容这种东西是有底蕴的,文化底蕴不同,拍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2015年,华联国际出品的小成本青春片《我的少女时代》在大陆上映,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在他看来,大陆青春片与台湾青春片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习惯在故事之外包裹一层民族和时代的宏大背景,但“台湾不管这些东西的,台湾只讲我今天快不快乐”。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区别是一起典型的文化冲突。设计师Jolor也有同感。他笑说,刚过来的时候,把一版作品发给客户,无论是什么品类的客户,反馈给他的修改意见都是“能不能再大气一点”。时间久了,他也渐渐理解。
挣脱瓶颈
老一辈的台商爱抱团,大多数人刚来大陆的第一件事是加入台商协会,就像拜码头一样虔诚。而台商圈子里也流传着一句玩笑——台湾人总怕被大陆人骗,但最后才发现,骗人的不是大陆人,而是早来几年的老台商。Jolor在创业早期也有这种心理,在一堆摸不清底细的供应商面前,怕踩到地雷,他都会选择台湾供应商。
这种保守在新一代的台湾创客身上减少了。
唯纶觉得,如果自己固守台湾式的保守,可能会令自己失去很多机会。她举例说,“假如我有两位朋友互不认识,其中一位想通过我和另一位做生意”,“如果我还是台湾的思维,我可能会犹豫要不要介绍,万一他们闹僵,我夹在中间怎么办。”现在她在大陆,逐渐习惯了一种互通有无的规则,“很简单嘛,直接拉个微信群,介绍一下就好,闹僵了关我什么事。”
她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后的那代台商,机遇太好,“闭着眼都能赚到钱”,而自己这一代创业者,虽然也有大把机会,但同样要花大量的努力。
Rachel的创业项目是面向儿童的财商教育,为此,她需要与银行、学校以及NGO建立紧密的关系。到上海创业之后,她参加过数不清的论坛和行业交流会,但几乎没怎么与其他行业的台湾创业者有过联系,“一开始就是进入本地的圈子”,这里有大把的人脉资源等待她开拓,同为台湾人这个标签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创业前,她在台北一家外资银行工作。2008年金融风暴后,她越来越发觉,天花板很明显了,哪怕做到银行行长,“也就那样”。
这种对于台湾市场的逼仄感,并非只是她一个人的感受。Jolor现在在上海开了家活动策划公司,承接了各大奢侈品品牌的线下活动策划。他清晰地知道,如果回到台湾创业,不仅客户给的预算会折半,更重要的是,他将会丢掉许多重要客户,因为大陆是各个品牌在亚洲市场的绝对重心。
廖子瑄有使命感在身。她说不清这种使命感从何而来,也许是目睹过父辈生意的变故,也许是源于她的正直与热忱。
看到对大陆抱有疑虑、迟迟不愿跨过海峡看个究竟的台湾年轻人,她很心急,“你看到一个东西好,就想赶快招呼朋友过来”。

她记得自己赤手空拳地过来,一开始没有任何销售通路,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上网搜各大超市和电商平台的办公地址,登门拜访。原本也有顾虑,设想过某种门路的存在,做好了吃闭门羹的准备,但最终发现对方很直接,最关心的是她能不能稳定供货,能就上。
她也遇到过波折,去年,原计划是主推一款产自阿里山的山葵,台湾的种植农民和大陆的销售渠道都谈好了,忽然接到通知,山葵进入禁止进口的产品名录。她心有余悸,“还好没下单,下单我就完了”。
现在,早上一睁开眼,她便打开国务院和各大财经新闻的APP,把最新的政策和新闻都刷完了,心中才有安全感。
总之,“过来才是真的创业”。
为了招募人才,她以雇主身份参加过一场面向台大学生的招聘会。对于加入初创企业,台湾学生们倒是保有极大的热情,但当她问到是否有人愿意去大陆工作时,场子便凉了,没什么人举手。
她有一位朋友,被大陆一家互联网企业看中并许诺高薪,但母亲说“不安全”,因此打了退堂鼓。她听着很不可思议,但也知道,确实有不少年轻人是这么想的。
现在,她同时帮金山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和青创院两家孵化机构运营社交账号,传播她的创业心得。她也回台湾上过电视节目,像推广大使一样鼓励台湾青年到大陆创业,“救一个算一个”,她觉得台湾“太舒服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唯纶对这个现象也有亲身体会,得知她要来大陆创业,“家里60岁以上的长辈全都不支持”,她的几位好友还在facebook上把她列入黑名单。“拉黑就拉黑了呗”,她撇撇嘴,不觉得生气,只觉得好笑。
台湾年轻人理解的创业很简单,多半是开家店,甚至就在路边支个摊。廖子瑄觉得这种创业方式不过是“昙花一现”——卖一点当下流行的,好吃的好玩的,然后呢?
华联国际董事长谢国梁对此看法相似,“台湾没有太大的创业环境”,年轻人创业基本上只能在生活方式领域小试身手,“如果你想新创什么,早就被大的集团抢先了”,但大陆不一样,“因为互联网的关系,你提供的价值和服务能很快在几亿的用户里取得市场”。
这一年来,廖子瑄成了金山区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的典范。一年前,她冒冒失失找上门来,结果歪打正着,这事已经成为一则段子,在圈子里流传。
她只是希望自己像父辈那样——他们“拎着皮箱走天下”,仿佛天底下没有吃不了的苦,也没有谈不成的生意。如今她跨过海峡,迫切地想找回那种感觉。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