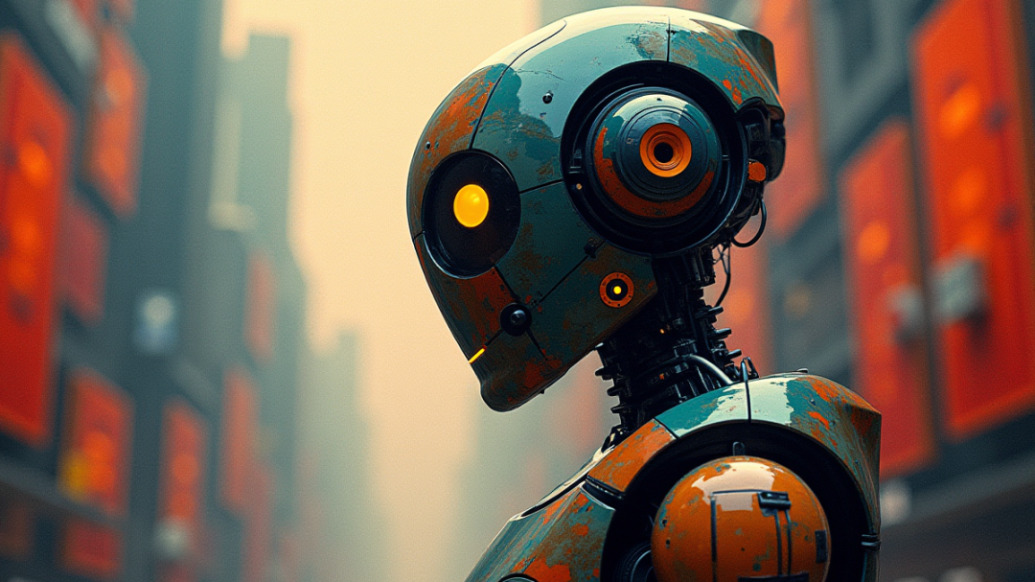- 94
- +168
为什么戴高乐放弃了阿尔及利亚

大家还记不记得一部电影,叫做《豺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Jackal)?这是根据英国作家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1938—)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在1963年,一名外号叫“豺狼”的杀手受雇刺杀时任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的过程。
这部小说描写的非常精彩。虽然是小说,但针对戴高乐的暗杀却是真事。如果你仔细看过电影和小说,就应该知道雇佣这个杀手的组织,叫做“秘密军”。
秘密军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法国军队的军官,在六十年代组织了多次对戴高乐的暗杀(至少发生了四次:分别发生在1961年9月,1962年的5月、6月和8月)。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都知道,戴高乐是法国的英雄,在二战期间功勋卓著,在法国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那为什么这些法国军人还要暗杀他?
这就要从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讲起。
阿尔及利亚的主权问题
一个强大、拥有悠久文明和众多人口的世俗主义国家里,有一片主要由穆斯林构成的边地。这一边地幅员辽阔、资源众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从本土迁入大量移民,这些移民在工作、地位、经济条件和居住地域上都高人一等、自成一体,他们自视是“文明开化”的先锋。国家对这块边地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投资的主要受益者还是外来者。
虽然在这里已经立足百年以上,但是政府还是焦虑于当地人的离心倾向。布置在那里的军队,主要执行的是民事监视任务。当地政府对穆斯林居民的宗教和文化持有某种歧视态度,认为最好的巩固统一的方法是尽快让当地居民向国家的主流文化看齐。但公平地说,国家还是为当地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秩序、医疗与教育服务,也多少提供了政治参与途径。外来移民虽然境遇较佳,但是还算自食其力。本地人虽然有不满,但同周边地区相比,生活大体上还过得去。有大批当地人进入军队和地方政府做事,还有一批人成为接受主流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不满于社会歧视,一方面仍然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以上说的是1950年前后的阿尔及利亚。当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但国际上的一般观感还是把阿尔及利亚看做法国的一个特殊部分,而不是普通的帝国殖民地(在这种领地中,由少数帝国官僚统治广大异族被统治者,比如法属摩洛哥)。当时的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关系,好比十九世纪的爱尔兰之于英国、现代的魁北克之于加拿大、巴斯克之于西班牙。二战以后,阿尔及利亚的本土居民开始要求某种政治改革,以便拥有更多权利。这种改革呼声后来又慢慢演变成某种武装抵抗。
对当时的法国政客以及人民来说,“l'Algérie, c'est la France”(“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但这恐怕不能一律斥之以殖民主义心态。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就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阿尔及利亚也是自己的故乡,所以他多次呼吁和解、共识。1954年,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开始以暴力恐怖手段追求独立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法国政治光谱中的各派都坚决反对。当时法国虽然是左派执政,主张改善民生,但在阿尔及利亚这个问题上,左右派其实没有什么意见分歧。
1954年6月至1955年2月短期担任总理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1907—1982)一向持反殖民主义立场,主持了法国从越南、突尼斯等地的撤出。他在一次国民议会中讲演时表示:
“当这个国家的内部安宁、团结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完整受到威胁的时候,是没有妥协可言的......阿尔及利亚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
1956年,中左联盟共和阵线在选举中获胜,总理居伊•摩勒(Guy Mollet,1905—1975,也是社会党总书记)本来打算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政治改革,从而在阿尔及利亚恢复和平。但当面对当时已经极端分裂的阿尔及利亚,摩勒也很快决定,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军管。
法国的左派尚且如此,其他的政治势力就更不用说了:有人想要保住帝国荣誉,有人想要挽回二战与越南战争中遭受的屈辱,有人要保护一百多万移民,有人看中了阿尔及利亚的资源与地缘重要性,也有人认为法属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现实,强行修改它会带来更大的不幸。
所以,基本上法国各派对维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主权持有共同意见。
法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其内部
在经济上,镇压阿尔及利亚也不是什么难事。固然,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一项巨大的耗费,一共花了500亿到550亿新法郎,占每年政府总预算开支的24%到32%之间。1958年(第四共和国末期)法国爆发了财政危机,经济趋于停滞。但这恐怕是由于当时的中左派政府在镇压起义的同时还雄心勃勃地进行了许多社会工程。
戴高乐政府在1958年6月上台之后,大幅度削减了这些建设,法国马上恢复了财政健康和经济活力,在战争的后半期(1958—1962),法国始终处于经济增长状态之中(年增长率都在5%以上),且在能源、机械、电子行业突飞猛进。从整个战争的跨度来看,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开销(包括军事开支与民事开支)顶点是在1959年,占掉GDP的2.8%,但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实际上,从经济史的角度看,1945至1975年这段时间被称为法国的“黄金三十年”(年均增长率在5.7%)。就此而言,法国完全有经济实力进行长期的作战。
那么,是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不如人意吗?
简单的回答:不是。法国军队自从从越南铩羽归来之后,就一直对游击战争和革命战争进行研究,在阿尔及利亚部署了一大批具有丰富反暴乱实战经验的军官。从军事角度上讲,FLN一直被法国军队压着打。比方说,该组织的活动重心之一是在省府阿尔及尔这种大城市,袭击、暗杀警察,针对平民进行爆炸。原因很简单,在大城市爆发暴力恐怖活动最能打击法国所维系的秩序感,凸显抵抗者的力量。但是法国军队派出了战争英雄马修将军(Jacques Massu,1908— 2002)带着他的伞兵旅,从1957年1月开始对FLN的城市组织网络进行无情扫荡。经过九个月的残酷作战,FLN的领导人、战斗员、后勤人员几乎无一例外或杀或擒,该组织在阿尔及尔的活动被全面终止。
在乡村地区,FLN还能保持一定的存在。直到1958年3月之前,FLN招募的人数还比其损失的人数要多,但是在4月之后形势逆转。法国军队将两百万人迁出山区,剥夺了FLN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到1958年为止,又成功封锁了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摩洛哥的边境,切断了FLN获得外部援助的渠道。
面对法军的攻势,为免报复,当地的阿尔及利亚社群通常拒绝与FLN往来。到1960年夏天,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的危机到达高峰,重要的地区指挥官开始撇开领导层,试着同法国进行谈判。由于法国人行之有效的镇压,FLN从来没有能够组织一次全阿尔及利亚范围内的罢工、示威或起义。
国际环境方面,法国似乎也没有遭遇太多阻碍因素。尽管美国在战后持反殖民主义立场,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作为也不是太高兴,但阿尔及利亚情况特殊,他们也是知道的,于是从来没有采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那种激烈的最后通牒式态度。苏联尽管口头上表示对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的支持,但当时其投送能力有限,很多时候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
既然在政治、经济、军事与外部环境方面,法国都没有面临明显的阻碍,那么为什么法国还是丢掉了阿尔及利亚?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好些个,比如说,法国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反战意见。虽然大家都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但大家也承认,阿尔及利亚同法国本土毕竟不一样。随着战争的日益延长、残酷(虽然成功),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将来要重建阿尔及利亚,收拾民心士气,将付出极大代价。也许要从法国本土转移大量的资源,可能会拉低法国本土的生活标准。换句话说,战争本身就减少了阿尔及利亚对法国的价值。而且当时东方的越南战争还在方兴未艾之中,有这个例子,法国人很难对阿尔及利亚产生过分的乐观情绪。这种现实与认知上的差距,这种对未来的忧虑,也许可以解释戴高乐最后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理由。
但是,对法国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可能不是FLN,而在萧墙之中。法国内部的许多人,开始越来越不安地注意到“黑脚”同军队的致命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致命后果。
不满政府的法国军队
1830年代,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之后派遣大批移民到阿尔及利亚以为爪牙。之后在法国历次政潮、革命中失意的人也纷纷涌到阿尔及利亚来开辟新生活,这些移民获得了一个外号——“黑脚”(Pieds-Noirs)。
到1950年代,他们的人数已达一百万之多,在本地也历经数代。对这些黑脚来说,由于地处帝国边缘与多族群生活的环境中,他们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更深的被威胁感。“狂”和“怕”是许多人的心态。他们反对一切让当地人拥有更多政治权力的改革,理由是不必要或太危险。法国议会中也有大量的议员同情黑脚,认为提出政治改革就是鼓励分离势力,就是软弱无能。
这里有一个例子:1955年1月,法国总理任命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1912—1990)为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主张扩大阿尔及利亚在财政和行政方面的自主权(向推行自治的方向靠拢),废除现行的“二元选举团”制度(当时阿尔及利亚议会五分之三的席位由欧洲裔人口选出,剩下的归穆斯林),使穆斯林与移民有平等的选举权利。他想以此来争取温和派穆斯林的支持,从而瓦解反抗力量。此举遭到了黑脚们的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向恐怖分子低头。他们利用在法国议会中支持自己的议员向苏斯戴尔施压,迫使他暂缓了该计划的实施。
面对独立运动,许多黑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支持不择手段镇压之,他们在军队那里找到了同盟。
当时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在反思越南的战败时,特别研究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一般来说,消灭叛乱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去区分叛乱者和叛乱者所在的人群,一律消灭或者驱逐;第二种做法是拉拢与威吓,把群众与叛乱者隔离起来;第三种做法则是打击叛乱组织的首脑、人员与后勤,这是纯军事的打法。
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军队认为,面对此种战争,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是不足的,以前在越南就是吃了这个亏。现在面对FLN,除了在军事上打击之外,还要对“鱼与水”中的“水”进行控制。所以军方特别成立了心理战部门,直接面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这种心理战逐渐变成了全方位的控制与胁迫。当时的法国政府,多少是支持军方这个决定的,决定放手让军队来干,逐渐将阿尔及利亚的治理权转交给军队。
1955年3月,法国政府宣布在阿尔及利亚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到1957年,军方掌握了阿尔及利亚的全部实权。当时的军方面对FLN的恐怖袭击与游击战,深感普通刑事程序与手段的不足。军方把每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和同情他们的法裔都看成是潜在的罪犯,决定依靠暴力和恐惧来统治。这种做法不仅被用在了阿尔及利亚,而且也蔓延到法国本土。当时有很多阿尔及利亚人到法国打工和居住,里面不乏FLN的支持者,军方和警方在很多场合下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违法的。
这么做的同时,军方对巴黎的共和国政府也越来越不耐烦。许多军人开始质疑民主政府的可靠性,他们联想起二战期间政府对军队的“出卖”,也联想起越南战争中政府的“软弱”,认为民主体制根本无法应付“革命战争”这种非常事件。一些军官开始声称:“我们要认识到,在当代世界,民主意识形态是非常无力的。”
法国的知识精英开始担忧这种现象的蔓延。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让-马利•杜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1922–1997)发表文章称:“在阿尔及利亚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不可能同法国的民主实践并存。……我相信,阿尔及利亚的法西斯主义……会掉过头来对付中央政府。……只要法国还在拒绝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愿望,那么阿尔及利亚战争就会延续下去。而只要战争延续下去,阿尔及利亚的形势就会持续不断的滋长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会不可避免地扩散到整个军队中去。我们正在同时间赛跑。”在1959年法国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5%受过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认为军方有可能越轨行事。
阿尔及尔政变与戴高乐临危受命

事情的发生果如所料。1958年5月13日,在阿尔及尔,政变发生。一位名叫皮埃尔•拉加亚尔德(Pierre Lagaillarde,1931—2014)的学生领袖率领群众冲击了总督府大楼,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坐视不理,并随后加入。之前提到的战争英雄马修将军出面,组织了一个公安委员会。
危险继续向法国本土蔓延。法国本土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在巴黎示威游行,共和国政府的首脑们悲哀地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指挥军队和警察。5月24日,科西嘉岛的伞兵出动,夺取政权,建立了本地的公安委员会。内政部长对内阁提出警告,科西嘉岛的叛乱活动有可能在5月27、28号在法国本土各省重演。这并非虚言。当时阿尔及利亚法国军队的总司令萨朗将军(Raoul Salan,1899—1984)以及马修将军已经制定了一个“复活作战计划”,具体来说,从阿尔及尔和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起飞的伞兵与驻扎在巴黎城外的装甲部队合作,一起进入巴黎,占领国民议会,推翻共和国政府。
共和国政府束手无策,只能请来了当时蛰居在乡下的戴高乐,请他重新执政,收拾残局。这样,1954年以来,不仅连续几届法国内阁都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而且总体军事政变也濒临爆发,在现代法兰西历史上,再次浮现了“佛朗哥化”军人专政的危险。这些事态真应了当初美国革命时英国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反对向北美殖民地派兵时所说的话:“取代它们而治理美洲的军队,糜费将更大,效果则不如;事到后来,军队会变得像它们一样难以驾御,真也未可知。”
对这次政变,戴高乐本人也不是全然无辜。政变者们事先跟戴高乐通过声气,征询过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未来的看法,戴高乐与之虚与委蛇。其手下一些人也打过煽动作乱、趁乱夺权的主意。政变的将军们认为,戴高乐一定会站在自己一方,将阿尔及利亚保留在法国版图之内。他们在政变时高呼“戴高乐万岁”,戴高乐也挟政变军队以自重,以要挟共和国政府,让他们授予自己全权。
应该说戴高乐本人的想法其实同军方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他也想保全法国的领土完整。他的想法是,一方面向阿尔及利亚投资,给予本地人经济、教育方面的优惠,另一方面重兵对付FLN,打怕打服对方,迫使或说服对方放下武器,然后他再展示宽宏大量,将对方纳入地方政府内,一道实现一项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永久联合的政策(可能是某种联邦体制)。
所以,戴高乐1958年6月正式上台之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收手,而是进一步出击,差一点就将FLN逼到绝路上。但戴高乐毕竟是戴高乐,有别于一般军事强人。他觉得同化阿尔及利亚人是做不到的事情(一百年前也许还行)。他知道,即使看起来叛乱是被镇压下去了,但却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它在五年到十年之内东山再起,法国终究不可能一再投入到绵绵不断的镇压活动之中。
法国军队把这场战争看作是恢复军队荣誉、保全法国领土和对抗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但是戴高乐却非常担心,这种“东征”会分裂军队和法兰西民族,并且有诱惑高级军官搞冒险活动的危险。戴高乐的权力欲望也不允许他自己受人挟制:军队可以推翻第四共和国政府,自然也可以推翻他(他去阿尔及尔视察的时候,在场的群众喊出来了“一切权力归军队”的口号,他非常生气)。一旦看清楚阿尔及利亚非短时间能够平定,他就另作主张。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和公安委员会,他示之以静,用明升暗降的方式将叛变的高级军官调到中央高高挂起,又把约一千五百名军官从阿尔及利亚或调走或强迫退休。帮助他上位的自己人,他也一律闲置。
军方对戴高乐过河拆桥当然非常不满。1960年1月18日,《南德意志报》发表了对马修将军的采访。马修将军说军队不再理解戴高乐的政策,帮助其重新上台也许是一个错误。他还说,他和大多数握有指挥权的军官“将不会无条件执行国家元首的命令”。戴高乐马上将他解职。此事顿时引发连锁反应。一星期之后,拉加亚尔德再次冲上阿尔及尔的街头,垒起街垒,高呼“绞死戴高乐”。法国军队有位朱安元帅(Alphonse Juin,1888—1967),在圣西尔军校就读时是戴高乐的学长,他冲到爱丽舍宫,对戴高乐大发雷霆:“如果你下命令开火,我就公开反对你。”戴高乐顶住了压力,镇压了这次叛乱。
一年之后,1961年4月18日,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高级将领(包括前任和现任的法军总司令)再一次举起了叛旗。情况异常危险,因为法军的精华都在阿尔及利亚,这甚至惊动了英国的内阁,他们紧急开会,商讨是否要派出部队援助法国政府。戴高乐自己也发表广播讲话,恳求道:“法国的女人和男人们,请帮助我。”结果到了4月27日,由于法军中的普通军官和士兵相应了戴高乐的号召,也由于叛军缺乏相应的决心,这次叛变就失败了。
但这并不是事件的结局。没有被抓捕到的叛变的军官转入地下,同先前的民间叛乱分子合作,建立了“秘密军”组织(OAS),这是一个地下的军事组织,由前军官、黑脚中的极端分子还有法国本土的同情者组成。很讽刺的是,他们的行动策略跟自己的老对手FLN差不多,企图打一场“人民战争”。他们杀害法国政府和社会中的温和派,斥之为“卖国贼”;迫害阿尔及利亚本土穆斯林,这是为了引发本地人的暴动和报复,从而迫使军队出面镇压,进而破坏法国政府同阿解的任何谈判;暗杀戴高乐将军本人。据法国《世界报》的统计,从1961年5月到1962年1月,秘密军队组织在阿尔及利亚共进行了5862次袭击,造成了269人死亡。
在镇压叛乱之后,1962年3月18日,法国政府与FLN达成停火。之前戴高乐曾向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提出呼吁,给出三种选择方案:独立、与法国合并(给予所有穆斯林法国公民权)、联盟(阿尔及利亚自治)。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穆斯林还愿意站在法国这一边了,所有的温和派都已经消失了(不是被FLN所消灭,就是被军方、黑脚和秘密军所消灭)。这样,要么是全面的军事征服,要么是可耻的撤退,再也没有第三种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后者。
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穆斯林选民在独立公决中几乎一面倒地赞成独立,而一百万黑脚们则踏上辛酸的逃亡之路,几十万阿尔及利亚人也随着他们到了法国。
这就是今天这个故事的原委。
阿尔及利亚战争告诉今天的我们什么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二战后去殖民浪潮中最血腥,也最动荡的一幕。在其他地方,前殖民者的撤出都是相对迅捷且无损失的,但阿尔及利亚却是一个特例。在这块九百万人居住的土地上,法国派遣了五十万军队,镇压三万五千名叛军游击队,四十万到一百五十万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
从很多标准来看,这都是一场内战,理由:一,大量死亡事件发生在正规战场之外,各种恐怖袭击、拷打、虐杀使之闻名于世,私人武装之间彼此进行报复;二,作战对手界限模糊,FLN的主要打击目标除了外国人,就是那些穆斯林中的温和派,法裔居民自己也组织了地下武装对部分法国政府官员和警察发动攻击;三,政治震撼严重,不仅连续几届法国内阁都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体制也因此而瓦解,几乎出现了军人专政。
力挽狂澜的戴高乐,在法国本土三番四次遭到法国激进分子的刺杀。如果阿尔及利亚战争只是普通的殖民战争,很难想象法国的政局会变成这副摸样。
这场战争告诉我们什么呢?
事后回过头来看,一个明显的教训就是,在这种事件中,即使握有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优势,也不要以为暴力与强制能够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有效手段,只以治安的思维来应对族群冲突、国家分裂恐怕是不行的。我们很难说戴高乐不是一个爱国者,或者说他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在当时那种场景下他选择壮士断腕,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另一个明显的教训是,在一场近似内战的战争中,在边地挥舞镇压大刀不可能不反过来对本土造成巨大政治影响。一场十九世纪的殖民战争只会涉及一小部分精英军人,只要政府的财政支撑得起,就可以长时间打下去,要结束战争也很简单,因此只需要考虑军事面与经济面就可以了。但是在一场内战中就并非如此。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情况下,边地存在大量移民,迎合他们的要求,就很容易把一场治安行动变成族群冲突,在这种族群冲突中,有限的警察手段将不能满足移民大众的需求,而很容易上升为全方位的社会控制与对抗。
这将不可避免地把本土社会卷进来。首先是,军队也许会在这些移民及移民的支持者中寻找到政治基地,从而出现藩镇之患。其次是,形成对原有政治秩序的冲击,一场内战(虽然仅发生在边地)将要求更有效、更严格、更协同的政治与社会管制,政治强人应声而起的风险将会增大,社会的分裂也可想而知。
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孙武的这句话可不仅仅适用于对外的战场上。
(本文据作者2017年12月在上海“TELL+历史”公众演讲活动中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有简化和重新编辑。)



























- 别背着我们谈
- 春节后热点城市楼市成交逐步恢复
- 央行:强化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

- 【收盘】沪指涨0.81%,创指涨2.03%:两市成交17210亿元
- 巴西宣布加入“欧佩克+”

- 杜甫的诗《蜀相》中,“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上一句
- 网络流行语,指孩子回到学校上课的日子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