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像哲学和文学批评,科学批评是研究者所寻求的
物理学家、哲学家马里奥·邦格(Mario Bunge,1919—2020),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通晓西班牙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1966年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1992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士,2014年获颁“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复杂性思维奖”。他一生共写了500多篇论文和120多本书,其著作在科学哲学圈有很大影响力,代表作有《基础哲学论》。
在邦格的《搞科学:在哲学的启示下》一书中,他考察了发展中的科学,即自然、社会和生物社会科学的实例显示的过程。他关注科学的研究过程及其哲学前提,并主张哲学前提构成了构思和孕育科学研究计划的某种母体。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该书中部分内容。

马里奥·邦格
经典的思想史家受到了正确的批评,说他们只集中注意山峰,而忽视了山峦,就像把一个城市只限于摩天大楼。与此相对照,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团队工作,而不重视个人的天才,甚至主张“社会通过个人来思考”,似乎社会有集体的头脑,并有完全的记忆和理论。
从孤独天才到研究团队
在20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普遍认为是该世纪或者甚至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近来,有些低劣的尝试想降低他的地位,声称他的相对论是他的亲密朋友圈集体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他的第一个妻子米列娃·马里奇,他以前的同学马塞尔·格罗斯曼和他的朋友康拉德·哈比希特、毛利斯·索罗文和米歇尔·贝索,后者是他在瑞士专利局的唯一同事。有人还提到亨德里克·洛伦兹和亨利·彭加勒已经知道洛伦兹变换,这被看作是狭义相对论的签名。所有这些是真的吗?爱因斯坦自己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可以简述如下。第一,狭义相对论是麦克斯韦的经典电动力学的顶峰。不用奇怪,那时候别人,特别是洛伦兹和彭加勒已接近它。但是他们缺少爱因斯坦年轻人的勇气去重建力学,所以它的基本定律是洛伦兹不变式,同电动力学中的那些相像。
正如爱因斯坦自己所说,狭义相对论可以由别的几个人来建立,相反,广义相对论只有他能够建立,这是他的引力理论,因为那时没有别人研究引力。
第二,当然,爱因斯坦同他的妻子米列娃,一位失败的物理学家,以及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讨论过他的新思想。但是后者的贡献却是不相称的:其中格罗斯曼是主要的,贝索是边缘的。确实,格罗斯曼教他的朋友建立广义相对论所需要的数学工具,即绝对微分几何或张量演算;两个人的科学协作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他们合作写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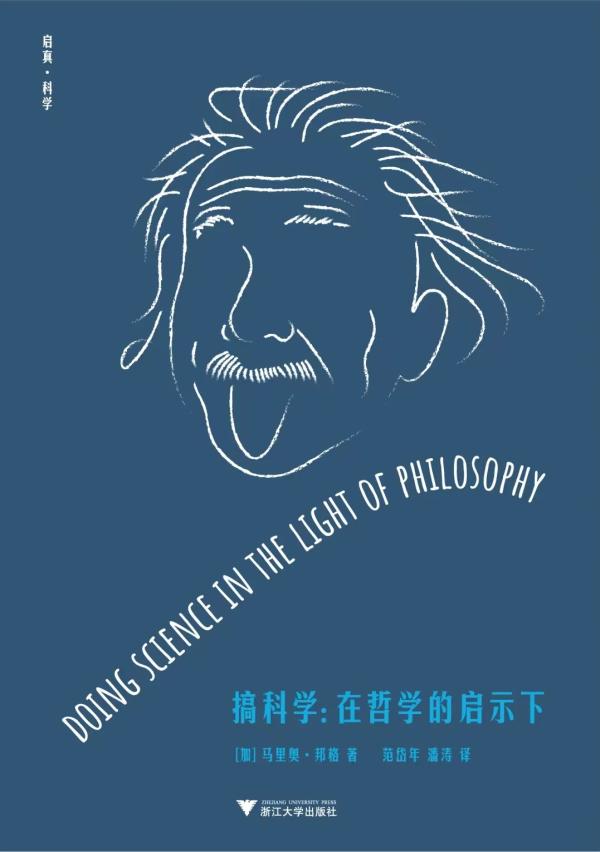
《搞科学:在哲学的启示下》
相反,贝索的作用,用爱因斯坦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夸张的朋友,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乱出主意的人。尤其是,贝索徒劳地试图让比他更年轻的朋友皈依马赫的现象论和操作主义:爱因斯坦仰慕马赫的实验技巧,以及他的简略的时空关系的观点,但他像玻尔兹曼和普朗克一样,是马赫主观主义的尖锐批评者,也是科学实在论的早期辩护者学术界的女性主义者主张,爱因斯坦从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那里窃取了狭义相对论。这个主张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没有说明狭义相对论只是他在1905年他的奇迹年所精制的四个原创性思想之一。它甚至没有说明为什么米列娃没有被邀请参加非正式的奥林皮亚科学院,这是爱因斯坦在1902年同康拉德·哈比希特和毛利斯·索罗文一起创立来讨论物理学和哲学问题的地方。
学术界的女权主义者还主张希帕蒂亚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但她们没有告诉我们她有什么成就。更新近,同一群人主张英国晶体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应该同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因发现DNA分子结构而同获诺贝尔奖。无疑,富兰克林确实对那项发现有所贡献,但其他人,特别是莱纳斯·鲍林,确实对同一计划做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但是只有克里克和沃森得到了获奖的答案。
总之,出成果的科学家并非孤立地工作,而是植根于过去的网络中的成员。甚至隐居的牛顿也不是孤立天才。事实上,我们从萨缪尔·佩皮斯的日记知道,他的思想,主要是他的问题,是在佩皮斯的圈子里讨论的。总之,伏尔泰在崇敬牛顿这件事情上是十分正确的。
研究团队
直到新近,大多数研究计划涉及单个研究者,有几个合作者辅助,他们的贡献在报告的末尾致谢中。从1950年左右起,典型的研究计划涉及主要的研究者和几个合作者,通常是他/她的博士生或博士后的学生,他们都被承认为合作者,获得同样的荣誉。实验粒子物理、天体物理、遗传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的研究团队增长到涉及一百个以上的研究者。有时候,一篇科学论文要有一百个或者甚至一千个研究者署名,以至于他们的名单,按字母顺序排序,要占科学期刊的一个整页。这类合作研究称为大科学,标志着与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小科学的区别,而小科学的主要研究者从申请资助开始,拥有全部荣誉,承担全部责任。
但是,理论研究不管多重要,仍然主要是个人的任务,单独地做,虽然在讨论班里讨论。一位理论家很少有机会被聘请来领导一个大的研究计划,那样他就不能做原创性的工作,当他的管理任务结束时也不能继续以往的研究。J.罗伯特·奥本海默在担任“曼哈顿计划”科学主管前后的生涯正是这种情况。
科学争论
科学研究计划从开始到终了都公开接受批评。但是,不像哲学和文学批评,科学批评是研究者所寻求的,因为它是特别富有建设性的:它由具有共同背景的同行执行,目的是要完善正受考查的工作,而不是一诞生就要用锐利的评论杀死它。
艾萨克·阿西莫夫称这类批评为内部异端,这与科学姿态的敌人的典型做法外部异端正好相反。内部异端的明显例子是,麦克斯韦对安培的超距作用的电动力学的批评,爱因斯坦对经典力学的批评,史蒂芬·J.古尔德对“自然不作跳跃”这个教条的批评。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批评为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论以及更新奇的实验铺平了道路。外部异端,即非专业人员的破坏性批评的一个例子是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这些著名的作家米歇尔·福柯和布鲁诺·拉图尔所进行的反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战役,后者是对罗伯特·K.默顿亲科学的科学社会学大规模攻击的领袖。
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变革的观点,可以认为独立于辩证法之外,而且可以看作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它假说物质利益,而不是思想,是社会行动的主要动力。这个观念对生命和人类的起源问题,以及对人类学、考古学和编史学有好的影响。例如,历史唯物主义提示人类学家,他们应该从研究他们的对象如何生存开始,而不是从研究他们相信什么和他们如何使自己快乐开始。它也发现了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根源在物质利益,例如在古代是控制贸易的通道,中世纪是为了土地,而近年来是为了石油。
唯物主义对编史学的另一个有益的影响,是揭穿特工部门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神话。真实的情况是,几乎每一次军事情报上的收获都被另一方的胜利所抵消。正如军事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所详细表明的,情报和假消息对军队只起辅助作用。
尽管情报也有助于赢得若干战役,但这次大战是靠斯大林格勒的苏联军队赢得的,而不是靠布莱奇利庄园的密码破译者。日本人的求和是在它的平民遭到燃烧弹的轰炸之后,甚至在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炸平之前。现代战争尽量利用头脑和肌肉,但它不是一种精神追求。因此,既不是薪金,也不是理解,它是诠释学的练习。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对编史学有好处,更有价值的是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和首先是费尔南·布罗代尔领导的年鉴学派的通史。这些科学家从研究物质起源开始,但也没有忽略政治和文化方面。
后现代主义者的滑稽模仿
直到20世纪50年代,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是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的任务,他们想发现有关科学(这是很著名然而又令人迷惑的野兽)的真理。回忆一下下列这些人所做的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就够了:约翰·赫歇尔、威廉·休厄尔、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皮尔逊、亨利·彭加勒、埃米尔·梅叶尔森、弗德利格·恩利克、皮埃尔·迪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卡尔·波普尔、毛利斯·拉斐尔·科恩、爱德华·迪克斯特惠斯、I.贝尔纳·科恩、李约瑟、查尔斯·吉利斯皮、恩斯特·纳格尔、理查德·布拉斯维特、艾因诺·凯拉、阿尔铎·密利、乔治·萨顿和罗伯特·K.默顿。
默顿在他的1938年的经典论文“科学与社会秩序”(发表在年轻的刊物《科学哲学》上)指出,基础科学的特征是无私利性、普遍性、认知的公有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不是孤立的研究者的怀疑,而是整个共同体的建设性的审议。

罗伯特·K.默顿
不像他的批评者,默顿不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是第一位职业科学社会学家。他的老师是当时的权威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乔治·萨顿和塔尔科特·帕森斯——以及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劳伦斯·亨德森,他拯救并普及了社会制度的概念。除此之外,部分由于他的妻子和同事哈里特·朱克曼,默顿认识了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告诉他是什么使他们行动,他们也从默顿那里知道,他们尊敬的科学共同体为什么有时鼓励他们,有时抑制他们。
总之,在1950年左右,默顿被公认为科学研究群体中最有学问的成员。他的研究也是他们之中最均衡的:默顿虽不是唯心论者,但他是唯一一个强调基础科学研究者的无私利性的人;而他虽不是实证论者,但承认科学的累积性,并且,他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强调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嵌入性,并且它受制于政治压力。
突然,在1962年,一位无名气的科学家托马斯·S.库恩在他的畅销书《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主张,科学家并不寻求真理,因为没有这种东西,也没有知识总体,知识在成长,并被修补,并日益深刻。他的中心命题是,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科学革命,革命前的一切都被扫除。尤其是,这种激进的变革不会解决长期存在的科学问题,而是对时代精神,或是对当时的流行文化中的变化做出反应。因此,科学家既不要确证也不要否定任何东西,而要像他的朋友和同志保罗·费耶阿本德宣扬的那样“怎么都行”。总之,这些虚无主义者向流行的科学观挑战。
由此开始,任何业余爱好者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就可以在许多“科学研究”中心或“科学与社会”纲领中找到工作,这些机构在过去几十年大大地增加了。
这场反革命规模是如此之大,来得如此突然,在学术界引起了风暴和惊讶。自那时起,所谓的科学大战也兴起了,更多的是噪音,而不是光明。澳大利亚的戴维·斯托弗是讽刺它的很少几个哲学家之一,但他提供的替代方案——回到老式的经验论——并没有说服任何人。只有阿兰·索卡尔发表在《社会文本》——它曾称赞库恩-费耶阿本德政变——上滑稽的恶作剧《超越边界:走向量子引力的变形解释学》告诉公众,他们被一帮小丑愚弄了。
我自己的对库恩-费耶阿本德反革命的哲学根源的详细研究几乎没有受到哲学界的注意。默顿关于基础科学的现实主义形象被大多数元科学的学生抛弃了,他们从右边和从左边,拒绝了纯科学的观念。
科学主义,一个世纪以前在人文主义阵营富有活力并有威望,现在变得衰弱和失去信任,在那里,弗里德利希·哈耶克关于它的有偏见的定义“试图在社会科学中模仿自然科学”广泛流行。近来流行的另一个对科学的误解是米歇尔·福柯把科学的特征古怪地描述为“不择手段的政治”——一个因多米尼克·雷瑙特对许多著名的科学争论的仔细研究所打破的神话。他证明,所说的争论是有关真理的,不是关于权力的。而最终是真理获胜。
这种情况的主要理由是科学研究寻求原初的真理,而不是实际的利益——技术的目的。例如,关于量子论是涉及物理对象还是只涉及测量操作的争论,是纯粹的认知问题:在近一个世纪的争论中没有一方有任何东西与意识形态有关。与此相反,社会科学中的某些争论提出了意识形态问题。例如,标准的经济理论因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而公正地受到谴责,因为忽视了不平等和表扬了自私;由威廉·狄尔泰所倡导的社会唯心主义哲学的罪责是忽视了物质需要和利益,特别是穷人的物质需要和利益。
真理,而非权力,同所有这些案例有关,也同雷瑙特所讨论的那些案例有关,是偏爱科学主义的一个立足点——孔多塞的命题,无论研究什么,最好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也是反对“人文主义”学派固有的直觉主义的立足点。
那些多产的社会科学家并不认为他们的学科是精神科学,需要它自己的方法,诸如狄尔泰1883年在他的反科学主义宣言中所赞扬的理解或神入的理解。确实,把自己放在A的地位(不是平凡的表演!)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A思考或B思考,但它不能说明B自身。同样,把A放入他/她的社会语境中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B要么被机构承认,要么被机构压制,但又是,它没有说明B自身。公理系统,确定一个理论的中心思想,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科学是自我推动和自我服务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