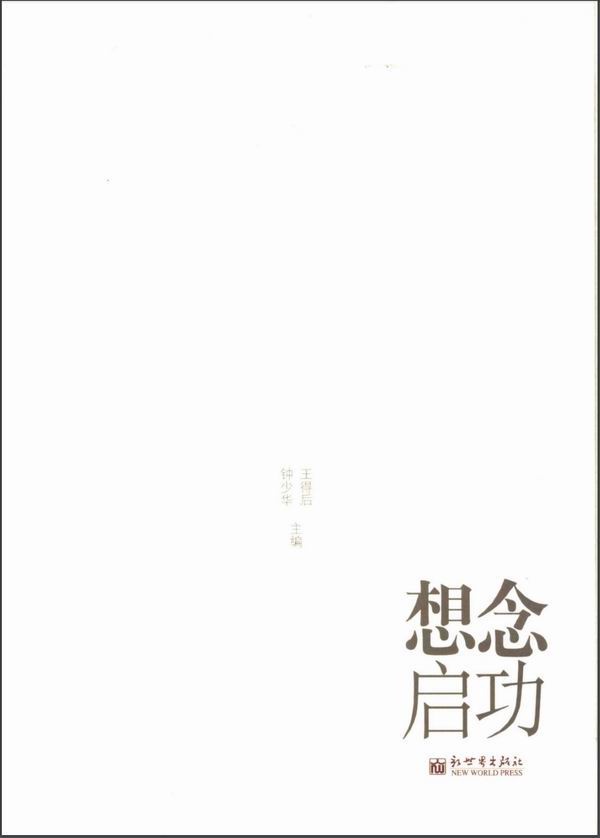10月
《我的书店:作家畅谈自己钟爱的书店》,[美]罗纳德·赖斯编,赵军峰、郭烨、赵安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9月版,48.00元。
整本书似乎只有一个作家对书店的感觉比较平淡,亦即他可以不去书店、不在书店买书。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有比网上书店更便捷的买书方式了。不过话说回来,对作家而言,书店是他们的作品接受读者检验的地方,是他们的新作推广的地方(尤其是这些西方作家并没有什么作协支持),他们爱书店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我的书店”这样的题目,要真有一本由读者来谈自己钟爱的书店,是不是会更真实一些?
我是用iPad读的,对这本书来说也是相当的悖论了。
《岭南书法史》,陈永正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13.60元。
以今天的出版眼光来看,此书黑白图版,状若复印,实在有些简陋。但岭南书法的整体面貌、内在流变,岭南书家之风气走向、成就大小,此书交足功课,做出了承前启后的研究工作。这是不管有没有清晰图片都无损其价值的一本书。写作此书时,作者正值盛年,用书法的评语来说,可谓是真力弥满。本书的每个专题章节都可以单独成文,对与书法相关的金石篆刻亦论述精当,在资料远不如今天齐备的九十年代,殊为难得。对当时在香港大学艺术系任教的庄灵所撰《广东书法简史》,本书有好几处不同意见,甚至谓“庄氏之论,自是门外之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与作者长期亲炙岭南名家如容庚商承祚等书坛艺林老辈有关。我相信,作者的某些论述,是来自一种师承之间的大体看法,这种文艺批评的总结,用今天的眼光看即使不怎么“规范”,其中的闪光处,也不是靠材料与理论者可以想见。这种研究方法,也是与现在的学人只研究文献资料不一样之处。作者在后记中说:
历代的岭南文人,由于僻处海隅,少与中原人士相接,加以他们深自敛抑,不善表襮,故其人其作,往往没世而无闻。其实岭南文人所取得的成就,比起同时期中原、江左的名家,不一定逊色,有时甚至凌而上之。这是我近年从事岭南文献研究,特别是主编《岭南文学史》后感受颇深的一点。
《红杏山房集》,宋湘著,黄国声校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4.90元。
因为要编一本宋湘的书法集,在网上买了此书做资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有名的“岭南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以整理岭南的古籍文献为主,特别是一些稀见的笔记、诗文集,开创先声,后来却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像此书也是最近听说有出版社出新版。可惜这套丛书早已经没有了下文,当年整理的一些著作,现在又成稀见版本了。
读宋湘的诗和书法,可以深刻感受到与他的前辈,如屈大均、陈恭尹之间的不同,诗、书都不再因人而重、因人而传,而是转为抒发自己心灵怀抱的工具。读与他同时期的张问陶的诗歌书法,同样如此,非独岭南诗人而已。大约社会安定,康雍乾以来的文字狱也消停了,是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大背景。这两位的崇拜者代不乏人,书后也辑录了大量的评论文字。前几天偶翻杨守敬的《学书迩言》,里面也是将这两人放在一起评论的:“乾嘉间之书家,莫不胎息于金石博考名迹,惟张船山宋芷湾绝不依傍古人,自然大雅,由于天分独高,故不师古而无不合于古。”“自然大雅”四字评论宋湘的书法是再合适不过了。
《旧京遗事 旧京琐记 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版,1.05元。
前一阵在豆瓣上看到一篇书评,谈论晚清时住在北京的日本教师船津输助的通信集《燕京佳信》,其中提到中国人的人情虚伪,其中有丧礼上客来主人哭、客去则谈笑如故等等怪现状。其实这些在中国人的笔记里早有记载,夏仁虎的《旧京琐记》开篇就是记北京的俗尚,其中便提到满人在丧礼上的这种“讲礼”。风土记这样的记载并不仅仅是保留了民众世俗生活的记载,而是作为历史,能予后人观照世事。每次去北京,都能在这个并不方便也不精细的城市,感受到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东西:何以这里成为了人文荟萃之地,人物流散而掌故不绝?它又是以怎样的优势吸引各个阶层的人在此谋生?成就这样一个人文荟萃之地,不是无因的。这些琐碎的记忆,有时候在后人看来也正是历史。
《苏忍尼辛选集》,刘安云译,台湾东大图书1988年1月二版。
苏忍尼辛,即大陆翻译的索尔仁尼琴,本书是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诗合集,有刘述先导言一篇,短篇小说六篇,散文诗十六篇。因为“苏忍尼辛”这个名字之故,他的小说难免会被套上简单的标记,比如压迫、苦难、控诉。这组散文诗似乎在大陆翻译的索尔仁尼琴著作中未见到,这组作品重要的不是可以见到他的不同体裁的文风,而是这种抒情性、自然主义(当然其中免不了也有“控诉”)的描写,就像《在耶斯林乡间》一文中写道的:
造物者所打进这间茅舍里的是何等样的晴天霹雳的天才,打进那急躁的乡村孩子的心中,那震撼使得他张开眼睛看到如许的美——在火炉边,在猪栏里,在打谷场上,在田野中,那千年来只是被人践踏、忽略了的美。
11月
《金蔷薇》,[苏]巴乌斯托夫斯基著,李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9月新一版,0.62元。
读这本书,又想起了初学写作的日子,尽管当时读的似乎是戴骢译本(《金玫瑰》)。如果按照现在的某些阅读习惯(遇到直接引语的回忆录、传记就放下),那么是不会读了。苏童在回忆阅读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经历时,大概说过,塞林格是一枚用旧的纸币。这种感觉和心情很适合重读巴乌斯托夫斯基。
《想念启功》,王得后、钟少华编,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版,42.00元。
微信圈关于书画名家的字画、掌故、乃至段子,阅读量总是很高。启功虽然比不了隔三差五就被卖萌的齐白石,但是关注他的粉丝多少是行内人,看今年北京的启功藏品展就知道。也正是因为没去看这个展览,将他过世后,友朋学生后人所写的纪念文集读了一遍。本书编者之一钟少华是民俗学家钟敬文的哲嗣,因为世交的关系,启功待他非同一般后辈,两家又住得近,因此钟少华便熟悉启功的日常生活。本书最后一篇便是他的日记中有关启功的辑录,保存了启功不为一般人所知道的故事、性情。前几天也是在朋友圈读到赵珩先生写学者袁行云的文章,其中提到袁住院,启功不仅掏钱,还给相关的医生都送字。启功虽然幽默的段子不少,但是细读之下,往往能见到大家的风范。
《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杨逢彬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40.00元。
最近读楚泽涵先生关于他父亲楚图南的文章,发现他的母亲原来是杨树达的外甥女,还有个姨丈是穆木天。当然相比这本由杨树达的孙子所撰写的回忆录,里面的人物关系就更复杂了。杨树达的几个子女在反右、文革中的遭遇,其折射文化世家的升浮,更觉深刻。
《罗孚友朋书札》,高林编,海豚出版社2017年8月版,112.00元。
罗孚是香港与大陆文化交流的一位推动者,即使在他北京居住期间,仍然撰文著书,联系两地。他是最早向大陆推荐董桥的人,这本书里收录了董桥写给他的信,每每以“罗先生”或“罗公”称呼,尊为前辈,而两人都是报人,特别是对写作、书画都有兴趣,因此这些信札读来,虽然散漫,却极富趣味,同道之间的惬意,溢于言表。这批信札虽未释读,但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代词宗夏承焘轶闻》,吴思雷编撰,自印本。
这是一本有意思的小书。作者是夏承焘的好友吴鹭山的哲嗣,也即夏后来的妻子吴无闻的侄儿。这本书以编撰的形式,收录了关于夏承焘的一百八十多条掌故、逸事,比如年轻时他与王季思同事,戏称王为“王老虎”,晚年夏承焘记忆力衰退,王季思见他便每每自称“王老虎”。书中还以补白的形式刊载了夏承焘的大量用印和书法作品,在今天看来,夏承焘的书法尤其不是“馀事”。
12月
《墨海生涯记》,王学仲著,中华书局2017年7月版,22.00元。
王学仲曾师从徐悲鸿李可染等人,此书为其自述学书经历。他生长在齐鲁大地,碑碣文字随处可见,加上自幼家中有学书的爱好,内外熏陶,他也走上了研习书法的道路。并且喜好传拓,他所拓的汉画像石拓片,经人送至天津古文字学家王襄处,王襄写成了《滕县汉画像石记》,刊发于燕京大学学报上,这位第一代甲骨文专家当时并不知道这批拓片的椎拓者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后来到北京入学京华美术学院,结识的艺术家就更多了。因此书中也记录了很多相关的细节与掌故,如吴镜汀的阿芙蓉癖,黄宾虹养的大鹅,张伯英的书论等等,都生动有趣。王学仲一生醉心于书法艺术,其人生经历亦颇丰富,此书称得上一部艺术回忆录。
《槐市书话》,拓晓堂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版,58.00元。
作者原供职于国图善本特藏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担任嘉德古籍部总经理。此书中文章,大部分是介绍其经手、经眼的古籍善本。如陈澄中旧藏、胡适存札、鲍耀明藏周作人书法文献等等。“阅书感想”一辑质量较佳,如《关于佛经版本的断想》。作者在自序中交待,槐市为汉代长安城东南定期聚散书籍的市场,以其地多槐树而得名,是最早的书籍交易市场,成为最早的书肆代名词。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梁培宽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版,128.00元。
“这个世界会好吗”,是一代大儒梁漱溟(1893-1988)历经晚清、民国、近代各种历史风云的总结,这句话已经被简化为一般人对于世事的感受。作为曾经当面顶撞过最高领袖的学者,梁漱溟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同情与尊重。这两本厚厚的往来书信集,还仅仅是劫馀文献,已经足征他经历的丰富性,呈现的人生也很复杂。书信往来,平实而已,不能与他的胜业乡村建设、著书立说相比,但其中探讨学问,特别是保持了终生的学习态度,在平实之中又给人以深沉的感染力量。为学问的一生,也是这部书信往来不同于其他学人书信集的特征之一,也是因为这种向学的精神纽带,联结了他周围的一批人,梁培宽先生在“辑录者前言”中提到的“创造朋友团体”,可谓精准的提炼。
《海上书画人物年表汇编》(一),乐震文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版,68.00元。
这本书有着匪夷所思的人名错误,或许可以归结为校对不精,就像豆瓣上某位豆友的评论,错别字不妨碍我们阅读(我们可以忍)。尤其是对于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来说,这些人名错误大概都是能校对出来,可以当做上一堂书画常识课。平心而论,对于一本粗制滥造的出版物,确实没有再恶评的必要,不过,就我的感觉而言,此书不能不说是重视文献、材料的,看旁征博引的索引就知道,但是像错误最多的陈巨来一文,很明显的就是以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加吴湖帆的《吴湖帆文稿》中的日记部分,敷衍而成,令人惊奇的是,在“敷衍”的过程中,撰写者甚至连主语都不更换就上马了——前人著书,特别是年谱,尤其重体例,既不是什么材料都能塞进去,也不是编撰者什么议论都可以发出来的。相比错别字,这种迷信材料又连一点甄别能力都没有的著述,更让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