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聚焦 | 大学生活 没有指南

九月校园,新生们包裹在迷彩绿中,一连一队军训,很快她们将接触到口耳相传的“大学生活指南”:要关心绩点,加入社团,广结朋友......
学长学姐们大多听着这些开启四年,杨婵最初也是这样想的,她拼力想成为指南里标准的大学生,却屡屡受挫——绩点卷不赢,社团面试失败,定了交友KPI、加了很多人微信却没交到真正的朋友,指南为她指出的方向使她精疲力尽,所获寥寥。
新新报记录了杨婵的挣扎与挣脱,大学四年,她花了两年才与“指南”中的标准大学生和解。有了喜欢的运动、要好的朋友和抒发情绪的渠道,她终于找到一点落地的感觉。
或许大学生活并没有一个适用于每个人的指南,指南之外,是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

2020年9月,19岁的揭阳女孩杨婵与学姐们拼同乡会的大巴车,摇晃了5个多小时,在下午到了深大校园,下车后忍不住呕吐。狼狈之中,她在陌生的校园中开始了第一周。与其他新生的好奇或希冀不同,她想起那一周,只有焦虑,和延续至今的尴尬。
开学第一天,她就遇到了难题。跟着室友走完报道、吃饭这些流程后,她要独自去解决问题——将新买的电脑连上网。
“宽带”、“网线”、“转换器”,靠着百度,她被这几个词汇搅得稀里糊涂。
电脑和接口间需要一条网线,杨婵跑去商场,买回来发现一米短了,再跑去买回两种,卷成一团的那种无从下手,送了朋友才知道拉出弹回很方便。杨婵自己用了另一条2米的网线,拖在地面上,三年里杨婵无数次踩到它,想起入学那一天的慌乱。
连接,输入账号密码,出错;连接,再输入账号密码,仍然出错。
冷汗浸透衬衫后,她第一次打开了校园网,红色页面弹出那一刻,她强忍着不让眼泪飙出来。
手机也带来很多麻烦,宣传社团的学姐很热情地递过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杨婵开始回忆前几天刚学过的“扫一扫”。
她可以瞬间记起十几个政治大题答题模板,但此刻忘了怎么扫微信。
“十九年来,我第一次尴尬到想要大哭一场,”她抠着手指,三轮车的吱呀声从记忆深处响起。
八岁那年,杨婵在台式电脑上注册了人生第一个社交账号,9个数字组成的QQ号,小姨帮她取名“小龙女”,当时很火的动画片主角。
“我初中同学的号码都是十位数,我的更早”,可是,“小龙女”的头像很快变灰了,一沉寂就是11年。
父亲把那台电脑放进堆满废旧家电的三轮车后备箱,当着她的面,三轮车消失在长长的小巷尽头。三轮车脚蹬子摩擦的吱呀声,夹杂车喇叭的嘈杂声,却留存了很久。
10岁的杨婵被送进寄宿学校,直至高中毕业。
“我失去了我的电脑,再没有碰过网络。我和这个社会脱节了。”
大一新生杨婵从封闭中被放出来,遭遇了完全陌生复杂的大学。
入学班会上,同桌两个女孩染了金色头发,前面女生斜挎着黑色皮包。杨婵第一次觉得黑色高马尾和双肩包不合时宜,甚至是扎眼。
班主任让每个新生上台自我介绍,她费力想了很久,完全想不起特长和兴趣,同学讲述初中暑假的旅行趣事,她勉强想起,那个假期她在补课,第一次穿了改短一点点的校服,却从没穿过裙子。
同学们三三两两走在一起,谈论学校对面高耸的闪着光的玻璃大厦,谈论新做的美甲。谈论同色系的饰品和长袜,要如何搭配短裙或短裤。
杨婵看着眼里有光的女孩们,妆容藏着女生的小心思——眼线若有似无,粉底熨帖得仿佛天然。短短几天,她们变成了深圳这个年轻城市的一员,并且看起来理所应当。
杨婵为臃肿的小腿纠结着,新裙子只在开学那天穿过就脱下了。她为开学前选了圆形黑框眼镜懊恼不已,为什么没选那副金边眼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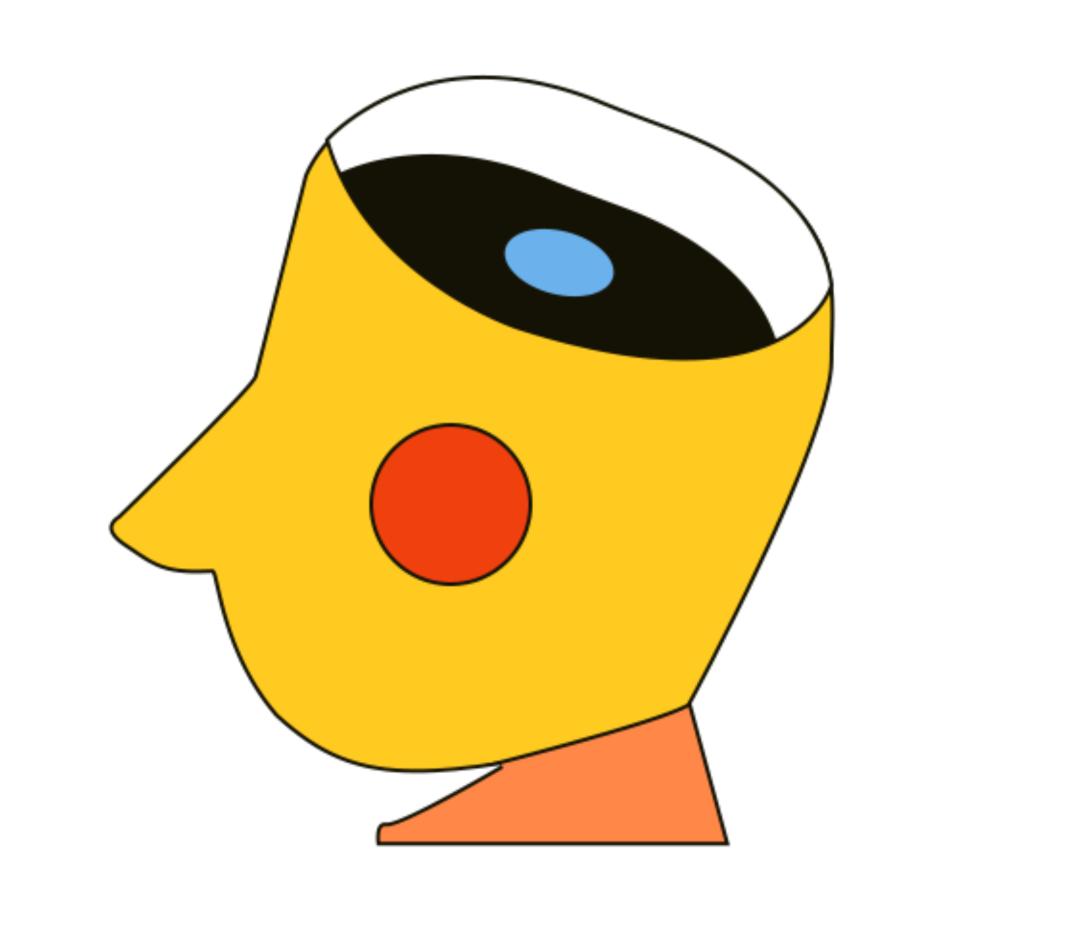
十几年里,她没有做过什么选择,初中到高中,几乎是同一种生活。
起床,排队,跑操,早读,上课,吃饭,晚自习,回寝室。无波无澜。
为了她的学习成绩,家里人十几年没有购买过智能机;除了冬夏两身校服,杨婵的衣柜里没有其他衣服;食堂饭菜每周重复,她吃了六年,偶尔面无表情挑出细钢丝;社团是普通班学生专属,杨婵所在的重点班被明令禁止参加;社交是耽误学习的,她没有聊得来的朋友。
文理分科,填报高考志愿,她把选择权完全交给了父母。“选择”两个字让她感到恐慌。
“不是数学选择题的那种选择,而是现实生活中那种对自己可能会有重大影响的选择,我很不擅长,或许有点选择恐惧症。逃避,或者让渡选择权,我几乎只会这样。”
“我只要学习就好了,只要考上大学。其它的事情交给爸妈和学校规章制度。”
2020年秋天,大一新生杨婵不得不依靠自己,学习适应,学习选择,走出社会化第一步。她扮演着“大学生”的人设,按部就班跟着听来的“大学指南”走。

杨婵面试了三个社团,前两个是热门社团,不敢选新媒体运营,她挑的都是别人口中“卖力气”的岗位。
她对体力也没有十足信心,认真读了宣传资料、编造了一大堆兴趣和特长、看了一堆面试技巧。
面试官面前,杨婵不敢让问题与回答之间有一秒的间隔,怕自己露怯,也怕气氛尴尬。
第三个社团她没做准备,她提前打听到这个小社团严重缺人,只要交点费用,每周一起喝茶聊天。
“室友们都在社团,我没加的话怪尴尬的,我不喜欢去社团聊天,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社团。”
杨婵开始尝试交朋友,给自己定了交友kpi——一周至少加十个人微信。
为了kpi,她尝试着和同班同学、社团同学去亲近,饰演一个随和大方的角色。刚开始杨婵为自己独立交到朋友的进步感到骄傲,也真拿到很多人微信号。几周过后,她开始在社交中感到无力。
“我并不觉得有发自内心的亲近。每次聊完天,走在路上或躺在床上,我都会开始复盘,今天说了什么话,有没有冒犯到他们。这样的复盘让我感到很累。我开始厌恶社交。”
挣扎了几次后,大二上学期,她和很多微信好友互删,退出了社团。
宿舍里不知谁第一个装上了围帘,杨婵迅速跟进,买了最长的1.5米的帘子,在宿舍打造出一个严实封闭的个人空间。
拉紧床帘,戴上耳机,把音量提到中挡位,打开B站,杨婵开始看一个日更up主煮菜带娃的日常。
“室友买新耳机时会找我,她们真的觉得我的耳机隔音效果很好。”
在没有课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B站、豆瓣和微博,前段时间迷上了小红书。这些没有熟人的平台让她觉得很自在。一天时间她能发十几条微博,相反,今年八月她只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对熟人社交的情绪与其说是讨厌,不如说是害怕。”但在没有熟人的平台,她很热衷于记录自己的心情和日常。
她说,朋友圈的自己是展现出来的自己,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里的自己才是真正的那个自己。
“其实也是在逃避吧”,每天早上八点半,室友燕华背着电脑包出门的时候,杨婵也从睡梦中醒来,听到关门声,她开始感到心慌无措,“知道别人在忙,但是不知道别人都在忙什么的时候是最焦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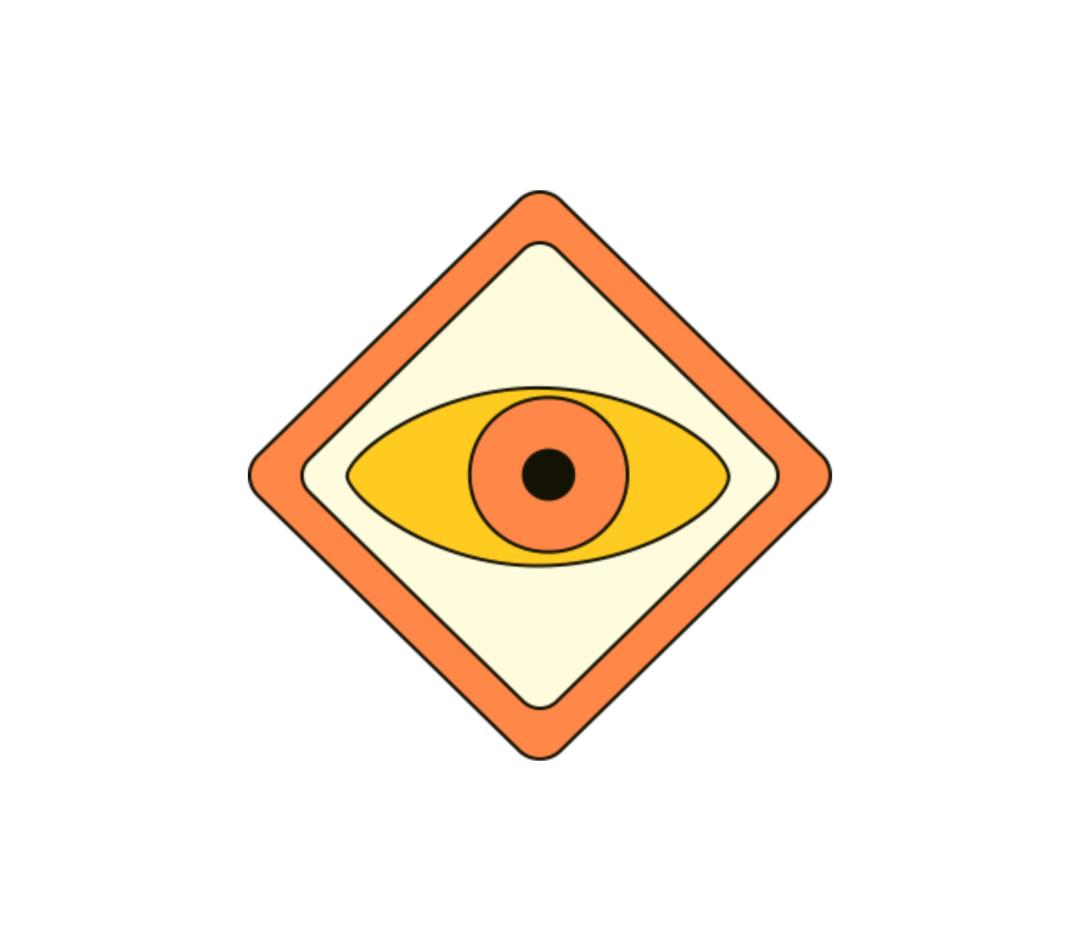
杨婵和燕华的交往并不算多,燕华早上离开宿舍,晚上十一点才回到宿舍洗漱,很多日子都是这样。
燕华是杨婵眼里最标准的大学生——绩点高,拿奖学金,学生会干部,穿衣打扮得体大方,学习非常自律,有好几个能力很强的朋友。
这些各具能力的朋友,有的从社团认识,有的来自上课分组。她们从大一下学期在一起做小组作业,不出意外的话,这也是她们大四做毕业设计的阵容。
燕华从小到大都是受人注目的好学生,成绩好、会弹钢琴、性格文静。顺风顺水了十二年,她经历的唯一一次挫折是高考失利。
高三上半年,有深大的师兄师姐到班级宣讲,发了一个印着深圳大学字样的笔袋,她带着上了高考考场,心里预想着,不能低于笔袋上的大学。命运使然,她来到被当作底线的学校。
“当好学生”已经成为燕华的习惯,这一次的失利她想要用其它的办法弥补,例如成为一个名校研究生,最好能通过保研的方式。
入学后她很快摆脱迷茫的状态,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像之前的十几年一样,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两年里,杨婵在无数个早晨听着燕华的关门声,有一次听到她不无遗憾得说,“你信吗,我还没有去过欢乐谷”。

前两年杨婵住在乔院,宿舍楼旁有一个生锈的小门,门外的世界是城市凹下去的一个角落,大家喊它城中村。
第一次沿着楼梯走下去的时候,杨婵觉得这里是任意门外的世界。
格子间商铺里,大叔操纵着三个锅煮面,游刃有余;小卖部前台,烫羊毛卷的大妈操着潮汕味的普通话在大声讲电话;街角踩缝纫机的阿姨头顶的灯光忽明忽暗,她戴着老花镜凑得极近;看手机的过路人、阳台上刷牙的年轻人、呼啸而过的摩托车,汗臭味、苹果味、汽油味、垃圾味、生肉味,交织、分离,具体又朦胧。
充满烟火气的场景让杨婵瞬间回到千里外的老家乡道。
用胶布粘着裂痕的脏玻璃窗倒映着她看到的自己,黑框眼镜、高马尾和臃肿的小腿。居然和周围的一起不突兀。
大一她有时做梦,梦到大嗓门的楼层宿管,梦见饭里的钢丝,梦见雨季下水道旁白色的浮沫,梦见二层小楼和路边浇花的阿姨,梦见涂鸦的墙壁和玻璃窗。梦境里,她分不清是高中学校、是老家乡道、还是几十米外的城中村。
“我整个大一都无比想要回到过去,回到那个一条路走到黑的日子”。
大二时杨婵去做义工时,遇见了比自己高一年级的女孩吴可。吴可成为她生活中特殊的存在,彷佛一条从生活的井里攀上来的绳索。
“吴可是我身边的人里我最羡慕的,因为她总是快乐的。”
吴可熟知学校里每一个漂亮但是没有什么人的犄角旮旯。她们每周至少见一次面,两人走过校园这些地方,然后去城中村吃竹升面和炒酸奶。
“我原以为学校没什么值得热爱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的秘密基地算是。”
吴可把杨婵的焦虑情绪归因于社交环境。在分宿舍的时候,吴可很庆幸自己能够分到三个和自己相似的室友。没完全适应大学环境时,她已经收获了三个可以谈天说地的朋友。
三年多来室友们一起逛街、吃饭、旅游,学习的时候一起组小组。“(我们)对自己的专业也不感兴趣,卷的时候一起卷,摆的时候一起摆。这样确实会少很多社交压力。”

杨婵感受得到同学们的“卷”,目标是电视台记者的郝离在大二就加入了“卷王”大军。
“大一努力交朋友,努力多读点书,大二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无论什么事情,我觉得有挑战的,我多往前冲一冲。”郝离的那股冲劲仿佛回到高中。
“我太需要外界的肯定了,有可能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很优秀,很容易可以得到他人的注目,但是到了大学哪有这么多人不断给你肯定,也不像高中一样,动不动就考试,考试之后就有成绩。”
在“卷”的一年之中,郝离常常陷入自我怀疑的困境里。“我感觉那时候自己有点本末倒置了,我需要想想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横冲直撞的一年里,郝离尝试过很多东西,她喜欢看各门各类的书,每天写作,试着摄影。“最开始只是迷茫状态下为了让自己有一技之长所做的努力,但是在做这些尝试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和新闻不谋而合。新闻是个很包罗万象很美妙的专业。”
杨婵没法像郝离一样,为了专业疯狂。吴可劝慰杨婵,“你心里觉得做这件事会让自己收获快乐,那你就去做,如果不能就果断退出,这种事是不能勉强的”,杨婵深以为然。
大四的吴可出去校外实习,和杨婵减少了见面时间。杨婵自己去学习了游泳,新买了泳衣,她约了其他的同学,等学校游泳池开了就去。

“今天你努力了吗?”
杨婵点开豆瓣小组,n条相同内容的信息挤出屏幕。
杨婵加入的这个豆瓣小组叫“躺平后起立互助联盟”。小组里的成员互相监督各自的“起立”进度,杨婵有时候也会在里面分享自己的“勇敢起立”的经历,小组称之为复建日记。
被同龄人卷到的时候,杨婵习惯于在这个网络上的小社区里寻求安慰,平时这里是她打鸡血的地方。
大二到大三的一年多来,杨婵习惯了不去追求“指南标准”,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
小组作业她会找最后没有组到队的同学一起做,被安排到什么任务就去做。如果作业获得高分,她会为自己的付出而骄傲;如若低分,她也会安慰自己,“我只是团队里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角色,或许主要责任不在我。”
她偶尔会和吴可或和室友一起吃饭运动,吴可备考公务员后,她更多时候一个人行动。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去南山博物馆看展、一个人去看音乐节。
“当我发现脱离集体的生活让我觉得很自在时,我突然发现那些大学生‘应该’做的选择,其实很多是可以放弃的,我可以不社交,可以不化妆、可以不用追求高绩点。”

前两年挣扎和逃避的痛苦渐渐消退,大三的杨婵可以理所应当的逃避“指南”——当她发现这些逃避带给她的影响是正向的。
“有时还是会焦虑,在这个环境里避免不了。”当杨婵发现社交平台可以成为一个树洞时,她几乎有一点小的心情变化就会在微博写一大段文字,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的一日三餐,在B站看一些温馨的生活类视频让自己平静下来,在豆瓣寻求有相似经历的网友的安慰和鼓励。就在前天,她和豆瓣上认识的同在深圳的女生约了十月份去看音乐会。
“网络会给我一些心里安慰,但是我也不觉得自己被网络控制。”杨婵不喜欢打游戏,不爱追新剧和综艺,不太关注热点话题,对追星也只是三分钟热度。

漂浮了两年之后,杨婵开始有了接触地面的感觉。
实习期的吴可找了一个记录档案的工作,并且在此期间开始备考公务员。吴可分享的外面的世界让杨婵觉得,自己也是有能力去找一份实习,找到一份自己和妈妈期待的“平常的工作”。
不久前,杨婵和吴可再次一起去城中村吃饭。
煮面的大叔依旧忙碌和唠叨,便利店的大妈永远都有打不完的电话,补衣服的阿姨头上戴了一个新的灯。
街上的玻璃窗映得出人影,穿裙子的杨婵换掉了黑色眼镜,烫染了金色卷发。她对着镜中莞尔笑笑,挽起好友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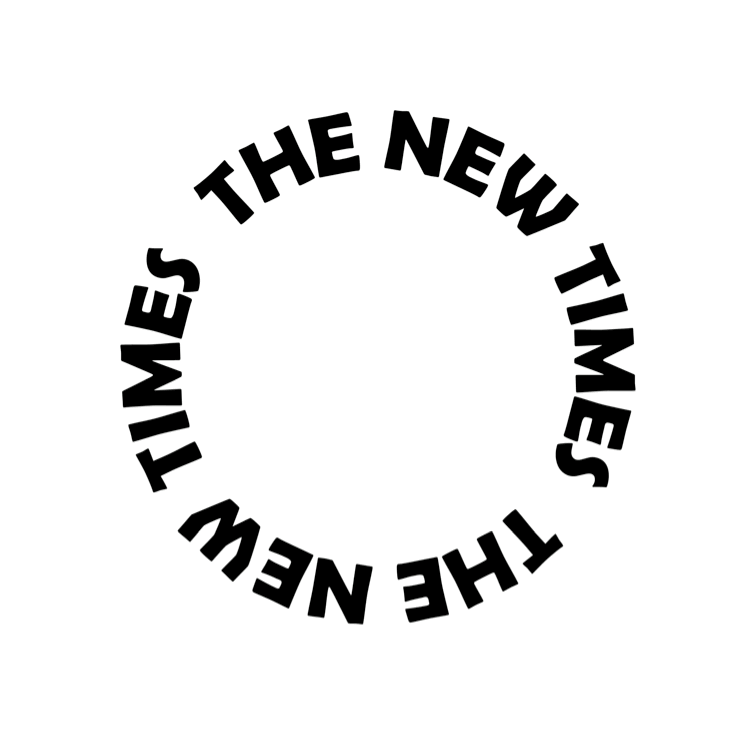
采访 | 高恩惠 方漪澄 蔡丽静
撰稿 | 方漪澄
原标题:《聚焦 | 大学生活 没有指南》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