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格伦·古尔德诞辰九十周年|重现古尔德的边园
【编者按】
今天是加拿大钢琴演奏家格伦·古尔德诞辰九十周年,其文集的中文新版《乐之边园》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为该书译后记《重现古尔德的边园》,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格伦·古尔德
距离《古尔德文集》中文版首度问世已过去六载。在格伦·古尔德的眼中,数字总是最重要的隐喻。于是,加加减减,“2022”便也不可能不引发联想:毕竟,若古尔德还活着,今年该有90岁了;而他离开我们也已整整40个年头。这一头一尾的大数,皆是拿来“旧事重提”的由头。必须说,我并非一个生卒年纪念爱好者,对在意古尔德的人而言,并非一定要在纪念日才想起他。鲜明的个性与风格注定了爱他的人会随时惦念,厌烦的早将他抛诸脑后。毕竟,在古尔德身上,并没有可以叫所有人都拍手称道或深以为然的中间地带,大众恰恰是他略过的对象。于是,当编辑询问是否为新版添加标题时,心里有了“边园”二字。一则,边园很接近古尔德远离大众、偏安一隅的思维哲学,这一点尤其在他的文字中彰显;二则,但凡古尔德在音乐中所做的尝试在文字中皆有镜像的对应,落在纸上的语词是另一组音符,它们既是音乐家创作哲学的对外宣讲,亦是其生命中每一次选择的自我确认与阐释,甚至偶有私密的情感曝露,在我看来,那是音乐家苦心营造的后花园,供疏离的灵魂、孤独的时刻、凝思的癫狂、思维的赋格栖息之地。
边园也可视作对已有园子的织补,借新版的契机,或许我们可以在旧作中引发新思。加拿大作家凯文·巴扎纳在其古尔德传记中曾有语:“历史上很少有古典音乐演奏家在死后这么久依然维持着如此高的知名度和流行性。”他甚至以“一个死后辉煌的生命”作为传记首个章节的标题。此说法是否准确有待分辨,但巴扎纳说出了古尔德身上饶有意味的一点:他总能与现当代的时空脉络同行;他的一些观点仿佛对着今天的世界而说;他借由音乐所拓展的跨文化领域,或许比我们当下媒体所做的更富哲思、更超前。甚至于近两年来疫情下的探讨,古尔德都未曾缺席:人们认为他的一生就是一场关乎审美的“自我隔离实验”。这位倡导保持社交距离的先驱恐怕可被称为最具“新冠时代代表性”的音乐家,大量关乎古尔德与科技、人文、精神领域的新观点喷涌而出;而古尔德思想内核中的疏离、孤独越来越成为当下所有人无可逃避的生命主题。于是,我充满好奇,重现古尔德的边园,能给我们怎样的慰藉与启迪?
回想那段漫长的旅程,历时两年,古尔德的文字成为习惯,像张嘴吃饭般让人头疼,让人饱足。困难堆积如山:音乐术语是否精准到位、逻辑是否顺畅、意思是否清晰……但我始终在意的是:读者是否可以看见一个渴望在个人化世界里独自狂喜又不愿舍弃尘世的真实的人。作为一个传奇的符号,行事乖张的古尔德总令人浮想联翩,那些古老的谜题一再重复:他不论春夏秋冬不变的打扮,鸭舌帽、大衣、围巾、手套;古尔德的椅子;他到底有没有女朋友;他为什么突然退出舞台;他真的说过音乐厅、剧院将于2000年消亡么?躲在这些逸事背后的古尔德愈发扑朔迷离。借新版的契机,我以读者的身份重读了全书,在曾经咀嚼多遍的文本中,更多新鲜的、当时未曾有的感受和想法不断地往外冒。关于古尔德,别人已说得够多,而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将一切收束,重现原点:古尔德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他自己想说些什么,想怎么说。但凡近四十万字能映射出哪怕一枚痣,一道肌理上的皱纹,仅一息之长的惊愕,都已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复述,这些给翻译过程以灵感与畅快的瞬间,我力图一一保留并传递给每一个可能与之相遇的人。
提姆·佩吉与《古尔德文集》
由提姆·佩吉编辑整理的《古尔德文集》(The Glenn Gould Reader)最早于1984年由纽约Knopf出版社发行。提姆·佩吉拥有多个头衔——作家、编辑、音乐评论、制作人与教授,更是古尔德研究的权威,音乐家晚年的亲密伙伴。1981年,提姆加盟哥伦比亚广播电台FM 89.9,这场“联姻”持续十一年,并孕育了一档知名的午后音乐节目。节目中他与包括阿伦·科普兰、维吉尔·汤姆森(Virgil Thomson)、菲利普·格拉斯、史蒂夫·赖希(Steve Reich)在内的一众作曲家、音乐家展开对话。他与格伦·古尔德关于巴赫《哥德堡变奏曲》1955年与1981年两个版本之比较的对话收录于2002年发行的古尔德的《哥德堡变奏曲》纪念套装中。先后为《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华盛顿邮报》撰文的提姆·佩吉成为古典乐评界不能错过的名字,1997年美国普利策奖在颁奖评语中称:这是一位清醒的、富有启发性的音乐评论家。评语中的两个关键词恰恰是古尔德所珍惜的品质,无怪他成为古尔德最后年月的知己与对话者。
古尔德一辈子所写文字无数,所涉话题应有尽有,一本文集当然不可能穷尽,对于个别钟爱的对象比如勋伯格,所作评述则完全可以单独成册地出版。他说:“如果不当音乐家,那么,我想当个作家。”古尔德生前曾多次与提姆聊起将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但最终总是临阵退缩,称时机尚未成熟。提姆称:“他是一名至上的完美主义者,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由他本人来编撰,最终会呈现出怎样的文本;到头来,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卷文集完全基于我个人的理解与选择,或许略微有遗憾,但也符合他难以捉摸的神秘。”在读完整整两大纸箱的手稿后,提姆决定保留未发表文章的原貌,不做任何改动;同时试图在文集中避免出现重复叙述的主题对象,当然其中的有些观点不可避免地一再跳脱出来。除却唱片说明与为杂志撰写的音乐评论,手稿中还包含着的大量未发表的广播剧本、电视脚本是提姆不得不舍弃的内容,因为要将它们成功地还原并保留原味地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非常困难,更何况用来读的文字与用来听的文字有着天壤之别。就该题材,提姆选用了已刊载的文章及录音脚本。最终,被选出的69篇文章分为音乐、表演、媒体、杂集四个部分。如果回头仔细琢磨一下目录,提姆对于材料的分类与重组是令人欣喜的,这几乎就是一首完整的音乐作品——有序曲、间奏和CODA(这里暂且将CODA称作终曲,演奏过乐谱的人都知道看到CODA字样意味着重返开头并走向终结,而“终曲”二字很难将这层意思表达完全),主体部分则类似四个乐章。序曲是1964年古尔德在多伦多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生典礼上的演讲稿,他义正辞严地提出“过分依照他人建议而活的人生将是毫无价值的”;终曲收录古尔德与提姆的对话,其中古尔德滔滔不绝地谈着自己何以在品位上总是如此与众不同,反复强调个体的净化过程,头尾之间有着近乎完美的对位精神。通过音乐结构的戏拟,整本书是一曲向古尔德致敬的音乐,最精妙的是,你若不仔细,它们便轻巧到不着一点痕迹,被略过去,但魂魄一直停在那里。
听古尔德说话
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说过一句名言,常引来各家不同的解释,他说:“狐狸知晓很多事,而刺猬就只知道一件大事。”依以赛亚·伯林之见,所谓刺猬般的人就是“把所有事情连入一个中心见解,连入一个单一体系。在理解、思考和感受力方面,他们清晰而连贯。他们根据一个不变的、统摄的,有时是自我矛盾或不完善的,偶尔显得狂热的单一内在视野来接受或排斥事情”。朋友布鲁诺·孟塞杰记得看过古尔德开着爱车“长哥”:在驶经曼哈顿市中心时,他真的戴起眼罩——“你知道,就是给马儿戴的那种”——只因为古尔德坚持不要看见时代广场、色情电影院和纽约街景。这件逸事的寓意实在是再逼真不过了,因为古尔德就是这么一位目光最褊狭、最没有包容力、认真到令人发笑的“思想家”。
普遍认为古尔德说的没有弹的好听,但这对他并不造成任何影响,他强烈的表达欲建立在刺猬哲学之上,不论有无人听、要不要听、听不听得懂,最好没有人听,有太多人附和追捧是最高禁忌。60年代中期,古尔德有过一段短暂的演说家生涯。1964年他只演出两场音乐会,却开了七场讲座,文集中收录的《苏联音乐》及为母校所作的毕业生致辞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讲台上,古尔德是一位风趣又有亲和力的人,但常常演讲内容并不能被充分理解。他在公众场合难免紧张、不安,似乎总是忽略台下观众的期待。评论家艾里克·萨尔斯曼(Eric Salzman)写道:“坐在台下会有某种不放松的感觉,不知道听众中能够感兴趣、跟得上内容的有没有超过五个人。”显然,一些听众宁可古尔德先生演奏音乐,不要讲话。

1959年5月19日,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在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排练休息。
宣布退出音乐会后的音乐家在写作与媒体领域找到了广阔天地,文笔滔滔不绝,空气中流淌的尽是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脚本:喜欢卖弄辞藻、故弄玄虚。古尔德把冗长、迂回的句子跟严谨与深度画上等号,因此常常掉书袋,“扮教授口吻”。一个字能交代的地方,他会忍不住放上两个字:比如关于“多乐章”(multi-movement)就一定要叫作“运用了一个多重乐章的结构”(employing a multiple-movement mechanism),又如“同一调性的乐段”就得写作“在乐曲结构中限制其转调的结构”。相比早期写作,其晚期的文本要顺畅许多。文字如人心,皆是纠结,作家古尔德的纠结。
但事有两面,就古尔德而言,我们往往需要再反向思考一番才算周全。或许“不好理解”恰恰是作者的本意。众所周知,古尔德总在试探、挑衅传统的想法——越是根深蒂固的既定思维,越要精进勇猛,在演奏表现手法最固定、共识度最高的作品诸如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奏鸣曲时,干脆来个大破大立。如古尔德的偶像麦克卢汉所说:“我提出一个试探,我不知道它们会把我带到哪里。不过,所做之事只是探索之旅的其中一段,而不是某个完结篇;我的目的是通过试探激发出人们的观点。”
当然,任何不被亲近的东西总有可贵之处,因为它不向世人谄媚,不讨好你的感官,甚至不让你舒服,它总能自行拣选出属于自己的读者,或者说找到与它亲近的人。真正的自然不就是如此么?在挣扎反抗中走向和解,如果都是些和谐篇章怕也不会怎么有趣。不少评论家认为古尔德的文字与演讲具有非凡的挑战性、启发性,相当精彩。如果古尔德打算用一个问号欢迎你走进他的世界,那么一定会在离去时还你一个惊叹号。我又想起古尔德关于“勃拉姆斯演奏风波”的自述:
事实上,这正是想象力中的极端挣扎——不完整的、有瑕疵的、偶尔莫名的突刺,经受拍打的生活与日子在音乐中的变形——它一反原有传统的古典训练要求,一反勃拉姆斯最终臣服的学院派情景,它令这部作品如此特别,像一个谜。如今,很显然,一个人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这部作品,可以强调它的戏剧性、对比性和棱角分明;亦可以完全反向处理,将音乐间的主题关系视作“不和谐的共同体”。这是近来处理浪漫派音乐的时髦方式。这种方式将作品解读为充满惊喜悬念的故事情节,充满矛盾的道德场。面对一个刻板的对象,从内在将阴与阳之间的对照一同拥入怀中,以纯粹的朴素无邪来处理传统钢琴奏鸣曲式的例行公事,格格不入终将在一元的世界里终结。我们可以选择从勃拉姆斯身上读出未来。
如果可以选择,古尔德愿意用这种古怪的方式来扭转人们看待音乐、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思路在类似本雅明的哲学家身上可以找到,古尔德的言语中隐藏着巨大的、尚未被开发的道德场。一个小切口,将有可能颠覆读者看待古尔德的角度,人们不应当为了舒服而牺牲它。愤世与尖酸的古尔德最终为自己找到一个富有柔和魅力的形象,如今这变成他又一标志性段子:伟大的音乐家,黎明时分在多伦多市动物园对几只大象高唱着马勒的《圣安东尼对鱼群的布道》。
这样的结局是所有不懂他的人的悲哀。
无形的秩序
古尔德的表达便是一味的含混吗?重返刺猬问题,将一切纳入单一体系的刺猬恰恰对复杂混沌之下的秩序有着相当严苛的“强迫症”。人们的惯性思路是将古尔德与巴赫相关联,不过在风格形成期,影响其创作观点最关键的反而是勋伯格的音乐观及“十二音技法”。他注意到以十二音列为构成前提的音乐里总有“冷静的”“坚韧不辍”“褪尽铅华”的东西。每一个法则所发挥的都是冷却作用,通过一以贯之的法则来降低音乐表面上激情的热度,最终实现整体上的“平”,甚至有些疏离的冷感,在这点上古尔德总是手法纯熟。
意识到这点对于理解古尔德的写作极有帮助,当人们受困于句子里不断穿插进入的注释、飞岔而出的话题时,退一步看,古尔德的论述常常在大格局的逻辑把控中表现出色,随处可见的秩序控制、镜像关系、精准对位,不断回到最初的原点令观点在螺旋中递进。类似通奏低音的持续音线索从一而终,充满变奏的写作背后是非常古典对称的精神。比如《阿诺德·勋伯格:一种观念》一文,作者不断重复同一个问题——人们现在真的认识阿诺德·勋伯格了吗?在文章结尾处,他转述了勋伯格在某次演讲中所说的关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一段不可思议、略带心酸的掌故。这位国王面对朝拜的人们发出一辈子的困惑:“所以,你们现在真的认识我了吗?”而显然,古尔德借此更是在叩问读者——你们现在真的认识我了吗?这段故事的写作呈现出奇特的、不止于一对一的镜像关系,文字将勋伯格、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与古尔德三段时空若隐若现地关联,引用环环相套,反射出无穷扩大化的空间与节奏感,但最终只是对最初拷问的回应,或者没有回应。在表面的繁复编织中,人们看到漂亮的弧线与力度,深沉的磁场紧紧抓住即将飞奔而出、企图摆脱控制的星光;它们是安静的涟漪,不断向更宽广的边界扩散。多么精彩的奇思妙笔!
反复翻看这些文章,究竟如何用文字描述古尔德向外发散又向内控制的质感一直是无解,直到我隐约嗅到了某种“建筑癖”:比如他对于城市规划的侃侃而谈,他关于柱头样式的品头论足,他评论巴赫《哥德堡变奏曲》时挂在嘴边的“建筑结构”,他在意如同赋格的建筑节奏,等等。其中最富洞见的作品是以声音为媒介对空间意义进行探讨,尤其以60年代借“对位广播”催生出的一系列精彩广播纪实片为代表——《北方的概念》《新来的人》《寻找佩图拉·克拉克》《斯托科夫斯基》。古尔德认为这些“声音书写”能实现时空距离的丈量、穿越的旅行,带人们从高空俯瞰都市与荒野的格局,甚至是启迪城市规划在现代社会文化现象中应当承担的责任。老实说,非常接近于我们近些年流行的“航拍”视角。从听觉、视觉、通感继而拓展到空间,所制作的节目具有类纪录片或者类电影风格,而原本声音这门关乎时间的艺术被赋予空间的雕塑感。声响变得更自由也更私密,可以随意分解、合成、重叠、剪贴,重新界定空间。尚未有人深究古尔德与建筑之间的渊源,显然,他对精准结构的看重,对合理与秩序的要求,对诗意化视觉效果的追求,与建筑手法极其吻合。最有意味的一段话来自他对巴赫的评价,他说:“巴赫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声音的建筑师、构造者,毫无疑问,他是那些逝去的声音建筑师中最伟大的一位,对于我们来说,这使得他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这句话似乎解答了某个疑惑,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
CODA
与古尔德同时代的美国作曲家拉·蒙蒂·扬(La Monte Young)如此回忆自己童年时最早的声音体验:
那是一年的冬天,在爱达荷州的熊湖山谷(Bear Lake Valley in Idaho)自家的小木屋里,寒风掠过水面,包围了整间屋子,在角落和阁楼里回荡。这幢木屋在阿尔法法(Al-falfa)的旷野中茕茕孑立,就像一具由贝壳包裹的身体,独自面对着外界种种事物。
扬对于木屋的声音体验还伴随着另外一些声音:
附近不远处的电站里,电话线杆上的变压器嗡嗡地响个不停。我问我的母亲:“风是什么?”我非常好奇……于是她开始解释风是什么。然而,在她说话的同时,我还听见这些电线杆发出哼哼的声音,持续而稳定。这种声音就是我所有工作最初的源头。
这段文字十分“古尔德”,混杂着动物、自然与建筑空间的剪影,却又似乎并没有说出什么。或许,想要简略地描述一个人本就是极为牵强、极为危险的事,更何况是他的内心,它们总是消散于无形,不断回到源头,书页上的文字最终只是一段旅程灵光蒸发后留下的痕迹。“用眼睛去听声音是杰出的才智”,这是古尔德忠爱的一句话,文字背后的盛景留待诸位继续探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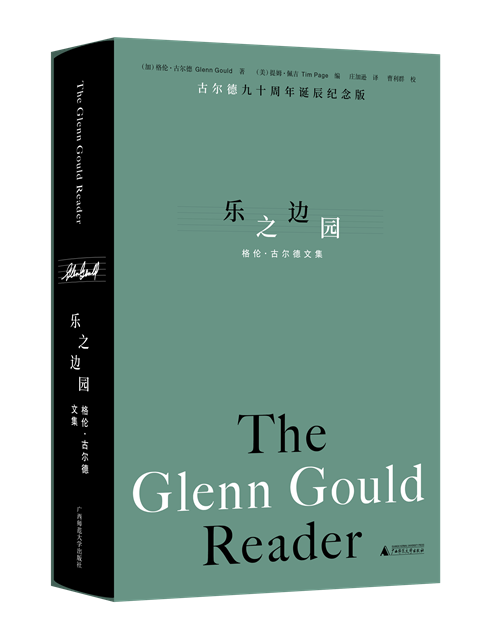
《乐之边园:格伦·古尔德文集》,[加]格伦·古尔德著,[美]提姆·佩吉编,庄加逊译,曹利群校,我思Cogito|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