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走出记忆,围猎时间 ——一场西西弗斯式的阿尔茨海默症照护|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图文 | 李百川
编辑 | 吴筱慧
编者按:
2023年9月21日是第30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随着中国社会不断步入老龄化,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约有1000万人。对于背后每一个被这种疾病笼罩的家庭来说,病患记忆的渐次模糊,注定了他们照护之路的特殊与无望。围困在这一疾患两端的群像,仿似对时间本身的围猎:一端,是被时间折磨到极度敏感的照护者,而另一端,则是对时间遗忘至强烈钝感的病患。二者对时间的围猎,像极了西西弗斯滚起土块爬向山顶的过程。山顶在哪里,无从知道。但似乎只要行进在路上,就无限接近那希望。一路蜗行摸索,一路琐事堆叠,不知不觉间,时间的围猎者们在推行土块的同时,便也握拥了滚起巨石的力量和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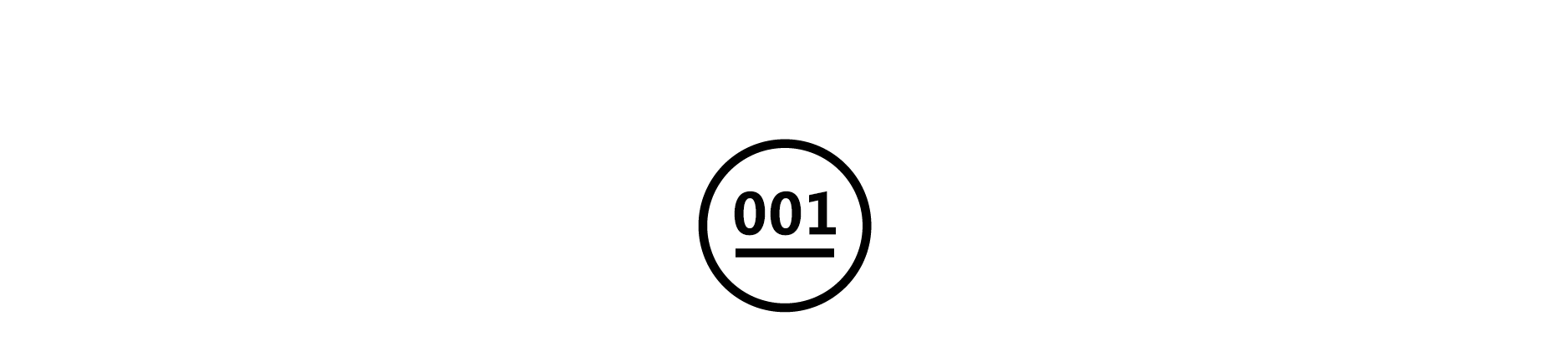
当路口出现
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慢性神经退行性病变。它起病的隐匿性和发病后的不可逆性,于照护者们而言,意味着在猝不及防间就可能踏上未知终点在何处的照护之路。
2019年3月5日,是80岁的李信声踏上照护之路的日子。
那是一个温煦的早春,她和老伴儿去离家不到一站地的建国门老年餐厅吃午饭。当日,在每位用餐老人的盒饭中,都配有一条约略20厘米长的烧鱼。“难得肉质肥美,个头儿又大”,老伴儿提议省出一条,打包回家作为晚餐。回到家,李信声取出打包盒中的烧鱼往冰箱中塞,“饭盒里是什么啊?”“鱼啊。”“哪来的鱼啊?”“这不是刚在餐厅吃饭,你说留一条晚上吃吗?”老伴儿抿了抿嘴角:“我没有印象了”。谈到此处,李信声语气坚定:“这并非一件平常的事”。如果老伴儿在十分钟之内把事情忘得如此干净,那绝非老年人普通的遗忘问题。
第二天,她就带着老伴儿去了医院。“看什么病?我没病!”“我有病,陪我去吧。” 到了医院,老伴儿似乎也不再急着争辩到底是谁有病。经过脑核磁、CT、神经量表、口头问答等一系列检查后,随着脑图像报告中“海马结构萎缩”结论的出现,老伴儿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
李信声的敏感是锄地式的。那些企图扎根匿迹于老伴儿日常的隐疾,如苗头一般,被她清晰地洞察、捕捉,然后就地拔起,谨慎剥离。得知老伴儿确诊的那一刻,李信声的心情不免沉重。但她转念一想,自己又或许是幸运的。毕竟,老伴儿的病症在阿尔茨海默症临床分期中尚属早期。

李信声回忆老伴儿的起病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发病是渐进式的。从起初的健忘和对时间的钝感,演变为沟通困难的增加,直至行为模式改变,甚至具有进攻性。
相较李信声,大多数照护者就不具备那么敏锐的洞察力了。他们更容易将阿尔茨海默症的初显病情判定为一种普遍的自然衰老,从而错过早期的照护路口。一同错过的,还有在医学定义中最宜治疗的窗口期。这双重的“错过”,令很多照护者的路口变得“千沟万壑”。
49岁的于娴,很不幸,就踏上了爷爷和父亲的中晚期阿尔茨海默症照护之路。
如果说爷爷的晚期确诊,是潜藏在90岁高龄健忘的表征下的遗憾,那么父亲的中期确诊,则是意外脑出血后连带着脑白病变的一种避无可避的无奈。因此,于娴的照护之路陡峭又凶险。爷爷和父亲的情绪张力常常以某种非理性的程度不断扩大。“他们好像都变成了小孩儿”,区别在于,爷爷就像一个无人管教的孩子王,“时常愤怒起来会砸碎茶杯”;而父亲则像一个怯生生的小朋友,“独自一人待在家里会害怕”。在他们身上,年龄和记忆化成乌有,她只能挣扎着继续在照护之路上艰难行进。
歧路多艰,不在一处。
51岁的佳云,是为数不多选择在家中安装监控探头来监测父亲病情的照护者。在她的家乡辽宁盘锦,人们大多对阿尔茨海默症是麻木的,觉得只是“老糊涂”的表现形式。因而,当父亲频繁健忘并总是无常撬门时,已然是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晚期患者。每逢发病,父亲唯一的念头就是出门。家中大门并未反锁,但病情的发展使他“天然地”忘记了如何开门。因而,在焦急和无措中,他总会选择撬门作为最直接的破门方式。为了撬门,他会使出浑身力气或者随手抄起一把菜刀,进攻性十足,也不认识所有亲人:把老伴儿和女儿统称为“姐”,固执地在武力与言语的斡旋中为自己争取撬开大门的机会。
当路口逐一出现,病患们的病情并不会因为得到治疗和照护而被等量地阻断,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病程的发展速度,且方向不可逆转。这也就意味着,在他们已然忘记许多的基础上,还将忘记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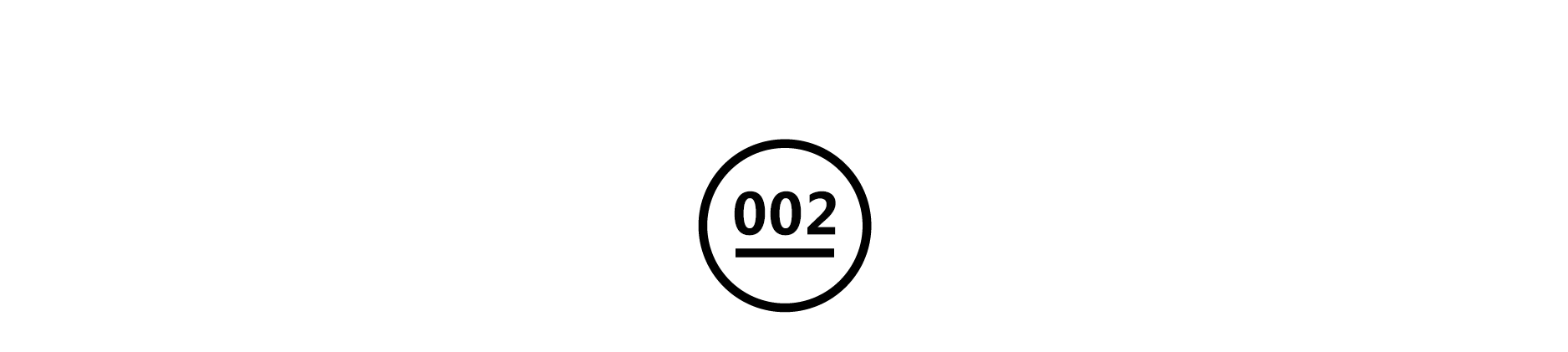
不断滚落的巨石
经由不同的路口,有若干条坡度不等的漫漫长路在照护者们的脚下延伸开去,那些路上不断滚落的巨石,是独属于中晚期阿尔茨海默症照护家庭的惊心时刻。
“拜托您了,两个门都注意堵一下!”于娴正在和保安部通话。电话另一端的保安,通过于娴格外精准的相貌特征描述,在小区的两个出入口留意着一位90岁左右的老人。她自己和女儿则分别把守在单元楼和小区地下车库的门口,整个动作毫不拖沓。电梯从十二层下到一层大概需要十五秒,而仅在这十五秒内,她完成了这通及时的电话。
这一幕并非警匪片中的场景,而是于娴爷爷于耀中的一次走失。
那天,于娴本打算陪爷爷去小区对面的超市采购。但就在那短短几秒“拧钥匙锁门的功夫”,爷爷便先一步径自进入电梯下了楼。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医护工作者,于娴早已习惯各种突发状况,但她在这次的等待中却慌了神。她频繁地从居委会、物业办、保安室进行信息的索取和同步,所幸由于小区出口有限,保安把守有素,爷爷被成功找到。只是,爷爷被找到时眼镜片掉了一块,衣服上多了像是新蹭上去的油渍。而这一次对于娴来说艰难又漫长的“围猎行动”,其实仅仅半小时而已。
事实上,这样的「围猎」是大多数阿尔茨海默症家庭最真实的照护写照。根据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统计,全国每年走失老人人数为50万,用固定比例推算,其中超过20万为阿尔茨海默症老人。那些在普通家庭听来遥远的「出走」,实则是每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照护家庭稍有疏忽就要历经的日常磨难。
但病患们似乎并不记得,也道不出缘由。当焦急的于娴问起爷爷出走原因时,得到的只是淡淡的一句“我没吃完的半截儿果丹皮不见了”,颇有点匪夷所思。1970年代,爷爷从复旦毕业后曾远赴德国留学,素来思维缜密、逻辑严谨。而这一切,似乎已无迹可寻,一位老知识分子的举止,就这样逐渐变得荒诞。
如果说,于娴爷爷的出走是一次幸运的及时拦截,那么,佳云父亲进攻性地出走,则让老伴儿在艰难抗衡之余饱尝无助。
佳云之所以选择用监控镜头监视父亲的日常病情,除了父亲发病时的狂,还有母亲固执观念中的倔。父亲发病时失控的进攻性,让她常常担心80岁的母亲,怕她只身照护既不安全也吃不消。为此,她曾多次沟通并尝试与父母同住,以便照顾他们。但年迈的母亲总以“老人需要自由空间”为由坚持独自照护老伴儿。佳云拉上亲友对父母轮番相劝,依旧未果后,她争取到了安装监控,与此同时,手机24小时开机变成了她的生活常态。
母亲的固执让她只能退身成为远程的第二位照护者,她时常在凌晨三点突然惊醒,在睡眼惺忪中察看监控中的父亲。
一段被她截取后的录像视频,清晰地记录下了这样一幕:晚上十一点,父亲一步步朝着门口缓慢移动,并开始徒手大力薅拽家门。“又干啥呢?”声音出现后不到三秒,母亲焦急地踱着步子出现在监控画面之中,用手拦着父亲,进行规劝。霎时,父亲像一枚被点燃的炸弹,毫无征兆地推搡母亲,将她从约略三四平米的门口,推向监控收录不到的厨房拐角。

监控记录下,佳云父亲薅拽家门未果后对佳云母亲大打出手
母亲一瘸一拐地蹭到椅子上,十分虚弱地拨通了女儿佳云的电话。女儿在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驱车赶到,与母亲一起,合力完成了这场对父亲的“二次围猎”。劝着、顺着、哄着、应和着,闹剧过后随着时间和体力的消耗,父亲终于慢慢安静。佳云则坐在离大门最近的椅子上,看护了一宿。
佳云也想过,与其持续这般煎熬,不如任凭父亲出门。但当她恢复理智,便会不由后怕起来。她也曾尝试为父亲绑上求助牌,以备不时之需,但都被父亲一个又一个剪断。

被佳云父亲剪断,拒绝佩戴的防走失求助牌
比起目睹亲人记忆破碎时的落寞和苦楚,这样见证亲人毫无缘由的狂躁和混沌,更让人无策而惶恐。用佳云的话说,“家里总有一颗定时炸弹”。
父亲发病时,常常生出像对待仇人一般的那股恶气,那本应与老伴儿携手安度的晚年时光,也变得一地鸡毛。但这些并非特例,而是大多数晚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身上的“通病”。阿尔茨海默症在攻击负责形成新记忆的海马区之后,会继而攻击负责逻辑思考的前额叶皮层。就这样,晚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会被这种疾病支配,和亲人发生对峙。
这是每一位照护者都必须躬身面对的难题:眼前那位曾经无比熟悉的亲人,会变得满身戾气且愈加凶悍,那些随日常照护而来的陌生感和无常失控的行为,更是将彼此间的对立演变至冷硬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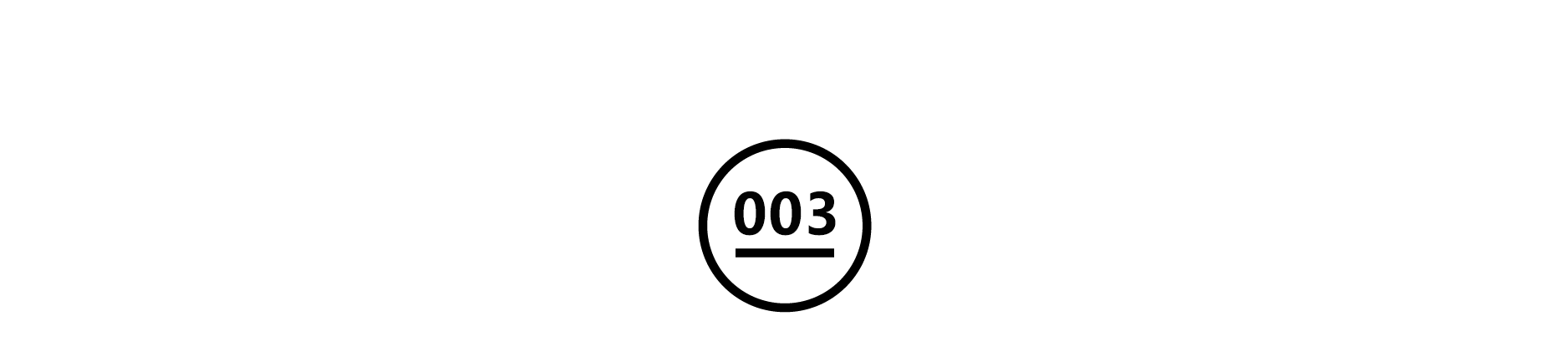
西西弗斯们
在2020年之前,并没有任何一款特效药能够有效治疗阿尔茨海默症。但对李信声而言,却从未因此对老伴儿的治疗有过半分懈怠。当她辗转数家医院问询和打听后,决定选用中药介入老伴儿的治疗。而所抓药方,需要根据老伴儿病情的变化动态调整配比。于是,李信声决定担起替他挂号开药的事务,每周三也就变成了属于她一人的开药日。
凛冬时节的凌晨四点,小区的照明尚未开启,李信声便出门了。通往东直门医院的24路公交车将在此时首发启程。
从小区到公交车站的途中,李信声总会生出“左右为难”的心理困境:一边担心在医院出了差池,又一边担心老伴儿有意外。寒风猎猎,“就总感觉像有个人影跟在后面一样”,她总是头也不回,在车站橘黄色路灯的投射下,她被拉长的影子仿似一位暮年的战士。
老吴是东直门医院唯一擅长用中药治疗疑难杂症的医生。每周三早晨七点半,当六个挂号窗口同时开放时,几乎每条队伍中排在首位的人都会挂吴医生的号。这意味着,李信声必须保证排在首位,才能在挂号开启时达成所愿。为此,她必须提前整整两个小时以确保万无一失。
自老伴儿确诊以来,这样耗时耗力的挂号,几乎成了李信声每周三的家常便饭。在迄今为止的40多趟挂号中,李信声甚至将药方中约略28种中药的名字熟稔于心。李信声提及,当她在小区内亲眼目睹了中晚期阿尔茨海默患者的失控和癫狂后,便对随时可能会到来的“坍塌”感到恐惧,“心里最直观的感觉,好像我是一位船长一样,得争取避开这场灾难”。即使不确定眼前的冰山是否只是一角,作为“船长”的李信声也想尽最大可能地打满舵,“老伴儿的病压倒一切,必须要把这一件事做好”。
与此同时,家中桌上则会留下一张字条,其间字迹被马克笔勾描得粗大:“我去医院取药,早饭你自己吃上,不要去厨房。”——这张字条是她写给自己开药期间独守家中的老伴儿看的。但每隔20分钟,李信声依旧会接到一通来自老伴儿的电话:“你去哪了?我找你半天!”“我去挂号开药了,你看看桌子上的字条”“哦,哦哦哦……”
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生活中,思维和记忆像割断的干草一般破碎。从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忆中,他们无法理出稍长一点的主线,只得凭靠照护者们更精微地捕捉与引导。
无论李信声还是于娴,在照护的过程中都会把“数清数量”挂在嘴边。她们对数字的敏感和对定量的严苛,源于家中那常有的“动感”。
于娴爷爷在家中是没有边界感的:他会径自打开微波炉,一口气喝掉里面不知道是给谁热的药;买回的蛋糕会被他藏进枕下、桌底和马桶水箱中;他甚至会毫无意识地把洗洁精当成调料,倒在碗里就饭。
比起物品的摆放错位,于娴更担心的问题是误食。那些依凭爷爷神情和舌苔颜色来反推误食的过程是极为忐忑的。于是,她渐渐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买来的物品先清点计数,依据类别和预判的危险等级细致分类,最后被摆到固定区域。
李信声家里也有相似的问题。刚买来的菜,她但凡收拾得稍迟,老伴儿就会把它们更换位置:譬如将萝卜藏进壁橱,将橘子塞进口袋,或者把苹果扔在阳台的旮旯里。“我买的萝卜呢?”“我没看见,我哪动了啊?你把钱给了人家,东西没拿吧。”老伴儿常常露出一股怯生生的诚实,似乎他才是那个无辜又急切的人。这样的寻找像是一种无奈的“探宝”,李信声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寻找中找到了技巧——观察那些不寻常的角落:比如,原来放在阳台旮旯低处的篮球忽然鼓得高高的,结果她在下面找到了那兜苹果;再比如,原本应该躺在箱子里的大蒜倒歪在地面上,结果她在箱子中找到了那袋新买的义利面包。
在李信声的观察下,老伴儿的每一次藏匿并非顽皮,而更像是对珍贵物品的一种守卫。“他知道这兜儿苹果要比一个旧篮球好,知道面包要比大蒜贵重,所以总是下意识地藏起来”。这种在惦念和遗忘中徘徊的藏匿欲,与《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安东尼总是执著于藏起自己的手表如出一辙,他们总是下意识地守护好各自认为珍贵的东西,又在保护中遗忘保护本身,在矛盾中寻不到出路。
他们需要有人帮助校对时间感。在长久的体力与心智的磨砺之下,照护者们发现,最好的校对方法,是用遗忘来对抗遗忘。
晚饭后的二十分钟,老伴儿款款挪着脚步,拉出了桌子。“这是干嘛?”“吃晚饭啊。”“不是刚刚吃完了?”“你吃了我没吃。”倘若之前发生这种情况,李信声会一遍遍向他解释已经吃过晚饭的事实,还会借助一切可用的细节来证实,譬如还没刷过的碗筷或是垃圾桶中的厨余垃圾。但换来的,是话音刚落,老伴儿再度把桌子拉开,不温不火地要求开饭。从发问到解释,一个相同的动作回合可以在20分钟里重复10次,当李信声怒气还未散去的时候,老伴儿已经不知道第多少次心态归零重新提问了。

李信声的老伴儿在家中看电视
李信声逐渐意识到,带着情绪说教或嚷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她要抓住老伴儿善于遗忘这一点来对抗他的遗忘,“能蒙就蒙,最大程度顺从他,他是病人”。当她深切地体认到这点后,便开始“使巧劲”:当老伴儿拉出桌子要求再次吃饭的一刻,“这里有个苹果,先吃个苹果,我马上给你做饭”,两分钟后,桌子再次被拉开,“你看这个剧,真有意思这对儿小年轻”……一推一置之间,老伴儿似乎慢慢忘记了“还没吃饭”这件执念已久的事。
在生活中校对时间感的,还有于娴。爷爷生前最大的爱好是读书看报,人民日报一直是老于的枕边读物。每到上午十点,一旦报纸没来,他就会变得暴躁而易怒。于娴可以保证在收到报纸的第一时间就拿给他,但邮递员却做不到日日派送得如此精准。
于是,她也想到了办法:把每一天的人民日报小心收好,第二天拿给爷爷。如是,每天十点能准时读到人民日报的爷爷,便变得乖巧而顺从。“而当病情发展到后期,他可能也看不懂报纸具体的内容,所以对日期也就自然不敏感了”,但似乎有了这一份报纸镇场,一切就不会那么无序又陌生。对读书看报的诉求,也是爷爷在病情后期少有能坚持记住的事。
回望整个照护过程,照护者们更像是陪同病患一起,在时间和记忆的棋盘间不停跳步的棋子。记忆是否被嫁接不再重要,判断是否精准不再重要,一切是否合理也不再被关注,只要能让彼此保持「同频」,就好。用来对抗记忆错乱的,是他们刻意错乱的时间。照护者与病患对时间的敏感和钝感,在看似无厘头一般的协同中得以中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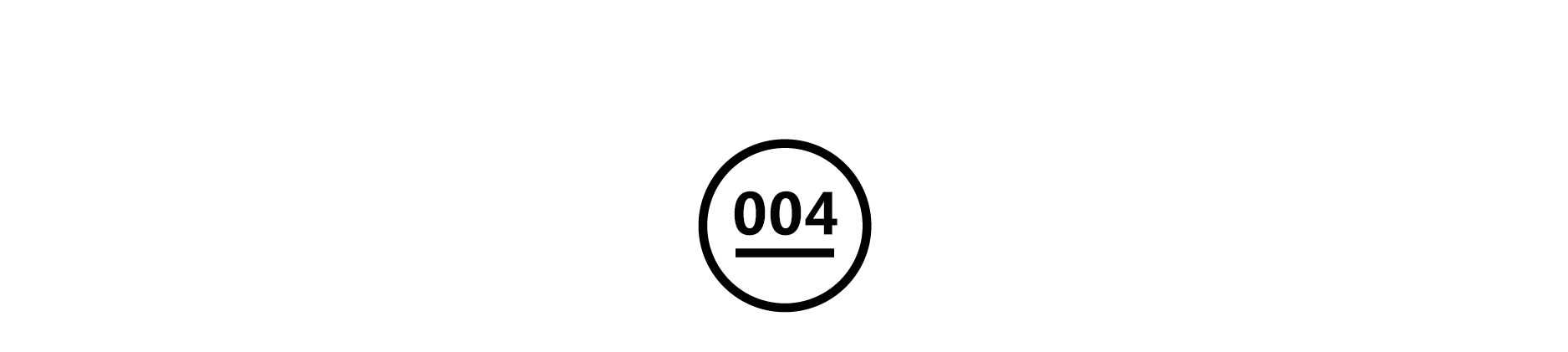
放下行囊之后
在那些坡度不等的照护之路上,“西西弗斯”们背负着各式行囊。“孝”和“爱”,这两枚读来短促的单音节字,落在他们肩上却漫长又重若千钧。
于娴,在照顾爷爷和父亲共计六年的时间里送他们离开了人间。
在于娴父亲离世之前,女儿拆卸了时钟表盘,一遍遍教外公识认时针和分针;通过拼合字卡的方式,尽可能多地引导外公表达。
于娴甚至在人口福利基金会的“换手环行动”中,为父亲申领了一只可以检测位置信息并能设置电子围栏的「黄手表」,以便在父亲走出自己设置的“安全范围”时,第一时间接收到提醒。于是,便有了父亲第一次在家门口的老家肉饼为全家买早餐的身影,有了他那句“我今天自己坐了趟公交车”小孩一般的喜悦和自得。
虽然每当父亲戴上“黄手表”出发时,于娴依旧会生出爷爷走失时那般惶恐不安,但于阿尔茨海默症病患而言,这可能是最有效的锻炼方式。

于娴父亲在世时家中曾用过的画板和黄手环
2019年12月31日,李信声在持续一年每周三起早挂号的坚持后,接到了令她燃起希望的一通电话:“来药了!”——一款治疗初期和中期阿尔茨海默症的原创新药上市了。
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李信声与药品供应商取得了联系。两天后,老伴儿成了第一批服用病患。老伴儿自2020年1月服药以来,坚持了整整两年。如今,她从捉襟见肘的窘境中逃离出来,稍有余力为老伴儿添置辅助类的药品和补品。每天配药时,她都会将几类药分装在几只印有“寿”字符文的味碟之内,其中除了常用的胶囊和药片,还有用于保健脑神经的椰子油和调理心血管的叶酸。

李信声为老伴配好的药碟
李信声在照护过程中,也常常会摸索和尝试一些能缓解老伴儿病症的治疗方法。据她了解,手指触摸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病患的认知神经,从而有助于延缓患者的病症发展进程。于是,厨房便成了老伴儿践行“触摸疗法”的“训练场”。洗黄瓜、削胡萝卜皮、切莴笋丝儿,这些看似简单的配菜备餐工作,在老伴儿那里都是高强度的“训练任务”。
李信声的老伴儿是土生土长的福建人,对于鱼虾等海鲜河鲜总能吃得利落而干净。一次午餐,他拿起筷子,仔细剥下鲈鱼肚皮中央和背部顶端的两块肉,小心地夹起,放进李信声的碗中。尽管老伴儿的记忆已被剥离得不再完整,却能清晰地记着鲈鱼是李信声的最爱。他也深知,吃鱼时极易卡刺,而鲈鱼肚皮中央和背部顶端两处的肉最是完美无刺。在他并不利落的行动中,似乎无言证明着:最好的东西,一定要留给那个最深爱的人,才对。李信声也被这样的感动击中,仿佛这一路上的艰辛也没有想象中那般冷硬而无望。
但慢慢地,沉重也开始压过来。李信声说,在照顾老伴儿的日子里,每天有且仅有两个时段可以和正常人讲话,而那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一是每天早上九到十点,她得空去楼下和年龄相仿的朋友们一起锻炼;二是每天晚上老伴儿熟睡后,她难得有片刻和几位老友语音通话。随后,她同我聊起弘一法师:“‘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被唱成家喻户晓的歌谣,只有当一个人老了,才能知晓其中的落寞。”
李信声曾是一名语文老师,年轻时才华斐然,如今依旧语出不凡。当她谈起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和杨绛的《我们仨》中关于孤独的理解时,言语间尽是满满的寂寥。
李信声也放弃了曾经无比热爱的写意画技。从前,她总会在闲暇之余手握毛笔,安然祥和地画上一片荻花、一弯新月,沉浸在国画的笔墨气韵中。而今,在对老伴儿事无巨细的照护下,她不得不放弃了这项爱好。

李信声曾经的国画习作
但不久,她又执拗地学起了创作成本更低的彩铅。对着手机中的亲戚或教过的学生,一笔一笔地勾勒起来——“我得通过这些方式来预防自己,不得上这种病,才能有资本照护好他,也不给儿子增添负担。”

李信声介绍起最近画的彩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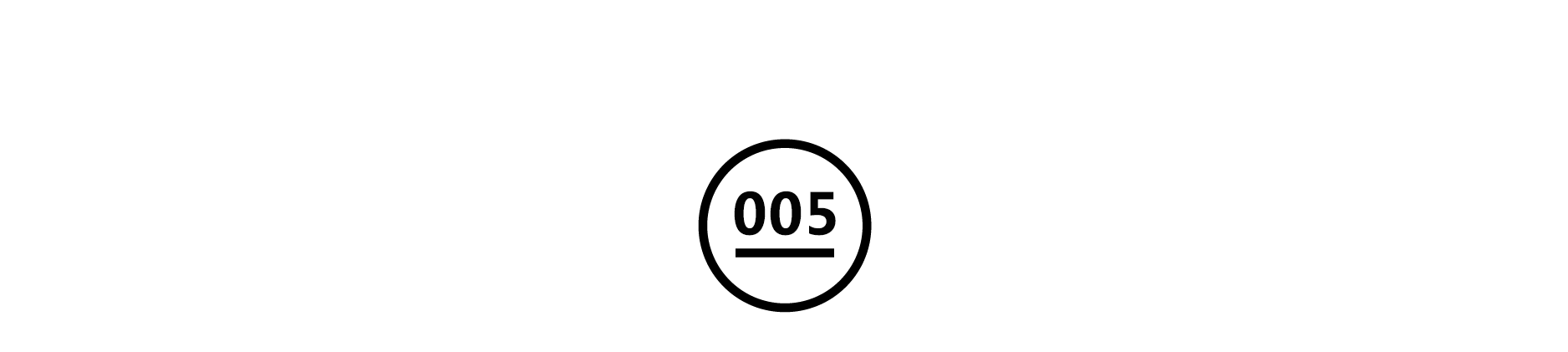
攀向山顶之前
与医生不同,照护者们是既能完整地感受发病过程,又能充分见证疾痛体验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昔日亲人间的温情过往还历历在目,如今竟变成自己的“独角戏”。照护者们不仅要眼睁睁地看着彼此的羁绊被遗忘斩断,还要接受病患发病时突然袭来的混沌行为和巨大的情绪张力。甚至,这台“独角戏”也可能变成“对手戏”,因为在病患眼中,照护者们早已被放置在了陌生人甚至仇人的角色之中。
但照护关系是双向的,于双方而言,或许「在场」就意味着一切。
一如照护者们不约而同提及的,“之所以要做这些,因为这些事情就摆在那里,人在就行”。在病患们接受照护的过程中,无论他们是否妨碍了照护的过程,「在场」本身,就是一种慰藉。对于照护者们而言,那些并肩同路的岁月,是他们不可缺失的人生体验,更是他们不可抽离的精神寄托。
照护之路还有多遥远,照护者们无从知晓,他们和李信声一样,坚信只要在路上,就无限接近希望。
在谈及那个不可及也似乎未可望的未来时,李信声板直手背,左手悬平,右手朝着相反的方向,指尖向内比出一个弧度,“这个病的速度,确实会无情地下滑。”旋即,她将右手向上抬了一些,开合的角度变得平缓,“我只想,哪怕必须一直向下走,只要慢一点,就好。”
晌午斑驳的阳光撒在老伴儿身上,满头白发在阳光下透出鲜亮的色泽,湖蓝色的衬衫朴素干净,领口齐整且似乎有被熨烫过的棱角感。
她一直努力确保他看起来得体、有尊严。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图片由作者提供)

目前镜相栏目除定期发布的主题征稿活动外,也长期接受投稿。关于稿件,可以是大时代的小人物,有群像意义的个体故事,反映社会现象和社会症候的非虚构作品等。
投稿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
(投稿请附上姓名和联系方式)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