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谈|梁永安×周嘉宁×金理:浪尖上的风与好运
9月17日下午,周嘉宁《浪的景观》新书分享会于思南文学之家举行,作家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梁永安、金理两位老师就作品内外进行了交流对谈,澎湃新闻经主办方授权发布部分对谈内容,以飨读者。

三位嘉宾在现场分享
周嘉宁:这本书里的三个中篇,从2018年开始写,到2021年写完,所以其实三年的时间我也就只写了三个中篇而已,差不多每个中篇三万多字。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勤奋的作者,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写作的速度会越来越缓慢。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也会有焦虑,但是三年过去,到了现在已经非常习惯用这种极其缓慢的速度去塑造一个世界,然后也以一个极其缓慢的速度陪伴我的主人公,在我所塑造出来的世界里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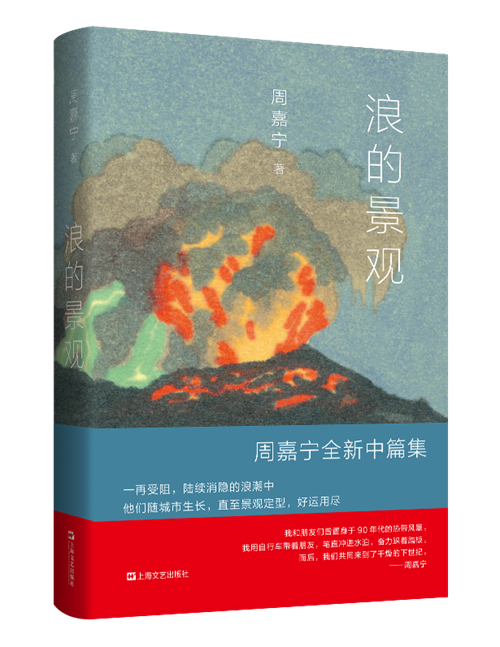
《浪的景观》开始写没有多长时间,2020年就开始了,之后外部的世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前几天碰到复旦新闻系教授陆晔老师,她说看了写作时间,意识到原来第一个故事是在2019年时就完成了,她说当时感觉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人对世界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她说这个话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她说完以后我想了想有可能确实是如此,经过这个时间点的转折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变化,或者这些变化还没有显现出结果,但是在过程中世界跟我们的关系也是在发生变化。也不仅仅是个人,所有的变化到最后都会汇聚成更大的力量,进而影响社会、影响世界,进入更大的作用和反作用力磁场中。
这本书的背景差不多就是这样。
梁永安:首先祝贺嘉宁,几年下来不容易,文学的人生不是一个客观,是自己生命的冷暖,跟世界的变化。我们以前总是有一种逻辑、一个框架,但是必然发生的这些变化是我们每一个创作者自己内在看世界的眼光和感受,我们心中有非常大的变化,变化过程中,对创作是很大的难度。
我对客观生活是有一些零星的体会的。比如有一次去会场因为堵车,就从车上下来打了一个黑摩的,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人跟我讲他的故事,妻子生病、孩子上高中要考大学,就开了黑摩的,讲了他的奋斗。我昨天看嘉宁书的时候有这个体会,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种种行为,作为书生的立场、单纯的看立场可能觉得很不好,里面充满了混乱,就像看《美国往事》一样,但是这是真实的生存。对学校出身的作家,受过科班教育,了解这些体会,是很大的跨度。确实一个作家的成长,相当不容易。
一个人的成长在文学领域里走着走着就拐弯了,其实对生活、生存有了很大的承受力、有很大的内在体会。不通过虚构,这里面的故事不是通过复杂、跳动、张力十足、充满大起大浮来塑造的,而是有状态感。同时不是那种跟现实对应的,现实的刚性碎片式的作品,就像马赛克做的拼图一样的,也不是这样。里面有自己想把握的生命,在现代社会青年的社会愿望、坎坷,想完成什么,但又屡屡受挫,伤痛和内心非常难以放弃的一些东西,在她的作品里面,也表达得非常有力。
金理:现在对三部作品依次展开。比如第一篇作品,我想跟两位交流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些嘉宁的行迹和心迹在里面,现在有不少研究者做这方面的研究,中国作家海外的经历,比如当年参加文学营、工作坊等对他们的影响。在很多作家的追忆当中,那个经历是决定性的时刻,比如说王安忆老师在爱德华遇到陈映真,他说没有遇到陈映真以后的写作就不是那样的,所以对嘉宁来说有没有决定性的意味,那段生活和经历。第二个问题梁老师谈到写作的难度,前天我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和学生讨论嘉宁的小说集,在三部作品当中,我们的讨论意见、矛盾比较集中的就是第一篇,《再见日食》,比如说主人公天才少女,这个人物太特殊,给我的感觉像一把特别锋利的刀,这把刀放在口袋里一定会把袋子戳破,这个人物背后所关联的历史风暴和人的关系非常近,这样一种紧张感、迫境,会给作家的辗转腾挪造成很大的问题,这个是太过尖锐的人物,整个作品当中第一个作品和后两篇有一点游离感,后两部作品可以作为同一个序列,第一部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有一点差异,想听听嘉宁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

周嘉宁
周嘉宁:《再见日食》这个小说,我自己的心情也是很矛盾,2018年还是2019年写完我不记得了,写完以后就放着,也没有看过。写完以后得到杂志上编辑意见的反馈各有不同。我自己也没有能够完全去消化所有的意见。但是到2021年年底书要出版时,不得不把这个小说重新拿出来,最开始只是想要做一点校对,但是在校对的过程中,不行,原来那个故事从整体上没有办法立得住脚,就像金理所说,里面女主人公的形象无论再用怎么样文学的方式去处理她,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回避不了。在这样的心情下,差不多把这篇小说大改了一遍,从头到尾全部改了一遍,又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一开始想要写这个故事的出发点是这样:2016年11月从爱德华的国际写作项目回来,从纽约坐飞机回上海,那天正好是2016年美国的大选之夜,在飞机上的时候气氛非常难忘,因为飞机上有2/3是美国人,每一个人都在使用网络、都在用平板电脑跟踪选举投票进程,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等到我下飞机的时候,我一打开手机铺天盖地的消息,选举结果产生了。因为在美国认识了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是学校里面大学的老师或者是研究生,所以他们全部都在表达一种极其失望的情绪。而我自己从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世界,因为是在一个很封闭的小地方待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从那样的世界回到上海,下机场的时候突然之间所有的现实问题又再次摆在面前,打开手机时又一次好像从这一刻开始,接下来的世界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变化?我自己不清楚,即便是到现在6年的时间过去,这个问题也没有想清楚。因为离开时我同时又有另外一种感受,借主人公的话放在第一篇小说的末尾,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发生的事情太美好,所以不愿意对任何人讲,这个话至今是我的心声。我觉得之前三个月的经历太美好,所以之后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叙述过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是在我的小说里也没有叙述过到底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情都没有写,但是把具体记忆中的世界做了一个影射,影射了一个虚构的世界。而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是一个投影。我可能用这样一种方式在那个时刻稍稍逃避了一些最严重的问题。但是这种逃避不是一种有意的逃避,可能至今都没有谈论这个问题,而且只是觉得越来越困难。
梁永安:当下的年轻人写海外的时候,有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到底是表达我们对世界什么样的一种观察、表达什么样的判断、在艺术里勾勒出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很大意义上没有办法有一个传承、有一个好的前面的东西,有一个让人写的时候具有一种文明连续性和含量的写法,这是一个困难。
矛盾在什么地方?每一个社会内部都特别不均衡,文学人很容易把不均衡抹掉,用一种艺术的情绪或者艺术的色泽,写出一个社会的机制、温度等等,会虚构出一个整体性。
我为什么喜欢嘉宁写的这个状态,非常有原生态,这个原生态是文学里面体现出来的原生态,里面很难去构造出一个人自身的自洽、逻辑性,人和人之间漂流之中、短暂、浮草化、真正具有现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人和人心相遇,不再是一个整体、民族、阶级、国家、政治性的,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每个人都有自己后面摆脱不了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前面很多的未知。所以这时人的状态、活力,有一些很简单的人,在一个不确定里面,人内心里把生命联系起来的东西,写得非常可爱。
这第一部里面很喜欢一个男人,马里亚诺,特别生动,搞文学艺术的人永远像个孩子,在生活里充满了天真气。但是上天给他很多坎坷、伤痛,最后给他一点温暖,给一点生命的依托。这个人的细节写得非常不错,看到这里时突然觉得嘉宁很适合写这种海外、国际。一方面有自己的质感、在国外的经验。另外呢,作家四个能力最基本:1、感受力,她在国外的生活把所见所体会到的东西,关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微表情、微形态,都在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传导。2、想象力,有很多人有很好的感受力但是缺乏想象力,一个东西只有一个可能,没有想象力的人看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逻辑,这个坏人、好人最后怎么样。文学的虚构性是高度真实,真实都是平常人们释放出来的东西,那个真实更本质。我们在生活里面都是被后面的,不是自己本心的东西所掌握的。3、凝固力很好,细节都很原生,这就克服了白话文学历史以来的大问题,历史上,李白、杜甫写作跟遭遇、体会、发生的事情,写作时间顺序很紧密,李白看庐山瀑布,估计当场写出来的,文学气质和心情和当下的视觉有一种活现的张力。但是今天的人都是回去坐在桌前沉淀下来再写,看上去很有趣,这个其实有很大的距离,这个凝固力对体会、细微的东西,是瞬间即逝,但是都可以传达。4、传达力,你的语言在现在白话文里面也不太好写,有很多多音词,古代是单音词多,《诗经》里面每词一句,所以这里面读出来的韵味非常好,但是白话就麻烦,两个字就把一个意思讲清楚,很直白,所以这时候读很难有一种像文言里面的光韵。所以,能够把这个复杂、人在漂流中的沧桑、细微、冷暖、光泽,都非常好地传达出来就很了不起。
如果看第二、第三篇小说,对嘉宁未来写成什么样子也没有数,但是第一个小说看下来心里就很定,职业作家的特点,有具体的四个方面的充分体现,后面肯定会再继续,就像牵牛花一样在尾巴上可以很好地延伸,这是对第一篇特别强的质感。
金理:刚才梁老师反复谈到“原生态”对作家特别宝贵,也是很难做到。嘉宁在最近的访谈当中都借用到一个词:“考古”,这个“考古”可以和“原生态”作一个比附,考古好像是一种事后的研究,从地底下挖了一个碗出来,把这个碗当做文物,放到博物馆里面去供奉,这是后人研究的一个起点。但是当你把它作为一个宝物、一个艺术品供奉起来的时候,同时也可能是破坏了这个碗在当时历史线上的生态。这时需要研究者或者一个作家,有一种想象力要把碗重新放回地底下,感受到这个碗在历史线上是如何使用的器物,可以组织起一个日常生活的世界,这是历史线上的一种感受。这跟跑到博物馆里,带着那种很仰望的眼光去看碗,把它当做艺术品,是完全两样的。
把这个感受落实到第一部作品当中,我喜欢这个细节,讲那群日本的棒球少年,他们去美国初次闯荡世界的时候,那段写得很抒情,就是“月光照在大地上面”。那个世界,经受着月光照亮的世界展现在棒球少年的面前肯定是有善意、带有希望的。对于那群初次出门闯荡世界的棒球少年来说,他们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世界,但是也许未来面对他们的是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嘉宁反过来又要告诉我们,那个瞬间是非常美好的,比如感觉到这群年轻人太浅薄、太天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但是不能折损这批青年人初次闯荡世界的少年的心智、气象。我真的感觉到新天新地新人,都是那么美好。哪怕以一个成年人、过来人的姿态去感觉到未来走向的可能不是那么光明、美好,但是在那个历史的现场、那个当口,他们就是那么欢乐,而且我觉得第一部小说跟其他几篇相比,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一篇是追忆、回忆的视角展开,尽管嘉宁在说写的是最快乐的时光,但是最快乐的时光是通过回忆来展现,寓意很伤感,知道好日子已经过去,回望中写得非常让人伤感,但是作品中除了那些故事前排的中年人之外,还有一群在营地,更年轻的一伙人,活得兴高采烈、懵懵懂懂,那群人就是初次闯荡世界的棒球少年。你在感伤、在怀旧的时候有一群年轻人就在把握着他们最好的时代、把握着他们最好的舞台。所以这两面结合起来,是这个作品带给我的感受。
我要抓紧时间谈第二篇,第二篇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两个主人公的形象在嘉宁的作品当中很少见,嘉宁作品当中比较高频率出现的是文艺青年,这两个并不是,其中有一段是这两个人的对话,说他们很浪漫,像堂吉诃德一样的浪漫。文艺青年是不会谈堂吉诃德的,文艺青年要跟你谈肯定是波拉尼奥。下面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我们要比那个更加浪漫,因为我们是开手动挡的,开手动挡的进货的车。这跟其他的青年作家的主人公形象,跟嘉宁以往的人物形象不太一样,这几个人行动力特别强,他们开着老爷车闯荡,去进货、去冒险、打架等等,这个特殊的人物形象以及这个形象所带出的个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这在我看来是今天的青年作家笔下不怎么看到的。
周嘉宁:这个小说也是很多年以前偶然听到一个播客的节目,里面讲到在北京的外贸市场,因为那个播客讲的是我同龄人,无非他们生活在北京,我生活在上海,但是我立刻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共鸣,因为我自己整个大学时代是在外贸市场度过的,那个时候非常爱打扮。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有原因的,我们高中的时候正好是西方流行文化开始大量涌入的时期,那个时候从音乐、从小说里面看到很多物质层面的东西,那些东西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
比如我问朋友,匡威是什么时候进入上海的,我朋友说最早只有市百一店的体育柜台有卖,375块钱一双,跟现在的价格也没有差很多,但是那是20年以前的事情,而且不是一直有,会偶尔出现一双。在高中的时候听流行音乐、看到电视里面的那些人穿着那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完全没有,后来第一次看到,就在外贸市场,襄阳路,华亭路,很破烂的雨棚下面,需要去讨价还价。走进那个世界,会发现在文学作品、电视里面、歌词里面的东西,突然变成了眼前的东西,可以触摸到。所以当时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这个人群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也会在买衣服的过程中跟摊主聊很多东西,那个时候的服装文化跟整个流行文化息息相关。流行文化又具备极其强烈的时代性。那种时代性如何在本土生根和发展,那些西方的流行文化是浓缩,当我们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分年代慢慢进来,是一下子从50年代到90年代,那些文化浓缩成一团,突然间扔到你跟前,你也分辨不出这当中时间的前后顺序,甚至分辨不清楚这个东西是英国还是美国的。只知道是外国的,然后就这么扑面而来,这些东西完完全全可以体现在衣服这件事情上。
所以我当时听了播客以后很有兴趣,所有的记忆都开始复苏,也因此查了一些资料,做了一些采访,试图把那段时间在上海的外贸服饰小小的变迁史,可以稍稍呈现在小说里面,同时也是因为那时觉察到世界的某一些变化,突然之间我的人物也好、自己也好,不能够坐以待毙,不能够再坐着、再在一个停滞的状态里,自己要行动起来,我的人物也要行动起来。他们也要走出去,要开上他们的车,得要在地图上能够开始他们的旅程。我自己的旅程是在我的人物开始了以后才展开的。从某种程度上一旦我有了这个决心,好像是先让我的人物行动起来了,而我自己本身的行动反而比我的人物更滞缓一步,等他们开始行动、上路了以后,我慢慢觉得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也找到了我跟社会、跟世界新的沟通和交流方式。这是写作过程中慢慢产生的一个意外收获。

梁永安
梁永安:这并不是完全现实主义的,因为可以看到青春、青年在路上开着破车,看上去好像是很艰难,里面很多辛苦,有很多非常让人惊心动魄的时刻,但是其实整体来看,是写出了一种价值、写出了值得一过的生活。所以这里可以感觉到一种精神的共鸣,在故事之上有一种精神,能够投入进去的东西。刚开始看这个书,我满怀期待,还以为是讲一个女性的故事,女性怎么乱,大悲大喜等等。当代人想象力大大缩减了,原始生命不行。但是一看是男主人公的故事,这里的爱情、包含破车,在西方小说里,不管《在路上》还是其他的,都是青年人和破车才相配,一旦配一部好车人就显得衰老,就被格式化。 一般来说西方青年人第一次买车,买二手破车,500美元就开出去了。青春就是这样,冒着烟往前走。
这个人做生意、做服装,然后开着车往山东等等去跑,这里读到的不是钱的问题,表层的是钱,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内在澎湃的激情,有激情才有浪,表面的浪再大,心里面没有浪,也配不上。整个社会在标准化里也获得了自己看上去很光鲜的生活,但是心里没浪,看上去表面和时代很相配,过着很优越的生活,但是没有质量,是大流水线上的一个单元。这个青年溢出了,自己去找生活。我们说“人生就是这样”,当下过得很平衡,下面很难说过得怎么样。但是当下过得非常艰难,下来一步跟今天就会不一样,就会有一种动力、一种非常大的内心的面向今后时空的欲穷,自我推动。这不是写普通的个体户。
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那次我们骑车出去,有很多人骑着摩托车,车上架着水,个体户都非常卖力气,他们在菜场卖最新鲜的一批鲜鱼,价格比别人高很多,但是人和人的区别就是目的,他们往往没有什么实力,形形色色、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无奈,干这个活,挣一些钱,而且挣得不错,万元户还不少。但是他的落点限定在这里。
所以我看嘉宁小说的时候想,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逐渐让人感觉到温馨的东西,他们跟老谢借钱,老谢也不是富人,拿出一个袋子远远超过了他们需要的钱,“远远超过”这个地方我看了也很感动,其实真正的人生是远远超过金钱的尺度。所以他们追求的也经得起风浪,风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也是青春对应的,如果中年就经不起了。越是积累的东西多越经受不起打击,越难把它放下。只有青春的时候不怕。这个特别适合拍电影,很有电影的感觉。这个小说里我觉得可以读出诗意来,故事本身是一个叙事的方式,但是要说的东西远远超过了里面现实的东西。这是一种真正的青年文学所具有的内在力量。
金理:接下来谈谈最后一篇小说。嘉宁的作品当中都有双主体的结构,两个人,又从两个人往外扩,朋友、集体生活,最后一篇很明显,从两个做电台的女孩子,然后再往外扩,还有指挥部的朋友,再往外扩,他们做电台时收到很多听众给他们写信的,也是代表着一个人群。还包括电台自建的网店上面有很多留言,这也是一个群体。再往外扩比如说听罗大佑演唱会的朋友,参加明日派对的朋友,五湖四海的朋友,从双主体一圈一圈,像涟漪一样往外扩,写一个集体生活,这是我很好奇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文艺青年不知道怎么会走到一起,大家因为共同的兴趣,比如星座、血缘好像就见面了,他们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积极的生活。另外一方面从文学上来讲,我之前看嘉宁的对话,早年青春时代,对这一代人的标签,他们只会写个人、只会写私人、很狭窄的生活。但是从今天来看,到现在这个阶段,并不是这样。这个请嘉宁聊聊。
周嘉宁:你刚刚说星座、血缘,我们周围有水瓶座的人,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饭时有一半人都是水瓶座,魔咒可能是这样。我确实想到我所写的这个世纪初的社会形态,文艺青年的生活形态会是什么样子,我在想还是一个BBS的时代,所有的发言在一个较为公众的空间上所呈现的。跟现在微信、有了朋友圈、有了公号,变成一个自媒体时代,就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发言平台,自己的平台会是一个系统和相对完整的,现在可以进行公共讨论的场所,变得越来越少。最早的时候没有自媒体,但凡要去进行一个事件的讨论,不管是社会事件还是一个书、一个电影,讨论在一个论坛上,论坛的作用可以汇集各种形态的人,网络世界90年代末、21世纪初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时候所带来的冲击,可能就是以不同形态的人找到一个平台,在那个平台上面可以相对自由、并且很重要的是相对平等进行一个发言。
我通过BBS交到很多朋友,我作为一个性格极其内向的人,当时生活经历比现在更少,更加内向,在网络上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整个文化的场景也是很融合的,会觉得现在写小说的人通常朋友会是写小说的人和一部分评论家。但是比如写小说的人和画画的人、摄影的人、做音乐的人,各个行业之间的隔阂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这一方面是由于各个行业的专业性变得越来越专业,20年前当大家刚刚开始涉足这些事情时,彼此之间没有那么分界,也没有那么强调所谓的专业性。现在这个时代对专业性的强调变得越来越严格,标准变得越来越高。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状态,在论坛里面就一个事件的讨论,各种行业的年轻人都会加入其中。并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这种人可能通常在现代社会当中很难获得成功,或者很难以自己非常盲目的标准很好地生存下去,但是之前当标准规则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是会让一些人在意外的情况下获得这些好运。但是这些好运并不会伴随他们终身,也会有用尽的一天。对每一代年轻人都是这样,我们这代年轻人有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好运气,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有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好运气,但是这只是一个好的运气而已。
梁永安:我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出文艺之星”,看小说时经常会勾起往事的感觉,一开始写罗大佑的镜头,当时都经历过。比如过元旦,不是喝杯酒吃一顿,那一年和几个人念了一夜的诗歌,天一亮我们几个人倒着走,从学校里走到五角场,那是时代的一种氛围。但是青年文化的底部非常脆弱。整个社会的发育、发展,还是在一个非常紧促、局促的发展状态。观念的一路形成,青年展开一种向往,这个向往相当于如何去把它建设,如何转化为一个现实的历史中的一种力量。所以凯鲁亚克《在路上》的结局,他们自己离开,后来的结局也是很伤感,嬉皮士那一代人很多人跑到一起去,在珠穆朗玛峰下面逐渐老去。
为什么感叹这一点,那些人跟我聊起来好像都有点自我嘲笑,有点后悔的样子,“哎呀,当年我还是文艺青年,现在不是了”。这里面有一种焦虑性,这一篇里面这句话特别多,非常不好写。写作要有动力,作家有什么动力写作是作家之间很大的区别。比如说爱伦·坡写悬疑小说、侦探小说的时候,有悬疑的压力,雨果写《悲惨世界》时就是一种强大的问题压迫。这个小说读的时候在想她的动力在哪里。可能是嘉宁自身的一个青春成长,然后自己的一个生命已有的,有一种自身非常强的不是自我实现的欲望,而是渴望现实,这里面有很多空白、很多怅惘,因为时间变了。里面写了很多对话,而且其实里面描述萧潇,他说“很远的地方过来,喝了很多酒,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特别高兴,脱了衣服在雪地里跑了一大圈”,等等这些。然后底下是短句,感觉像海明威作品的叙事,对话很多,短句很多,这就是青年说话的特点。很多东西是感发,而不是把一个事情讲出来。大部分的情况下一方面是询问或者回答,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相互之间无形的、默默交汇,跟成年人不可能这样说话。
这个地方是某些逐渐消失的东西,看了觉得很珍贵。看罗大佑的演唱会,就有点寂寞了,年轻一代跟他之间有一定的代差。这部分嘉宁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如果是一般通俗性,或者传统的作家,可能故事、情节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对话是推进情节。但是这个对话的主要功能不在这里,主要功能是内部的相互交织倾听、相互的发泄、相互的相识,而在这个碎片化的社会里面,这是很难听到的东西。所以这是作品里真正属于青年在经过历史长河之后有一种非常悠远的心情在里面,有一种愿望。这是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的。一般的作家写不下去,他没有一个大情节,没有前后剧烈的人物转折变化,他觉得推不下去,没有办法渗透。嘉宁在这方面可以内化,可以给定一个东西,故事本身和上面释放出来的,那样一种无形之中的时代感,以及打开内部的语言,这是嘉宁特别宝贵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