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汪天艾︱那声你没哭出的哀歌,我为你而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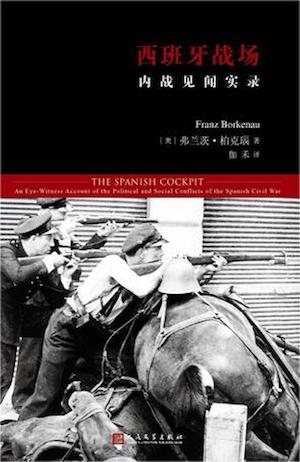
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内战爆发。很快,纳粹德国开始向佛朗哥一方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海军,意大利法西斯的近五万士兵也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的加迪斯港口登陆。英法两国官方的“不干涉”政策并没能阻止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奔赴共和国一方的前线。美国的“林肯纵队”亦从大洋彼岸抵达。苏联的库斯克号军舰满载物资停靠西班牙东海岸的阿利坎特港,先后送来了七百余架飞机和四百辆坦克。德国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阵线也将他们的斗争搬到了西班牙。一场国家内部的战争迅速演变成两种、甚至多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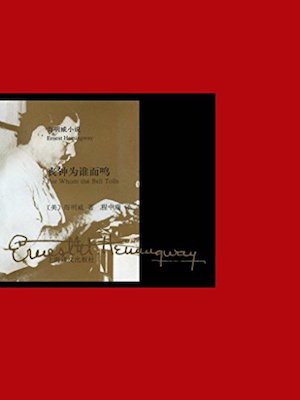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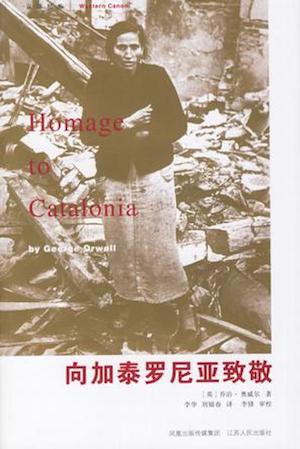
1936年8月柏克瑙出发前往西班牙的时候,他也像多数外国人一样觉得,“这就像是在欧洲发生的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之间的斗争”,然而此后两年间的两次造访共和政府辖域,让他意识到西班牙的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在开始真正对西班牙战场的见闻记录之前,他花了不小的篇幅,结合历史对西班牙的社会结构与各方面的不平衡性,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这些分析放在被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搅得焦头烂额的今日西班牙,亦能点中不少值得深思的要害之处。回顾西班牙的近现代史,社会学家的素养和敏感让他从战争的表象之下挖掘出西班牙问题的根源:十七世纪以降曾是海上帝国的西班牙一路衰败,成为“西方文明主干上最枯萎的一支”,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反抗各种朝向“现代”的进步,民众对“强加于人的现代文明”的憎恨与激烈反抗,让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走得极为缓慢艰难,同时奠定了他们原始的斗争模式与落后的思维习惯。
对许多内战的旁观者而言,西班牙人做了许多“毫无意义”的事情,柏克瑙却提出,大家忽视了“我们的目标也许不是他们的目标,我们的价值不是他们的价值”。在忠实记录了1936年和1937年两次造访战时西班牙的见闻之后,他从西班牙人的国民品格出发对当时西班牙战场对“外国人”的吸引做出了自己的思考:“欧洲人一心崇尚‘进步’,被停滞不前的西班牙吓得目瞪口呆”,但是“几乎每一位外国观察者,无论身处哪一方,都感到一种进入魔力的吸引。不少技术顾问气恼得想一走了之,却终究没有离开”。这一切除了内战本身的意义,还因为“在这里,生命还未被效率化,未被机械化;更看重美,而非实际用途;情感重于行为;荣誉高于成功”。
柏克瑙的战时日记是从他1936年8月跨越西法边境开始的。当时大批的国际纵队志愿者和外国记者也都从这条路来到战火中的西班牙。他们在西班牙战场经历的一切,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正如内战结束后从伊比利亚半岛回返的记者弗兰克·哈尼根所写,“所有前往西班牙的记者在翻越比利牛斯山之后都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从纽约或伦敦本部传来的问题清单都变得好像细枝末节的干扰”。因为,他们已不再是纯粹的旁观,而是参与了这场战争所象征的所有恐怖、悲情与险途。几乎很快,无论这些外国学者、作家和记者最初是为了学术考察、文化信仰还是新闻报道出现在西班牙战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走进了西班牙人的日常与更为内核的战斗当中。抱着近距离观察西班牙斗争状况的目的前来的柏克瑙。也确在此后的停留中被卷入战斗,曾被空袭压得抬不起头,甚至因为被己方诬告锒铛入狱。与此同时,西法边境又见证了另一种反向的跨越与改变,在内战的最后两年,许多西班牙知识分子也是从西法边境开始漫漫流亡路。1938年2月,“二七年代”的重要诗人塞尔努达站在西法边境的车站,写下“背后留下的是你淌着血的、废墟里的故土。最后的车站,国界线另一边的车站,你在那里与故土分离,她只剩下骷髅一具,扭曲的金属,没有窗,没有墙——一具地里挖出的骷髅,连白天最后的光都将它弃绝。面对所有人的癫狂,一个人能做什么?没有回眼望,对未来也没有预感,你就这样走进陌生的世界,秘密地离开已化陌生的故土。”——由此开启一场二十五年的流亡,直到生命终结再无归程。
1939年年初,共和国军节节败退,辖区里的人们按下声来焦心忡忡地互相问着:“你想过,我们可能会输吗?”那个流亡作家马克思·奥部(1937年。正是他委托毕加索为巴黎世博会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展馆作画,成品即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格尔尼卡》)笔下“没有名字的一月”,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开始从加泰罗尼亚翻越比利牛斯山向法国逃难。车已无法挪动,所有人都背着行囊沿着山道步行。
在逃难的人群中有西班牙“九八年代”最伟大的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2月22日,流亡途中的马查多病逝于西法边境的小镇科利尤尔,口袋里装着他一生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诗:“蓝色的日子,童年的太阳。”在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为马查多书写的挽歌里我们读到:“再走几步就是逃离。”在彼时的设想里,西班牙即将坠入法西斯的深渊,逃过西法边境来到法国就是逃离。谁曾想到,仅仅一年之后,法国也危在旦夕,固守中立的西班牙反而成了无数欧陆知识分子逃往美洲的中转之地。
1940年6月,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本雅明在德国人拿着逮捕令闯入他家前一天逃离巴黎,8月取得美国签证之后他从西法边境逃往西班牙,以期借道葡萄牙前往美国。在边境小镇布港(正是柏克瑙抵达西班牙的第一站),本雅明得知佛朗哥政府取消了一切过境签证,所有从法国流亡而来的犹太难民将被遣返。9月25日,他在旅馆自杀身亡,长眠布港的海边。墓碑上用德语和加泰罗尼亚语铭刻着从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历史哲学论纲》中摘录的话:“没有任何文化的记载不同时记载了野蛮。”
“没人能为这样的梦魇披上夜色的长袍”
诚然,柏克瑙的见闻录撰写于1937年,内战并未过半,战局尚不明朗,他的观察与推断中也有一些只能停留在当时的背景下。例如在造访孤儿之家的时候,他注意到西班牙内战引起的心理震撼“意外地小”,民众对革命中恐怖活动的反应之平静令他震惊,“这些儿童经历惨痛变故,却没有心理失衡。西班牙人面对这场剧变,依然安静沉着,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健全的人”。如今看来,当时看上去平静的儿童恐怕更多是巨大震撼下的应激性情绪关闭。
在内战中沦为孤儿的孩子们,许多都经历了令人唏嘘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推向下一个不知危险与否的港口。他们中的一部分(比如遭受德国空军重袭的巴斯克地区)在国际纵队的救助下前往英国,却要在迫近的几年后经历同样的炮火。而1942年2月,列宁格勒战役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天,正在前线采访的意大利记者库尔奇奥·马拉帕特被叫进驻扎拉多加湖的纳粹芬兰部队将军的指挥室。将军说:“我们抓到了十八个西班牙俘虏。”马拉帕特一脸疑惑,“西班牙人?你们现在和西班牙开战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有十八个说西班牙语的俘虏,他们说他们是西班牙人,不是俄罗斯人。我们得审讯他们。你肯定会说西班牙语。”——“其实……我不会。”——“你是意大利人,你总归比我更西班牙。去审讯他们。”
于是,马拉帕特用极慢语速的意大利语向这十八个西班牙俘虏提问,对方用很慢的西班牙语作了回答,双方居然可以完全互相理解:“我们是苏联军队的士兵,但我们是西班牙人。”原来,他们是西班牙内战中的孤儿,父母都在轰炸与战火中丧生。有一天,他们在巴塞罗那被集体送上了一艘苏联舰艇。在俄罗斯,他们得到了食以果腹,衣以蔽体,并最终受训成为了红军士兵。后来,他们和许多红军战俘一样被掩埋了在冰天雪地的列宁格勒。
对在战争中长大的那一代人而言,无论是否因此有实体性的失去,内战都是他们生命中永远的疤痕,影响着此后的轨迹。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安娜·玛丽亚·玛图特将她所在的这一代人叫做“茫然的孩子”——他们经历了战争中最平民日常却与前线战场同样残酷的年少时代,因而长大后拒绝归顺于一个由奖惩、由善恶两分统治的世界。而内战爆发那年才十五岁的拉伯尔德塔,在年过半百之后忆及1936年写下的诗句更令人震颤:“我们透过纯真的双眼惊恐地看见/黎明行刑的恐怖/摇晃的卡车排成长队/角落深处蜷缩的人/像驱赶的兽群被领向死亡/那是战争是恐怖是一场场大火,那是自杀的祖国”;他问:“为什么要由我们来赎买我们/嗜血的古老民族集体的罪责/谁来偿还我们被摧毁的青春/哪怕我们没进过战壕?”;他想:“但我想在这里对你讲讲我这失去的一代/讲讲他们愤怒的白鸽停在等候大厅,钟永远停着不走/讲讲他们再不能追回的亲吻/讲讲他们的快乐/被不幸的历史谋杀/讲讲那场恐怖的疯癫飓风。”
除了创作时代导致的某些历史局限性,《西班牙战场》的见闻集中在共和政府辖域,作者曾试图探访佛朗哥辖域而未能如愿。与他所记录的支持共和国的几个党派南辕北辙的主张相仿,佛朗哥一方也面对多方力量与利益交织的复杂局面,因而产生了不少同样值得玩味的命题。正如在共和政府辖域内柏克瑙看见的西班牙人“迫切需要外国人的援助却无法违心地表示亲近”,意大利法西斯几乎向佛朗哥送上了他们的全部,从最新型的战斗机到最老式的坦克,以及“一战”流传下来的机枪,长枪党的军队却很不领情,他们把墨索里尼派来的意大利“志愿部队”的缩写CTV,改写成首字母相同的三个西班牙单词:¿Cuándo te vas?——意思是,“你什么时候走?”看着德国空军的炸弹撕开西班牙的血肉、碾平城镇也让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羞耻。
再比如,最令佛朗哥麾下的本土军人感到厌恶难堪的是柏克瑙书中亦有短暂提及的摩尔人军团。佛朗哥利用自己曾是驻守北非的将军的势力,召集了大批摩尔人为他征战。这些几百年前被天主教西班牙赶尽杀绝的族群的后裔回到伊比利亚半岛,却是在为内战中更捍卫天主教传统的一方作战,且依旧遭受长枪党“正规军”的厌恶与压迫。此外,还有不少不明就里的非洲雇佣兵到了西班牙本土,才知道是来送命的。1937年,朗斯顿·休斯作为几家非洲裔美国人报社的外派记者启程前往西班牙。途径法国时,适逢在巴黎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作家大会,休斯在会上做了关于法西斯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发言。他清楚地知道那些被征兵送往前线为佛朗哥一方而战的非洲和摩尔人所遭受的压迫。在《西班牙书笺》中,休斯描写了国际纵队中的黑人士兵在与摩尔士兵对垒后的心理活动:“在被我们夺下的村子/他躺在那里奄奄一息。/我望向非洲的方向/看见那里的根基颤动。//因为如果自由的西班牙赢得这场战争,/那些殖民地也会自由——/那么一些美妙的事情也将发生在/像我一样深肤色的摩尔人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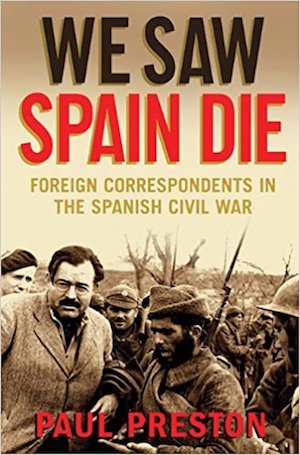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西班牙近现代史的保罗·普莱斯顿教授曾经出版过一本见证西班牙内战的外国记者与文人实录,题为《我们看见了西班牙死去》。这本书的西班牙语版书名翻译成《子弹下的理想主义者》。的确,来到西班牙战场的外国志愿者中,有许多就像塞尔努达1961年遇见的那个林肯纵队老兵那样,“一切对他遥远/而陌生,他却选择去那里,/决定,若时机已到,就为那里赌上性命,/对着那时候木板上挂出的理由/他宣誓,尊严就是/为倾其一生的信仰奋斗”。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理想,后来都在这片土地上遭受了失望与打击,然而,“欢呼、失望乃至幻想的破灭就是革命史的组成”,柏克瑙在日记开端如是说。西班牙战场上发生过的一切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彼时彼地,这或许也是柏克瑙这本著作自1937年首版以来不断再版的缘由之一。正如加缪所言:“在西班牙,人类学到了我们可以是正确的但是依旧战败,学到了蛮力可以毁灭精神,学到了有时候勇气本身并不是足够的奖赏。毫无疑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世界走到尽头的时候把这场西班牙戏剧视为一场个人悲剧。”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