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龚龑|柏克的第三副面孔:十八世纪英国的政治斗争与社会改革

沃斯通克拉夫特
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下简称沃氏)写的《女权辩护》(1792)不少中国读者都知道,而她的《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1790)一般不为人知。其实,《权利辩护》是问世最早的驳斥柏克《法国革命论》的文章,沃氏也因此声名鹊起。沃氏的丈夫戈德温(William Godwin)如此评论《权利辩护》:“这本书的措辞十分激烈,难免被大加指责。有论者说,对这位大人物(引者按:指柏克)的攻击,太轻佻、浮薄,简直是无理取闹。但这并未损害玛丽(引者按:指沃氏)这本书的成就。那些致力于追求自由和宣传启蒙的朋友,曾经十分爱戴柏克先生,现在,他们认为是神圣的事业,柏克却猛烈攻击,他们感到愤慨和厌恶。”
一、《权利辩护》的价值
《权利辩护》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界定何谓“自然权利”,也就是“天赋权利”。当然,比较而言,潘恩(Thomas Paine)在稍后的《人权论》(1791)中更清晰、更系统地论证了自然权利及其保障。因而,一般的政治思想研究都是将柏克笔下的成规惯例(Prescription)与潘恩的自然权利理论加以比较。第二,批评世袭制,尤其抨击世袭政府和财产。沃氏指出:“财产这魔鬼一直盘桓左右,伺机侵犯着人们神圣的权利。权利的周围扎满了篱笆,这篱笆就是那些糟糕浮华、罔顾正义的法律。”这样的社会制度是有害伦常的,不惟各个阶层的男性,对中等阶层的女性,尤其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已经预示了后来的《女权辩护》。
今天重读《权利辩护》,不妨注意其中的史料价值,藉此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柏克。最好先从“辉格史观”说起,它代表英国十八世纪政治史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一派。“辉格史观”起源于柏克和麦考利等辉格党人的政治宣传。看法大致是这样的:英国十八世纪辉格党和托利党相互争斗,他们分别拥有自己的纲领,轮流入主政府。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时期,辉格党把持政局,确立了行政权归于议会多数党领袖的原则。1760年乔治三世继位,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辉格史观”学者认为,乔治三世自小受到博林布鲁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爱国君主论》的熏陶,即位之后宠幸托利党,一意孤行地推行自己的政策,导致了“威尔克斯与自由”、美洲独立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这些政策及其后果也促成了以罗金汉姆侯爵为首、柏克为其代言人的辉格党兴起。按照此派学者的说法,柏克揭露了乔治三世的独裁行为,确保英国政治重新回到君主立宪的轨道上来。

表现“威尔克斯与自由”的漫画
但是,柏克还有一副众人熟悉的面孔。从十八世纪的托利观念过渡为现代托利主义,标志性的人物也是这位柏克,尤其是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政坛,辉格和托利分子并不秉持“进步”的观念。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实用主义的,是对具体情境的回应,并不关乎今天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到了十八世纪末,柏克回应法国革命者及其在英国的不从国教崇拜者的政治构想,雄辩地阐明了政治理性的不可靠。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进步”的社会理想和运动,成为此后英国乃至欧洲的政治景观的永久特征。不妨说,到了十八世纪末,才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之争。
十九世纪的英国保守党,主要是从后期柏克的思想中,发掘出现代保守主义的意涵。举其大端而言,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国家和教会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二,谨慎的渐进主义。柏克极力呼吁对过去或者传统的忠诚,同时他也认为,有必要采取零星的、务实的和渐进的变革措施。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坎宁(George Canning)直言不讳:“柏克先生最后的作品和文字,是我的政治指南。”同样,另一位政治家皮尔(Robert Peel)的《塔沃斯宣言》(Tamworth Manifesto)也包含着谨慎应对变革的态度。如同柏克,皮尔也认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根本性的举措,但又不否认进一步变化的可能性。同理,1832年的议会改革是对一个重大宪政问题的“最终的和不可撤销的解决”,当然,皮尔也不反对随后的与时俱进的变革措施。这一实用灵活版本的柏克学说告诉我们:英国的保守主义关注的是变革的程序,而不是变革的内容。确保实施变革的恰当方式,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不是选择如何保留过去或者回到传统。从这个角度看,柏克变成了现代保守主义政治的“教父”。借用苏力的话,这个柏克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有了神圣的光环”(《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2页)。
二、柏克的第三副面孔
沃氏的《权利辩护》给我们展示了柏克的第三副面孔:充满妒忌和愤懑的政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潘恩就不必提了,后来,马克思也曾评价,柏克是一个“马屁精”。其实,这样的看法能够得到另一派历史学者的支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史学家纳米尔(Sir Lewis Namier)猛烈攻击“辉格史观”,影响了此后英国史学的发展。有学者认为,1930-1970年可以算作西方史学界的“纳米尔时代”,八十年代该派的势头开始减弱,但其影响依旧很大。纳米尔采用极端实证的方法,将研究对象聚焦在1761年的英国下院。他详尽地调查了几乎每个议员的政治状况:他们如何得到议员席位?他们的家族究竟是托利党还是辉格党?他们所忠诚的派系是哪些,宫廷、辉格党世家,还是托利党领袖?纳米尔的研究表明,当时的政客尽是浅薄之徒,一心中饱私囊,决不会为党派原则所左右。支配十八世纪英国政客的,主要是个人和家族以往的恩怨和眼前的利益。需要指出的是,纳米尔并不否认当时英国政治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团体。他强调的是,十八世纪英国政界的党派意识,远没有二十世纪这样深刻,它的组织纪律也远不像今天这样严格。

纳米尔
沃氏在《权利辩护》中的几项指控,比如,柏克对不从国教者普莱斯(Richard Price)的个人怨愤,对乔治三世的恶意攻击,还有《法国革命论》写作之际柏克在辉格党内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不必讳言。1776-1783年美洲独立战争期间,伦敦的“美国之友”大多是不从国教者(dissenters)。此处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词的历史语境。1660年王政复辟后,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恢复国教(圣公会)的法令,在国内实行宗教歧视政策。1661年颁布的《市镇机关法》,要求市镇供职人员必须采用国教的圣餐仪式。1673年的《誓证法》重申:一切官员必须按英国国教会的礼仪领受圣餐,宣誓效忠英国国王,否认天主教教义中的“圣体转化”。相对于“国教徒”,此时产生了一个叫做“不从国教者”的群体,他们是“二等公民”,某些民事、政治和宗教权利统统被剥夺了。当然,针对不从国教者的压迫政策并不能贯彻到底,总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调整。光荣革命后,由于《宽容法》的颁布,完全强制不从国教者在星期天到国教教堂做礼拜,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无论政府还是教会法庭。领受圣餐者的数量,明显地下降了。更有甚者,在信奉三位一体说的不从国教教徒当中,还流行着“临时尊奉国教”(occasional conformity)的做法,藉此,某些“二等公民”可以规避《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等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也可以“有条件地”担任公职。不过,也有坚定的不从国教者,尤其是那些不信奉三位一体说的,比如普莱斯,拒绝为此宣誓,哪怕是一年一次也不干。在漫长的十八世纪(1660-1832),这些不从国教者曾做出各种努力,试图让政府取消《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变成了日后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当然,也变成了一股可以拉拢或者利用的政治力量。
美洲独立战争期间,柏克所属的辉格党处于“在野”状态,需要得到不从国教者的政治支持,以便更有效地攻击诺斯勋爵为首的内阁。柏克与这些不从国教者往来密切,其中,那位激进的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就深得柏克的赞许。到了1783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辉格党领袖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竟然和诺斯结成联合政府,这是英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政治联盟。1784年大选之际,为了争取宗教信仰自由,许多不从国教者转而支持新任首相小皮特,福克斯为首的辉格党遭遇了重大挫折。对不从国教者的“背叛”,柏克恨之入骨。“1784年后,柏克之于不从国教者,可谓敌意重重,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个人怨恨。对柏克来说,这种个人因素,永远不应该被低估的,因为情感上的忠诚和仇恨,往往会影响他的政治观点。”(F. P. Lock, Edmund Burke, Vol.2, p26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6)当下最权威的柏克研究者,就是这样说的。

普里斯特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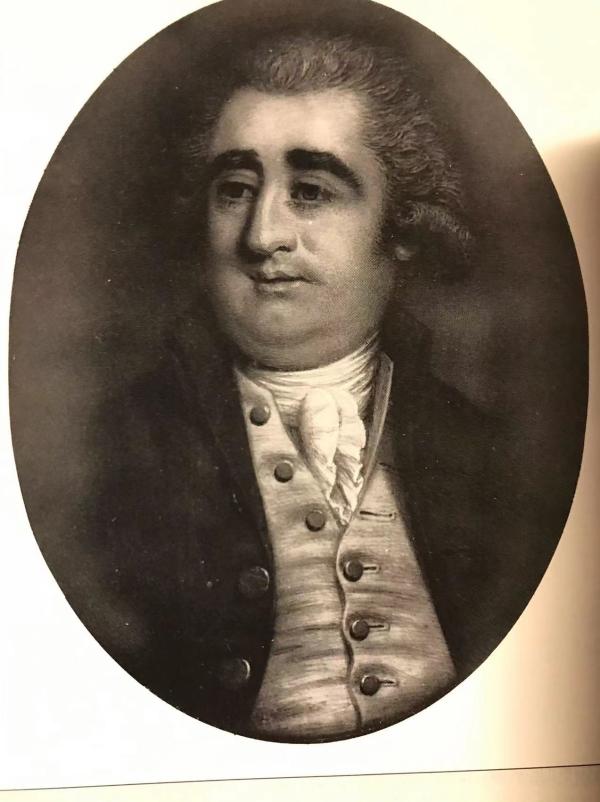
福克斯
再来看沃氏的第二个指控。1788年11月,乔治三世被诊断患有精神病。英宪中没有现成条款来规定此种紧急状态下的摄政事宜。小皮特内阁能否生存下去,或者,福克斯领导的辉格党能否重新组阁,都取决于乔治三世的病情。这是一个诱人的机会,柏克突然转而拥护他此前猛烈攻击的世袭主义立场。他争辩道,摄政王(就是日后那位臭名昭著的乔治四世)的权力不应该受到议会的任何限制。柏克极力鼓吹,摄政王可以通过“世袭权利”来继承君主的全权,就如同乔治三世已经“自然死亡”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氏这位激进的王权批评者,却在《权利辩护》中对那位“疯癫”国王及其家人深表同情:“阁下(引者按:指柏克)面前上演的,是如何惊心动魄的一幕!父子生死别离,一位丈夫和深情的妻子,从此天各一方,两地茫茫——一个人同他自己,分手道别,从此形同陌路,天涯沦落!”

摄政王
当时,连福克斯都不认可柏克有关“世袭权利”的极端说辞,更不必说一般不从国教者了。这种对王权的新兴热情,潘恩在《人权论》中讽刺道:“尽管柏克先生两年前为摄政法案和世袭继承问题费尽心机,拼命挖掘先例,他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把诺曼底的威廉揪出来,并且宣布:这就是名单上的头一名,这就是荣誉之源;这个婊子养的,这个英国民族的掠夺者。”(《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2001,191页)没有想到的是,1789年2月,乔治三世突然转危为安,柏克颇感尴尬。同年5月,由于弹劾英国的前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被指控为“杀人犯”),柏克受到下院的谴责;福克斯也故意回避柏克,反倒越来越和另一位辉格党新秀、也是著名的剧作家谢里丹(R. B. Sheridan)握手言欢。柏克和福克斯曾经联手提出“东印度法案”,弹劾该公司的高级主管黑斯廷斯。1790年1月,福克斯突然放弃了这一“事业”,柏克的愤怒达到了顶点。这就是沃氏所谓“阁下近来人望有所失”的背景。
三、十八世纪英国的不从国教者和社会改革
《权利辩护》中不乏奚落和谩骂,这样的语言,是当时的政论风气使然。柏克意欲削减或者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自主权,制止他们在印度的横征暴敛,黑斯廷斯弹劾案历时长达七年之久,柏克的不懈努力,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不过,本文关注的,是普莱斯所代表的不从国教群体,以及它和沃氏、柏克之争的思想关联。1770年代,英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大多都是不从国教的校长和牧师。当下的“修正派”历史学者克拉克(J. C. D. Clark)列举了其中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尤以博格(James Burgh)、普赖斯和普里斯特利最为著名(《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姜德福译,商务印书馆,2014,490页)。这些人中的多数,又被认定为阿里乌派信徒,比如普莱斯,或索齐尼派信徒,比如普里斯特利。简而言之,他们都坚定地反对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大力攻击国教的霸权地位。
沃氏和上面提到的三位不从国教者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沃氏和普莱斯的交往,戈德温的《忆亡妻》中有如下评论:“两人彼此十分关心,这是一种最纯粹的精神追求。虽然玛丽是在英国国教的信条中长大的,但她敬重这位德高望重的不从国教牧师,偶尔也会参加普莱斯的公开布道。”在《权利辩护》中,沃氏更是流露出无限的崇敬之情,不妨说,普莱斯是沃氏的“精神之父”。从回忆录可知,沃氏和博格夫妇私交甚密;同样,《女权辩护》也透露了她和普里斯特利的友谊。前面已经说过,在美洲革命时期,柏克曾经也是这些不从国教者的朋友。普里斯特利如此评论,“他(引者按:指柏克)深受不从国教者的喜爱…… 我们一直认为,他是我们可以依赖的人,特别是他在筹集资金或捐款事务中为我们说话。而且,他与我们拥有共同的事业,热心地支持美国争取自由”。但是在1790年,柏克改变了立场,普利斯特里的评价,也为之一变:“一个公开的美国革命的朋友,竟然与法国革命为敌,而法国革命是出于同样的原则,这在我看来,真是匪夷所思。”(转引自J. C. D. Clark e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Introduction”, p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柏克为何与这些不从国教者分道扬镳呢?或者,换一个角度来提问,沃氏为何与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不谋而合呢?
让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些不从国教者的观点和做派。博格的《政治论说集》以沃波尔和佩勒姆等英国首相为靶子,批评十八世纪早期的政治腐败,寄希望于宪政的重建,以遏制政府专权和道德沦落。“七年战争”之后,这些不从国教者开始染上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博格和普莱斯不仅参与废除《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的抗议活动,还大力促进议会改革的事业,特别是扩大选举权、废除腐败做法(主要指拉拢选票)和重新分配选区,从而确保更公平的代表权。这些激进吁求也是《权利辩护》的主要论点。博格写道,“只有民众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意愿和喜好,才是他们对其政府形式做出抉择的充分理由”(《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476页)。这样的言论和普莱斯那篇著名布道《爱国论》的主旨,简直如出一辙。
普莱斯认为,道德判断是理性的功能,它包含永恒的真理;他采取了一种自由意志论的立场,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自主地做他认为是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事情,而不必受所处环境的束缚。普莱斯相信,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都是可以理性地加以证明的。这些观念也都是《权利辩护》和《女权辩护》的思想底色。沃氏同样相信上帝的全能和仁慈;两个“辩护”均指出:每一场看似不幸的灾难,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是神圣目的的一部分。今天的女权主义主要是世俗意义上的,难怪当下某些女权主义者对沃氏的宗教关怀不以为然。
相对于沃氏及其丈夫戈德温,博格、普莱斯和普里斯特利年长一些,虽然接受了不从国教派牧师的熏陶,像平信徒一样生活,至少还是关注政治的虔信的基督徒。而沃氏的丈夫戈德温(还有那位倡导功利主义的詹姆斯·穆勒)则代表了年轻一代的不从国教者,他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转而基于无神论的原则,试图开创更为激进的政治制度。这里强调不从国教这个群体,是因为以克拉克为首的“修正史学”对英国“旧制度”的崩溃提出了新的解释。克拉克指出,1832年“旧制度”的最终危机并不是外来压力的结果,而是政府和国教自身退让的结果。也就是说,人口变迁、工业革命、城市化等等都不是酿成最终危及的关键因素,最为致命的,是宗教和社会政策的调整,尤其指1828年《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被取消了,1829年又通过了《天主教徒解放法案》。
四、宗教和启蒙的关系
沃氏和柏克都是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启蒙和宗教并不是对立的。哈耶克曾经说,法国人本着一种建构论的知识主义精神来解释英国人的传统、制度和理念,法国人这样的思路,哈耶克称之为“唯理主义”。那么,这位“亲法”的沃氏算不算是一个“唯理主义者”呢?哈耶克解释如下:“对于唯理主义者来说,理性不再是一种当真理凸显出来的时候认识真理的能力,而变成了一种从明确的前提出发进行演绎推理而达致真理的能力。”(引自《哈耶克文集》,邓正来选编、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484页)《权利辩护》以及《女权辩护》都清清楚楚地表明,沃氏的理性首先是“认识真理的能力”。这样的理性能力,恐怕柏克也不会否认。
柏克和沃氏都是国教徒,尽管沃氏怀疑柏克的信仰。《权利辩护》中有云,“或许阁下有所顾忌,不便公开谈论自己的信仰”,这里暗示柏克可能是一个隐蔽的天主教徒。这样的怀疑,在当时大有人在。如果说沃氏的思想有前提的话,那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也一定是柏克的前提。柏克自有深刻的宗教关怀,这使他与许多福克斯盟友自然拉开了距离。人是“一种宗教动物”,这是柏克整个职业生涯中的一贯立场。为社会生活的宗教基础进行强有力的辩护,这与辉格式的自由主义也并不矛盾。需要注意的是,柏克笔下的“教会”,若不加限定,指的是一个普世教会,罗马天主教派、英国国教会和新教不从国教者等,都包括在其中。沃氏在《权利辩护》中明确指出,自己不属于罗马天主教派,也并非新教不从国教者。戈德温在《忆亡妻》中说,尽管不定期参加礼拜,但妻子仍是国教徒,这样的说法是可信的。不过,沃氏对其他教派的态度同样也是宽容的。那么,柏克和沃氏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呢?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展开,柏克正向英国国教会的高教派立场靠拢。法国大革命之后,柏克思想中的新元素不是对君主制的赞美,也不是对贵族的称颂,而是他对英国国教作用的高度强调。比较而言,沃氏属于国教会的低教派,这和她所处的社交圈子有关,尤其指前面提到的不从国教者。柏克看问题的态度悲观一些,沃氏则更为乐观。这里再次可见普莱斯的影响,后者对人类可以无限完善的教义,一贯充满了热情。在普赖斯、普里斯特利的思想中,都有一个强烈的千禧年主义的因素。普莱斯和沃氏都相信,上帝干预人类历史,是为了使这个世界逐渐改善。因此,千禧年主义可以与社会进步的信仰相互调和,并行不悖。普里斯特利曾言,“我们正向着完美而迈进”,因此“无论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其结局将是辉煌的、天堂般的,超出我们的想象现在能够设想的程度”。柏克同样相信上帝干预人类历史,不过他所谓的神意,主要是通过“成规惯例”(也可以译为“因袭”)实现的。质言之,财产和权利是漫长的社会关系演化出来的产物,是约定俗成之物,就仿佛漫长的占有时间足以保障现存财产和权利的合法性。沃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此推论,时间可以洗去一切原罪。柏克的悲观表现在,面对“成规惯例”或者“因袭”的过程,我们实际是无能为力的。
柏克和沃氏的差异,恰好可以追溯到一种高/低教会神学教义的传统及其伴随的道德心理。大致而言,对原罪的信念越坚定,就越不轻易相信人类的制度设计可以克服它自身的缺陷。而且,柏克来自爱尔兰,在那里成长、接受教育,爱尔兰的国教(Irish Anglican)让他染上了更加强烈的怀疑气质,这也是其政治立场的促成性因素之一。普莱斯、沃氏也许没有意识到全面、大规模改革的内在危险。他们或许都没有充分地领悟到,习惯、习俗、偏见和惰性等在多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日常举止。乐观者往往低估了任何问题可以理性地加以解决的难度,或者夸大了人们乐意倾听和诉诸理性原则的程度。但这不意味着,贬低人类的理性,就是可取的。柏克嘲弄普莱斯是一个精于“计算”的神职人员、夸夸而谈的“形而上学者”。普莱斯的启蒙老师曾经是牛顿的好朋友,在数学和物理方面,普莱斯都掌握了非常扎实的知识。除了道德哲学和神学,他更以概率论、精算学和人口统计学而出名。他也精通实务,人寿保险业在十八世纪英国的迅猛发展,自有普莱斯的功劳,正是他最终说服那些专业人士:没有理由向女性收取更高的保险费,因为她们的预期寿命要比男性长。他还极力倡导拓展偿债基金业务。普莱斯的职业生涯告诉我们:一个精算师的技能,或者基于数据的合理计划,是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普莱斯和谢尔本勋爵关系密切,而以后者的宅邸为中心的那个社交圈子(Bowood Group)可以说是十八世纪英国政府的“智囊团”。无论是律师界、军队和教会的发展趋势,还是政治、经济和金融事务的最新动向,他们都掌握第一手的资料。
柏克赞美的国教会、(未经改革的)议会和贵族制度等,在1815年以后再次受到了各方的激烈批评,用克拉克的话说,那个令人心仪的“旧制度”很快就“轰然崩塌”了。可以说,当下民主国家或者社会奉行的大多制度或者观念,恰恰是普莱斯和沃氏所捍卫的:国家和社会机构,应被视为全体人民的公仆,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管理,而且,所谓的“民众”,决不是一个由少数精英阶层组成的群体。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