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笛安《亲爱的蜂蜜》:与“童年”再次相遇,扭转了心灵风向,也变动了写作风格
笛安《亲爱的蜂蜜》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巡礼
作家笛安长篇新作《亲爱的蜂蜜》刊登在今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并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项目支持名单。
新作展现了笛安写作风格的新变化,她借助一段成年人与儿童的“忘年交”让自身写作探入了家庭生活内部,让时间真切流动起来,并尝试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相连。

成为父母,面对人生角色的转变,这种巨大的现实变化并不会常常显露在作家笔端,许多作家善于或是极力隐藏这一切,但对作家笛安而言,她毫不隐藏这些对自己写作的影响。2014年,她推出了第一部古代历史小说《南方有令秧》,这部作品从开始到完成,正好横跨了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成为母亲。这种影响并没有突然涌现在她笔下,几年后推出的长篇小说《景恒街》里,她触及了金融行业职场题材,里面的主人公依然想着逃离芸芸众生、心怀不甘,这部小说为笛安的写作画下一个浓重的分号,之后她开始直视自己成为母亲的人生,并将一些感悟感受放进了中短篇小说中,其中有一篇越写越长,直到成为小长篇,近期它以《亲爱的蜂蜜》之名刊登在今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并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项目支持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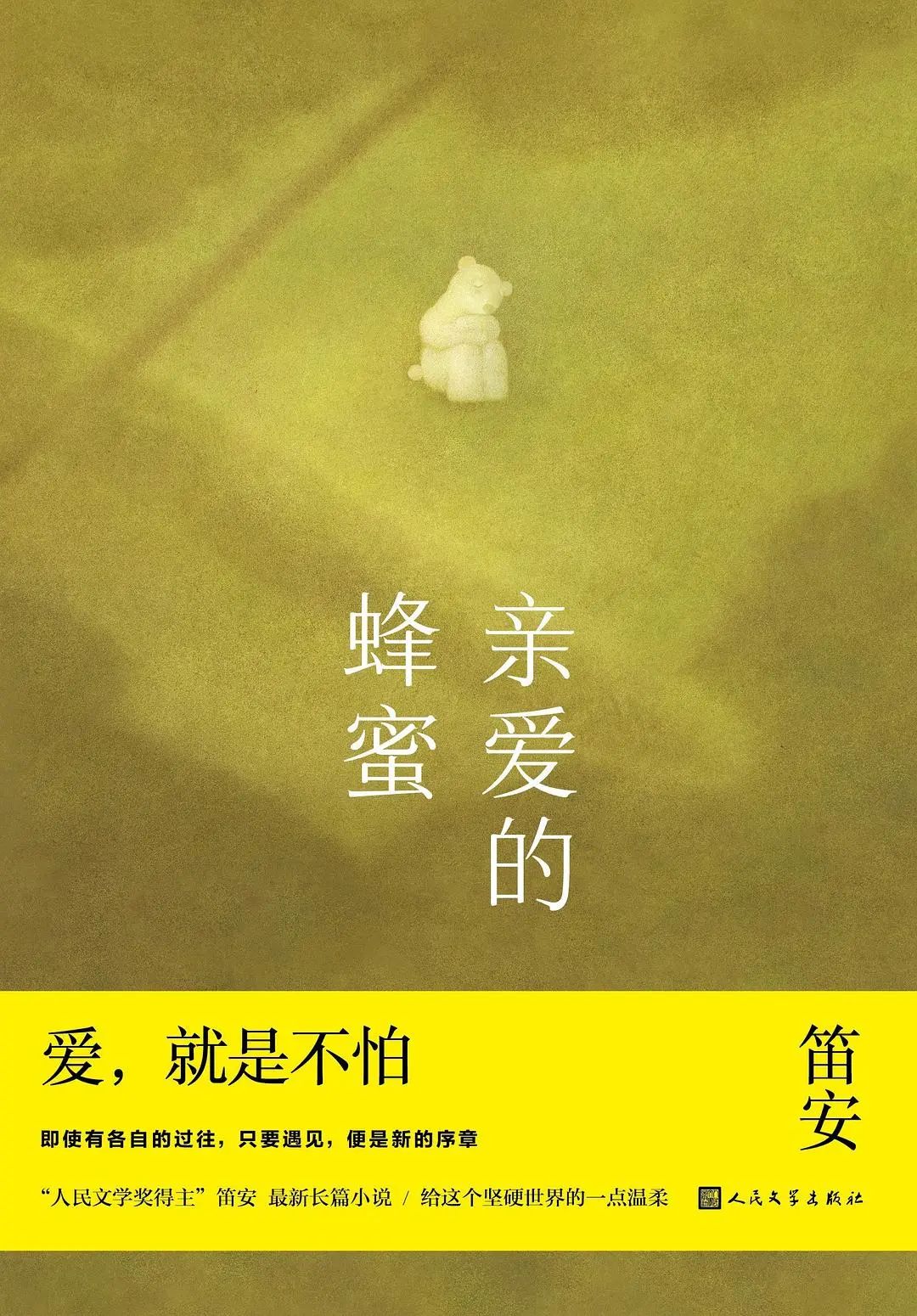
对一个青年作家而言,生命中许多顿悟的时刻迟早会渗透进文本中,有些是转折点,比如等来一个人类幼崽。在《景恒街》的后记里,笛安已经透露了这种感受,“四年来,人生经历过很大变化,可是,剧变之后,世界运转如常,往日内心深处的台风海啸,不过是种不高明的修辞。我像是恍了神,置身事外地站在阳台上,像凝视日出一样凝视自己的人生,没有感情也毫无感慨,只是当最绚烂的霞光消失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刚刚消散的,是我的青春。太阳自然会照常升起,可是明天此时,站在这里看日出的那个生命体,已经不会是我。天道如此,无须多言。”略带伤感的告别青春,颇像新作《亲爱的蜂蜜》里,36岁的熊漠北第一次听到约会对象崔莲一拥有一个三岁女儿时的心理落差,等到初次和小名“蜂蜜”的小女孩接触之后,熊漠北感觉对方的眼神“像中学教导主任的表情”,那天带给他的另一个感受是,“幼儿是洪水猛兽,我们文明人在他们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

笛安在这部小说里显然进入了一种因为熟悉而产生的“很愉快的体验”的写作过程,关于如何照顾人类幼崽以及蜂蜜行为对应的种种外界反应,都在她的现实体验之中,也因为这种母职体验,让她的写作第一次如此明显切近的进入家庭生活内部,让当下成为父母的“80后”读者感到格外熟悉。而笛安也表示,身边有些朋友表示,有了女儿之后,她的文字风格变化了许多,“我说不上这件事好还是不好,但它确实发生了,而且说明这个幼崽对你的人格有一个重新塑造的作用。”女儿的出现,唤醒了笛安自己童年的许多片段记忆,过往这些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几乎以为它们不存在,当因为女儿的出现而被重新捡拾回来之后,这为笛安带来了许多新的感受。她在小说中开始关心一个生命如何照耀另一个生命的过程,但她巧妙地转化了小说里的主角,不是母亲崔莲一如何被蜂蜜改变,而是突然出现在蜂蜜生活里的陌生叔叔熊漠北,他的人生发生的转变。在创作谈中,她坦言自己的目的,“当一个崭新的稚嫩的生命降临到一个成年人的人生里,TA将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这个视角的转化为《亲爱的蜂蜜》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感,或是如评论家何平所言,“时效性”和“此刻”。作为“独生一代”的熊漠北,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的社会变化,多多少少呈现出一些有共性的特征,他过于重视物质价格,忽视亲情关系,他会合理化自己的自私,“只要我还活着,漫长岁月中,我有的是时间一遍又一遍把自己做过的所有选择都合理化,实在不合理的就用‘当时还年轻’一带而过。在心里的某个角落暗自忏悔的,都是些无伤大雅的疏漏——这种忏悔类似于健身,可以给自己的心灵制造一些绝对能够克服的困难。”直到和蜂蜜经历了深入接触陪伴之后,熊漠北从纯真的蜂蜜身上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他蜕变成了蜂蜜眼中的“大熊”,一个有耐心和蜂蜜讨论冰激凌为什么会融化的大熊,一个会在深夜和蜂蜜等待花开瞬间的大熊,一个把自己汽车喷成蜂蜜最爱的粉红色的大熊。他仿佛回到了童年,改造了自己不够美好的童年,相信“一个人在百分之百表达惊喜与‘羡慕’的时候,能够没有丝毫卑微,没有丝毫自惭形秽”。

蜂蜜的角色任务,似乎完美契合了现代文化所构建和崇拜的“儿童”形象——充满童话感,等待启蒙,让成人世界自惭形秽。但笛安还未止步于此,她写作这部小说不仅是让蜂蜜的童年去激活一个成年人的童年记忆,另一个目的还在于探讨这些彼此相遇的人如何应对现实中重要的历史时刻。小说中,熊漠北与崔莲一感情并不那么顺利,如果没有蜂蜜这个“粘合剂”,或许还显得过于理性与脆弱,而新冠疫情的到来让他们再度审视自己生命未来的不确定性,确证彼此还是应该走在一起,“我和崔莲一会百年好合的,一定会。因为我们这些幸存者别无选择,百年好合,是唯一的出路。”在小说结尾,熊漠北说道。何平评价笛安的中篇《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时曾说,“作为新世纪新北京人之渺小的一个,笛安有为这浩大群体命名的雄心,让其中籍籍无名者有名,让他们有个人的命运史和心灵史。橘南、章志童和洪澄,虽为房东和租客,却属于同一个阶层,故而他们可以成为暂时的精神共同体而相依为命、守望相助。”这个评价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亲爱的蜂蜜》的结局,等疫情结束之后,两个成年人是否还会如此确信这份感情,并不那么重要,他们的命运史和心灵史已经发生了改变,并且被清晰勾勒了出来。
对笛安而言,她借助这段“忘年交”让自身写作探入了家庭生活内部,让时间真切流动起来,并尝试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相连。她的写作风格已经发生变化,她曾观察文坛一些青年作家的话如今也像是在形容自己,“我现在明白,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的丰富,最初语言里鲜明的个人特色,会越来越平、越来越少。一开始非常锋利、非常露锋芒的那种特别的东西,它是会随着时间减退的。风格形成后,它会幻化成别的东西。”

小说选读
题记
大熊说——我应不应该留在这里,替蜂蜜守着这朵昙花呢?
莲一说——反正有蜂蜜在,人生再没有意义,我也不能死。
蜂蜜说——为沙玛亚?
一
那是我和崔莲一的第三次约会。
我有点后悔把车开出来,起初怕周五,又是晚高峰,电影散场叫车会太困难。但是还没走完停车场出口的坡道就已经被塞住了,我注视着前车的车牌尾号——它的尾号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知道,只不过我已经开始将“京N**762”后面三个数字在脑子里任意重组——如果没有开车,晚饭是不是就可以顺势喝几杯,也许两个人就能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多说几句,不小心流露非常真实的感受——最有意思的部分通常就在这里,然后就心领神会了:我们之间是到此为止,还是可以期待下一集……我往副驾上看了一眼,崔莲一今天异常地沉默。
我自认为没说错什么——除了刚刚从座位上起身的时候,我沮丧地表示这部电影是个烂片——而我知道导演碰巧是她的朋友。但是这应该算不上是冒犯,崔莲一跟这位导演的友谊并没有深厚到那个程度。后面的车开始狂躁地按喇叭催我,狂躁在持续——好像他的下属们完不成本月KPI,他的小孩由于父母社保问题无法获得朝阳区的学籍号,他老婆越来越瞧不起他……这一切都怪我没有及时地踩油门。
我缓缓驶出了坡道,汇入马路上的车流,继续塞着。
崔莲一关掉了电台,我以为她有话要讲。安静是与两百米之外的绿灯一起来临的。这让我有种错觉,好像“安静”这个词本身就会散发绿色光芒。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那个命,在绿灯消失之前走完这两百米。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她把全部的头发都拂到了右边,在右边的胸口垂下来,以至于我能清楚看到她左半边脸上凝固着有点尴尬的微笑,以及她的脸庞后面的夜色。
她看了一眼窗外的巨幅广告,“熊漠北,我有件事和你说。”
我听见了自己在呼吸。那个导演——应该不至于给她献过血吧。她的声音有种若隐若现的脆弱,说话之前,先笑了笑,“我就开门见山了,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怎么办?可是现在离订了位子的餐厅还有至少三个红绿灯——我转过头认真地看着她,她却没有回看我,“但是我不知道老杨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你知道的吧——我有个女儿,快三岁了。我自己带。所以,可能我有很多时间必须得给她,如果你介意这件事,我们就……现在说清楚比较好……”
我转过了头,直视着正前方,我说:“我当然知道,虽然我自己对小孩没有经验,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
前面那辆“京N**762”开走了,留给我一段难得干净的路面。看着绿灯转红,我踩了油门。“哎,不行!”崔莲一的声音警醒了我,轮胎在路面划出刺耳的声音。我看着她,她集中精神的时候脸上总有一种好奇的神情,我总算回过神来,说:“因为你自己从来不提,所以我也不好意思主动问。等你觉得方便的时候,介绍我们俩认识,就可以——如果你完全不想介绍我认识她,也没有任何问题,决定权在你。”
她笑了,然后咬了一下嘴唇,继续笑,“我等会儿想点他们店里的那个柠檬迷迭香烤鸡,”她用两只食指认真地比了一个距离,“点一整只。”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是在那个她如释重负的瞬间,开始爱她。
其实老杨并没有告诉我她有个女儿,我刚才是第一次听说。可我当然不能让她看出来这个,否则,显得我太没见过世面了。
那天深夜,我还是给老杨打了个电话。毕竟我顺利地恋爱了,得对介绍人表示感谢。顺便礼貌地问一句,他最初为什么省略了如此重要的信息。老杨一脸无辜地回答:“对啊,她是有个小女孩,特可爱,我没说吗?……哦,就算我没说,你跟她加上微信以后不也能看到她朋友圈?我还给那个小女孩的照片点过一两次赞……哎哟,看来她最近三个月都没发朋友圈,设置的是仅三个月可见——所以你还真没看见……可是这怎么能怪我呢,我早跟你说了,自从忙活我家双胞胎上小学的事儿开始,我的脑子经常不够用,你不能像过去一样什么事儿都指着我,我就是牵个线,剩下人家的背景资料不是应该你自己去做功课的?——这不是刚开始嘛,又不一定走得到需要你跟孩子相处那一步,瞧你这点儿出息……人家可还不一定愿意嫁你呢,八字没一撇的事儿……”
全是他一个人在说,我只能静静地听,顺便想象他所有的表情,以及把电话夹在肩膀上,便于解放双手在空气中做出相应的动作。读书的时候他选修过一年的意大利语,没学会多少单词,却跟那个给他上课的意大利博士生学会了说话时飞舞双手。
不对,我的名声怎么不好听了……算了,多年来一贯如此。老杨总有办法成功地让我忘了一开始要说的内容。
那晚之后,大概是两个多月以后吧,我第一次见到了成蜂蜜。
那天我和崔莲一原本约好去看一个多媒体艺术展。我像平常一样,提前十五分钟到达展厅入口处,正打算给她发个信息,却突然看见某个方向蹿出来一个摇摇摆摆的小姑娘,准确地说,是因为身材比例大概是四头身造成了视觉上的那种卡通感,让我认为她行进的方式是像小动物那样摇摆着。我试着躲开她,避免撞到我的膝盖,她仰起脸,以一种严肃的神情看着我,我还以为那是个错觉,但其实不是。就在这时,崔莲一的声音从这个小家伙身后传了过来。
“熊漠北,你来这么早。”崔莲一有点措手不及地把一个硕大的帆布包甩到身后,然后弯下腰,熟练地抱起这个小家伙。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平视对方了。“真不好意思,阿姨今天临时请假了,就在中午——我来不及安排,所以只能把她带来。”我真笨,其实直到崔莲一这样熟稔地把她抱起来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个小姑娘是谁。“蜂蜜,这是熊叔叔,来打招呼。”崔莲一跟她说话的语气有一点微妙的不同。我的姓氏实在太不占便宜了,熊叔叔,根本没有选择只能扮演憨厚老实。
她依旧毫不退缩地看着我。她的头发绑成两根冲天辫,像是圆脑袋上的天线,只不过这两根天线的末梢还绑着两只草莓;苹果脸过于饱满,脸蛋嘟出来以至于牵扯得嘴角都有一点点下垂;漆黑的圆眼睛,像阿拉蕾——当然也许是她胸前那个阿拉蕾头像误导了我,总之让我觉得相似。可重点是:冲天辫,苹果脸,小胖手,阿拉蕾的眼睛,却匹配上一种眼神像中学教导主任的表情——的确令人过目不忘。
......
原标题:《笛安《亲爱的蜂蜜》:与“童年”再次相遇,扭转了心灵风向,也变动了写作风格》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