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汤晓燕评《时尚及其社会议题》|从阶级到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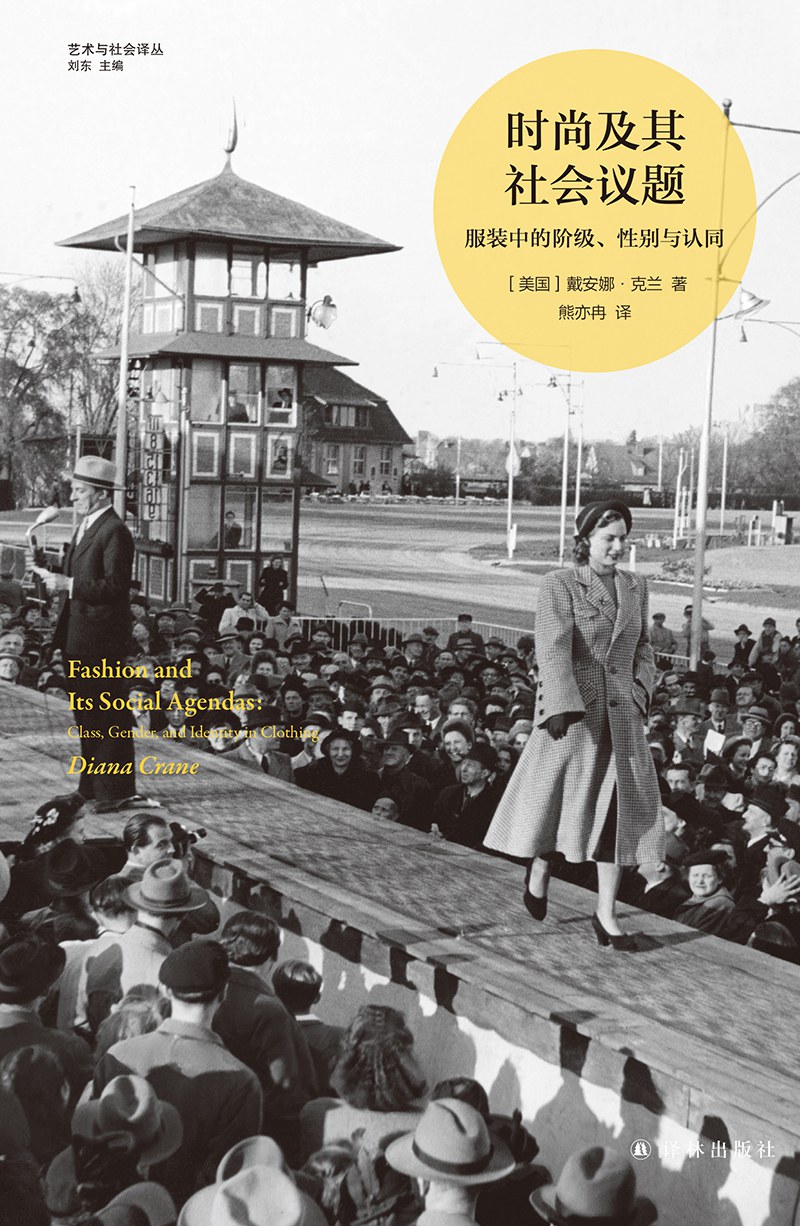
《时尚及其社会议题:服装中的阶级、性别与认同》,[美]戴安娜·克兰著,熊亦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2月,350页,68.00元
戴安娜·克兰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常年关注艺术、文化、媒体和流行文化等领域。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克兰非常重视对于时尚的研究,因为她觉得“作为最显著的消费形式之一,服饰在身份的社会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着装选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研究领域”(第1页),并且“作为一个社会学主题,时尚处于该学科几个核心主题的交叉路口”,有鉴于此,她认为时至今日,关于时尚的研究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许这是因为它有时被视为“资本主义对公众的操纵”并与“女性的追求”相关联(Patrik Aspers and Frédéric Godart, ‘Sociology of Fashion: Order and Chang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3, Vol. 39 [2013], pp. 171-192)。克兰出版于2000年的《时尚及其社会议题:服装中的阶级、性别与认同》可以看作对上述观点的详细阐释。
这本文集共八章,第一章为概要,第八章为总结,作者在其余部分详细讨论了时尚与阶级身份、性别建构以及它与生活方式选择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些内容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便是:
作为社会地位和性别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服饰有效地维护或者颠覆了符号边界,并显示出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感知自己的社会结构中的定位,以及如何协调不同的地位边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服饰也是在公共空间中实现身份认同的主要手段。(第1页)
这一观点看似与时尚研究的经典观点,即格奥尔格·齐美尔的“滴流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齐美尔在1904年有关时尚的文章中提出,时尚的扩散是由上而下的“滴流论”。“滴流论”可简单概括为,时尚由上层精英创造、用以展示自身的社会地位,而较下层的群体会去模仿这些时尚的服装款式或者配饰,来“假装”自己也属于前者所在的集体。当某种款式被大范围的模仿之际,也意味着它失去了此前精英阶层用来作为身份标识的意义,精英阶层便会抛弃它,再去创造另一种新的时尚。这样的“创造-模仿-抛弃-新的创造”的模式是时尚现象的内在机制。对此,麦克拉肯曾经概括道:“该模型背后的社会过程是模仿、社会传染和分化”(McCracken 1985, 39)。换言之,地位较低的群体通过采用地位较高的群体的服装来寻求获得地位,并启动了一个社会传播的过程,即风格被地位较低的群体相继采用;作为对这些发展的回应,地位较高的群体再次寻求更新的款式来以示区别。简单而言,齐美尔相信,时尚的背后是阶级区分的需要,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区隔》中也持近似看法,尽管后者的理论更为复杂,更强调作为审美与文化的阶级在时尚生产过程中的影响。
那么,克兰此书是否只是在老调重弹呢?显然不是。克兰的书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不平等对时尚传播的影响。在她看来,在这样的社会中,“阶级地位比生活方式更为突出,人们通常倾向于接受相对固定的社会身份,但地位较低的群体会试图效仿地位较高群体的风格与行为”(23页)。第二部分,她则着重分析在二十世纪的“碎片化”社会中,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职业环境依然是地位等级分明的领域,但在其外部,社会区隔更多以生活方式的面貌呈现。因此,时尚的传播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渗透”,需要用新的模型来解释“着装在当代碎片化社会中的作用”(24页)。第三部分围绕着时尚中的性别议题展开。
从阶级区隔到时尚的民主化
在本书的第二章,作者借助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普莱(Frédéric Le Play)对十九世纪法国工人阶级家庭所进行的个案研究,把时尚作为“阶级文化与符号边界”讨论。勒普莱的社会学调查可谓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有关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是他和合作者一起调研一百五十份家庭案例的研究专论,他们在1850-1874年、1875-1909年两个时间段分别调研了法国的四十二个家庭和三十九个家庭,这八十一个家庭分属于巴黎熟练工人、巴黎非熟练工人、外省的熟练工人、外省非熟练工人、拥有或租用土地的农民以及非熟练农场工人(31页)。访谈记录的内容包括“每个家庭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该家庭所居住的社会环境”,甚至详细到资料中包含作为调查对象的“所有家庭成员全部衣物的完整清单和每件衣服的价格”(第6页)。资料的其他部分则是有关英国和美国的类似调研记录。正是在此基础上,克兰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得出了下述结论: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服装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尽管拥有一件以上时尚单品的工人人数有了较大提升,但时尚风格的扩散仍然仅限于特定的物品。并且,虽然他们的总体收入水平有了提升,但是除了西服和大衣以外,他们对中产阶级其他时装类型的占有度却没有什么变化。(38页)
另一方面,作者惊讶地发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法国工人阶级中最时髦的群体并不是收入最高的巴黎熟练工人,而是这一阶级中更下层的那些工人。也就是说,在工人群体中,较低阶层比较高阶层还要时尚(45页)。齐美尔的“滴流论”在此明显失去了解释力。或许要引入不同人群对于服装的态度差异来对此加以阐释,克兰认为,对于底层工人阶级以及以女仆为代表的年轻女雇员来说,“衣着作为一种表达身份认同的手段,与闲暇、梦想和抱负相关,而并非由卑微的职业所赋予”(65页)。
随后的第三章主要讨论时尚与民主化的议题。在此章节中,作者不再使用勒普莱的调查数据,而是“借助各类汇总数据、历史学家对阶级结构的描述、服装史学家对着装行为模式的重构、针对美国和欧洲家庭预算中服装支出的研究以及大量记录人们衣着情况的照片”(70-71页),讨论关于服饰是否有助于“模糊”社会地位进而作为摆脱社会约束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在克兰之前,李·霍尔(Lee Hall)等人时尚领域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在服装工业大规模发展之后,时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服饰或者时尚民主化理论“意味着服饰的最终标准化,社会阶级的差异在这种标准化中将不再明显或已然消失”(66页)。那么,是否真的如不少服装史家们所提出的那样,随着服装产业的兴起,此前外表上显而易见的等级差异此时开始逐渐消失呢?克兰的研究表明,关于人们在十九世纪的着装与十八世纪相比,是否呈现出更不明显的阶级差异这一问题,其答案比想象中更为复杂。
她通过分析帽子的社会意义表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帽子用以彰显男性社会差异,但在此之后,帽子的角色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帽子比夹克和外套的价格要低得多,所以它们为模糊和改变传统的阶级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契机”(89页)。同样的情况既出现在法国也出现在美国工人阶级中,这说明,价格相对较为低廉的配饰使人们能够“部分实现”他们所渴望获得的更高社会地位的愿景。再加上新式服装样板的大范围销售以及机器制造服装产量的提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工人阶级能够穿得更体面,在外表上更靠近中产阶级。不过,这只是所谓的时尚民主化的一个方面,在硬币的另一面,克兰告诉读者,无论是从服装的面料、质量还是帽子、手套和披肩的数量来看,阶级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这些细节证据表明在十九世纪,时尚或许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民主化,但是它的民主化效应并不应当被夸大。

格奥尔格·齐美尔
综上几章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克兰的看法确实有与齐美尔或者布迪厄的观点如出一辙的部分,但在她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这部分占的比重并不大。更重要的是,克兰希望进一步证明,在效仿地位较高群体的风格与行为的过程中,较低阶层并非作为一个整体行动,收入、社会关系以及性别等差异都会影响其接受较高群体时尚时的反应。或者可以这样说,齐美尔等人提出的早期经典时尚理论对于十九世纪晚期的情况并不完全适用,或者说在使用时需要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或者限定。因为,一方面,此阶段的时尚或许依旧遵循着“滴流论”,但是它向下扩散的方式并非依次向下,有的时候是越过了某些阶层,跳跃式地向下传播。与此同时,克兰还向读者证明了,那些接受了中产阶级服装的工人阶级并不一定完全模仿前者的价值观或者生活方式,有时他们甚至强烈地拒斥这些方面。
“碎片化”社会中的“集体选择”与“个人选择”
事实上,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以齐美尔为代表的“时尚-阶级区分论”就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说克兰的观点是对上述观点的修正或补充的话,那么另外一些社会学家的看法就更具有颠覆性。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布鲁默(Blumer),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时尚的“集体选择理论”。布鲁默提出,齐美尔将精英在时尚运作中具有的影响看得非常重要,精英所使用的那些区隔徽章成为时尚;但这种观点几乎忽略了时尚的核心。事实上,不是精英的声望使设计变得时尚,而是设计的适合性或潜在的时尚性吸引了精英。也就是说,设计必须符合消费大众感兴趣的方向。此外,布鲁默还认为,“时尚运作的领域非常广泛。将它限制在或集中于服装和装饰领域,就是对它的发生范围有一个非常不充分的认识”(Herbert Blumer,‘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Summer, 1969, Vol.10, No.3, pp. 275-291)。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了包括法国社会思想家吉尔斯·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在内的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即时尚可以应用于任何领域的核心社会现象、机制或过程。
另一位社会学家麦克拉肯(McCracken)则提出,向上流动的地位群体似乎被激励采用新的风格作为新地位的标记,以将自己与原本从属的群体区分开来。而那些地位最高的群体,他们的地位稳固且拥有巨额财富或者遗产,所以往往对最新时尚相对漠不关心。换言之,麦克拉肯相信,时尚是属于新近加入上流社会的精英阶层用以隔绝自己“出身”的某种方式。拉海耶和丁沃尔考察了二十世纪以来的时尚流行,他们发现,由于青少年亚文化的成员通常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有时是奢侈品时尚物品的最狂热消费者,他们会在某种新风格流行之际,迅速效仿它,并会在它失去时尚声望之前丢弃它。上述现象的出现以及社会学家对它们的深入分析,使得时尚传播的理论变得更加复杂。
在上述反对者的声音中,布鲁默的“集体选择论”被认为是最有力的。克兰此书的后半部分几乎可以说是围绕着“集体选择论”展开,尤其是本书的第五章。
在这章中,作者关注的问题是时尚生产与全球化的关系。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时尚体系在机构组织、数量以及新风格的创造者及其传播过程等多个层面发生了至关重要的改变。克兰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来自从“阶级”时尚到“消费”时尚的变化,在取代了阶级时尚的消费时尚中,风格多样性得到了大幅提升……消费时尚“不再以社会精英的品味为导向,而是融合了社会各阶层的品味与关注”。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大类风格:奢侈品时尚设计、工业时尚和街头风格,并且这三类风格的变化与传播过程各不相同(154页)。更有意思的是,和前一个世纪时尚在不同国家发展路径的大同小异相比,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法国、美国和英国的设计师的地位和角色也出现了较大差异。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将其一一对应,但从其描述来看,似乎这三个国家各自主流的时尚恰好对应了上述三大风格,而这又与这三个国家的设计师在各自时尚行业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不无关联,或者用作者的话来说,“这取决于时尚组织的性质及其与消费者的关系。……三大时尚界(巴黎、纽约和伦敦)有着各自截然不同的侧重点。在每一种背景下,时装设计师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角色群,这从他们将自己定义为艺术家、艺术工匠或企业家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191页)。例如,在法国奢侈品行业,设计师们引领的是“趋势”(la tendance),而不是直接向公众传播他们的奇思妙想。事实上,众所周知,法国时装周上的时装基本上也无法让大众穿到公共场所(186页)。而英国的设计师可能更爱好“城市街头文化的丰富性,着装意识形态作为颠覆而非从众的个人声明”(185页)。概言之,新风格的源头再也不像十九世纪那样集中于巴黎的精英阶层,它的来源变得愈发不可捉摸,因为消费时尚实际上就是在贩卖这样或者那样的生活方式,而当多元文化日渐取代被广泛接受的某一种单一生活方式或文化审美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相互背离甚至冲突的价值观需要用不同的时尚风格来表达。
在这里,克兰把对于时尚的消费与生产过程结合起来,从而对其整个传播过程进行考察,并且她注意到不同国家与地区在这一庞大的时尚体系中担任了不同的“职能”,或者说侧重于满足不同的需求。概言之,新的时尚系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逐渐出现,并对十九世纪传统时尚机制形成严重挑战。克兰对其进行了准确的概括:
在新系统中,对时尚的顺从不再主要受社会阶层地位的渴望影响,而是成为表达基于性别、性取向、年龄、种族和民族观念的个性细微差别的一种手段。服装的选择是基于个人品味,而不是符合时尚权威制定的规则。对风格的个人诠释的强调改变了新时尚的开发方式和向公众展示的方式,并导致了精英时尚界的扩散。它们的代码通常是不透明的,但对于内部人来说却是有意义的,它们为他们提供了构建社会身份的基石。
其实强调时尚中的个人色彩,并不是克兰的首创也不是她理论的重点。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利波维茨基已经充分强调在时尚发展历程中个人选择的重要性(Gilles Lipovetsky, The Empire of Fashion: Dressing Modern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76 pp),他认为尽管阶级竞争的社会动力和追求区分符号在时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质疑时尚完全基于经济和物质因素的观点,坚持将个人作为社会分析的单位,并拒绝让个体差异屈服于对社会变革的系统描述。克兰的观点更像是介于利波维茨基与布鲁默之间的折中主义,即作为个体的个人选择从属于某个集体,然后以能表明这个集体身份的装束展现自身。或者,用苏珊·凯瑟的话来进一步描述其中的复杂性,即:服装风格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澄清和表达矛盾心理。然而,各种各样的服装风格,加上自我生产的倾向,导致个人构造的外表高度模糊,其含义必须在社会互动中集体协商。服装风格未能解决文化矛盾导致时尚变革(Susan B. Kaiser, Richard H. Nagasawa and Sandra S. Hutton, ‘Fashion, Postmodernity and Personal Appearance: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Formula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14, No. 2 [Summer 1991], pp. 165-185)。有学者认为布鲁默观点的优势之一是与“阶级分化”相比,“集体选择”的实证更有效。但他的理论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其中之一便是布鲁默忽视了社会心理所起的作用,也完全没有处理社会心理与时尚产业以及时尚进程之间的关系。在克兰此书中,这一重大问题显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当然,倘若作者能提供更详实的社会调查对其观点加以切实证明,可能会使她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小结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二十一世纪以来,关注时尚的研究者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时尚研究可供挖掘的议题远超预期。不论是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化学家或者是性别研究者,都可从中找到充沛的论证资源。正因为如此,时尚研究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同样由于不同学科都对其产生了极大兴趣,时尚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跨学科的讨论。从这个视角来看,克兰的这部著作很好地向读者表明,充分运用历史社会学的资料对时尚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让抽象的时尚传播系统模型变得生动具体且更为贴近事实。
不过,本书也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领域,尤其是与性别相关的几章内容。例如:在第四章“作为非言语反抗的女性着装行为:符号边界、另类着装与公共空间”中,作者虽然较为详细地呈现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西方女性对于男性装束的采用情况,但是基本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对此给出相应的阐释。原本应为书中主要内容之一的“性别”,在这里显得有些浮光掠影。事实上,其他研究者已经充分注意到,在该阶段,白领劳动力中女性人数增加,人口增长,体育运动的推广,着装改革运动的影响,以及成衣大批量生产的民主化效应等因素催生了美国女性服饰上的显著改变。换言之,穿衣自由度的增加反映了美国女性可担任社会角色数量的变化。从性别服饰方面来看,有些女性开始自由选择男性风格为己所用,而绝大部分的男性依旧固守那些长久以来彰显男性气质的服装。
此外,第七章“时尚形象与女性身份的争夺”这部分,作者通过访谈调查的方式,让实验对象对某些时尚广告中的模特及其隐含意味发表看法,以此进行研究分析。这样的社会学调查实验,无论从实验的设计、样本量,还是结论的导出,似乎各个环节都略显粗糙。研究时尚的学者很难回避性别问题,因为当时尚与外表紧密关联时,性别一定会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仅仅讨论二者在现代社会的关系,是无法解答这一问题的,必须深入到性别建构的历史过程中,考察服饰/外表在社会性别分工、性别意识塑造等各个方面所担任的角色,才能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性别、社会群体差异或认同的深度联系。
虽然社会学家肯定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学对时尚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渊源,对于更好地理解该领域当下正在解决的问题类型非常重要。并且正是古典社会学研究将时尚的理论分析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但事实上,除了上述时尚中的性别议题以外,关于如何界定时尚,时尚在特定社会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时尚和我们身处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有关时尚的诸多深层问题,都需要重新回到时尚的历史脉络之中。抛开历史,我们无法窥探到时尚的真面目。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