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谈︱从细节中重新认识中国女性历史的复杂性
9月4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莉教授围绕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精选版展开对谈,对谈由《南方都市报》高级记者黄茜主持。本文为思库与澎湃新闻合作刊发的文字稿。对谈稿已经主讲人审定。
打破有关传统中国妇女的刻板印象
黄茜:今天我们的分享会主要围绕两本书展开,一本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伊沛霞的《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另一本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学者,一位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冬梅老师,另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莉老师。
前段时间历史剧《梦华录》热播。在该剧中,几位小姐妹突破了身份和性别的界限,在一起轰轰烈烈地搞事业。宋代的女性真的能活得这么飒、这么有风采吗?伊沛霞教授的《内闱》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宋代妇女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首先请两位老师谈一谈,这本书里有哪些内容让你们觉得刷新了对宋代妇女的认识。

赵冬梅:这两本书都不是新书,它们翻译过来有十多年了,是经历了时间考验的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把西方人研究中国的所谓“他山之石”成建制地翻译过来,让中国的读者能够了解海外的人怎样看我们的历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由刘东老师主编,至今已经34年了,我是这套书的译者,翻译过两本书。这套书一方面是要让中国的读者了解海外的学者对中国的观感,另一方面是要让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学术界能够相对迅速地了解到西方的同行在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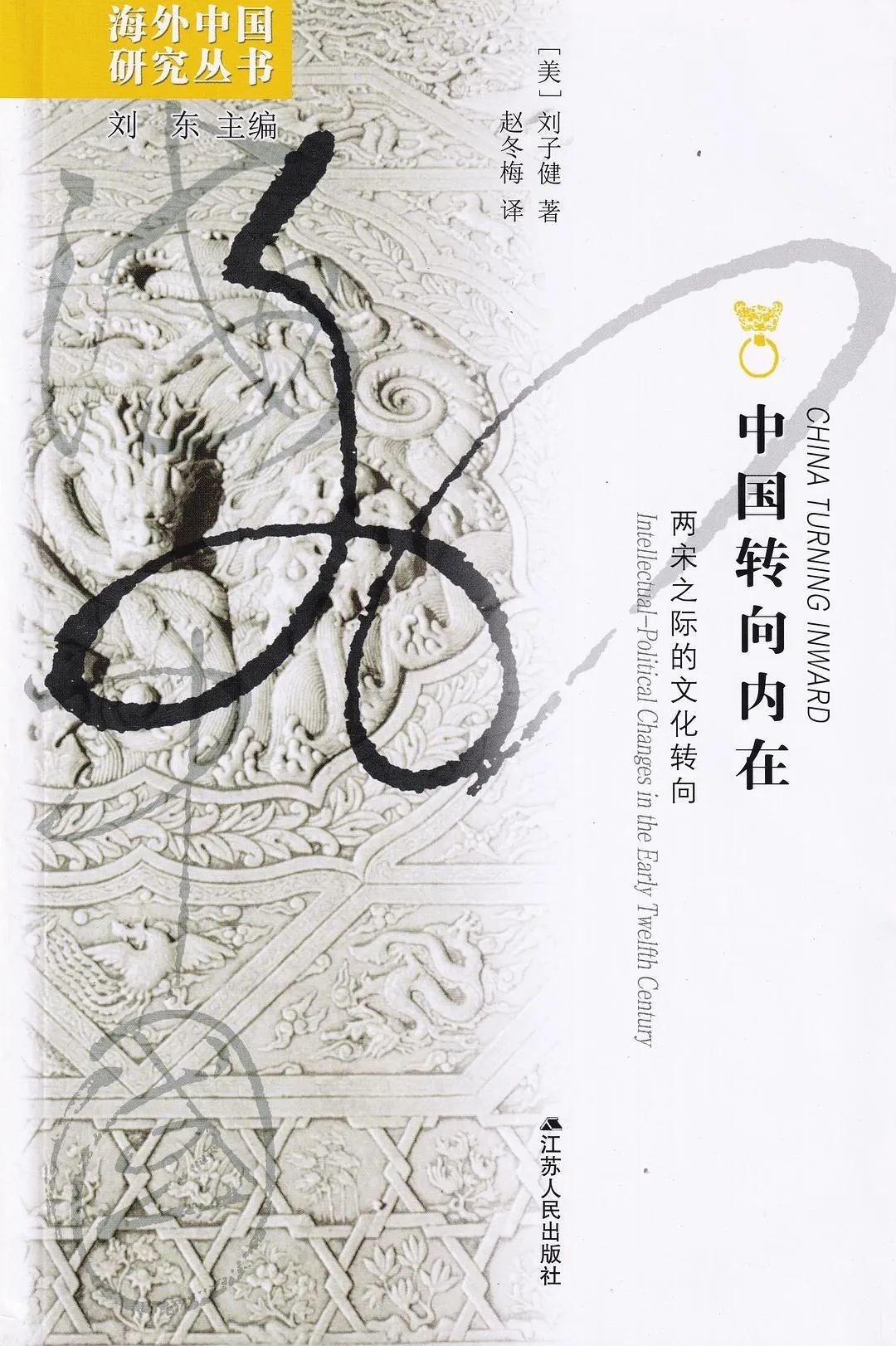
赵冬梅教授翻译的两本书

赵冬梅教授翻译的两本书
这些在海外的学术生产环境中生产出来的书,有两个特点。一、完整,基本上每一本书不管题目大小,都做得很完整——这个标题之下应该做什么,这本书是自洽的,结构上是完整的。二、它面向的是对中国不够了解的读者,所以会相对浅出,翻译过来之后刚好填补了一个空白。我们这边学术的东西是纯学术的,不太平易近人的。所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来一本就火一本,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读者当中。
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这两本是写宋代女性的《内闱》和写明清女性的《闺塾师》。尽管我不做妇女史研究,但是宋代的妇女史我是肯定要读的,而且我教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女性的东西也是要关注的。这次我重读这两本书的感受就是,这两本书有一个很强烈的企图,就是要打破有关传统中国妇女始终处在被压迫的状态、处在无声的状态的刻板印象。
尤其是《闺塾师》,你会发现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着女性写作者,而且出现了出版女性作者著作的小高潮,这是我们之前不能想象的。还有一点就是,在传统中国,我们三个人坐在这儿对谈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在传统中国的社会规范当中,女性是被限制在inner quarters/内闱的。我们通常会认为,当时能够在公共领域出现的女性,要么是妓女,要么是女道士、尼姑,再有就是三姑六婆,是完全上不得台面的。但是这本《闺塾师》告诉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女性结社活动的,在传统上相对由男性所掌控的领域里还是有女性的发声,有女性的存在。这是这本书比较震撼之处。
张莉:赵老师是作为译者,我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读者。我第一次接触到《内闱》和《闺塾师》是18年前。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很偶然地买到了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对我有非常大的触动和启发,当时我已经开始写我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为什么看这两本书会有很大的触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是基于女性视角的研究。伊沛霞也好,高彦颐也好,她们都是西方的女性研究者,她们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也是女性。我当时非常好奇她们要怎么去理解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那些女性,怎么理解她们的生活、书写她们的生活。
我了解宋代女性的生活是从《内闱》开始的,对我来讲,《内闱》是掀开了我们并不知道的女性生活的另一面,而《闺塾师》是让我们看到了更鲜活的女性写作、女性阅读、女性结社和女性出版。
伍尔芙曾经有一个说法:世界的女性写作者,在试图通过自己的笔让更多的人了解不为人知的女性生活。她把这样的写作者视为“持微火者”。不管是高彦颐,还是伊沛霞,她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比文学更接近于“持微火者”。在此前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认为女性生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暗哑的、灰暗的、充满血泪的历史,但是当我们真正地回到宋代、回到明代,我们会看到那些具体的、活生生的女性,她们是怎么活过的。女性研究者做女性研究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感同身受那些女性当年的情感和体会。当一个女性面对不如意的婚姻、不理想的姑婆环境,面对家族内部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在这些书里面可以看到。
传统的历史其实把所有的女性经验打包了——她们是被压迫的。但是如果你把女性作为主体,你就会发现女性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处境之下,固然有受压迫的那一面,但是她们也有反弹或者说反应。所以正是前辈们的生活,给了我们一个母性的传统。这两本书揭示的是古代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平衡婚姻和家庭、怎样平衡写作阅读和日常生活,你会从细微处认识一个女性。重读中国女性历史,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女性的生活。

赵冬梅:我想补充几句。伊沛霞教授是美国宋史研究领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前辈。我们现在看到的女性系列这6本书,是20多年前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女性的研究,中国人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是滞后于西方的,她们是我们的前辈。我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是88年上大学,92年大学毕业读硕士,我有两个同班同学,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读的是妇女史研究,他们两位都是历史性的人物,是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第一位女硕士和第一位男硕士。
这些书的作者是我们的前辈,她们打开了一扇窗,启发了后来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妇女史的研究。这两本书的性质略有不同,高彦颐那本特别典型,它是针对一个特殊地域的特殊群体的研究,所以它的人群对象材料非常扎实,是一个整体。因此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些书的学术价值、阅读价值都还在,不仅没有被时间冲淡,反而被时间加固了。
黄茜:事实上大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就已经有了妇女史相关的学术著作,比如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刚才赵老师提到的90年代以来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和陈东原时代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之间是有一个传承关系,还是中间有断裂?
赵冬梅: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出现在五四以后,等于说从那时开始中国就有人在做妇女史研究,但是中间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断了很久,在50年代以后,妇女史在历史研究领域是非常边缘的。我们妇女史研究的重启是在西方的东西进来之后。如果以我的那两位同班同学念硕士为某种标志的话,真正的开始是在90年代。
陈东原那个时代的妇女史是什么?他的逻辑是:中国是落后的,在造成中国落后的诸多因素之中,其中有一个就是男女的不平等、女性的被压迫,因此我们解放妇女就等于是救亡图存的一部分。在这个逻辑之上,他写出来的妇女史,能够关照到的东西,你是可以想象的。
我常常喜欢打一个比喻——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如果没有光打上去,过去就不会被你看见,只有当光打上去的时候,过去才会被看见。而被看见、被诉说的那部分过去才是历史。打上去的是什么样的光、从哪个角度打上去,你就会看见什么,过去就会呈现什么。陈东原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史,它的光就是这样——中国女性的被压迫、被剥削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因此解救女性就是我们民族救亡图存的一部分。
但是90年代以后,在西方研究启发之下的妇女史,就完全不是这样子了。如果大家认真去读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它们的前言里边都在强调:我是要打破刻板印象,我是要跟陈东原的叙述划清界限,要发现一个相对而言真实存在的更复杂的女性的状态。
传统社会规范和女性地位
黄茜:《内闱》这本书中有一些让我很惊讶的地方。比如在宋代,丈夫40岁以前不可以再娶,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犯了通奸罪,男女都要判刑。可见宋代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女性的。另外让人吃惊的一点是,宋代嫁女儿的嫁资非常丰厚,在老百姓中有一个流行的风俗,嫁女儿比娶媳妇要花更多的钱。请两位老师谈一谈,这种嫁资的上涨、嫁妆的丰厚是不是代表着宋代女性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地位、性别地位的提升?古代女性和财产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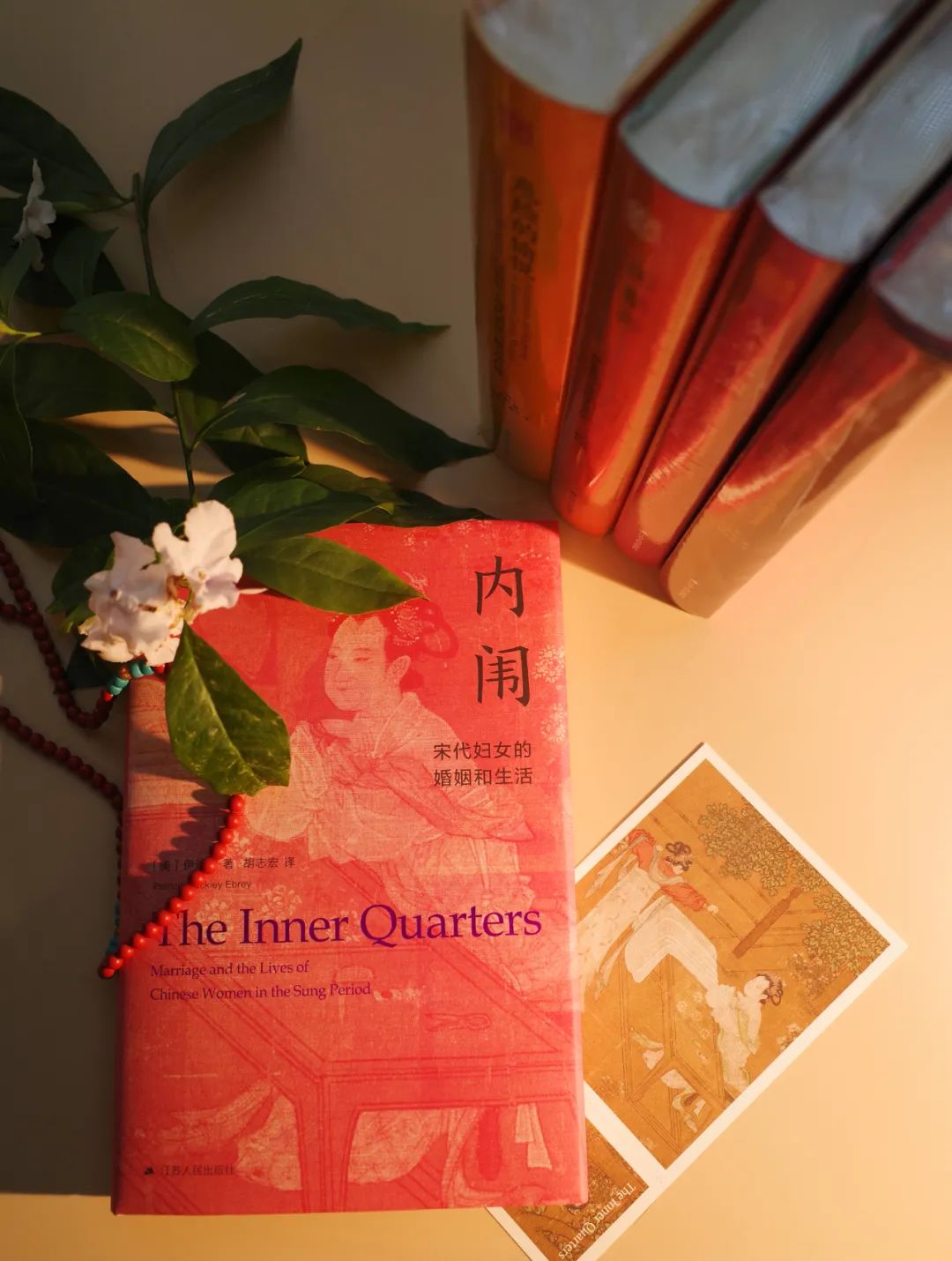
《内闱》,[美]伊沛霞著,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436页,98.00元
赵冬梅:其实女性的财产权问题,是宋史研究、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宋代的女性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拥有了更高的财产权,这个更高的财产权体现在她的嫁妆上。嫁妆是什么?它是父母在女儿出嫁的时候给她的一份财产。北宋最早有资料说,如果哥哥娶媳妇是一百贯,那么妹妹出嫁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一半,起初的嫁妆是彩礼钱的一半,到后来变成了男孩子分得的家产的一半。古代史的研究和史料阅读有一个非常大的魅力,当你深入地读下去,你就会发现细节,会在细节中发现真实。
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是有名的官员写的判词,大部分的判例涉及的是民事,比如家庭的财产。其中有些涉及比如父亲死了怎么分钱的问题。假设这一家父亲死了,要分家,一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都还没出嫁,那么应当怎么分?儿子只得二分之一,两个女儿各得四分之一,女孩子得到的嫁资是男孩应当分得的家产的一半。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被法律承认的惯例。而这一部分财产作为嫁妆跟她进入丈夫的家庭之后,仍然是归她所有、由她支配的。
有一个例子说,老公因为没钱,想要借钱去为家族把坟地保留下来,那是很大的一笔钱。这个时候有钱人家嫁过来的、带着很多嫁妆的女孩子就勇敢地、很有担当地站出来,把自己的嫁妆钱拿出来帮她老公解决了这个问题。墓志铭的书写者会很赞美这个女孩子愿意把钱拿出来,但是另外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个钱是这个女孩子的,她如果高兴分享就可以分享,不高兴分享就可以不分享。
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里还教育男孩子不要藏私,比如你不要借着你老婆的名义置地,如果你把财产置在老婆名下,以老婆的嫁妆钱置产的话,有可能会“肉包子打狗拿不回来”。这关联到当时女性相对的婚姻自由,宋代的女性、男性享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而在这个思想自由之下的女性还享有相当大的财产权利、改嫁自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宋代女性的财产权是处在历史上一个相对而言的高位。

张莉:赵老师提到的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是最早的一部妇女史著作,它反映了五四以来典型的妇女史观。在此之前中国女性是缠足的、不能上学的。所以清末民初中国妇女解放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就是“不缠足”和“兴女学”,也就是要放脚,女孩子要去读书。我们今天每一个女性都是“不缠足”和“新女学”的受益者。为什么提倡妇女不缠足、去学堂?因为这些女性是国民之母。
更彻底的妇女解放是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这个逻辑是:女性和男性是一样的,男女平等。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重新认识女性,即使一个女性她不是妻子,不是母亲,她依然是一个人,她应该和男人是一样的人。
刚才听赵老师讲宋代女性的嫁妆,我很感慨,因为它的细节非常生动鲜活,让我们马上联想到古代女性在当时的处境。我们今天讨论古代女性生活,是要靠想象力的,这个想象力分为两种层面。第一种层面是古代女性的生活地位比男性低,但是这从现代男女平等的角度、从法理上来讲是不应该的。也就是说,不平等是个事实。第二种层面是,历史上就每一个家庭而言,女孩子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在一些家庭,女儿也可能是被疼爱的,被看重的,也有独生女的父母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宋代女性的地位依然是低的,但是这本《内闱》让我们看到女性处境的复杂性和弹性。这两本书切身地站在女性的角度看到压迫,也看到松动,或者是黑暗之中的光亮。但不能说它是完全光明的,只能说是在黑暗之中会看到点点的光。
赵老师刚刚提到“细节”,我很赞同。历史学家如何理解“细节”,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历史想象力”。就是回到那个历史语境,理解那个人的处境,但是你又不会被那个时代完全牵着走,我觉得想象力特别重要,这两本书都特别具有历史的想象力,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得懂,而且会赞同它们的很多看法(不是完全赞同),会有启发性。它们打开了我们对历史上那些女性生活的想象力。

黄茜:《内闱》之所以叫“内闱”,是因为古代女性生活的主要空间是在家庭里。在家庭里她的主要身份是妻子、母亲、祖母。伊沛霞探讨的宋代上层社会理想的妻子,应该嫁妆丰厚,孝顺公婆,能干管家,还需要能写会算,能够启蒙孩子,一些上层社会的妻子,年纪稍长的时候还会皈依佛教。这是宋代社会对于理想的上层阶级的主妇所具有的期待。但是每个女性个体会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追求,在社会期待和个人追求之间,总会有冲突和矛盾。古代的女性中有没有在这两者之间做到平衡,既活出自我,又不去过于冒犯社会规范,维持和谐家庭的案例?
赵冬梅:这个问题特别像所有成功的女性企业家、演员等都会被问到的:你是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呢?
刚才张莉老师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历史最大的分歧是什么?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歧。传统和现代最大的分野在哪里?在于社会存在的基础性的伦理不同。在现代社会的理想状态下,我们每一个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的,我们有理由追求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并且把它最大化,这样才会被视为是一个有价值的、积极的生命。观念是传统和现代之间最大的鸿沟,也是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异,很难跨越。传统社会的伦理是什么?人都是在家中的,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忠臣出于孝子之家,推孝为忠。传统逻辑当中的女性,首先是属于家的,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进而她可能还是祖母,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今天想考研的人、考博的人都会努力去联系导师,然后如果哪个导师说我要你,你就会很开心。但是在北宋,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在诗词方面格外有天赋,她的天赋被看见了。当时最厉害的女导师李清照说:“你跟我吧,我教你。”但是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拒绝了李清照。因为她觉得读书识字,是为了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而诗词是外向的、社会性的、相对娱乐性的东西,她觉得这个不是她的本业。就像《甄嬛传》里的沈眉庄,她明明是饱读诗书的,但是当皇帝跟太后问她“读了什么书没有啊?”,她垂着眼睛说:“没读什么书。”她一定要装成那个样子。
实际上在传统社会的大的规范中,女性首先是女儿、妻子、母亲。当然她可以是屏风之后的一个高参,她会跟老公说“你今儿来的那仨人有一个特别不地道,然后谁谁谁是可以交的朋友”,她会把钗环当了,就为了招待儿子靠谱的学友,她还可能主导儿子仕途上很多重大的决定,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男性的。包括我们读到的《闺塾师》里明末清初这些以作家身份示人的女性,尽管我们今天看她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但是她们的写作其实还是没有出圈,仍然是“丸在盘中”。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比喻——“这个弹丸它在动,但是它没有出这个盘子”。我们现在谈到的《内闱》是写宋代的女性,《闺塾师》是写明末清初的女性,你会发现明末清初的女性跟宋代女性相比,生活的状态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所有不同都是“丸在盘中”的不同,是有非常复杂的变化的。陈东原的时代是不在乎这个还在盘中的变化,他关心的是把“盘”打破,我们今天是“盘”已经打破了,但是我们去看古代的时候要了解到“丸”还在盘中,它有复杂丰富的多层次的玩法,你要承认它的复杂性,去追寻那个细节,那是历史学者该做的,这两本书都很具有典范性。
张莉:所谓的理想女性生活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因为当时的女性生活完全是在家内的。今天在我们看来很有意思的女性,在当时是不能被纳入那个价值体系里的。一些有才华的女性,写了一些文字留下来,但按当时对女性的价值判断,才华算不上她的优点。比如在宋代,你会理解那个不愿意跟李清照学词的女性。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女性,而且她很有可能在古代找不到和她的智商相匹配的男性,她是没有恋爱自由的。
文学与古代女性的生活
黄茜:我们对古代女性的具体生活了解甚少,主要因为她们在历史文献里面往往是缺席的。这两本书有所突破,是因为它们用了一些文学作品作为材料,比如《内闱》这本书里面就用了宋代的志怪小说《夷坚志》《睽车志》《清尊录》《旸古漫录》等等。正好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历史学者,一位是文学学者。我想请教,在历史学术著述里使用文学性的、虚构性的文献材料,这种做法是恰当、合理的吗?文学和历史之间是否真的能够形成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

赵冬梅:肯定是合理的,原因是什么?故事是编的,但编故事的人是真的,而且每个人所能想象出来的世界是基于他所生活的真实世界的。他不可能超出他生活的真实世界,但是他可以想象,可以夸张,而夸张变形之后,我们还能找到原来的样子。比如《夷坚志》,被研究历史的人频繁使用,伊沛霞在这本书里大量使用了《夷坚志》这种叙述性的材料。
比如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一个男的他老婆生了女儿,没有生儿子,然后他就在外头找了年轻的女人,不怎么搭理家里的妻子。妻子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于是开始偷偷变卖家财。最后两个人离婚了,县官还支持了这个女性的抚养权,因为这个男的在外头跟娼妓混在一起,不可能给女儿良好的教育。离婚之后,妻子就拿着她倒腾出来的钱继续做生意,前老公还过来指点,他说你这个不赚钱,妻子说你管我呢都离婚了,于是这个老公就再也不来过问了。妻子就用这个做本,把家资增值了,并且把钱全给了独生女。丈夫反而跟娼妓很潦倒,没有过到头。最后夫妻两个人都死了,他们的女儿出于孝道,想把两人合葬。把尸骨挖出来,骨头连好了盖上衣服准备要埋的时候,一不留神发现那个已经变成骨头的女的把脸背过去——她不要看着他。但是这个女儿出于对父母双全的渴望,还有要行使孝道,所以她最终还是坚持把这一对已经离了婚的怨偶合埋在一块了。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是从中我们能看到真实。一是离婚的自由,二是作为下层商人的女性拥有财产,并且能处置财产。女性对财产的处置权,在整个传统时期时不时是有的,尽管它越来越收紧。汉代有一个材料,一个女的临死的时候对如何处置财产立了一个遗嘱,分财产的这些子女还不是她跟同一个老公生的,你能想象吗?
《夷坚志》是一个志怪故事集,它有虚构的一面:两副尸骨,怎么可能背过脸去。但是它真实的一面就是这个处在下层的商人之妻,她主导了自己的婚姻,增值家庭的财富,让女儿能嫁得好,在宋代是可以做到的。文学作品、虚构作品里的材料,属于普遍性真实,是完全可以使用的,因为它鲜活,所以非常了不起,当然这个史料是要和真实材料去对照的。

张莉:首先我认为用小说做材料是可以的。比如《史记》,它是历史学者们要看的,也是我们学古代文学要学的,那它到底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是历史还是文学,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
我们现在看一些历史研究,研究者引用当时的小说,引用哪一段、哪一个事件,怎么去引用,我觉得都是有讲究的。这依赖于研究者对历史的想象和认知,要判断哪些细节是基于真实、哪些细节是基于小说家的想象,这需要历史学家的判断。有历史想象力的学者,他肯定要从小说或者志怪传奇中拿很多东西,而他也深知有些东西是溢出真实范围的。比如《梁祝》,在这个故事里边,主人公先女扮男装去上学,然后两个人谈恋爱,父母不同意。这是基于现实之上的想象。你会发现这是当时人们对现实不满的想象,你不会完全把这个故事当做真实,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是真实之上的传说。而这里的真实是什么?是人们渴望有一天男女可以自由地一起坐在学堂里。
小说可以当作历史解读吗?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的。但是哪些拿过来、怎么拿,需要方法。好的历史学者可以使小说变成自己著作中非常好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那么好的历史学者,可能就会因为引用了一个不靠谱的材料去充实他的观点,而被认为他的著作也不靠谱。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想象历史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可以使用的渠道很少,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
赵冬梅:我想起来一件特别好玩的事,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人看过徐克导演的《梁祝》?里边有一个情节,令我拍案叫绝。祝英台出嫁的时候,她不愿意出嫁,哭到流出血泪,那个妆就上不上,还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祝英台的爸爸气急败坏地说:“用我的粉!”这个情节,充分说明徐克那一版《梁祝》的编剧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原因是那个年代中国男子比女人还讲究相貌,化妆敷粉。祝英台爸爸的粉肯定比祝英台妈妈的粉要高级,而且平常舍不得给她们使。
黄茜: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经济非常发达,出版业兴起,很多市井的读物、戏剧小说出现,同时也培育了一大批女性读者。江南地区女性读物里面最流行的是汤显祖的戏曲《牡丹亭》,几乎所有闺秀都对之痴迷,很多人把杜丽娘作为她们的偶像。在两位老师看来,为什么《牡丹亭》能够对当时的女性产生那么大的冲击力?
张莉:《闺塾师》讲的是闺阁女性的生活,尤其是她们的文学生活。当时女孩子们在家里读《牡丹亭》,它最重要的主题是爱情。杜丽娘如何死掉,又为爱复生,还有柳梦梅和她之间生死相随的爱情,非常吸引当时的读者。这个剧出来以后,很多的闺阁女子喜欢阅读,在当时出现了非常著名的女性读者。《闺塾师》里面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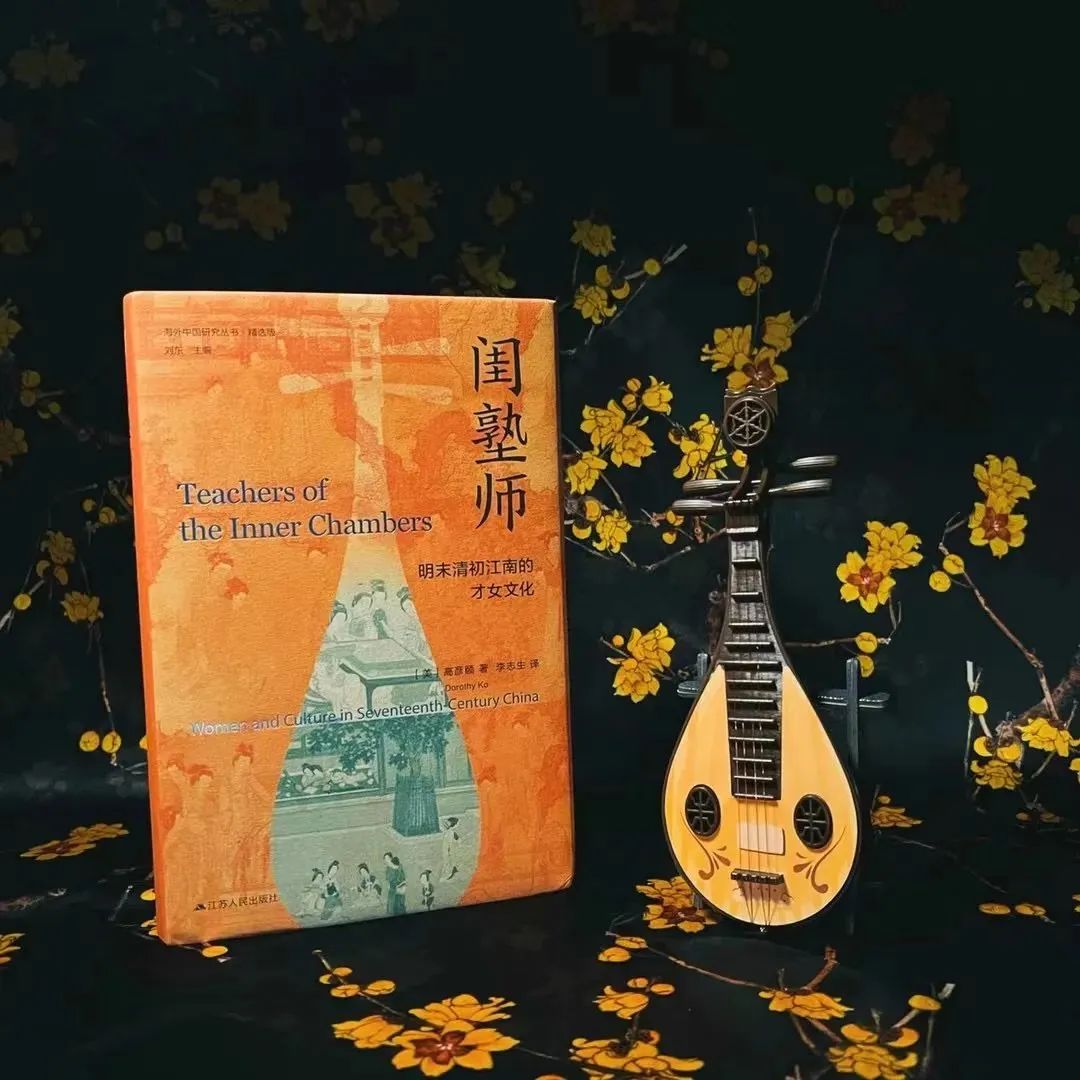
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先后娶了三位妻子,她们都喜欢看《牡丹亭》,丈夫就把他三任妻子对《牡丹亭》的批注出版了,这本书出来就叫《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闺塾师》这本书里边解读了这三个妻子,三位非常杰出、非常有文学敏感力的女性,是如何理解《牡丹亭》的。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这几位女性读《牡丹亭》,痴迷到认为杜丽娘是真实存在的。她们会在家里供起她的画像来,给她放一株梅花。也会代入自己是杜丽娘,正如今天我们观剧时会代入自己是女主。她们对柳梦梅是赞扬的,觉得柳梦梅这个人是值得托付终身的。还比如杜丽娘和柳梦梅之间的婚前性行为,这三位女性读者,她们在批注中就认为正因为杜丽娘和柳梦梅之前有过肌肤相亲,所以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才会美满和幸福。
这些女性在不屈不挠地书写,她们把自己的才华展现了出来,并且以这种方式创造了一种主体性,我觉得这个是要注意到的。我们现在都会追剧,其实我认为那些女性在看《牡丹亭》的时候,就是在追她们那个时候的剧,她们会互相给杜丽娘设计人生,会讨论她们的结局,这样去看的时候,你会把我们和当时的那些女性的处境联系在一起。古代女性虽然有很多规矩,但是她们也有聪明、才智,甚至狡猾和调皮,还挺可爱的。
赵冬梅:我补充一点,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妒忌往往就发生在妾进门之后,女性的妒忌本身就是男权控制的产物,是男性在操纵女性。吴吴山的三个老婆接力评《牡丹亭》,最后第三个老婆甚至愿意拿出嫁资来完成出版,这反映了女性的友谊。这三个女性其实并没有在同一时空生活,她们跨越时空传递了情感。
《闺塾师》里还提到了“蕉园七子”。江南某一大户人家不同辈分的女性,在一个爱好文学的长辈(这是已经成为了寡母或者寡祖母的女性,她是有权势的,她在整个结构当中其实是一个家长)的主持之下,结成了一个文学社团,举行文学活动。在“蕉园七子”的例子中,有一个共识:女性之间的友谊,丝毫不逊色于男性之间的友谊,她的支持力度可以是更大的。
女性传统上是属阴的,是柔顺的,在这种柔顺的教育之下,女性会更加容易适应社会的变化,会更倾向于不断地通过学习调整自己的姿态,让自己变得更美好。
才女文化的价值和成就
黄茜: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们不仅会读,她们还能诗善赋,所以才有了我们说的“才女文化”。《闺塾师》里列举了几个数据,比如说16—18世纪出版的女性作品选集有12种,其中1667年由王端淑编辑的《名媛诗纬》收录了大概1000名明末清初女作家的作品,1773年汪启淑编辑的《撷芳集》涉及了大概2000多位清代女性作者,可见这个时代女性写作群体是十分可观的。这种女性写作的繁荣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该怎么评价这个时代的女性写作,以及她们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赵冬梅:我们自古就有才女,比如蔡文姬、班昭、李清照、薛涛。但到了明末清初,一是才女成片、成群地出现,二是才女写的东西被及时出版,已经进入了出版市场。《闺塾师》这本书里有很多东西会颠覆你对古代的认知。比如出版商会表明身份,让才女们给他投稿。当然他没用“投稿”这个词,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家里头有人写作,你可以把这个寄给谁、寄到什么地方。
在《闺塾师》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时间性和区域性。时间是历史学要把握的最核心的东西,历史学追寻任何事情都会根据时间线的变化,《闺塾师》的时间是在明末清初。《闺塾师》并不是对全国女性写作的研究,它研究的仅是江南地区。江南地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比如苏州、扬州、杭州。明末清初的江南出现了像草原上的蘑菇圈一样的、一圈一圈的才女,她们成片地出现。而且她们大部分是通过婚姻、血缘相关联的,是有亲戚关系的。
从蔡文姬的年代到现在,背后隐藏的是经济的发展、物质条件的进步。在蔡文姬和班昭的时代,写作都是写在竹简上。从4世纪开始,中国人才大规模地用纸来取代之前的竹木简。到10世纪开始了雕版印刷的时代。到了明末清初,印刷技术取得进步,就像这个书里边提到的,印刷效率大大地提高了。效率提高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字体,统一的字体,可操作性更强,印刷效率更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宋代以来识字的人群不断增加。北宋,科举制度和雕版印刷使得知识传播变得更快更广。到了南宋,越来越多的人考不上科举,在政治上没什么上升空间,就跑去教育大众了,又继续往前发展。元代我们看见什么?文学史上讲元曲的繁荣,常常会提到儒生上进的路是时断时续的。元代的科举跟之前不太一样,大部分科举无望的读书人就去写剧本了,把剧本继续发展下去。到明代,读书人识字率不断地提高,再加上江南这个地方的特殊性(江南的开发虽然晚,但是江南遭受战乱骚扰极少,大概最近的一次就是太平天国),总体上江南处在一个持续的发展中,因此到了明清,江南非常富有,印刷业发达,阅读的面在扩大。还有江南又富裕又发达,它有发达的雕版印刷行业,所以才会出现女性的书籍,大家注意到女性写的是不一样的,它有噱头。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些女性是有才华的,有真知灼见的,因为她不在贾宝玉说的那个“臭男人”的规范之中,所以更有活力和创造性,这就造成了我们在《闺塾师》里能够看到的一群人。
张莉:其实从整个世界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女性作品的出现,都是跟经济有关系的。首先女性出版人很重要,比如英国有钱的寡妇会资助女作家的出版。另外刚才我们说的江南地区,在当时,经济发达,消费观念也超前。我认为,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包括女性写作,其实都跟传媒方式的变革有关系。女性写作的发展总是会跟新媒体有关系,比如五四时期报纸副刊的涌现,对整个女性写作的推动非常大,因为它有大量的女性读者。为什么说晚报很重要?它是今天印了,明天就可以到千家万户手里,所以一是需要大量的稿子,二是需要满足它的读者,中国第一个家喻户晓的女作家冰心就是这样出现的,第一天报纸上刊登了冰心的作品,第二天读者就写信说写得好,随后编辑马上把读者来信登出来。19岁的冰心一年之内在《北京晨报》发表了十来篇小说,一下子就成名了。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媒体革命的时代,网络的出现打破了发表制度,于是更多的女性写作者出现了。之前,发表是一种权力,编辑的权力很大。2000年开始,网络越来越发达,网络女作家,女性文学写作者非常迅猛地发展,到现在,微信公众号、微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注册,催生了大量的女性写作、女性文学的繁荣。说到16—18世纪,所谓的空前繁荣是相对于之前的,也是跟它的经济和印刷方式有关系,可在今天我们看来那根本就不叫繁荣。
黄茜:我感到很困惑的一点就是,既然这个时期女性出版这么繁荣,为什么却没有一个才媛能够进入文学史。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竟然没有再出现一个曹大家或李清照,是有什么客观原因吗?
张莉:一个时代要出现优秀女作家,其实从理论上来讲,只有基数到了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一个真正优秀的作者,跟社会进步有很大关系。

比如说莎士比亚的时代只能出现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妹妹是不会出现的。因为莎士比亚他享有发表权、受教育权。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些女性也可能识字,也可能书写,但是人数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个女性写作者就很少,很少的写作者里面出现一个杰出写作者就更少了。李清照是文学史和女性写作史的骄傲,但是要成为李清照何其难:找一个合适的丈夫,丈夫不仅爱你,更爱你的诗才,还要有一个家庭,父亲很欣赏,早早阅读了大量的作品。并且,这个女性还有彪悍的性格和完全的无拘无束的个性。这些条件凑起来,都是偶然中的偶然,所以在大的历史环境中,对女性价值的判断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就不可能出现一个优秀的女性写作者。
赵冬梅:张老师是从偶然性来谈李清照,比如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老公。但是李清照的才华毫无疑问是碾压赵明诚的,她的才华就算放在男性写作当中,仍然是出类拔萃的。
我们从性别的角度来观察、回看李清照。李清照成长的环境固然是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环境,可是就她的个体而言,她受到的教育的良好程度、她家庭的背景、成长中的支持,包括旅行见世面,是不输男性的。女性在跟随父亲、丈夫、儿子宦游的过程中,见的世面是很大的。李清照的丈夫在经历宦海浮沉中,她是伴随左右。另外还有写作者的培养,我觉得写作者的培养除了生活给你的以外,还包括你个人的悟性去面对之前的文本。对于李清照而言,之前的所有对男性开放的文本对她也都是开放的,以她的条件是可以接纳到的。
我们判断事情会谈平均数,会从概率出发,可是真正的不世出的天才其实不在你的概率之中。你有这样一个环境有可能会产生,或者说你觉得它理应产生,但是它不一定能产生。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宋代基数小,但是有李清照。
关于李清照的出现,我还想补充一点。陈寅恪先生在谈到韵文写作的时候,特别是谈到“赋”这种文体写作的时候,曾经作了一个非常敏锐的判断。他说:“赋”这种文体是非常难写的,它既要完美地达意,也要有外在的表达——“骈四俪六”,在文辞上要求朗朗上口。“赋”难写在于它外在的形式美和内在内容表达想要达成一致非常之难,因此一个能把“赋”写好的时代,一定是思想自由的时代。他总结中国历史上“赋”写得好的两个时代,一个是六朝,一个是天水一朝——宋朝,这两个朝代的思想最为自由。
我们可以把这个解释移用到李清照的出现。今天坊间一个最大的笑话和躲懒,就是把宋明理学看成铁板一块,把宋和明看作是完全同质。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同质的古代,甚至在一个朝代内部,它的发展也不是同质的,质地始终是有变化的,尽管传统和现代的区别是最大的,但是在传统内部,“丸在盘中”的变化是持续发生的。
如果我们抛开宋明理学禁锢人们头脑的刻板印象的话,会看到宋朝,特别是北宋,是一个思想非常自由的时代。在这个自由的时代才孕育了那么多伟大的男性,这就是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背诵天团”。在那样一个思想相对自由的时代的尾巴上,李清照被孕育成长,她得到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滋养。当整个世界都是自由的时候,女性也是自由的,所以她才爱喝酒,她脾气很硬,她还嫁过一个不靠谱的老公,最后也成功地靠关系、讲道理和这个老公离婚。这样鲜活的生命只有在宋朝,而且是北宋才孕育得出来。

张莉:要把李清照当成女作家看。我说她是偶然,意思是在古代文学史上只此一位。关于性别与文学成就,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把她的性别身份去掉,她依然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她不依赖性别。当我们讨论文学或者作家的时候,我们强调“女性文学”,是因为女性文学在历史上极少,但是当我们判断一个真正好的女作家时,也不能完全依赖性别这个维度的,也就是并不因为她是女性写的就天然伟大,这个逻辑并不成立。李清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她的作品,比如“绿肥红瘦”,在整个文学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比喻,它既有女性的感觉,同时放在整个文学史上都是非常敏锐的,这是天赋。所以,我的意思是,判断一个人的文学成就不能强调性别,如果去掉女性的性别身份,李清照依然能够成为文学史上的很好的作家。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