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澎湃思想周报︱博索纳罗还是卢拉;绿色农业能养活世界吗
卢拉会再次获得改变巴西的机会吗?
巴西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事关重大:是让博索纳罗的反动、腐败、右翼统治再持续四年,还是让巴西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总统卢拉回归。
巴西选民在10月2日面临的选择再明显不过了:要么博索纳罗再干四年,这位热爱枪支、敬畏上帝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在任期间发生了数十万起疫情死亡事件,亚马孙雨林遭到创纪录的破坏;要么让2003年至2010年统治巴西的工人党代表卢拉回归。

当地时间2022年8月28日,巴西圣保罗,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在首次电视总统辩论中出现在屏幕上。
虽然卢拉的两届任期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进行了一些渐进式改革,但对腐败的指控(大多是毫无根据的,被右翼恶意利用)和针对其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的司法政变助长了反对势头,最终使博索纳罗于2018年上台。自担任总统以来,博索纳罗尽可能多地实现私有化,缩减社会福利计划,并培养了一种有毒的沙文主义和怨恨气氛。
卢拉在四年前因虚假的腐败指控入狱后,正在进行政治上的复出,他现正宣称将“击败极权主义威胁”和“重建和改造巴西”,但风险很大。
距离选民投票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巴西生态社会主义者Sabrina Fernandes向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Loren Balhorn介绍了博索纳罗的糟糕记录、反对现任总统的状况,以及左翼可以从运动经验中学到什么。访谈发表于《雅各宾》杂志,节译如下。
博索纳罗的四年统治下,巴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前临时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已经开始实施紧缩议程,并对工人权利和养老金进行倒退的改革。博索纳罗上台后制定了一项计划,要拆除更多的东西,比如将公共公司私有化。他的经济部长保罗·格德斯被博索纳罗的支持者认为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他们实际上想要私有化更多的公司,比如巴西的邮局Correios,或者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
新冠疫情本应是展示公共医疗保健力量的时刻。 但由于特梅尔时期实施的紧缩计划,以及博索纳罗的进一步推动,政府声称没有钱。
你认为博索纳罗有一个连贯的意识形态议程,还是说他更像是一个为巴西资本服务的右翼机会主义者?
我认为描述博索纳罗的最简单方式是自由主义的保守派。
他也不是一个大的保护主义者。他的经济议程实际上是在和帝国主义权力玩。他与唐纳德·特朗普的联系在这里很重要。当特朗普是美国总统时,博索纳罗觉得自己与美国真的有联系,因为巴西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我们正从“粉红潮”中走出来。很多右翼政府在整个拉丁美洲上台,如阿根廷和智利,然后是玻利维亚的政变,博索纳罗认为自己是这个趋势的一部分。
就国际资本主义阶级而言,博索纳罗确保了巴西公司的外国股东受益,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巴西的土地。但传统的巴西精英阶层可能是最高兴的,尤其是农业综合企业。即使博索纳罗不是一个传统的保护主义者,他也一直在为民族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劳动人民的情况如何?卢拉政府的社会成就是否被逆转了?
卢拉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大胜利之一是他的反饥饿计划。巴西在历史上有一个巨大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卢拉将消除这一问题作为优先事项。他启动了一项名为Fome Zero(或“零饥饿”)的计划,将学校的食品计划、扩大国家储备以帮助调节食品价格、信贷和现金转移相结合。卢拉对这些举措非常自豪,家庭补助金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以至于世界银行将其作为一个模型。它可能不是很激进,但它非常重要。
现在在博索纳罗的领导下,巴西又回到了粮食不安全的深度状态。这反映在数据上,但你也可以随便看看,我们有更多的人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在肉店后面捡骨头,因为他们买不起肉,等等。
对于环保主义者和原住民活动家来说,巴西一直是相当危险的,但在博索纳罗的领导下,情况变得更糟。这与对自然的整体破坏结合在一起。博索纳罗对此负有很大责任。现在女性自杀率和性别暴力率也高得惊人。
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生活能力的恶化。这不仅仅是在大流行期间有60多万人死亡,也不仅仅是博索纳罗在获得疫苗方面的拖延,或者他拒绝采取适当的行动来阻止病毒的传播。
如果博索纳罗是这样一个灾难,我们如何理解他当初的崛起?他是如何能够击败曾经非常受欢迎和成功的联盟的?毕竟,他的背后甚至没有一个政治机器。
有一个共同的解释,它与围绕粉红潮和当时的商品繁荣的很多分析相联系。这些政府非常重视再分配,但由于经济蛋糕在增长,创纪录的高利润可以与再分配并存。这意味着部分精英阶层对社会项目相当满意,因为他们也在赢。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些资本家试图改变游戏规则以保留他们的利润。
这当然是故事的一部分,但我认为事情不止于此。为了理解博索纳罗,我们需要谈论保守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领导人的作用,他们对劳工党政府的进步政策感到不满。例如,非洲裔巴西人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平权政策奔走呼号,其中一些政策是在巴西劳工党领导下实施的。这足以改变部分中产阶级的看法。
工人党是一个民主化的项目,但它也是一个提高工人阶级意识的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中产阶级开始认为自己与工人阶级是分开的。
保守主义和巴西社会某些部分享有的历史特权也发挥了作用。一些人看到他们的家庭清洁工现在有了更多的权利,可以和他们一起旅行或在同一个商场里闲逛,感到很不高兴。这在部分中产阶级甚至部分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不满,然后这种不满又被政府腐败的指控所放大。
卢拉在目前的竞选中表现如何?
很明显,卢拉不可能以“纯”左翼的选票获胜,他们不得不从中右翼选人。
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他们从中右翼选人——这是我所预料的——而是他们选择的特定人选Geraldo Alckmin。后者曾担任过四届圣保罗州州长,并与许多腐败行为有关联。他还来自一个政党,帮助发起了针对左翼的抹黑运动,并在假新闻出现之前推广假新闻。
巴西左翼的很多人认为,Alckmin是获胜的关键。这不仅仅是来自卢拉或劳工党内的一小部分人。卢拉的部分社会运动基础对Alckmin的存在感到很满意。
我们得看看结果如何,但我认为这对他有伤害,特别是在圣保罗州,贫困社区在他的统治下真的很痛苦。当教师工会进行罢工时,他们会被警察殴打。当你说:“听着,我知道这个人对你不好,但你必须和他打交道,因为这是我们需要赢得的人。”这就有一个信用问题了。
卢拉背后的联盟非常重视与博索纳罗的斗争。如果卢拉的主要对手不是博索纳罗,而是其他温和的中右翼人士,他可能不会采取同样的策略。但现在是为了清除博索纳罗,人们有一种倾向,即接受竞选中的某些事情,只是为了确保博索纳罗被踢出去。
你说,尽管有所有的批评和限制,卢拉仍然是巴西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统。同时,他的极左批评者都没有在推进更激进的议程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你认为在建立左翼多数派方面,是否可以从巴西劳工党的历史记录中得出任何一般性的教训?
我们在巴西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的政治非常集中于我们建立的机构——工会、政党和社会运动——而不是如何使这些项目与社会其他部分产生共鸣。其中一个挑战是,我们的左翼常常是蚕食自己。我们在争夺同一个基础,却不太关心如何扩大这个基础。
我不确定左翼是否已经吸取了这个教训,特别是如果卢拉回来,人们又习惯于认为有选举基础就足够了。但是,至少劳工党领导层中的一些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想实施卢拉的一些更大胆的建议,他们将不得不让人们重新走上街头。他们将不得不动员起来。
您提到了“粉色浪潮”,即卢拉的胜利是拉丁美洲左翼政府浪潮的一部分,以及它在过去十年中面临的挫折。在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其他地方取得一连串的选举胜利之后,你认为卢拉的胜利会对拉丁美洲产生什么影响?
卢拉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政治家,这一事实在拉丁美洲一体化方面也有很大帮助。如果他真的赢了,假设没有发生政变,他对于加强这些新的进步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调和一些紧张关系将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智利的博里奇政府和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之间肯定存在紧张关系,我认为卢拉可以对此有所帮助。
卢拉也是围绕该地区替代性治理机构(如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及反对美国在该大陆的霸权主义进行对话的关键。但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拉丁美洲。卢拉对涉及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和其他伙伴关系的南南合作非常重视。同时,他在欧洲和美国也很受重视,特别是因为博索纳罗的表现很糟糕。
绿色农业能养活世界吗
在气候危机的影响下,人类的食物体系将会发生改变。《纽约书评》近日刊登了澳大利亚哺乳动物学家、环境保护专家提姆·弗兰纳里(Tim Flannery)对新书Regenesis: Feeding the World without Devouring the Planet(暂译《再生:喂养世界而不吞噬地球》)的评论,对农业和食物的未来展开了探讨。
《再生》一书的作者乔治·莫比奥(George Monbiot)是一名英国环境作家和环保倡导者。即使气候的影响不像一些人预测的那么严重,工业化农业及其创造的所谓全球标准饮食对于环境而言都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正在快速破坏地球土壤,我们已经站在了世界性灾难的边缘。我们能够用来重塑食物系统的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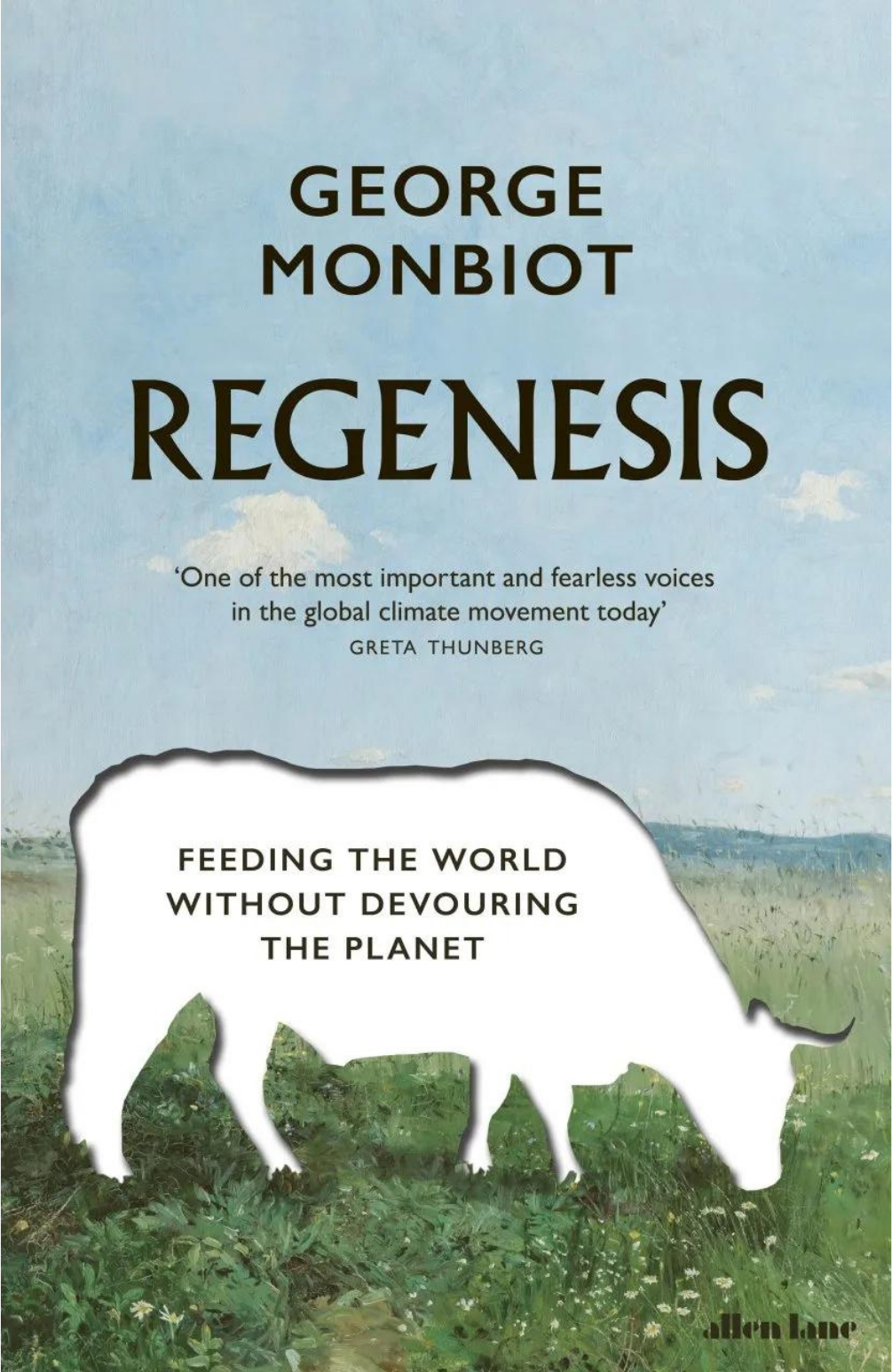
在书的开头,莫比奥探讨了一个诱人的想法,我们至少可以在自家后院或是院子附近种一些食物。任何吃过自家院子里的果蔬的人都知道,自家种植的有机食物不仅是营养的来源,还带来骄傲和满足感。然而即便只是种一棵生菜也困难重重。如果不用杀虫剂,那么晚上要捕捉蛞蝓和蜗牛,白天要捉毛毛虫。为了防止更大的害虫或动物的破坏,植物周围要围上栅栏,想要作物茁壮还必须浇水和施肥。天气之神的眷顾也必不可少。作为专业人士,莫比奥深知这些困难使得哪怕种植一小部分食物作为补充也是一项耗时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他在牛津租了一块土地用于种植苹果树,他的果园已经在经历气候变化的影响。一年春天,白昼宜人,夜晚温暖,果园里结出的果实前所未有的多,然而到了五月中旬,一场严重的霜冻杀死了每一棵树上的每一颗果实。
莫比奥还在书中介绍,果园的每平方英尺土地里都居住着数千个物种,从蜈蚣到跳虫,每一个微小的有机体都在维系这块地方的生态健康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相比之下,大多数田地则是生物沙漠,因为现代农业实践越来越多地采用水培模式,只需要在一种无菌生长介质中添加养料和水。商业农地因此无法保持其肥力和生态平衡。相反,每年必须使用大量的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这些物质会流入相邻的土地和水道,毒害整个生态系统。对于垄断食物供应的少数大企业而言,这个系统有利可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们拥有垄断市场,农民不得不购买作物所需的养料和添加剂。同时全世界的农民都必须为用水付钱。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成为了一种劳役,导致债务和绝望的不断增加。他们被迫在遭到破坏而失去了自然之美的环境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眼看着抵押贷款比农作物更稳定地增长,一些人甚至开始怀疑继续活下去是否值得。在一些地区,农民的自杀率高得吓人,印度尤甚。即使是在法国、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富裕国家,农民的自杀率也几乎是整个人口自杀率的两倍。
一方面,食物的售价过低,对很多农民而言无法维持生计,但对很多消费者甚至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而言,食物还是过于昂贵,很多人都在经历饥饿和营养不良。莫比奥在当地的食物银行发现,最新鲜和健康的食物都供不应求。新鲜产品的保质期短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食品供应系统本身的问题。他写道,超市的商品如果没有卖出去就不需要向供应商付款,超市因此倾向于过度订购,然后慷他人之慨地把多余的商品捐给慈善机构。而位于食品链更上游的加工商和包装厂和购物者没有直接关系,即使扔掉经手的大部分食物,在企业声誉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食物银行里往往塞满了含有大量脂肪和糖的高度加工食品,依赖这些食品的人容易在肥胖的同时营养不良。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数据,好的饮食要比仅仅提供足够热量的饮食贵五倍,饮食不全面引发的高比例的糖尿病、心脏和血液循环问题会导致早逝。很多专家声称肥胖者的问题是缺乏“意志力”,对自己的饮食“不负责任”,这种说法忽视了贫穷和不平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莫比奥认为,“肥胖是一种传染病,它的传染媒介是企业”。
我们的食物生产体系也不安全。全球标准饮食中主粮的产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然后被分发到全球各地。考虑到气候的影响,这似乎很不理性,而俄乌冲突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做法的愚蠢程度。乌克兰和俄罗斯几乎占全球小麦和大麦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冲突扰乱了这些主粮的生产和贸易,从而对非洲、中东和南亚的进口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过度使用化肥、草甘膦(广泛使用的除草剂的主要成分,也被怀疑是致癌物),加上破坏土壤的耕作方式,已经破坏了地球上最具生命力的土壤,也破坏了更广泛的环境。造成环境破坏的不只是化学制品。由于立法不健全和环境保护不足,工厂化养殖的勃兴正在破坏英格兰的河流。莫比奥追踪了怀依河上游的污染情况,发现污染源经常是一个容纳4万只鸡的巨型钢制谷仓。据估计,怀依河流域现有2000万只鸡,雨水将它们的粪便冲进河流,杀死鱼和其他水生生物。在珍视其“清洁、绿色”形象的新西兰,乳品业的废物正在将曾经纯净的河流变成臭水沟。
莫比奥呼吁结束这种破坏的循环,但他检视了一系列潜在的解决方案,发现都不尽如人意。例如,在城市中种植食物的想法被否决是因为他认为城市中没有足够的土地,垂直种植的问题在于能源和其他成本,但他还是认可在当地种植食物可能“对心理健康大有好处”。他还认为,快速传播的替代耕种方式都无济于事。他认为使用生物炭或焚烧有机物可以提高土壤的生产力,但过于昂贵;越来越流行的牲畜管理方法,例如轮流放牧,在他看来也没什么用。但在弗兰纳里看来,莫比奥在否定这些举措时过于草率和笼统了。生物炭的成本可能会随着生产方法的改进有所下降,一些情况下轮流放牧对环境大有好处。在澳大利亚,90%的土地无法适应农业生产,轮流放牧等方法已经带来了显著的土壤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弗兰纳里认为,莫比奥的书聚焦于英国,在描述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的细节时很有力量,但这种地方性观点在这里是一种阻碍。
莫比奥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广泛采用不包括动物产品的饮食,但他也欣然承认,即使采用普遍素食仍然是不够的,因为种植农作物本身就极具破坏性。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莫比奥遇到了一些进行不同尝试的英国农民。人称托利的农民Iain Tolhurst在俯瞰泰晤士河的峭壁上租了7公顷燧石覆盖的土地,经过多年的试错,发展出了许多适用于石质田的独特种植方法。在接受莫比奥采访的前一年,托利收获了120吨蔬菜和水果,没有使用任何杀虫剂、除草剂、矿物质、动物粪便或任何其他化肥。同时土壤肥力增加,这片农场成为了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的天堂。然而背后的代价是大量的人力投入,托利自己整日工作,旺季时雇用了12名工人,然而利润却很微薄,必须要靠他的半份退休金、咨询费用和对地租的价格控制才能生存下去。什罗浦郡的农民Tim Ashton在500英亩种植谷物的土地上进行“免耕”耕作。他用除草剂消灭杂草,然后将种子钻入土壤。这个系统在气候变化面前显示了韧性,四年后作物产量恢复到了耕作时的水平,化肥使用量减少了85%,化石燃料消耗也大大降低了,最大的问题在于草甘膦的使用。与托利的农场一样,他的农场也收入微薄,必须依靠其他收入维持。弗兰纳里由此感到整个农业系统是如此破碎,以至于无法进行改革。
莫比奥在芬兰见到了“太阳能食品(Solar Foods)”的创始人Pasi Vainikka。这家创业公司探索了一种解决粮食危机的潜在方案,莫比奥称之为“大多数农业终结的开始”。这一突破包括在发酵桶中种植一种名为Knallgas的奇怪细菌,这些微生物在1989年首次被分离出来,其特别之处在于能够将氢气作为食物来源。Vainikka想到给这些细菌投喂来自太阳能的氢气,收获一种他称为Solein的产品。细菌的数量每三小时翻一倍,一天可以收获8次。Solein是一种淡黄色粉末,蛋白质含量为60%,可以被添加到许多食物中而不改变原来的味道,具有成为一种主食的潜力。莫比奥尝到了用Solein做的煎饼,觉得“味道丰富、醇美、饱满”,就像他成为素食主义者之前吃过的煎饼一样。
这种技术解放的土地数量将是真正的变革,但虽然Solein可能减少食品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但它不一定能增加粮食安全,因为它会使我们严重依赖单一的蛋白质来源。微生物的培养会受到污染问题的困扰,一旦一种有毒的细菌能够入侵并在Solein种植桶中生长,后果将不堪设想。并且,充满细菌的大铁桶缺乏传统苹果园甚至是托利的混合农业方法的浪漫引力。它听起来是未来主义的,冷酷的,甚至可能是怀有敌意的。然而如果太阳能食品成功实现商业开放,Solein似乎很可能被悄然地加入我们的食品当中。
弗兰纳里最后指出,人类成为农民只有大约一万年时间,在这之前,我们是狩猎采集者,地球只能养活几百万人。农业让我们向食物链下游移动,更多人得到了喂养。但生产谷物的农业系统对环境造成了破坏,我们现在面临着再次跃向食物链下游的细菌的前景。尽管我们对食物的迷恋如此彻底,很难想象由干细菌制成的粉末是健康、新鲜和对地球有益的。也许第一个在旧石器时代在猛犸象和野牛牛排烧烤场向大型猎物狩猎者分发谷物烤饼的人也曾面临同样的困扰。
原文链接: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2/09/22/its-not-easy-being-green-regenesis-monbiot/?lp_txn_id=1376133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