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我而言,“性同意”这一概念来得有些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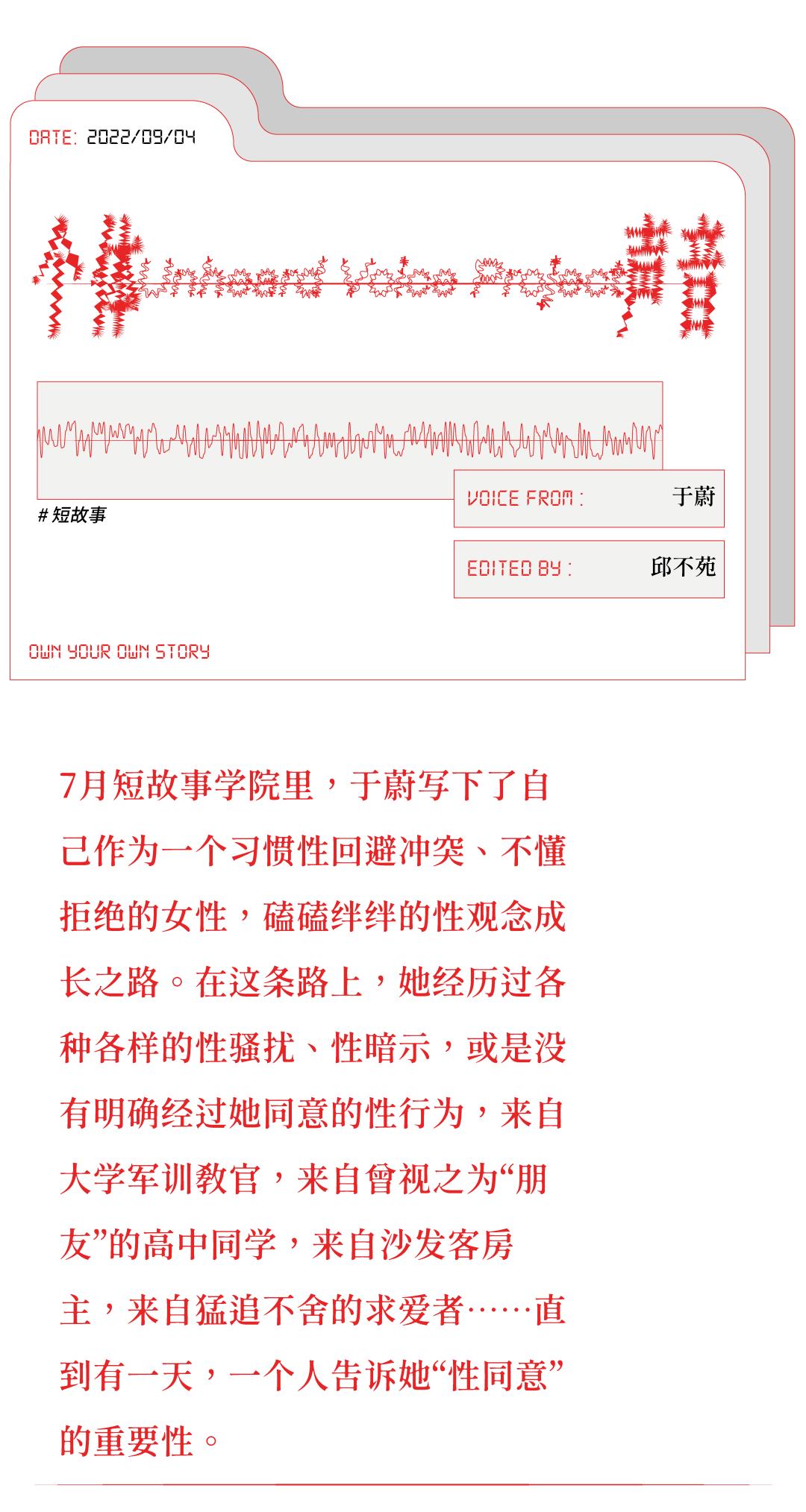

“嫂子,来喝酒!”
我刚坐下就有不认识的教官端着酒杯凑过来。这声嫂子叫得我莫名其妙。我扭头诧异地望着加我微信的教官,期待着他能跟对方解释清楚我们的关系——我们明明只在微信上聊过几次天。
“瞎说什么呢!看把人家小姑娘吓的!” 他看起来在喝止对方,嘴角却有一丝得意的笑容。
我尴尬得想走,屁股却好像被粘在了座椅上动弹不得。怎么开口呢?
“你们不要瞎说,我俩才认识几天!”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却说不出口,只能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尴尬地陪笑。
来敬酒的教官并没有放过我,他端着酒杯挑衅似的看着我。我也来劲儿了,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可一举动反而让在座的其他教官们兴奋起来,大家拍着桌子起哄让我再来一个。面对这一桌子的成年男性,我真是骑虎难下。
几天前我在宿舍打开了微信附近的人。这个功能有点儿意思,只要你把头像换成好看的自拍,每天都能收到十几二十条打招呼的消息。当然,打招呼的都是男性。工科大学里的男生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认识单身小学妹的机会。小学妹,这个词自带一种柔弱和不谙世事的气质,真是个完美的猎物。大概是想要证明自己在高中被校规校服和高考真题压制已久的性吸引力,刚被松绑的我心甘情愿当一只“猎物”。每当打开微信看到附近的人旁边那个红色的蹭蹭上涨的数字,我就暗暗开心,然后心满意足地点开消息列表,一个个查看跟我打招呼的人的头像和朋友圈。
“哟呵,这人是军训的教官啊!”我点开刚跟我打招呼的男人的头像,一眼认出这是在我们的军训操场拍的。刚进入大学,我对稍稍年长的成年男性是充满了好奇的,尤其是这群身穿深绿色军装的教官们,他们应该会和我们这帮学生很不一样吧?带着好奇心,我接受了他的好友邀请。
但没聊几天我就有些厌烦。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跟我提起他的战友在军训时和自己带的学生好上了,后来还结婚了。我总觉得他话里有话,好像在暗示什么。后来他还邀请我晚上和他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我们的校园是出了名的面积大树多,大晚上的和他散步,想想也不太安全。于是我总是编排完美的借口说实在无法赴约。至于为什么不实话实说——说我刚跟他认识怕危险——这有点儿太直接了,他应该会难堪吧?
很快军训就要结束了。临走前他极力邀请我和教官们一起吃个午饭。我内心有些纠结。一方面这些天的交流下来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感觉,另一方面,能被教官邀请一起吃饭似乎是一件有点儿威风和与众不同的事。我心里痒痒,最终虚荣心占了上风,我去赴约了。
可正是这唯一的一次见面,他作为教官在我心中的滤镜碎得稀烂。彼时的我坐在一众成年男教官中间,任凭他们打量调侃。他们好像在帮加我微信的教官把关一样,虽然我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暗示过我对那个教官有好感。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明确地拒绝吗?后来我才明白,在很多男性心中,不拒绝等于接受。
第二天,教官们坐着大巴离开了校园。当其他同学泪眼婆娑地挥手告别的时候,我却暗暗松了一口气。这下应该不会再见面了,我终于可以拉黑他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天不是军训的最后一天,如果不是我们没有任何共同好友或熟人,我可能也没有勇气拉黑他。因为习惯性地避开所有引发直接冲突的风险。在拒绝别人这门功课上,我总是作弊。要么编瞎话找借口,要么拉黑直接消失。

转眼到了大学第二年,我渐渐熟悉了大学生活,却还在探索成年女性这个新鲜的身份。大学女生的宿舍夜谈总是充满了对异性和性的想象。我作为宿舍里唯一有过恋爱经验和擦边性经验的人总是夜谈的焦点。当然,这里没有一个人有过正儿八经的性经验。更可笑的是,作为医学生,有天晚上聊到女性生理构造,一个室友惊呼到“我们竟然有三个洞!”可见医学生们的性知识也是贫瘠得可怜。
与这场身份探索并行的是高中同学之间的“大串联”。刚成年的我们终于被允许独自出游,而首选目的地总是高中同学就读大学的所在地。因为关系要好的同学总是会尽心招待,尽地主之谊。
在高中和我关系不错的他也来找我玩儿了。我们是高三的时候才熟悉起来的,高考后还一起报了补习班。我对待异性会分为两类,一类让我心动的,和一类我没有感觉的。如果这个男生我没有感觉,我就会把他放在朋友的安全区。在这个安全区里,男性朋友是被去性化,没有威胁的。这个男生就被我划分到了“没感觉”的安全区范围。不过,朋友来我的城市旅行,我自然担起了导游的义务。
我记不清那是一个夏天还是秋天,只记得太阳直勾勾得晒着,天空很明朗。在太阳下暴走了大半天的我们好像两只脱水的骆驼。
“哎,我订的酒店就在这附近,我们要不去歇会儿?”他应该是走不动了。
“好啊,先歇会儿,歇会儿再逛。”我对这个提议双手赞成。
穷学生出去旅行最多订一个快捷酒店。他订的酒店在一个七拐八拐的小巷子里,人少,安静。房间很小,推开房门就是一张双人床横在那里,房间显得更加局促。床对面是个紧闭的小窗户。阳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房间很明亮。正是这抹明亮的阳光给了我莫名的安全感。
“我搁你床边儿上躺会儿啊,可把我累死了。”我说完就往床上一躺,没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迷迷糊糊我忽然感到有一只手在我的胸上揉搓。我整个人立刻僵住了。是他吗?他在摸我?!他并没有发现我醒了过来,手还在我身上摸索。我甚至听得到他的喘息。
我感到一股热血涌了上来,脸热辣辣的,心也砰砰狂跳。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摸我?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我想张开眼睛冲他尖叫,拨开他的手质问他为什么。可我什么也没有说。羞耻感让我的眼睛闭得更紧了。
我该怎么办?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各种可能的选项和后果。我首先放弃了睁开眼睛质问他。我不是担心他会采取更暴力的动作——这种隔音不好的快捷酒店应该挺安全的。我担心的是如何面对冲突,以及撕破了脸后如何面对彼此。更何况高中同学的圈子这么小,如果我从此跟他一刀两断,会不会有好事之人问我发生了什么?
要不我继续装睡?我的心还在砰砰狂跳,而他的手就在我的心口,装睡是装不下去了,他应该随时都能发现我的异常。想到这里,我愈加焦虑,眼睛更是死死得闭在一起,仿佛不睁开眼睛我就可以像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一样获得片刻的安宁。
我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解决方案让我和他一起全身而退。最好的情景就是,我睁开眼睛,在他跟我解释之前告诉他我不在乎。这样他就可以不用解释什么,我也不用面对该不该原谅他的问题。
是的,我可以不在乎。我被摸了损失了什么吗?我又不是明朝的寡妇,被男人摸了手臂就断臂以示贞洁。我甚至可以尝试享受这个过程。他也许喜欢我?这是他表达喜欢的方式吗?想到这里,我的心跳终于慢慢恢复到了正常的频率。
我睁开眼睛,气氛有些暧昧。
“你干嘛呢?”我的声音很轻很轻,语气也温柔极了,像一个姐姐发现了淘气弟弟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他见我醒了,有些不好意思地缩回了手,讪笑着说:“嗨,看你睡着了然后没忍住。”
“那你下次要跟我说啊。”这句话有两层意思:首先,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计较,你不用害怕,我不会跟你要一个说法,更不会跟你绝交。其次,你如果问我,我是不会拒绝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对他说,也是为我自己的角色扮演而铺垫——在这个暧昧的氛围里,我扮演着一个行为奔放的女性,直面对方对我的欲望。
显然这句话让我俩都松了一口气。
他并没有继续。我俩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甚至开起了彼此身体的玩笑——这个角色我适应得真好。如果你看到这里,请不要鄙夷我。一个人要生活下去总要有一个自洽的逻辑。当我既不想撕破脸面对冲突,又不愿接受自己的懦弱,不在乎是我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出口。
他离开后,我们保持着一段时间的联系,但最终渐行渐远,成了彼此朋友列表里的边缘人。对我而言,我早已相信了给自己编织的谎言——那天下午只是两个性欲膨胀的少男少女一场暧昧的试探。

我并没有停止自己对性的探索。尽管我始终没有踏出最后一步:对于那件事,我期待但又恐惧。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同龄人大多没有经验,过来人又耻于说出口。系统解剖书里会详细地告诉你男性与女性的生殖系统构造以及生殖过程,但没有任何关于两性是如何从性中获取愉悦的描述,尽管很多时候性交并不是为了生殖。性的愉悦保持神秘,我知道它是存在的——在那些擦边的性行为中有时我会感受的到,可不了解原理的我实践起来永远像是在买彩票。
大四的时候我交了大学里的第二任男友。那时我刚和上一任分手。在上一段关系里我一味地付出和讨好,到头来却被前男友嫌弃不够好看。在我还没完全走出失恋的阴影时,第二任男友出现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人有些胖,年纪不大却老气横秋。他会买一些我根本不需要的礼物,在宿舍楼下等我然后一把塞给我。我拒绝的话他就让我扔掉,更多的情况下他会丢下礼物扭头走掉,留我一个人不知所措地面对校园里路人的别有深意的眼神。我十分烦恼,礼物还也还不掉,丢了又怕有更多的麻烦。可他总是不吝赞美我,我感觉从他那里我可以找回在上一任男友那里丢失的所有自信。我心存侥幸:如果和一个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得不到好结果,那为什么不试试找一个喜欢我的呢?
我说服了自己,接受了他的追求。但很奇怪,在一起之前他可以卑微到尘埃里,在一起之后他忽然强势了起来。我穿短裤他会说只有妓女会这样穿,我和别的男生多说了几句话,到他嘴里就变成了我要扑到人家身上去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生了关系。这件事他跟我提了很多次,但我是怕疼的,我不觉得我对他的感情足以让我我克服疼的障碍。直到我读到一篇报道:
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的研究表明,相对于17岁(人群平均性生活开始年龄)有性生活的人们,那些22岁才开始有性生活的人更容易在性生活中遇到问题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高潮获取困难,性唤起困难以及保持勃起困难。
于是出于对将来无法到达高潮的恐惧,我和一个我不怎么喜欢的人发生了关系。

那段关系自然是长久不了的。
恢复单身的我,尝试了几段单纯的肉体关系。这样的尝试并不是因为寂寞,而是我急于成长为一个能把性和爱区分开来的现代女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脑中的现代女性一定是一个可以在一场云雨后就潇洒离开的形象,一个调换了性别的情场浪子。这也许是因为我不满家庭和社会提供的处女—娇妻—贤妻—良母式的传统模版,也可能是因为一个拥有性自主权的女性模版是缺失和不被讨论的。
可成为我脑中现代女性的路很崎岖。通常情况下在得到了性之后,我就不由自主地渴望更深层次的依恋关系。我的阴道是直通大脑的吗?我有时忍不住会想。二十二岁的我,不用恐惧性生活达不到高潮,但对性和爱的关系还是困惑的。
大学毕业后我搬去了欧洲。在这里,我解锁了新的约会方式。
对于这里的单身人群来讲,手机里下载约会软件是稀松平常的事,有的人可能同时拥有四五种不同的软件。每个软件的用户组成会有稍许差别,比如bumble的用户大多寻求长期稳定的关系,Inner Circle 的用户更偏精英化,Tinder的很多用户旨在寻求快餐式的肉体关系。不过我和现在的男友W就是在Tinder上认识的。
W文弱瘦高,有时候会被刚认识的人误判性取向。他还具有敏感和共情能力强这两个经常被认为是女性特质的特征。我俩后来讨论性别时,都一致认为性别应该是从负一到正一的连续数。我与他的性别都多多少少偏离了两极而靠近于零。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似乎更能察觉女性的困境。
我俩第一次约会是在五年前。不同于之前和别人约会那样经常出现短暂而尴尬的沉默,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就聊得手舞足蹈停不下来。可是因为一些原因,我们认识的前两年并没有一对一地约会。期间,我们一边约会其他人,一边和彼此保持着一种介于朋友与恋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约会经历绝大多数都仅仅只是见面和聊天。在欧洲这样一个对性开放和包容的地方,面对性关系我反而比在国内更加谨慎。好像一个叛逆的青少年忽然失去了约束,也就失去了对外部约束抗争的动力。对我而言这是好事,不再叛逆让我的选择理性了不少。
频繁的约会经历迫使我成长。当我发现自己礼节性的互动会被对方当作有好感的暗示,没有明确的拒绝在对方看来就是还有机会时,拒绝自然成了逃不掉的必修课。
但我依旧有翻车的时候。
2018年我自己一个人旅行,为了省钱决定做沙发客。那次,一个年轻小伙接受了我的蹭沙发的请求。我在沙发客网站上点开他的个人主页,是个非常帅的男孩子,棕发绿眼,笑起来温暖治愈。
我到的那天他们公司正好开party。他在公司楼下接我,并邀请去他们公司参观参观,还可以认识一下他的同事们。他真的很热情,甚至极力留我参加公司的party。那天晚上我在party欢乐轻松的气氛下喝了很多他和他朋友递来的酒。我醉到不知道是怎么回去的。只记得他吻了我,我也回吻了他,紧接着他抱着我上了床。我忽然就清醒了大半。我是喜欢他的,但远没有喜欢到要和他上床的地步,毕竟我俩才认识几个小时!我可以说不吗?我很醉,如果我反抗了,我要离开他的公寓吗?大半夜的一个醉醺醺的女孩子能去哪里呢?
我放弃了,只是和他反复强调要用安全套。他立刻起身熟练地翻出了一只,并且拿到我面前跟我说:“你看,我拿了安全套,你看到了吗?” 那一刻我忽然有个一闪而过的念头:我肯定不是第一个落入圈套的猎物。这样的想法让我不安。我又一次为了自洽说服了自己——即便我是清醒的,我也应该不会拒绝他。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甜蜜美好的假期,就像两个热恋期间的情侣一样。
我和朋友提起这次假期的时候总是隐去了那天我喝醉了的信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和一个醉酒的人发生性关系是不对的,这会是我美好假期回忆的污点。我在替他遮掩,也在替我的懦弱遮掩。
是我在较真儿吗?可这件事并没有给我带来糟糕的影响。但我总忍不住地回想,并对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告诉我在性同意上需要较真儿的人是W。方才提过,和他认识的头两年,我俩并没有一对一地正式约会。有次我在Tinder上认识了一个男孩子,我们聊得挺好,也有共同的爱好——喝啤酒,但我觉得他更适合做朋友。这件事我跟W简单地提过。后来那个男生邀请我去他家尝尝他去比利时出差带回来的精酿。那天我俩在沙发上边喝酒边聊天,我挑了一瓶带有巧克力香味的斯陶特。一杯酒下去,我感到气氛有些暧昧。他主动吻了我,我没有拒绝,接下来的事情你自然也猜得到。但结束后我就有些后悔,我觉得自己破坏了朋友间的界限。
我把这件事跟W分享了,连同我对自己没有原则的抱怨。
“你当时喝得很醉吗?你有没有觉得受到胁迫?”W的第一反应让我意外。
“呃,这倒没有,我当时还是挺清醒的。” 但我上次去旅行可是醉得不轻,我暗想。
“那你想和他发生关系吗?”他追问。
“在那个时刻,那个暧昧的氛围里,我是不拒绝的。”
“可不拒绝是不够的。只有你表达出了积极的意愿才代表可以。”
我多想有人可以早点告诉我这句话,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漆黑的森林里独自摸索。

我和男友W已经正式交往三年。几个月前我们一起看了一场电影,《最后的决斗》。电影用强奸犯、受害者和受害者丈夫三个人的视角讲述了中世纪一件性侵案。在强奸犯的眼中,受害者所有的拒绝都是欲拒还迎,就连她逃跑时掉落的鞋在他眼中都是故意的引诱。
晚上我俩躺在床上讨论从电影引发出的有关性同意的议题。性同意实际操作起来是有些困难的,尤其在一个女性不被鼓励表达对性的欲望的社会。在传统情境下,女性总是被默认为被动的,而男性却被默认为主动的一方。于是双方都被规训出了一套行为标准——女性不拒绝,男性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我想打破这个困境的一个办法就是说出自己的欲望,当自己不想要时明确的拒绝。可如果男性选择无视这些拒绝的信号呢?如果女性因为一些原因无法拒绝呢?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几年前那个打破了我的信任伸手去摸我的高中同学。十年了,我不想再为他承担羞耻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和W讲起了那个下午。当我回忆到我紧闭着双眼被羞耻感包裹的时候,我委屈极了。W抱了抱我,轻声说道:
“你没错。”

那天晚上我抱着W哭了一场。
我感到自己发泄了这些年作为女性受到摆弄的委屈:刚踏入校园时教官对我不怀好意的调笑,大学时趁我睡着摸我的同学,读研时在我醉酒时和我发生性关系的沙发客房东。这些事说小不小,说大好像又没人会管。可这些都给我留下了一道道疤痕,每逢阴雨天便又痛又痒。因为它们面目丑陋,我从来都不敢掀开衣服给人看,只能隔着衣服悄悄挠抓。
现在我要把伤疤亮给你看,不是想博取你的同情——在一个性教育贫瘠的系统里,一定有人比我更值得同情。我只想告诉你,这些伤疤本不该存在。这不是我的错,我只是懦弱不会拒绝,而伤害我的人利用了我性格的弱点,在一次次试探中得寸进尺。同时,这个系统在不断地包容一个个越界的试探,而这些试探的人好像总能若无其事地走开。尽管绝大多数的人都明白性侵是错的,但在让人不适和性侵之间还有很多行为处在一个灰色地带,它们或是不怀好意的调笑与玩笑,或是取证困难的触摸,或是因为难以拒绝而默许的性关系。又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这些行为是不妥,甚至是错的呢?我该指责这些人吗?可如果没有性教育,你又如何指望他们能够意识到呢?
对我而言,性同意这一概念来得也有些晚。当我受到伤害用仿佛自洽的逻辑为自己寻找出口时,如果我了解性同意,我是不是会更有底气和勇气来维护自己?相反,那些值得回味的恋爱经历与性经历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我从始至终都主动表达出了积极的意愿。这里面包含了非常关键的一点:我遵从了内心的感受,并做出了让我舒服的选择。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快要三十岁的我好像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航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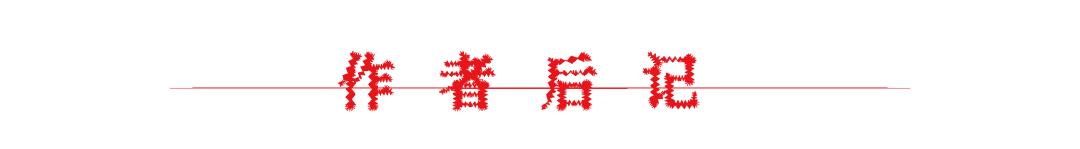
在最开始选题的时候,我只是想写下那天下午熟睡的时候经历的背叛与猥亵。但写着写着,很多貌似不太相关的回忆一个一个地冒了出来。这些回忆都有一个共性:它们都是难以言说的秘密,都是我曾经试图隐藏和忘记的过往。但不论我多么想要忘掉,它们还会时不时地在某个时刻冒出来,带给我一阵恶寒。当我落笔写下这些回忆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都是以一种荒谬的方式来处理冲突的。我时不时感到的恶寒,来自于对自己处事方式本能的羞耻感。
我们从小都被教育要懂礼貌,要积极地帮助别人,要替别人着想,但拒绝和说不的教育是缺失的,也是不被鼓励的。于是,为了面子上的好看,为了别人的感受,我只能不断压缩自己的舒适空间。这样的处事方式延伸到了我对待性的态度,尤其是在性教育以及性同意教育缺失的情况下。
当我把这些回忆写下来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羞耻感在慢慢萎缩。
原标题:《对我而言,“性同意”这一概念来得有些晚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