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读她的小说,即使最虚无的心也会爱上生活
小说《鲨齿蟹》选自新世代海外华语文学作家王梆的首部小说集《假装在西贡》,讲述了一个青春与谋生混杂的水涔涔的南方故事,银春发廊的一对双生姐妹花,她们野蛮生长、苦中求乐,绝不甘心生命像商品一样被交易。开篇第一段“我妈死了,我自由了”,乍泄出令人心惊的叛逆。。

红红将湿漉漉的紧身裙一把扒下来,扔到脸盘里,然后俯身冲着赖在草席上的我说,我妈死了,我自由了!那是1991年的盛夏,天空突然被人割开了一个大口。暴雨不断,建筑废料堵住了下水道,洪水迅速地把广州,那个正在沦陷为工地的城市囚禁了起来。腐烂的西瓜和瘟鸡从上流漂到下流,尿黄色的积水底下,蠕动着形形色色的虫豸。
当红红发梢上的雨水滴到我的脸上时,我正在一场关于鲨齿蟹的记忆里游荡着。鲨齿蟹、鳄鱼、山魈……在所有这些和洪水相关的食人兽中,我最怕的就是鲨齿蟹了。鲨齿蟹不像鳄鱼,它们体积微小,繁殖速度像球菌一样,颜色和洪水一致。吃人后脚跟时,小卒先上,趁人不备,冷不丁啄出一粒脚皮肉,血渗出后形成咸腥的红色信号,大军们再追风逐电,聚拢而来,不出半炷香,被抬出水面的人就只剩半截脚了。泡过水的皮肉煞白无血,看起来就像被削掉了软骨的猪蹄。每次发大水,街道变成河流,小孩们全副出动,把桌子掀翻过来当船筏,踢水皮球,或者用晒衣杆打水仗,只有我缩在阳台的栏杆后面,疑神疑鬼,心神不定,和此刻这个“鸟样子”一模一样。

我妈死了,我不干了,我自由了!红红扳着我的肩膀,把我立了起来,水淋淋的头发粘了我一脸,这下我才彻底苏醒过来。
在银春发廊里,我是小鸡,红红是我的母鸡,老板娘是老鹰。红红自由了,那我怎么办?
从我进入银春发廊的第一天起,老板娘就一直处心积虑地要把我赶走。有天晚上,她突然披上了一条崭新的花披肩,说要带我去白宫喝夜茶。老板娘平日连包子都不肯多施舍半个,怎会披条披肩就变得绰阔起来?果然,一个颅骨凸出,重心不稳的印尼老华侨,从满堂蒸笼包的白气里冒了出来。
这妹仔太小,放在我们那里不合适,你带她走啦,她可以在你的士多店里,帮你卖卖嘢……吃饱喝足,老板娘边用牙签捅着满嘴的牙缝,边漫不经心地对印尼老华侨说道。冇问题,冇问题,我会看住她的啦!为了使两边的口轮匝肌对称,印尼老华侨费劲地笑着。
我才不要去,我说。你不去?哪个养你啊?你要不要去站街?你要站街,我就给你留下……老板娘说。我不要站街!我噘起嘴。不站?那你带她走,即刻就带她走,快快催催,免得阿Sir找上门来说我窝藏幼女!老板娘朝印尼老华侨努了努嘴。

那我的行李呢?我的衣服呢?还没有告诉红红……我央求。红你妈个黑!她边有得闲理你啊?她客那么多。你咁中意她,你同她做啊,你们一对姊妹花,不如一起做双飞,我同你们四六开,好唔好?老板娘抬高嗓门。哎呀,你对小妹仔说这些干什么?印尼老华侨黏在老板娘的肥臂上,伸手夹起一只凤爪,话咗她也不明嘛!放心啦,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你那些旧衣服扔掉就算啦,我已经买咗新的给你,牙膏牙擦,都是新的……
上了最后一班开往黄埔港的渡轮,我就开始后悔,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渡轮很小,甲板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每个人的脸看上去都是阴沉沉的。当船头淌过污浊的珠江水,朝一个更宽广更昏暗的航向迈进时,印尼老华侨用他那夹着卷烟的黄手指,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掐了一下——隔着二十多年的时光,那块被掐陷的部位仍保留着清晰的身体记忆,就像让一个有洁癖的人去淘粪,指缝里因此便染上了粪便的记忆一样。

我想给红红打电话,渡轮上似乎没有电话亭。我想起来红红也没有电话,只有老板娘有电话,白天象征性地搁在收银台上,打烊后锁在柜台里。那一年我只有十五岁,十五岁的肉联厂职工的女儿,全副身家不到十元五角钱,胳膊被人拽得死死的,目光所到之处只有一顶顶破草帽、一只只破网兜和一双双沾满污泥的脚。黑色的波涛正一刻不停地吞吐着白色的唾沫,红红,我的母鸡你在哪?
一进士多店,我就开始琢磨逃跑的路径。士多店是间青砖房,看起来年代久远。汽水、廉价香烟和水果糖堆在售卖架上,角落里一把竹梯通往阁楼。阁楼昏暗狭窄,站起来得猫腰。没有床,杂木地板上平行地铺着两张麻将竹席,一张看起来汗迹斑斑,另一张摊放着一条加小码的乔其纱连衣裙,价码还没剪掉。一股被风干的鼠尸味,侵蚀着楼阁里的所有物件,从吃剩半碟的粉饺,到挂在墙上的夏威夷花衬衫,再到衣橱上的蛤蟆太阳镜和假牙……
阁楼没有厕所,只有一只搪瓷尿壶,大便得去后院。后院是个天井,四周是与士多店相连的青砖楼,模样看起来像家茶餐厅。夜深人静,通往茶餐厅的铁门已经锁上了。两只潲水桶发着恶臭,一块巨大的砧板横在院子中央,上面的内脏和积血足以喂饱一个苍蝇王国。不远处有一口八角井,井边爬满了湿漉漉的水蛇。用砖砌成凹形,顶上铺了半块石棉瓦的,就是印尼老华侨的蹲厕了。发现了这个藏身之地后,我就二话不说,拉上门钩,将自己反锁了起来,任凭印尼老华侨如何软硬兼施,任凭蚊虫如何叮咬,也无动于衷。那晚的月亮锐不可当,像一把剃刀。我从少女变成了猫头鹰,睁着橙黄色的眼睛,站在陡峭的岩石上,隔着一大碗漆黑的江水,向红红频频发射着求救信号。

凌晨时分,我终于听到了脚步声,接着是霹雳哐啷的铁门声,然后是茶餐厅勤杂工疲惫不堪的哈欠声……我冲出茅厕,穿过铁门,迈过茶餐厅的门槛,不顾一切地往码头上跑去。当第一班渡轮移近时,红红果然屹立在甲板上,像一个信心十足的狙击手,无情地扫射着对岸的一切。她那发育未全的乳房,被清晨的阳光镀上了一层结实的金。从那以后,红红和我做回了银春发廊的一对姊妹花。
我的铺盖紧挨着红红的铺盖,尽管我俩在一起睡的机会实在不多。有时候我起床时,红红还没有回来。不过只要她在,我们就有说不完的话。她如果天亮前下班,还会附在我的耳边说早安。
我们的卧室是一个热闹非凡的通铺。到处都堆满了发亮的裙子,廉价香水,开裂的粉饼以及莫名其妙的笑话。每到清晨,姐姐们就会从黑夜的内脏里钻回来,脱掉香臭难辨的连衣裙,敞开汗淋淋的肚皮和大腿,四脚朝天地倒下去,仿佛重力并不存在,身后的空隙布满了繁星。有个姐姐,长得不算好看,但只要笑一笑就能让自己光芒闪耀,有段时间她一躺下就笑,仿佛草席上藏了两个胳肢鬼。连体人姬无双被砍成两半,各自平躺在地上时,也曾窃笑不已,但那是武侠故事,现实中能笑着躺下的人实在不多。红红私下告诉我,那小骚精爱上了一个修手表的,也是外地人。能笑赶紧笑吧,以后有得他俩哭,红红说。一个月总有三到四天,红红闹痛经。不开工,她便把双脚架在低矮的窗台上,说抬高脚踝对痛经有利。骑楼上只有硬邦邦的杂木地板,象征性地扫了几抹朱红色的劣质油漆,几床破棉胎和几张褪色的草席,占据着红蚁、蛀虫和蟑螂的领地。

窗台底下放着一只蚊香式电炉,我们用它来开小灶。红红的小灶总是鸡蛋。鸡蛋用处可多了,红红说,能补血、补钙,还能用来穿耳洞。红红总想赶在天气还不算太热的时候,给自己穿上耳洞,尽管她每次穿完都发炎。这是我妈传给我的祖传秘方,不会有错,她说,边递给我一只在生姜里消过毒的银耳针。这秘方听起来似乎也有些科学道理,蛋煮熟后,连壳带皮在耳垂上滚,待耳垂通红发热,像水煮过的橡木那样绵软而麻木时,就用针扎进去,只要足够狠,一针便可通过,若稍有迟疑,就得补针……说起来很轻松,红红却总是疼得泪腺充盈。
那还要不要穿另一边?我问,手中的银耳针微微颤抖。当然要啊,不然好运通!红红说,看你这个屎样,针拿来,我自己穿!然后红红就会咬着厚嘴唇,对着镜子,掉着眼泪,扯着红肿的耳垂,冲着已经长合的洞眼,一针又一针地扎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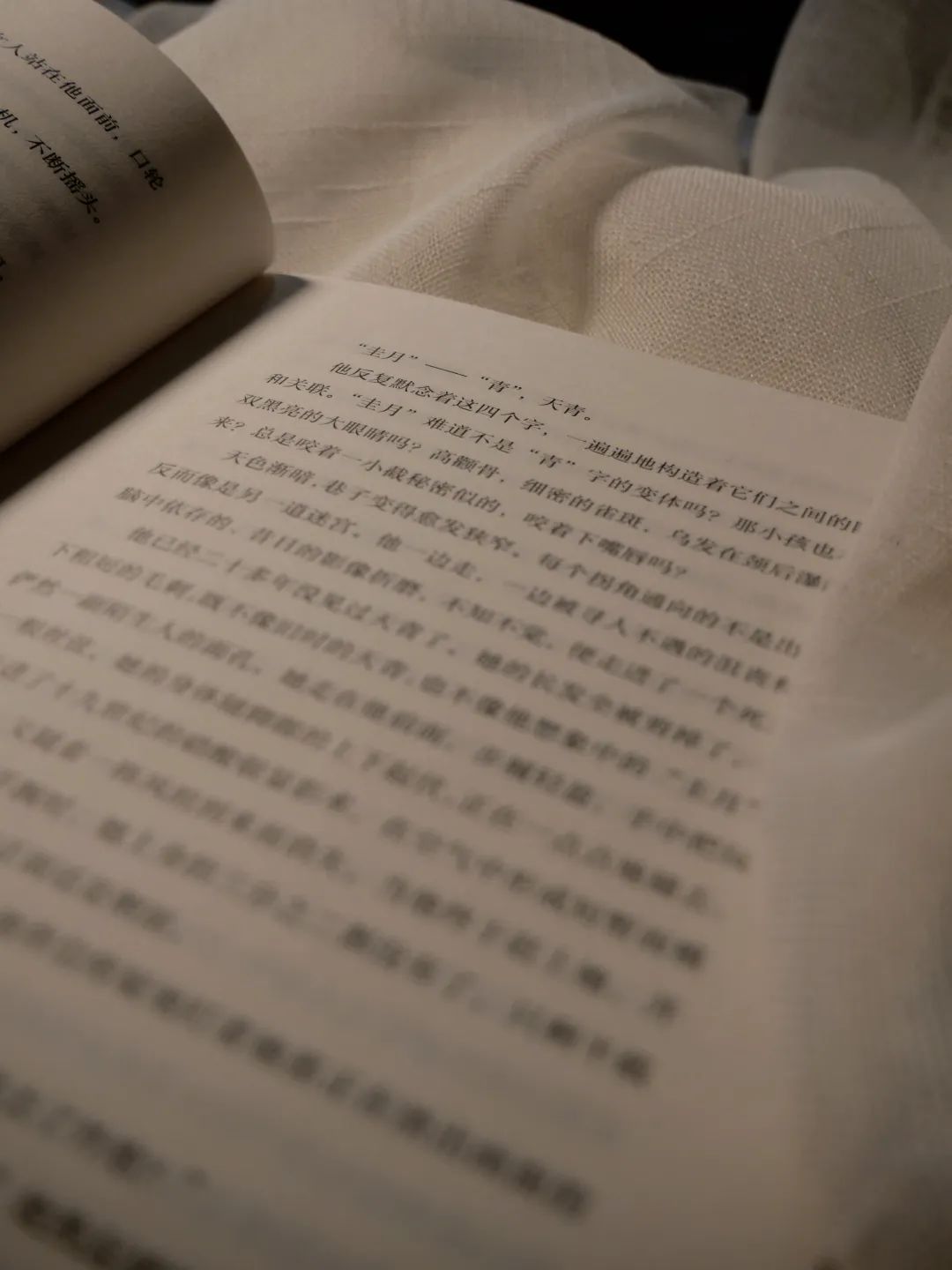
红红原本在东莞一家卖假飘柔的地下工厂里做工。一年前,红红的母亲患了子宫癌,家里的猪全卖了,也不够换一次化疗钱。红红不单要付哥哥在技校的伙食费,还要给母亲治病,于是她便给自己定下了每天只吃三个榨菜包的规定,结果在一次痛经后染上了突发性贫血,被两个工头一头一尾地抬到了厂区外的一栋烂尾楼里。到了广州之后,她就变成了“红红”。十九岁的红红长着一对丹凤眼,嘴唇丰厚倔强,不开工的时候,喜欢在长发上插一朵绢红花,对着镜子没完没了地端详自己。
红红和姐姐们开工的地方,在银春发廊附近一栋隐蔽的出租屋里。一楼住着两个马仔,房间里终日烟熏火燎。二楼住着一个老太,据说是老板娘的表姨,也是绝世烟鬼,吸烟时手指上还戴着两只慈禧太后式的铜指套。三楼是七个板间。板间不算太小,能塞进一张双人席梦思和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上还有一台不时骨折的钻石牌风扇。有时候发廊里没闲手,我就得把刚剃完头的客人领到那里去。抱着一沓干硬的旧毛巾,走过烟雨凄迷的小巷,眺望着不知谁家的温馨灯火,看墙头上的牵牛花和衣而卧,用眼神问候路灯下偶尔闪过的折耳猫……整个路程既宁静,又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一点都不像去逛窑子,反倒像去墓地凭吊。

当然大多数时候,我哪也去不了,只能待在发廊里,一边做这做那,一边斜眼望着那些脖子上满是碎头屑,不安地打着脚震,把烟抽得像蚊子吸血似的男人。他们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红红呢?听说这条街上有个姐姐,意外咬伤了某个客人,就被打掉了半排牙齿。
你别瞎操心,客人们不都是这样的啦……红红边涂着胭脂,边从镜中抛出一个媚眼,他们只是脑袋不够灵光,灵光的人就不会上我们这了。金子又不是沙子,能随便淘?搬一箱马赛克才两块钱,月底还得把钱寄回老家给老婆小孩花,够可怜的,就这样还要从饭盅里悭下十块二十块,满足一下皮肤饥渴……
立夏一过,阳光便如同砂纸,被它摩擦之后,就会掉一层皮。烈阳隐去便是暴雨,伴随着摄氏三十四度的高温,城市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蒸笼,蒸笼里是一具具黏糊的皮肉和一条条迟钝的神经。那几天,红红经常梦见她做工的床底下有只手,时不时地,尤其在客人快要“到”的时候,就冷不防伸上来,一把掐住她的咽喉,往死里掐,不死就不罢休。一个月以后,红红就接到了她母亲去世的消息。红红说,那一定是她母亲的手,要她置于死地而后生。

你自由了,我怎么办?我用指甲抠着地板,一筹莫展。暴雨稍歇,暮色渐凉,我们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经过漫长的讨论,红红得出了我应该回家的结论,因为我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家的”,在这里待着只是“尚有可浪费的青春”。她说的也许对,我从印尼老华侨那逃跑回来以后,老板娘不但继续不付我的工钱,连我的伙食也从一日包三餐降到了一日两餐,即午饭和晚饭。午饭通常要等到下午三点左右才有得吃,因为那是姐姐们睡醒之后的时间。每天早上,我都得七点起床,打扫碎发,擦亮镜子和剃刀,洗净姐姐们的衣服,浇富贵竹,开门迎客,为客人洗头,为理发师递发卷,浇冷烫精,冒着暴雨或烈阳走三里路到那一区最便宜的农贸市场买菜。回来后一毛五分地和老板娘报账,完了还得用累得几乎报废的双脚,撑着合页形的身板淘米做饭……要不是红红常给我五毛钱让我去换包子,我早就饿死了。
你回去吧,好好听你爸妈的话,别和他们吵了,不值得。上个补习班,再进一家好学校,说不定以后还能考上大学。你比我幸运一万倍你知道吗?你不像我,我已经是不干净的人了,有家也回不了了……红红一边喋喋不休地为我打着气,一边翻来覆去地查看我的掌纹,试图找出她认为我定有作为的证据。

至于我么,我已经想好啦,先去深圳看看。有个老乡在那里的一个染织厂,挣的钱肯定没这多,但干净!红红边说边微微昂起了脑袋,一刻钟前凝聚在空中的乌云,仿佛真的被一块巨大的抹布擦掉了。
我终于答应回家,红红如释重负。她掏出钥匙,打开行李箱,取出一件厚棉袄,用剪刀拆开衣角的缝线,在棉絮里掏出了几捆皮筋扎好的钱。她把钱摊开,分成两份,将其中的一份装进一只绣着粉荷的针线包,然后连同针线包一起送给了我。那是五元和十元一张的、分量十足的八十元。接着我们趁老板娘不在,到火车站分别买了次日回家的硬座票。
在回程的公共汽车上,红红突然决定要请我去看花灯。满世界都是洪水,哪有花灯?我迟疑。红红坚信工人文化宫有个花灯展,她说她在一张包着富贵竹的报纸上看到的,我们便在中途下了车。水还没退,天色却已经有些暗了。我们蹚着鲨齿蟹色的脏水穿街过巷,我感觉自己的后脚跟在渐渐变凉,仿佛被吸入了一具行尸的口腔。

工人文化宫是五十年代在一座孔子学堂的遗址上建造的,学堂里阴魂不见,只剩几只金鱼在深褐色的池子里有气无力地吐着气泡。我们绕过漂浮在水面的残枝败叶,踏上了总算有点干燥的大理石台阶。那里大门紧闭,别说花灯,就连屋檐下挂着的两只红灯笼,也被狂风吹瘪了。这里真凉快啊!红红噘起她的厚嘴唇,干吹了几声口哨,丝毫没有悔意。啊,好久没吹过风了,我们去找风口吧,这附近肯定有风口的!她是那种只要起了念,就马上要付诸实践的人。我们总算在两堵高墙之间找到了一个风口,那里的风很大,在风口里我第一次向红红袒露了我对鲨齿蟹的恐惧。那怪物有多大?红红问。我将两片指甲尖夹在一起打了个比画。红红笑了,别怕,针孔那么点大的玩意,有啥好怕的?它敢咬你,你就一针扎死它!
风更大了,我们的头发被吹成了两条又长又黑的“斜坡”。
乜嘢?奔丧后就不回来了?听红红说要走,老板娘的表情显得极富戏剧性,不过似乎很快也就接受了。你想要返你的身份证?得啊,不过,你点都要做完今晚再走吧?老板娘说。我妈死了!我妈等着在火化前见我一面呢,你也是当妈的,你他妈的不懂吗?红红说。俩人为此僵持不下,红红气得全身的骨头都要暴出来了,在发廊里大吼大叫起来。你今晚不放我走,我就把这里一把火烧了!我说得到做得到!红红边说边抓起了挂在镜子上的一把假发,举到了吱吱燃烧的香炉上。老板娘每逢初一十五必为菩萨烧香,为此,还专门请人定做了一座齐人高的红木神龛。
啊呀呀,你同我过不去就算啦,你和菩萨过不去做乜嘢?快点将它拿开,烧咗神龛,在阴间有得你受的……老板娘边劝,边悄悄拿起电话,看样子是要叫她的马仔。红红用眼神暗示我去抢电话,我一不做二不休,把端在手中的一碗滚烫的稀饭,朝电话上泼去。哇有冇搞错啊,你们……你们两个食碗面反碗底……老板娘带着哭腔干号起来。这场斗争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以三个马仔把我和红红分别用人字拖狂扁一顿而告终。

今晚是礼拜六,一定很多客,人死不能复生,有钱总是要赚的,赚咗钱俾你妈买靓香烧,我话得不对咩?又话了,你在我这里住咗这么久,好吃好穿的我都省省的,留一份给你,我几时有亏待过你?你要这个贱人留下,老板娘斜瞥了我一眼,继续往下说,我都应承咗你,不是咩?就当我求你啦,好唔好?!你做完今晚,我明日一早就还你身份证……老板娘边说,边抱着红红那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不停地抹清凉膏。
红红终于妥协了。她爬上阁楼,将身体埋入一堆眼看就要扔掉的纤维里。开工之前,她吸了半包香烟,然后才跟在一个肥胖的客人后面,走出了银春发廊的门。今晚早点睡啊,不要等我,别耽误了明天上午的火车。如果明天早上我还没有回来,你就自己走吧,给你的钱收好了?她鼓起腮帮,吹了吹我的肩膀,上面有些香灰。

那朵她没戴走的娟红花,被窗外的霓虹灯照射着,一会变蓝,一会变紫,在浓重的阴影里,怎么看都不再像一朵花。
那天夜里,我仿佛躺在不断浸水的甲板上,一身大汗却感觉冰凉刺骨。将近凌晨的时候,我被阿Sir的吆喝声震醒了,他们以老板娘“涉嫌教唆未成年少女卖淫罪”为由,用手铐把我铐上,将我作为“人证”带回了派出所。在遭到我的坚决否认后,一位女警把我关进了一间单人牢房。牢房里只有一张铁床和一条毛巾被,飞蛾们在一盏瓦数极低的吊灯底下亡命扑飞。进了牢房之后,我就开始大哭不止,用手铐上的铁链反复击打床架,上厕所也不停歇,电棍唬吓也不顶用。我哭了两天两夜,直到我那在肉联厂杀猪的父亲突然像一堵肉泥做的墙,面色铁青地出现在牢房门口为止。为了对他那隐藏在体内的突发性暴力有所准备,我擦干眼泪,拉直四肢,竖起耳朵,拾起涣散的视线,准备随时还击。然而我的父亲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扬起头,相反,他一反常态,情绪稳定。在离我不远处的一炷蚊香旁,我看到他用配合的食指,在一沓文件的最下方,按下了一个红印,然后我们就被带上了一辆警车。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车开到了一栋办公大楼底下。父亲问是否可以让他留在外面,请示获准。父亲掏出香烟,殷勤地给司机递了上去。
脱掉裤子,内裤也要脱,在一间宽敞明亮的体检室里,女医生下着命令。铁床是一只折叠的金属托架,上面铺着一块白布,我把瑟瑟发抖的上半身放了上去。他整天就知道吃,才94.9厘米,却已经有17.8千克了!女医生说,边戴上一副乳白色的橡胶手套。17.8千克挺正常的,不用担心,女助手说……对话声渐渐远去,我听到阴道内传来薄冰碎裂的声音,我感到自己体积正在不断缩小,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流质在我的身边荡漾开来,黏稠,温暖,比洪水还要漫无边际,比落日还要昏黄。二十多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返这片神秘的水域,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就算水里真有鲨齿蟹,针孔那么点大的玩意,没啥好怕的。想到这里,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了鲸鱼,摆动着巨大的尾鳍,奋力向前游去。

▲ 王梆,旅英作家,著有非虚构作品集《贫穷的质感》、电影文集《映城志》、法文版漫画故事《伢三》以及数本短篇小说绘本集。作品散见于《花城》《单读》等,入选美国“文字无边界”文学网站,2016年秋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故事新编”中国当代艺术展等。曾入围2019年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收获文学排行榜。英国国家写作中心2022才华扶梯计划唯一非母语入选者。
文字丨选自《假装在西贡》,王梆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8月
图片丨选自电影《燕尾蝶》(1996)剧照
编辑丨曼旎
原标题:《读她的小说,即使最虚无的心也会爱上生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