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小调查|那些曾经喜欢现在却觉非常遥远的书
喜欢总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成分掺杂其中,或许随着时间飘落,或许随着时光沉淀更显深沉。如果以相对视角来看,与我们的现在相比,过去的自己往往显得几分稚气,或许那时也可称“不识人生之味的年代”。
如朴树所唱,“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有的回忆往往有美好的滤镜加持,为过去的体悟镶上舒适的金边,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都像是镌刻进生命的印记,未必可以抹去。
那么回顾过往,有没有哪一个自己曾经喜欢现在却觉得遥远或者不可思议的作家或作品?一定会有某一本书打开了通向他的大门,然后看见一个世界。之后随着年岁增长,视野不断扩大,对世界认识的圆的半径不断向外延伸,彼时与此时的阅读体验一定大不相同吧。
小李
如果是说曾经喜欢而现在觉得没那么喜欢,甚至觉得有问题的作家,在我看来可能是金庸。青少年时代或中学时代,非常喜欢的他的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他的十四部我基本都看过。其中尤其喜欢《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令狐冲、杨过等是非常对我胃口的人物。

当时年少轻狂,一方面向往快意恩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纵情江湖,不为世俗羁绊,一心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另一方面,也符合当时的心境,金庸也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武侠世界,在这里可以跟随主人公做好事当好人,正所谓金庸对郭靖的评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写作文经常用到,并觉做人当如此。
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样未必可以。金庸的价值观本质上属于精英史观,很难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平常人,他塑造的基本上都是大侠客,即便韦小宝也属于市井中的精英,而平常人顶多只是被一刀捅过去的小角色。
对老百姓而言,不能祈求某个大侠拯救,大侠杀完人终究要走,而且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大侠,靠郭靖、杨过、令狐冲等个别侠客是不可能的,终究要靠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才是正途。
徐驭尧
我曾经喜欢过的作家,现在看起来仍旧都挺喜欢的,或者可以说现在看来也能谅解过去那些喜欢,并不觉得讨厌或者遥远。

讲一个曲折的故事,我大概中学时候比较喜欢梁文道、王小波等这样一群作家,会觉得他们所描绘的理想政府图景很有道理,但在读大学后自己读了一些学术类的著作之后,会觉得他们的作品很简化,对比看来非常浅显。
年轻人尤其是本科大一大二时,会觉得如此浅显的作品怎么能入眼,这多没有意思,多没水平。但随着年龄又大一点,视野更加广阔,见到更大的真实世界,发现描述浅显的东西未必没有水平,从过去喜欢到猛烈批评的过程是比较愚蠢幼稚的,不过是一个知识上的“弑父”情结。此时重新再看,发现对这些作品有了不同于前的喜欢,这实质上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从“曾经喜欢”到“现在却不喜欢”了。
举个例子,比如刘瑜,她写的书简单易读,能用如此简明流畅的语言来讲一些政治学道理,非常有趣,尤其对于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来说更是有吸引力。但当自己学了一些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以及美国历史知识后,会觉得她的很多说法可能存在问题,在理论方面也有局限。不过,如果让我在那个时间节点,哪怕是现在,要在公共平台写一些东西,我也可能按照刘瑜的路数来写。毕竟偏学究的文章其实并不适合公共传播,或者说在严肃的公共传播中必须写成那样,而且写成那样也未必不好,有时复杂的东西也没必要讲那么清楚。
吴心琦
我的回忆可能要追溯到很久之前了。那是一个周围小伙伴都在看杨红樱、郑渊洁以及《冒险小虎队》的年代(暴露年龄),我偶然接触到了张之路的《第三军团》。

印象中这本书讲的不是一个大团圆的故事,虽然这个青春故事中依旧有校园,里面依旧有热血的男孩、有清纯的女孩;很正义,很崇拜,很激动人心,但也很复杂;并且——没有完美的结局!这对于一个期盼着好人有好报的小学生来讲,是多大的冲击!但就是因为这样喜欢上了这个作家,几乎把他那一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书都读了:《空箱子》《极限幻觉》《蝉为谁鸣》《有老鼠牌铅笔吗》《魔表》《霹雳贝贝》等等,有一些甚至因为情节太悬疑、科技感太强造成了一些莫名的童年阴影……但是真的依然很喜欢!看这种一波三折、情节跌宕甚至有一些暗黑风的故事,在阵阵脊背发凉的瞬间,有一种被文字撩拨的微妙感觉。
现在回头看张之路老师的作品,感觉其中一些作品甚至可以称作成人童话。哪敢想象小时候的自己会有勇气和兴趣去看这些有点难过、有时荒诞、充满悬疑的故事。现在的我反而胆小如鼠,害怕哪怕一丁点负面元素在作品中呈现;所谓的大团圆结局反而是长大以后更想读到的了,毕竟生活艰难……总想从一些好的结局中看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生前景……但不管怎么说,张之路老师对幼年的我的启蒙作用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比拟:如果没有他,我可能真的一辈子沉浸在对甜蜜美好的大团圆故事的想象之中了。
三氧化碳
曾经喜欢偏实践类的书,比如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熊培云的文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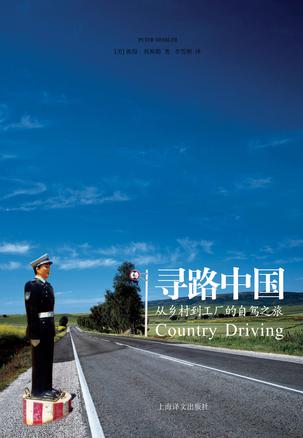
当时处于从医学院向社会学转专业的阶段,这些书对我非常有帮助。而后来进入社会学专业进行系统学习时,发现与正规的范式和路数相比,这一类书并不深入,论证也比较浅,就会觉得有些野路子的感觉。他们不是剑走偏锋,而是功夫不到家,而且带有“诱导”成分,不符合价值中立的学术规范,与马克思和韦伯“刻意引导”的概念不同。
当然,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剑走偏锋可能越来越难,比如很难再出像达尔文、伽利略这样的人了。其实再比如民科,可能不入科学家的眼,但在当时仍旧是比较有帮助的。
何奕廷
对我而言,对于文学作品的喜爱,不存在一段时间非常喜欢,但后来对之非常不喜欢,不存在这种价值观上的剧烈转变和前后逆转的体验。但一定要说的话,可能不是针对某一个作家或者某一部作品,而是针对一种文学类型——婉约词。我对婉约词确实存在前后比较大的审美差异,并不是说不美,但目前是不太喜欢了,一方面觉得婉约词本身意向有很多重叠,主题也有局限;另一方面,可能是年龄大了,对诗词的审美也走向宏大。比如秦观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当时非常喜欢,因为其在意向描述上的确很美,但随着自己人生阅历的增加,面对这些意向的堆砌,会觉得有些矫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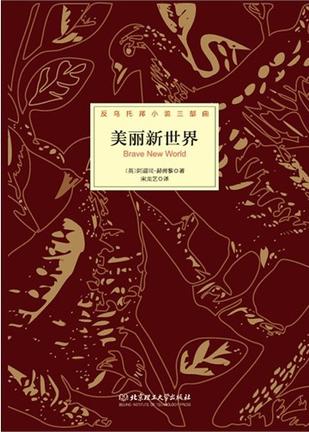
此外,我对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前后看法也非常不同,以《美丽新世界》为例,初次的阅读体验是觉得这个世界很可怕,科技慢慢渗透生活,人类无法成为自己的主人,忘记自己的意识,错过人与人交流的机会,每个人都被视为一种工具。当时我对赫胥黎提出的这种世界观是非常认可的,这可能成为反乌托邦的雏形。
后来我对这一类通过虚构图景来预测人类未来发展的一类作品是不太感冒的,更像是文学作品,其刻画的更多是作者自身的担忧。基于对社会科学的学习,我会觉得这些“担忧”是缺乏实证基础的,即便这包含着作者一定的洞见性。比如说,其中体现的人类自主性或工具性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了?这类作品的实际测量都是有问题的。
很多人会崇尚所谓的历史神学或科幻神学,认为这样一类作品可以为人类指明方向,比如有人会觉得《海底两万里》好厉害,这么久以前的人也可以预测到未来的发展,从而将其视为金科玉律。但就我来说,这一类通过勾勒人类未来阴暗场景的作品仅仅处于在文学作品层面上,并不会成为非常具有洞见性和预测性的著作。我对它们的看法就从非常崇拜转向了还行,只是一部作品而已。总之,对于宏大视角的小说,我从前觉得非常准确地揭示了人类的发展趋势,现在因为社会科学思维对自己的影响,这些小说都显得非常遥远了。
无知的瓜娃子
我曾经喜欢过一个不是很有名的叫童非非的青春感伤型作家,“童非非”应该是笔名。

她写过《死了都要爱》《夏洛,不哭》等,我都看过,还有一本叫《我很想爱他》,是我当时比较喜欢的一本。内容记不太清,大概是一个女追男的故事,男主故作冷漠,历经曲折后在一起了,但真相却是女主在喜欢男主前失忆了,而且这段记忆中她爱上的是被自己害死的哥哥,记得当时自己还看哭了。因为当时这本书刚好可以在离家近的书店买到,而且在满是少女心的年纪,格外喜欢封面,还临摹过。
之所以喜欢,是因为其能满足一个无知少女的粉色幻想,而很多其他“正规的”的作家,阅读他们的作品大多是老师布置的,我也会去读并且也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并且对现在也影响深刻,但并不能否认我曾经喜欢过童非非的作品。
后来觉得,童非非的小说都是一样的套路,作为青春小说来“骗骗”小女生。现在回想起来只是一笑了之,不过不能否认,这也是一段青涩的青春记忆,一段成长的历程,回忆起来也挺美好的,并不觉得当初的阅读是浪费时间。
房子涵谷
小时候还不宽敞的家里就专门有一面墙放着巨大的摆满书的书架,密密麻麻的几百本书是父亲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读师范起就开始陆续搜集的。想来一个清寒书生,既要日常教书以养家糊口,又要挤出时间写诗、拿出积蓄置书,也是那段平凡时光中老文青的写照了。自那时起,“书原来可以作为一种收藏”的观念就在我头脑里慢慢落地发芽了,读书也成为了一种快乐。

高中开始关注龙应台,初次认识她是因为《大江大河1949》。在青春澎湃的岁月里,燃起了我内心不小的火花。历史对我而言不再是飘渺的过去,每每拜谒古迹也总多了一种“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余光中先生也很爱念这句诗)的思绪。此后陆续读了龙的多部作品,并且试着模仿她的文笔,比如写议论文仿《野火集》,写记叙文仿《目送》,写书信仿《亲爱的安德烈》。不得不说,在语文老师眼中,这种写法还真是讨喜。
等读大学后开始转移到新的兴趣点,慢慢发现龙的写法本身的确是很讨喜。她的文字总体特点是清新、文艺、温润,容易引人入胜又令人反复品味,可是重阅她的《大江大河1949》等作品却再也找不到以往那种震撼感。李敖的《大江大河骗了你》,对龙的批判或许有些用力过猛,但是龙的作品中的确充满了“堆砌故事、煽情文字、忽视大历史”这种套路感。也从这时开始,我不再关注她的作品。
2016年的《大河就是大河》基本上扭转了我对她的印象。作为一个比较倾向“找回国家”立场的政治学学生,对这类小清新的“去国家化”色彩的论调很不感冒。龙女士是个好作家,但不见得是个好的思想家;她适合去怀旧,适合去宽慰困难的人们,却不见得能够摸索到历史的规律,给予有益的启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龙女士的诸多作品——就如曾喜欢过的一些乐团和流派,只是本人某个特殊年龄时期的写照。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