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被生活困住的你啊,不要忘了向上飞行

无论人生多艰难,都要保持上扬的姿态
我们总是在日复一日中重复着自己的生活,无力感有时就像影子,悄然尾随,无法摆脱。你是否也有这种感受?好像生活被什么东西困住,总让你力不能逮,找不到出口。它可能是乏味的工作、让人疲乏的人际关系或是变换无常的环境,也可能并不是具体的事物,只是某种无能为力的感受、无法突围的困局。
新世代海外华语文学代表作家王梆的首部小说集《假装在西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锋利的生活态度,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书中的人物同样为生活所困,但却拥有一种爱莫能助的向上的冲动。他们是泥泞中的挣扎者,却拥有飞向天空的力量,他们在无望中淬炼希望,在虚无面前奋力活出自己的生机。手握倔强与坚持,成为飞向天空的孤绝的伊卡洛斯。
在全书第一篇小说《天青》中,主人公是那样脆弱,又那样不甘。他那像影子一样生存的少年时代,只有天青和她的吉他声,作为遥远而清凉的慰藉。他是怯懦的,并不敢出面维护被戏弄的天青。但天青在他心中,一直美丽而特别。
他攥紧裤袋里的弹弓,一次次地,把自己想象成护花使者,却从未出面阻止。他不怕打架,只是心里没有赢的胜算。更多的时候,他缩在一旁,用余光偷偷地瞟着她,他觉得她的雀斑挺美,配上她那乌亮的大眼睛和高高的颧骨,有一种突兀的和谐。她还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吉他,他在她窗下听到的第一首成形的曲子是《雨滴》。她仿佛在用看不见的针线,一颗颗地穿着阴天的水珠。
天青的边缘和他的卑弱就这样安静地流露出来。
天青一直不去上学,对外声称是因为身体不好需要在家休养,但因为他在一次失控下对天青的接近,她的秘密终于暴露,天青一家只得搬家。面对父亲的暴戾,他想反抗却不能。
他退缩了,他拎着羽毛球拍,迅速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不是怕挨揍,他已经挨揍挨惯了。他怕一种比皮肉之苦更深切的痛苦,从小到大,它笼罩着他,分裂着他,却不知道它是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他渐渐明白,发生在他身边的很多事情都是不对的,但他仍旧不知道,那种让他畏缩的痛苦到底是什么,他只能假设,它可能和“对错”无关。
他将自己重新锁进房间。第二天,他收到了佳瑶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他面无表情地撕掉了那张纸条。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能,不管他的外表有多酷,弹弓也好,香烟也好,喇叭裤也好,那是一块自幼生长在他体内的“不能”。如今,它已经在他的身体里钙化了。
王梆用一个个细节抓住那些孱弱的时刻、抓住生命中最真实的不甘与脆弱,用文学的悲悯描摹那些力有不逮的时刻。人性的懦弱与缺损、不被理解的青春、生命的遗憾与苦痛,都融化在故事邈远的琴声中,萦绕不去,绵长久存。
在同名篇《假装在西贡》中,“我”向认识的人“假装”自己的身份和去向,想要在他人面前自圆其说,但“我”和身边人的交集都如萍水相逢般脆弱。“我”想要在假装离开之前将自己的处女作送给朋友吉吉,却在温吞聊天后与对方告别,“把书从背囊里掏出来,顺手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筒”。和网上认识的凌志一起睡觉,却彼此都无法感觉到爱,于是浅浅相聚,又浅浅离开。随便选中一个昵称为“死神,Bleach,Skip Beat,美鸟日记”的网友聊天,对她说“我”在西贡的牧场看人为母牛接生,晚上去便宜的酒吧喝老虎啤酒。对方15岁,喜欢日本动漫,想要一只有美鸟的盾牌,“我”在凌晨仔细地为她画了一副盾牌想给她看,她却再也没有上线。
尽管屡屡挫败,但“我”却始终没有放弃与他人建立连结。在故事结尾,从“假装”中回归的“我”走出了家门:
我走到街心公园,坐在一张长椅上。远处滑梯上滑下来一个小女孩,那么小,就像玩具一样。滑下来,消失在滑梯后面,又滑下来,重复着。我拾起一块鹅卵石,放在掌中心,当作遥控器,对着那小女孩,逐渐掌握了规律。我就那么和那孩子无声地玩耍着,乏善可陈,心情平静,仿佛终于参透了某种被遥控器定格的人生。
在无声的画面中,生活就像默片般漫漫展开。“我”的“假装”就是一次对生活的冒险与实验,而作者同样用“我”的归来告诉我们:时间的波纹无法掩埋对于乏善可陈的生活的不甘。
王梆用她锐利的笔触回应着现实,读她的小说,我们可以与身边的世界建立一种有力的连接。
在她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的真实写照。《谁偷了罗马尼亚人的钱包》中在英国当按摩工的四川女孩双喜,《奶牛》中为了推销牛奶而扮演成一只奶牛走入高档小区的“她”,《鲨齿蟹》中在发廊里苦苦讨生活的“我”和红红,都是万千在外漂泊的异乡人的缩影。
尽管窘迫不易,但他们的生活并不只有苦涩。卑微中的骄傲与坚持、灰暗日子中雀跃的时刻,都是属于他们的独特光亮。王梆把这些盛满悲欢的细节一一摊开在我们面前,把生活的百感交集和盘托出。
在《奶牛》的开始:
她像往常一样,套上那件肥大的,满是卷毛的奶牛装,顶着两只粉红色的绒布牛耳,挎着一只印满订奶电话的牛奶箱,坐上长途巴士,到郊区某个新开发的别墅区推销牛奶。
而在故事结束时:
坐上末班巴士,早就过了晚饭时间。今天她没有推销掉任何一个品种的牛奶。也许明天会好一些,她看了看手腕,露出微笑。虽然这个城市对她来说只有四个月旧,它却已经是她脑海里的一张地图,印着一只只隐秘的、告别过去的出口。
她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因为一整天的推销无果而懊丧,而是露出微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相信也许明天会更好。
在《伦敦邂逅故事》中,一位高级瑜伽教练与一位场馆清洁工在伦敦邂逅。他生活优渥,从小接触古典音乐。她则来自匈牙利,是一位单亲妈妈,为了养活自己的两个孩子来伦敦打工。他们互生情愫,却又无法真正彼此接近。
在最后的分别时刻,她为他弹起自己仅会的一首钢琴曲——17岁时她怀孕了,便不能再学下去。
当琴声终于由远及近贴近他的耳畔时,他还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暮光色的梦。黑白相间的键盘渐渐不复存在,而她似乎变成了一只鸟,一只心脏中扎着针线的鸟,一只在墓园般的静寂里默默挣脱空气阻力的鸟,如此隐忍,他几乎得将整个身体伏在她的羽毛上,才能听见她的撕裂和断羽。
她的眼中渐渐噙满了眼泪,当泪珠终于涌泻而出时,她又突然变成了一只用翅膀冲击瀑布的鸟。她的羽毛和羽毛裹挟的渺小肉身一次次地消失在万丈水雾之间,又一次次地、遍体鳞伤地,带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决绝的美,俯冲到他的身前。有好几个瞬间,他似乎突然丧失了听觉的敏感性,在低音里听到的尽是山崩海啸……就连视觉也逐渐失灵,他看不到自己的衣领,看不到自己的鞋子,更看不到那一度连他自己也视为神秘的平衡点。
当她的演奏快结束时,一段贝拉·巴托克式的不谐和音,几乎把他抛回了人生的某个起点,从未有过的沮丧袭击着他发凉的膝盖。除了他和她,室内的每一双眼睛都看到了这幕无奈,虽然它们全都属于那些偶尔来过又以死亡离场的人。
这不过是一首练习曲,他的指法、技巧、娴熟度都远在她之上,但她所拥有的,成为钢琴演奏家或瑜伽大师最需要的某种潜质,他却似乎永远也无法拥有。
他那高处不胜寒的自恋与自傲,在这样一个神性的时刻被击得粉碎。而她只是平和地拥抱着自己的人生,却实现了卑微中的一次无法复刻的绽放。

寻觅人生风景,从午夜到黎明
“我并非无家可归,我的世界值得回去。我会空手而入,空手而出。”
在《女巫和猫》中,少女跨越荒野与险境,只为找到她的猫“小炭”,她将它作为铭印纹在了肩上。她坚定而执着,一遍遍确认着小炭不死的可能。隔离区和开放区是两个世界,两者间有着鲜明的穷困荒蛮与先进现代的对比,来自隔离区的她被视为女巫被带入了开放区,被人用傲慢的眼光审视着。她在这里见到了和她的小炭看起来一样的猫——DD,尽管它只是在科技操纵下的投影,从未存在过,但她仍固执地想要拥抱它,相信它就是她的小炭。她就这样怀着一种赤诚的天真,试图在这个不属于她的地方完成一次对未来的跨越。
女巫旋即也闪人了芭蕉叶中,浅蓝色睡裙被她紧致地折入大腿和小腿之间,小腿肚子看起来结实饱满,踮起的脚后跟红润光滑。她将掉到额前的头发捋到耳后,便向DD伸出了戴着电子手铐的那只手。啊,小炭,真的是你呢!她一边轻轻叫唤它的名字,一边抚摸它那黑亮温软的皮毛。缺毛的地方都长回来了呀,太好嘞!仿佛真的见到了久违的主人,它的尾梢激动地在她的脚踝上蹭了起来。舔我吧!她命令道,边将手心凑到它的下巴底下,它竟然也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舌头。它的舌头是粉红色的,像一把动情的小鬃梳,在她的手心上梳个不停。在我即将扭动电子手铐的遥控装置时,她突然一把抱起了它。
它没有挣扎,白色的爪子驯服地缩在脚掌里,小脑袋幸福地枕在她的胸前,眼中那蓝色的火焰变成了玫瑰色。她扭过头,掷给我一个胜利的、女巫的微笑。
《钩蛇与鹿》的女主人公安同样不满于现实的桎梏,她攥紧自己破碎的尊严,无数次无谓的消磨与徒劳的牺牲,仍旧无法磨灭她对自由的渴望。安和阿南这对夫妻和其他带有辐射的“病人”一样被运到废弃多年的老旧建筑中,一种叫“日程管理”的芯片,像贴身护士一样,料理着他们的住院生活。每天几点到几点,该做什么,芯片会准时向大脑发射指令。而安总是一次次试图攀爬与逃脱。安说:“悬崖,谷峰,海岸线上最高的礁石,灯塔的塔顶……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身边的处境,那是因为我们身在谷底,所以必须登高远望。”
安抬起头,在那深不可测的天穹的拱顶,无人机正定定地朝她闪耀着,仿佛在不露声色地调着光圈。尽管如此,安还是抓住了摇摇晃晃的铰链扶梯,一节节地爬了上去。这是一种向上的、爱莫能助的、破坏的冲动。她没有办法抵制这种冲动,她生命中的许多时刻,比如五岁时偷食橱柜顶上的巧克力,十三岁时尝试初吻,十六岁以后就与父母的训诫背道而驰等,都是这种冲动的产物。
这种冲动最强烈的时候,她觉得体内正在生出长尾,掌上隆起的肉垫越来越坚实,步伐也变得愈发矫健而沉稳起来。在她的身体下方,地面正在划开一个神秘而耀眼的裂口,源源不断地吐出那种海边才有的白色细沙和带刺的龙舌兰,太阳也露出红色的脸庞来了,那种她最喜欢的石榴籽的晶红。太阳在金色的晨衣里冥想片刻,便离开了云朵的坐骑,飘升起来,顺带把她也托上了半空。这让她感觉放松极了,像一枚浴火重生的箭羽,一去不返的伊卡洛斯。反正都会死,就让我在最接近太阳的地方死去吧!
同《钩蛇与鹿》一样,在《巨岛海怪》中,作者也想要通过灯塔,或者位于高处、飞逸于生活之外的事物,作为主人公的精神地标,形成一次对于绝望的突围与超越。这些突出于日常之外的事物,是生活的一块飞地,也让故事中的她们柔软而不同。
它们见证着人在深渊面前的渺小与无望,也同样标记着她们在面对宏大的无力感时微弱而固执的坚持。
《巨岛海怪》里在学校里曾是优秀的小提琴手的卓茹如今在为生计发愁,女儿佳佳同样习琴,但她却日渐无法负担高昂的费用。不止如此,失败的爱情、窘迫的生活、对女儿无望的爱、让人倍感不适却又无法拒绝的求爱都将她紧紧包围,无法呼吸。
然而在故事最后,佳佳当众向正在演奏的王茜的女儿嬅嬅丢香蕉皮,让局面变得慌乱而狼狈,但卓茹却不忍责怪女儿,因为佳佳是为了她而生气。在回去的公交车上,母女紧紧依偎,台风悄然止息。而回去后,佳佳依然满怀热情地向母亲证明着她所标记的灯塔的移动。

电影《正常人》剧照
当风雨来临时,“灯塔底下一个小孩都没有,除了佳佳”。尽管生活一地狼藉,卓茹还幸运地拥有佳佳,这个由她创造,却又完全独立于她的生命。在佳佳笃定认为移动的灯塔下,生活的裂缝魔幻现形,而当中恰好深藏着她一直寻觅的人生风景,从午夜一直到黎明。
一股被拥抱的渴望,突然变得如此迫切……她想念女儿顽强的小身体,她非凡的胎记,她那韭菜莲的坚韧,她那小皮鼓似的,张弛有力的心跳。
扑通,扑通……
她想念被那只小皮鼓定义的时间——那些美好的时光。
美好的时光,曾经如此沉实具体,就像石头一样,可一旦化成回忆这种模棱两可的语言,便瞬间失去了重量。当卓茹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时,母女俩已经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了。佳佳的小脑袋依偎在卓茹的肩膀上,卓茹的双手被佳佳紧紧捂在怀里。台风突然平息了,像一只筋疲力尽的巨鲸,拖着两片肥厚的大叶尾,沉入遥远的海平线。城市在疲惫中睡去,只有母女俩的脚步声,均匀有致地敲在小巷石板上。
“妈妈,灯塔真的在移动,不信你看……”临上楼前,卓茹被佳佳拉到了灯塔底下。
灯塔早已偏移了用饼干盒画下的一个个方形记号,它四周的水泥地面,还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条条裂缝,有的裂缝甚至有蟒蛇那么粗。一只嘴巴很长,长得像海马似的老鼠,鬼鬼祟祟地溜到佳佳的脚边,纵深一跃,便跳进裂缝里了。卓茹被这个现象吓了一跳,但很快恢复了镇定。佳佳看上去比卓茹更镇定,她捡起一根断成两截的晒衣杆,走到一条裂缝旁边,弯下腰,缓缓地,将晒衣杆直挺挺地捅了进去,越捅越深,仿佛捅进了一道云间罅隙,剩下最后一小截,一不留神,从佳佳手中挣脱出来,眨眼就被裂缝吃掉了。母女俩不约而同地趴在裂缝两侧,伸长脖子,朝内望去。
裂缝里的世界,先是一片漆黑,看得越久,就越具体起来,像是夜空,又像一片墨蓝色的大海。浪花卷起微凉的晚风,海面上漂过一朵朵灰云,灰云被灯塔那飘忽不定的白色倒影追逐着,追啊追啊,从午夜一直到黎明。
王梆 |《假装在西贡》|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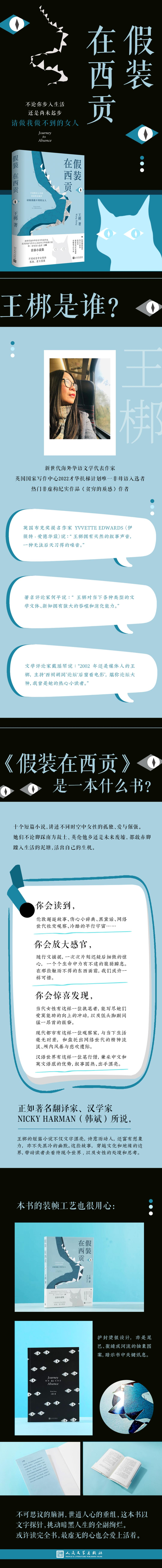
原标题:《被生活困住的你啊,不要忘了向上飞行》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