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个艾滋病人,消失在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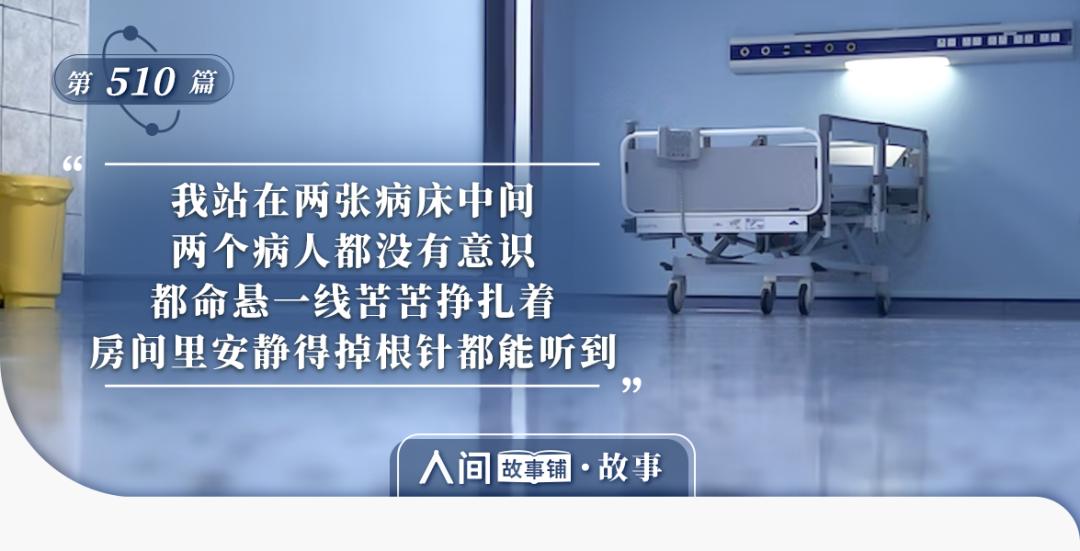
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但在医院这个场景下却屡见不鲜。每间几平方的病房内,充斥着不同浓度的痛苦,有人明天就能痊愈出院,有人却从此一病不起。
病床上全力抢救、痛苦挣扎的痕迹,清扫过后便消失不见。当时间匆匆流过,还会有人记得曾经有个患者在这里和命运斗争过吗?
1
午间1点多的阳光照得人昏昏欲睡,连值班的同事都抵挡不住困意跑去隔壁休息室躺下了。因为下午有个病号要办理出院,我早早来到了科室准备手续。
慵懒的风透过窗户缝飘进了办公室,吹得一沓资料哗啦作响,又很快安静下来。鬼使神差地,我在住院系统上又一次搜索了李灿的名字。
电脑上显示他的最新住院记录是半个月前。
我左手把保温杯递到嘴边,右手轻点鼠标,各项住院文书在屏幕右侧展开。
会不会还没出院呢?我漫不经心地想着。
仰头喝水的间隙,眼睛不经意瞥了一下屏幕,最后一行死亡记录猝不及防闯入视线,我刚喝下去的温水此刻就好像带着冰锥一样随着我的血液流遍全身,痛得我五内俱崩,动弹不得。
我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为他已经好了的。
2
第一次见他是在大半年前,彼时我正在感染科轮转。
初春的天还是冷得彻骨,刚出电梯眼镜就结了一层雾。办公室里传来悲怆的哭诉声,在临床待了大半年,这种场面我已经见怪不怪了。顺手掀开白大褂用里面的毛衣蹭了蹭眼镜,我走进了办公室。
一个比我妈稍年长的妇女此刻就坐在主任身旁,哭得鼻涕眼泪连着头发都黏在脸上。
主任向我使了个眼神,我心领神会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阻绝了外面病房走廊上探头探脑的病号们好奇的目光。
我自觉坐到离两人最远的电脑旁开始写病程,但办公室太小了,即使我刻意忽略,声音还是断断续续飘到了我的耳朵里,“怪不得他从来不谈对象……之前跟他一块回家的那个男孩……我一提他就跟我生气……”接着是一阵震人心魄的哭号:“他还那么小,你们一定要救救他呀,求求你们了医生。”
我拉住恰好路过的值班医生,小声询问:“什么病呀?”
值班医生小心地回头瞅了瞅哭得几乎要晕过去的那名妇女,贴近我耳边几乎用气声回答了我:
“艾滋病。”
我猛地抬头对上她意味深长的眼神,在她的瞳孔里看到了我自己吃惊的表情。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及科普的开展,艾滋病被越来越多人了解并接受,这个病在我们科也算得上常见病。刚入科室,主任就给我们讲解了两个艾滋病的典型病例,现在这两个ppt仍在示教室大电脑上挂着。
第一个病例是本地的男大学生,因某次不洁同性性行为不幸感染,转至我院时已是昏迷状态,虽经积极抢救仍无力回天,当天就因呼吸衰竭去世了。
第二个病例是50多岁的公务员,姓徐,已有家室,得病途径被主任含糊带过。
“二十多年啦,不是我说,我就是把人喊过来站到你们面前,你们也猜不到人家老徐有这病。”主任咂咂嘴,满脸骄傲,乜了我一眼,“说不定体能比你们这些天天不运动的小年轻还好。”
当年的主任还不是主任,是个跟我一样的青瓜蛋子,当年的人们还没那么包容,听到艾滋病恨不得给自己耳朵消个毒。主任顶着巨大压力收治了这个艾滋病人,谁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人还好好的。
二十余年弹指间,老徐也见证了主任从半吊子住院医到科室扛把子的升级打怪过程。
我在感染科的轮转计划只有一个月,而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我每天接触到的只有各种肝病患者。
主任也不止一次感慨,自从疫情暴发后每个人出门都戴口罩,也不聚集了。每年这个时候病房里应该住满了患流感的小孩,现在竟一个也没有了。往年把病房加床都住满的手足口病患者今年夏季也只收了三四个,各类呼吸道感染患者数量急剧下降,病房现在能收的病种着实单一。
此刻病房里突然出现一个艾滋病患者,宛如在平静湖面掷入一颗巨石,震得每个人都心潮澎湃。
第二天恰好是我跟张姐值班。
结束一天的忙碌,我和张姐刚坐下打开餐盒准备吃两口饭,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逐渐清晰,我和张姐对视一眼:这饭是吃不踏实了。
“医生,小灿说头疼得厉害,你们去看看吧。”满脸沧桑的妇女此刻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焦急地说道。
“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就过去。”我起身把凳子拉开,去护士站拿了一副消毒过的听诊器。
病人在5号房26床。虽然整个科室病房早已人满为患,加床都已经加到厕所门口,但是这间双人间只住了他自己。
我们医院坐落在某农业大省十八线小县城里,弹丸之地,宗亲友邻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生活几年,不夸张地说,走几步路就能碰到认识的人。手机发通知还要传播一阵,把消息随便告诉一个坐在路边的大娘,不一会儿整个县城就传遍了。
流言蜚语比疾病更能快速杀死一个人。

昨天在关上门的办公室里,我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中拼凑出了这个病人的基本情况。
病人名叫李灿,男性,今年三十一岁。在我们本省一所颇有名气的本科院校毕业后就入职了省会的某医药公司,从事推销工作。像所有为了梦想奋斗的年轻人那样,朝九晚五,偶尔加班,不那么忙的时候还会去健身房泡上大半天;喜欢玩游戏,吃饭靠点外卖,熬夜更是常态,但好在年轻,身体几乎没出过什么问题,一年到头可能只会因为失眠而踏入医院。
他家庭条件一般,父亲在工地打工,只在农忙和过年时才回来几天,母亲留在老家种地,还要照顾家里的4个老人,上面还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姐姐,早已结婚生子,而他本人目前还是单身。
他的家庭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村家庭的缩影,他自己也是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唯一不同的是,入院文书里记录他本人承认有嫖娼史。
这或许就是他得病的原因。
在办公室里大家提到他语气里不无嫌弃,又很八卦地问李灿的主管医生他长什么样子。
李灿的主管医生跟我一样,刚刚参加工作,很认真地想了一下,仰着脸回答:“我觉得长得还可以吧。”办公室里大家哄堂大笑。
到了病床前见到李灿,说实话,他长得比我想象的要秀气很多。
他皮肤很白,眉毛是认真修剪过的形状,长长的睫毛随闭眼的动作细微颤抖着,鼻子小巧而耸立,下唇比上唇稍厚一些,此刻上面布满了皴裂的死皮。乍一看竟感觉有些像女孩。
“李灿,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我站到病床一侧,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李灿极其缓慢地抬起了似有千斤重的眼皮,眼睛里血丝纵横交错,眼球感觉也稍稍突出了点。他认真打量着我,好像要看清我是谁一样。
见他不说话,我又问了一遍。没想到他竟缓缓地把眼睛闭上了。
“刚才,他一个劲哭着说头疼,用手抓自己的头。”李灿妈妈粗糙的手穿过自己的发丝使劲抓了几下,“就像这样,一直说疼,太疼了,我赶紧去喊你们了。”
我们医院并不是李灿此次发病的首诊医院。在他带来的病历资料里显示,一周前他因头痛、发热前往省医就诊,住院行核磁提示脑膜炎,腰椎穿刺术示颅压升高明显——这就是他头痛的原因,此外脑脊液里验出新型隐球菌阳性,抽血检查回示HIV抗体及梅毒抗体初筛阳性,CD4细胞明显下降。
上面这些结果都指向了艾滋病的可能。
确诊艾滋病需要抽血送往疾控中心,他们在省医只住了三天就办理了自动出院,还没来得及做这项检查,紧接着就回到了位于老家的我们医院。昨日主任就已经安排人抽血送检,具体结果大约要等一周。
“我觉得我脑子都不转圈了。”躺在床上的李灿突然冒出没头没尾的一句话。
“你说什么?”我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与他的眼睛平齐。
“我说,我觉得我的脑子好像不转圈了。”他复述了一遍,像个生闷气的小孩一样声音里带了点抱怨。
“1000减3等于多少?”我笑着问他。
他嘴里重复着我问他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很费力地想了想:“997。”
“还行嘛。”我夸他,“再减3呢?”
“994。”这次回答快了很多,他抿着嘴笑了,颧骨随着笑容的扩大高高耸立着,我才意识到他竟然这么瘦。
“小灿,吃点东西吧。”李灿妈妈不知道从哪抱出一大罐黄桃罐头,殷勤地递到他嘴边,李灿只抿了一下就不肯吃了。
“怎么只吃这个啊,没什么营养。肉啊、菜啊,都是可以吃的,他不用忌嘴的。”我瞥了一眼那黄桃罐头就知道是在附近超市买的,便宜大碗,里面不知道加了多少甜蜜素,一口下去齁死人。
李灿妈妈摇了摇头:”他不肯吃。主任跟他说过几次让他多吃点饭,他一口都不吃。”
李灿又闭上了眼睛,这是逃避的姿态。
李灿妈妈叹了口气,把罐头小心放到旁边桌子上,揉了揉眼睛:“他从小到大一直都特别爱吃黄桃罐头,我这次特地给他买了一罐,偶尔有胃口了他还能吃两口,其他什么他都不肯吃。”
说着说着李灿妈妈又要哭了。
“我小时候也爱吃黄桃罐头。”我试图缓和气氛,“我妈说那时候穷,一年吃不了几次,我每次把黄桃吃完还要抱着罐子把里面的甜水喝干净,然后齁得接下来几天看见甜的就摆手。”
我作势摆了摆手:“现在不行了,黄桃我都吃不下去了,甜得我想打胰岛素。”
阿姨笑了,李灿虽然仍闭着眼,但我看见他把头扭到一边笑得被子都在颤抖。
我出去的时候阿姨跟了过来,把我拽进了开水间了,张口还没说话,眼泪就先下来了。
阿姨的年纪比我妈妈大不了多少,看得我心里难受得很。
“医生,我是个农村人,我也不懂,但是人家都说得这个病一定会死,是不是啊?”提到这个敏感的字眼,阿姨的情绪像是被打开阀门的水龙头一下迸发出来,还得顾忌着走廊加床病号的情绪,压低声音捂着嘴呜呜咽咽地哭开了。
“不不不,您不能这么想。”我适时地递上了纸巾,“我们病区每个月都要收上几个这种病人,只要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按时复诊,活几十年的也大有人在呢。”
老徐的身影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一刻是真想感谢老徐,给了我说话的底气。
“真的吗?我都不懂,医生,你们只管治,钱我去想办法,砸锅卖铁我也得把小灿的病治好。”阿姨本来情绪都快好起来了,不知道想到什么又哭开了,“你都不知道,我恨啊,我恨我自己。小灿一星期前就跟我说了他发烧、头痛,我没在意,我那时候为什么不劝劝他早点来医院看看呢,如果我知道会是这病,我一定早早让他来医院检查......”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这种固有思维在临床上已经是常态了。病人家属往往先是表现出不相信:人平时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了?继而就是后悔:为什么我平时没注意到呢?为什么没早点来医院呢?最后就是开始接受并认命。
对旁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个故事。然而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个中滋味有多煎熬,每一秒,都在做无数斗争。
李灿的症状虽然是这一周才开始表现出来,但按照艾滋病的普遍潜伏期计算,他染上病毒起码也得是出现症状的半个月前发生的事了。
阿姨是无辜的,罪魁祸首是那个传播艾滋病病毒的人,可眼下李灿对此事守口如瓶,我们也没有立场去报警或者追踪源头。
可怜天下父母心。
安慰好了阿姨,我揣着满腹心事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值班室。
这一夜,风平浪静,我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下夜班,我打开社交软件,在某个粉丝很多的博主那留言有没有好吃的黄桃罐头可以推荐一下,我想送给患者。
出乎意料的是我收到了一百多条回复。本着货比三家的心态看完评论,我精挑细选地在购物软件上买了一箱黄桃罐头。
眼看着五天过去,物流一点点更新,黄桃罐头即将要派件了,李灿却出事了。
3
其实李灿的状态一直都很不稳定,每个值班的医生早晨交完班都要抱怨几句李灿整晚都在因为头痛大喊大叫,搞得夜班人员一直都在仰卧起坐——刚躺下就得立刻弹起来看病人情况。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另一个组的肝硬化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心电监护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护士长推着抢救车在狭窄逼仄的走廊里走得飞快,主任又从急诊带过来了一个因去私人医院做流产手术导致大出血突发失血性休克的年轻女患者,整个病区忙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
女病号要抢救,肯定是不能住走廊的。但是病房已经全都住满了。
除了李灿那个房间。
这个时候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抢救病人要紧。
女病人被七手八脚地抬到床上,主任把病人家属叫过去询问情况,正好轮到我收病号,上级医师安排我守在女病号床边,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隔五分钟量一次血压。
门被关上了。女病人躺在床上,整个人泛着一层诡异的苍白,翻开眼睑没有一点血色,手指尖也白得发青,皮肤摸着像蛇一样冰凉,让人无端地从心底升出凉意。血压量了几次都低得吓人,胳膊上开了好几个输液管道,挂着生理盐水的那个输液器开关全都放开了,里面的液体就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样一股股往血管里灌。

这个时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就是生命。不把握时机快点把血容量补上去,她年轻的肌体可能永远暖不热了。
本来正在沉睡的李灿突然醒了过来,大声哭叫着,不顾手上的针头去抓自己的头发,并使劲捶打自己的头部,整个人都在这张小小的病床上剧烈挣扎着。
镇静剂药效过了,病毒感染上行到了脑部,出现了剧烈的头痛,短短几天就把他折磨得面目全非。
我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使劲按在床上,防止他进一步伤害自己。李灿妈妈站在旁边,佝偻着腰,拿手背默默擦着泪。
“李灿,别动了,一会儿就好了。”我没有松开他的手,一直在试图安抚他。后来想想,其实没用的。脑膜炎加上大剂量镇静剂使他一直处于混混沌沌意识不清的状态,那时候应该已经是感知不到外面的声音了。
但没想到李灿竟然真的慢慢安静了下来。他的手反握住了我的手,住院期间疏于修剪的指甲在我手背上划出了几个小月牙。
疾控中心已经把李灿的结果发了过来,确诊就是艾滋病,由此引发的脑膜炎也格外棘手,长期高颅压使得他双眼眼球凸出,刚开始还不太明显,这两天已经彻底闭不上眼睛了。请眼科医生会诊后也无计可施,只能用些保持眼结膜湿润的眼药水。
他现在瞪大着眼睛躺在那里又陷入昏睡的状态,如果不是心电监护上还在显示着连绵不断此起彼伏的曲线,看起来与去世的人毫无两样。
我慢慢抽出了我的手,女病号的血压又该量了。
血压还是没上来,女病号刚开始被抬上来时还能嘟囔一句“别碰我”,这下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一点生气也没有了。
我站在两个床中间。两个病人都没有意识,都命悬一线苦苦挣扎着,房间里安静地掉根针都能听到。我的心堵得难受,堵得我眼睛发酸。
我在心里不断哀求主任快点谈完话,把病号家属放回来,把我叫走。
门就在这时候被推开了。我惊喜地抬起头却发现是对面病房的床被推了出来,走廊太窄了得从我们病房借道掉头。
“怎么了,小王。”我拉住从对面出来的同事,他表情凝重,看起来很不好。
“病人家属放弃抢救了,让留着一口气回到家就行。”小王小声丢下这句话就走了。
我的心情更沉重了。
到临床上我才知道很少有病号直接死在医院里,除非是突发疾病来不及抢救。人们还是信奉落叶归根,对医院最后一个要求就是吊着一口气保证病人能在弥留之际回到家里。家属往往趁着患者身体还软热,慌乱地把提前准备好或者临时买的寿衣套上,再塞进医院联系好的车,一路疾驰回家。
在这个过程里,我见过哭天抢地悲痛得几乎晕过去的家属;也见过一言不发冷静安排相关事宜最后走的时候还记得把门带上的家属;也不乏听见医生隐晦暗示抢救没多大意义时面部扬起笑意又赶紧压下,最后干嚎几声拼命想挤出眼泪导致整个面容狰狞的家属。
医院是面浮世镜。每个人看到的自己都是赤裸裸的。
“小灿,小灿,你怎么了......”李灿妈妈惊慌地喊叫声像一只无形的手把我的心使劲攥了一下又提了上去。
我冲到床边时,李灿全身紧绷着,头和腿向下使劲弯曲着,而胸脯却像被一个无形的钩锁勾着向上使劲吊,他整个人以一个诡异的姿态在床上扭曲、抽搐着。
是角弓反张!我在临床上还是第一次见到,竟跟教科书上描述得一模一样。
这意味着脑膜炎还是在进展。
“快去办公室把主任叫过来!”我不能离开病房,这个时候必须得保证有医生在场,防止出现意外。
李灿妈妈慌慌张张推门而去,我试图再次握起李灿的手,却发现因为肌肉强直,他的双手紧紧贴着床单怎么也抬不起来。
主任很快来了,只看了一眼,就让我立刻去联系重症监护室。
李灿刚入院就被下了病危通知书,主任跟李灿妈妈提过两次转重症监护室治疗的想法,都被李灿妈妈拒绝了。
老徐的成功给了主任莫大的信心,即使他不说我们也都清楚,每次遇见艾滋病病人,主任总是比以往更充满活力一些,毕竟艾滋病也算不治之症,看着一个病人在自己的医治下生龙活虎了二十多年,无论对哪个医生来说都是莫大的成就。
老徐已经不是老徐了,他是主任这辈子最大的招牌,行走的活招牌。
所以在李灿妈妈拒绝转科时,主任也没坚持,每次都只是让签了个拒绝转科知情同意书就算了。
但老徐的成功并不是那么容易复刻。这次,主任应该是下定决心要让李灿转重症监护室了。
重症监护室相比较于普通病房只有两点不好。一是不能留陪护,病人进去后所有的情况只能等医生查完房后那一小会谈话时间才能知晓,家属也无法知道病人在里面是什么状态;二是经济原因,这是每个患者家属都躲不过的一座大山,不夸张地说,在重症监护室里,每一口呼吸都在燃烧人民币。
李灿妈妈当初放弃资源、医疗水平更优越的省医来到我们医院,很大可能就是因为经济原因,毕竟在老家能报销更多。可这次不一样,阎王在后面穷追不舍,钩子眼看就要拉到人了,命还能用钱续已经是万幸了。
李灿被重症监护室的人拉走时,我正坐在电脑旁把键盘敲得噼里啪啦作响。失血性休克的女病号也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光是入院沟通我就要建十几个,入院大病历还没写,想想就觉得头都要炸了。
等我忙完一切去病房找女病号家属签字时,李灿的床位已经空了。一些来不及带走的生活用品散落一地。再过一会儿就会有保洁阿姨过来将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所有痕迹抹去,仿佛这里从来不存在过一个苦苦挣扎着的年轻人。

下班后我从快递驿站取回了那箱黄桃罐头,很沉,压得我喘不过气。
4
接下来的时间过得飞快。女病号比李灿幸运得多,当天血压就慢慢上来了,没过两天就停掉了病危。住满一个星期后,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待在医院,闹着说自己没事了,要回家,医院没有权利限制她的自由。
主任摆摆手,我拿出打印好的自动出院告知书,家属在上面用花体字潇洒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两个人走的时候还在商量着去哪儿吃大餐。
主任嘱咐我把这个病人的出院记录写写,弄完后就可以下班了,不要总是加班。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主任叹了口气:“哎,主任也不好当呐,一会儿开完会我还得去会个诊才能下班。”
最后我还是没能提前走,因为主任去会诊的病人正是李灿。他又要转回我们科室了。
我厚着脸皮问主任要下了李灿,主任十分高兴,在办公室夸了我好一会儿,说在我身上看到了他当年的影子之类的话。
我很不好意思,尴尬得脸都红了,毕竟我是存了自己的私心才想接管李灿的。
那箱黄桃罐头我还是想送给他。
李灿这次被推进病房时状态比进重症监护室时好了很多。他转科后我每天都会在系统上搜索他的住院号,看看他在重症监护室的情况,病程记录里提到他慢慢恢复了意识,虽然每天都还是昏昏沉沉的状态,还是不愿意吃饭,头痛起来还是会暴躁痛哭,但总归是在朝着好转的方向前进。
他的眼球凸起得更厉害了,眼睛一直睁着,所以无法判断他到底是清醒状态还是在睡眠中。我蹲下来轻轻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告诉他,他又回来了。
他的头很细微地动了一下,喉咙里咕哝了一声,我凑近听了听,他在说:“我还记得你。”
老天爷,我觉得我的眼泪都快忍不住了。
李灿很快又睡去了。
寝室里堆放的那箱黄桃罐头自打我抱回去就引起了室友的好奇,我不好意思说是给患者买的,随便找了个理由含糊带过。只有我从高中玩到现在的几个好朋友知道这件事,但她们都不赞成我送李灿黄桃罐头。原因就一个:万一李灿再出什么事,家属把原因归到是因为吃下送的这箱罐头上怎么办?
这番话无疑是在寒冷的冬天给我泼了一大盆凉水,也让我从盲目的冲动里清醒过来。虽然不能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但医患纠纷也是横亘在每一个医生面前的一座大山。对于我这种还没经历过社会毒打的年轻医生,这样的医患纠纷来一次就足以断送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纠结了两天,眼看明天就要出科去新的科室了,我还是把罐头塞进了我上班背的包里,打算下午下班时大家都走了我再送给李灿。我计划了这么久,还是不想放弃,而且我觉得吃个罐头而已,不会出什么事的,况且李灿还不一定接受我的好意呢。
下午我背着一大包罐头溜进值班室,做贼似地塞进了柜子里。出科前的交接工作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病程也都已经完善,现在就等着下班了。
等我在值班室坐得腰痛腿麻打算去走廊转转时,刚推开门我就听见李灿痛苦的吼叫声和他妈妈的哭喊声,他的病房前放着的赫然是一辆抢救推车!
我的心一瞬间提了起来,我真后悔过去的那一个小时里我都躲在值班室里玩手机而不是去看看病人的情况!
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一个小时里他又出现了上次转科前的情况,甚至更严重,主任请了神经内科和重症监护室会诊后一致决定还是转往重症监护室。
我飞快地跑进了病房,主任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我心里有些惴惴不安和绝望,出科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我犯了这个月最大的错。
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还是像上次一样留在病房观察病人情况,会诊申请单还有转科需要的手续已经有其他医生替我在办了。我羞愧地点了点头。
不同于上一次的安静,李灿这次尤其狂躁,大概头得厉害,他开始不断地用头撞墙,嘴里发出类似于野兽临死前的嘶吼声,李灿妈妈在一旁吓得惊声尖叫着。我们普通病房是没有约束带的,我只能跪在床上拼命按住他,他的口水全都喷在了我的白大褂上。
“为什么还不转到重症监护室,你们是什么黑心医院,命重要还是手续重要,天天让我签字、签字,签的都是什么啊!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转走?还说一会儿让我签了字才能转科,拿来啊,我签,我什么都签!除了让签字你们这些医生还能做什么!”李灿妈妈站在我旁边撕心裂肺地朝我吼着,我听见我的心底慢慢有什么东西裂掉了。
李灿妈妈什么也不懂,她只知道转重症监护室会让她的儿子不那么痛苦。
李灿大概是没有力气了,过了一会儿又安静下来,还是瞪着眼睛,胸廓微微起伏着。李灿妈妈也仿佛卸下了全身的力气,跪坐在李灿床边,哭着一直喊他的名字,抬起一只手轻轻抚摸着他闭不上的眼睛,嘴里念叨着:“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啊?小灿,你太辛苦了,你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
李灿是听不到的,即使听到,他的眼睛也是闭不上的。我的眼泪默默滑入了口罩里。
主任喊来了两个男同事帮忙把李灿推到重症监护室,我拉住车的边缘也跟着去了,主任在后面喊我,说两个医生跟着就行了,我就不用去了。我固执地攥紧床沿没有松手。主任也没有再喊我了。
从我踏入重症监护室那一刻,全程没有一个人说话,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压抑得都想要尖叫了。

我们走的时候正准备把鞋套脱下扔进垃圾桶,就听见身后传来护士惊讶的声音:“呀,他排大便了。”
我回过头,李灿不着一物的身下,一滩稀薄的排泄物正在白色床单上蔓延。
5
那些罐头被我原封不动背回了寝室,直到过期都没再碰过。
第二天我就去了新的科室,接管了其他病人。但每天在系统上搜索李灿的名字已经成为我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这次恢复得尤为缓慢,都快一个星期了,还是昏迷状态。但好在,病情没有恶化,家属也没有放弃治疗。
又过了一周,李灿又转回了感染科。
我没有回去看他。当时那种狂热的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李灿妈妈最后说的那段话到底是她这段时间压抑在心底的真情实感还是情绪激动下宣泄的产物我不得而知,但每次回想起来仍觉得委屈无助。
去看了又怎么样,我又不是他的主管医生,不能让他的病情好转,更不能让他医药费便宜一毛钱,说不定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了。我在心里暗示自己。
其实我知道,我还是害怕了,在找借口给自己一个慰藉。
李灿没多久就出院了,后来他因复诊、头疼复发又过来住了几次院,在这半年里我已经轮转了三个科室,但定期在系统上搜索李灿的名字仿佛已经形成肌肉记忆,成为我在每一个科的习惯。
我颤抖着手点开死亡记录,最后一行落款时间赫然是昨天。
悲痛与悔恨如潮水般席卷了我,使我动弹不得。
我昨天做了什么?日复一日地医院、寝室、食堂三点一线。最近很忙吗,还好吧,这个科室也没有忙到让人脚不沾地,所以为什么我昨天不顺手搜索一下他的名字呢,像过去大半年里无数次那样。那样的话,我是不是还能过去看他最后一眼,再握一次他的手,告诉他有个人一直在惦记着他,所以他也千万不要放弃啊。

我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默默流着眼泪看完了他这次住院所有病程记录。
这次入院第二天就出现神志不清、双侧瞳孔不等大、叹息样呼吸等濒死病人的症状,但所幸经过抢救暂时稳定了病情。后来的几天里他一直都是高热状态,每天的病程里都提及病人家属拒绝转重症监护室并自愿承担一切不良后果,后面括号里写的是包括病人死亡。
在此之前,李灿妈妈就因为经济原因终止了一次治疗,办理了自动出院带李灿回了家。自那以后,李灿就一直处于失明、失聪状态。
谁有资格去指责这个可怜的母亲呢,自李灿入院,一直是他的母亲在照顾着他。如果没有经济压力的话,谁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意气风发前途光明的儿子如今只能躺在床上,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痛得厉害时候不管不顾地吼叫、用头撞墙。
病程记录终止于这次入院的第九天,抢救记录里记载李灿那天再次出现叹息样呼吸,心音微弱,血压极低,李灿妈妈拒绝心肺复苏及其他相关抢救措施及药物应用,在二十分钟后,李灿呼吸及心跳停止,心电图回示心脏静止,医生宣布临床死亡。
我不敢去想,李灿妈妈做了多久的思想斗争最后才下了放弃抢救的决定,也不忍心去想,在这最后二十分钟里,她是以怎样的心情自己一个人陪伴着随时可能死亡的李灿走完了人生路上最后短短的一程。
在两点半上班前我办完了病号的出院手续,并给主任发了消息请了一下午的假。在空无一人的寝室我哭到头痛,想起李灿在病房几乎没有安稳过,头痛得撞墙时眼泪更止不住了,李灿走的时候头还在痛吗,人们都说会有回光返照,那他是不是跟妈妈告别了呢。
李灿曾经也是一个鲜活的人,或许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抱怨工作,吐槽领导,有喜欢的人、爱吃的零食。某一天,他突然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社交软件再也不更新,其他人给他发出的消息也石沉大海,全无音信。
一个月,两个月,曾经那些身边的人会觉得他是去旅游了?或者重新换了个工作?可谁能想到他会在一个十八线小县城里蓬头垢面地躺在病床上,意识模糊、失明失聪、全身插满管子、大小便失禁、双眼凸出再也闭不上呢。
天堂没有重症监护室,希望李灿在另一个世界有永远吃不完的黄桃罐头。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题图 | 图片来自《神之手》
配图 | 文中配图均来源网络
(本文系“人间故事铺”独家首发,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原标题:《一个艾滋病人,消失在秋天》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