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张杨评《世界帝国史》︱帝国的死与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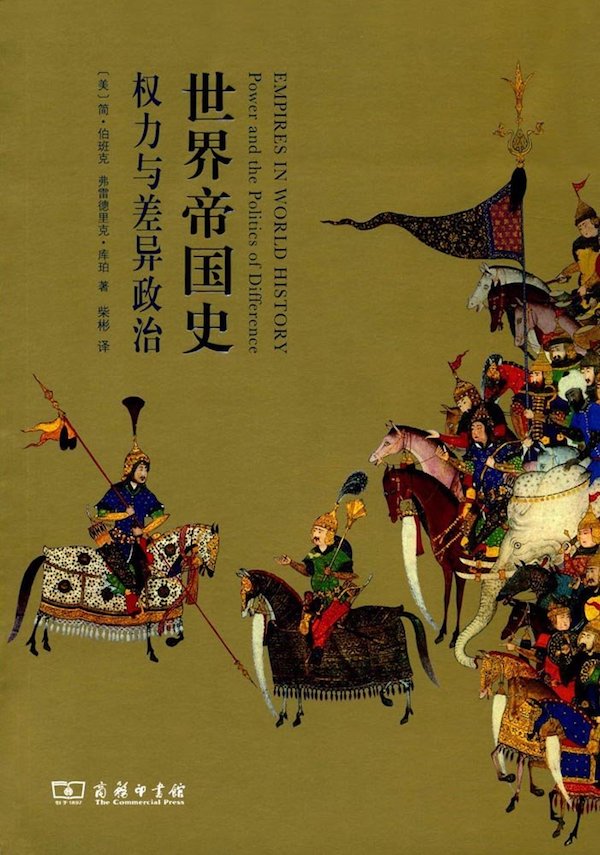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帝国是时间持续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内部差异最大、组织力量最强、影响人群最多的统治形式。今天,生活在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中,我们已经习惯把民族国家视为(唯一)合理、正当、自然的国家模式,而将帝国看作不合时宜的历史古董。可是,帝国只是历史的遗迹吗?它们是不是仅仅剩下残垣断壁,让我们只能同爱德华·吉本一样登罗马而发思古之幽情?如果它真的已经寿终正寝,数千年的帝国史还留下了什么智慧和教训吗?
美国历史学家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2010年合著出版的《世界历史上的诸帝国:权力和差异的政治》(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就旨在纵览古今帝国的兴衰演变。这本书体例宏大、跨越时空,贯穿从古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两千多年历史,论及拜占庭帝国、卡洛林帝国、伊斯兰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欧洲现代殖民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美利坚帝国等数十个帝国。两位作者虽然都是历史学家,但对历史社会科学的概念却信手拈来。在美国分类严明的学术出版体系中,这本书的风格介于专著(monograph)和教材(textbook)之间:它看似教材,但每一章内容的深度却又远在一般教材之上。此书在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大获好评,既获得了2011年世界史学会年度图书奖这样的专业性奖项,也在关于帝国的历史学和历史社会科学课程上被广泛选用为指定教材。现在,中文读者也有了两个中译本的选择:台湾出版的《世界帝国二千年》(冯奕达译,2015)和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帝国史》(柴彬译,2017,后文用此版译名、页码)。

这本书开阔的视野和独特的风格与两位作者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伯班克和库珀是一对学术伉俪,现在都执教于纽约大学历史学系。该书即肇始于两位作者在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共同开设的一门“帝国与政治想象”课程。这两人中,伯班克是研究俄罗斯帝国的知名历史学家;库珀以对法属非洲殖民地研究见长,但又猎涉广泛,作品跨越学科:他的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2005)一书是后殖民研究的重要作品;他与社会学家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2000年合作发表在Theory and Society杂志上的Beyond “Identity”一文,是过去十几年里影响最大、引用最多的社会科学理论文章之一;在出版《世界帝国史》一书后,库珀笔锋未减,又完成了一部研究法属非洲去殖民地化运动中民族形成和公民权建构的专著,同样广受赞誉。这些无疑都奠定了《世界帝国史》一书历史与理论兼具、视野与叙述俱佳的基础。
作者似乎有意回避像社会科学家那样用一个覆盖型的概念或理论来统率全书,但通览全书,可以发现两个核心词:“帝国的武库”(Imperial Repertoires或Repertoires of Rule)(第7页),以及“帝国的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Empire)(20页)。不难看出,这两个概念受到查尔斯·蒂利在抗争政治研究中情有独钟的“集体行动的剧目”(Repertoires of Collective Action)和“抗争的动力学”(Dynamics of Contention)的影响。首先,正如蒂利追溯了欧洲近现代以来集体行动的剧目创新,《世界帝国史》亦运用“帝国的武库”这一概念,在各章节突出强调不同帝国在特定时空中具有想象力和操作性的统治策略,并将这些统治策略置于同时代诸帝国竞争冲突的权力网络中。在作者看来,帝国能够持久统治不仅仅是因为其规模优势,更在于能够因应变化而在统治技术上推陈出新。

Dynamics of Contention
第二个关键概念则是“帝国的动力学”,而且是复数意义上的动力学(商务版翻译为“帝国的诸动力”)。帝国的动力学与帝国的武库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帝国统治策略的创新从来不是无中生有,而往往来自于竞争推动的观念和技术创新,以及权力冲突带来的挑战。这种竞争不仅仅是来自于同时代的其它帝国,而且还来自非政治领域的组织性力量:比如宗教,特别是一神教与帝国的联合、冲突和分化,以及近现代欧洲在经济组织方式上的一系列革命。同时,这些变革对帝国所造成的影响往往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无心插柳——亦即社会学意义上的非意图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比如,近代欧洲的海外殖民地扩张,就是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地中海贸易通道而导致的偶然结果。一言以蔽之,帝国的兴衰更替是诸帝国斗争的结果,以及与其他新兴社会力量竞争、重组和结晶的产物。这里,在“帝国的动力学”背后除了有蒂利的影响,还可以隐隐看到另一位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影响: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指出,重大的社会变迁往往来自于多重重叠和交错,但从未闭合的权力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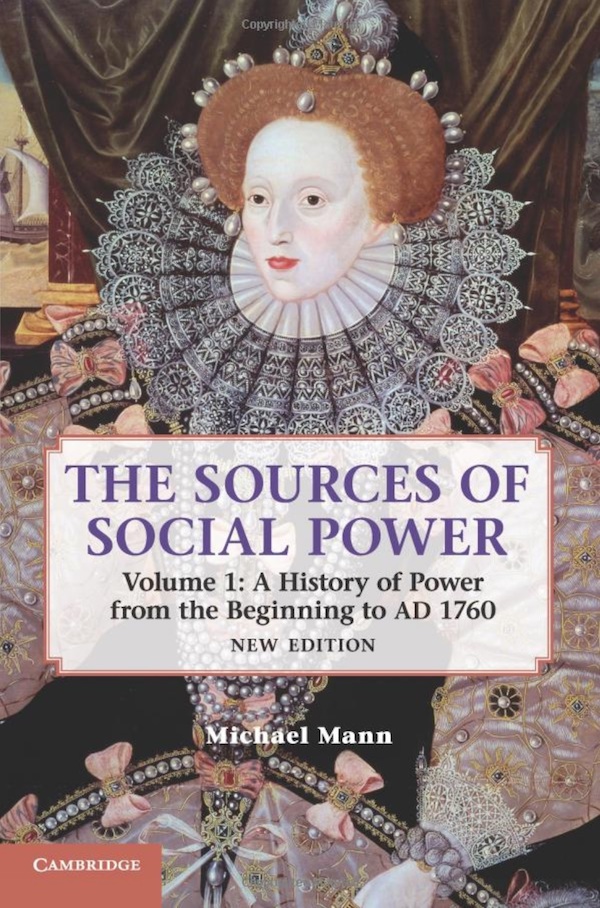
除了这两个概念,作者特别希望纠正的是传统历史叙事和主流社会科学对帝国和民族国家关系的认识——这也是全书近现代部分的一条最重要的主线。正如作者所言,传统叙事把帝国走向民族国家视作线性进程,把历史上局部的,且目前还是短暂的民族国家,当作是自然的、必需的和必然的。这样的论述在作者看来已是陈词滥调。他们认为:首先,十九世纪仍然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这时帝国远没有被民族国家取代。实际上,大英帝国的版图在1920年代才臻于至大,而全球殖民地面积和人口所占比例在三十年代末期才达到最高峰。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主要的国家组织形态,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去殖民地化运动爆发才成为现实,迄今也不过七十年时间。法国,仅仅是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才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其次,帝国与民族国家并非此消彼长的线性关系。恰好相反,近现代欧洲国家的强大,正是帝国海外扩张的一个结果。或者说,至少对于近代帝国,国家建设和帝国建设是一体两面、齐头并进的历史过程。
第三,尽管民族主义在十八世纪末期兴起,但肇始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革命并不能被简约地视为(仅仅)是新兴民族主义对帝国的挑战,即使不少革命以此为名。而且,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帝国的结束,而可能只是帝国统治主体的变化。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带来的是美国替代英国,作为一个帝国,在北美大陆经营扩张事业。早在美国成为一个海外帝国之前——通常认为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美国就已经是一个开疆扩土的大陆帝国了。
第四,取代旧帝国的未必是(多个)民族国家,而可能是一个旧疆土上的新帝国,或者至少是一个有着很强帝国传统的多民族国家:苏联,就被有的学者称为“多民族帝国”(empire of nations)。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革命创建的新帝国,能够运用新的普适性意识形态,整合帝国内部的多样性。
最后,帝国和民族国家作为两种统治形态并非泾渭分明,在概念上和实践中都可能是一个连续统,也就是库玛(Kumar)所谓的“作为帝国的民族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帝国”。而且,帝国建设非但不是民族构建的反面,而往往通过武力、胁迫、糅合、涵化等多种手段最后引发了后者:比如大英帝国在爱尔兰、威尔士数百年的帝国经营,最后却形成了一个英吉利民族(English nation)。把帝国和民族国家视作对立的观点无法看到历史的延续。当然,《世界帝国史》的这些观点并非全新,而是吸收了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史、全球历史社会学、帝国研究的一些观点。

全书大部分章节都有两个或多个帝国的横向比较:比如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第二章),罗马之后的基督教诸帝国和早期伊斯兰教帝国(第三章),并雄地中海的西班牙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五章),在美洲和亚洲早期扩张的欧洲诸帝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第六章),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帝国(第七章),十九世纪经营两个大陆的俄国和美国(第九章),以及二十世纪中叶在去殖民地化运动中垂死挣扎的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第十三章)。作者并没有使用比较政治学里常见的平行比较和归因分析,因为这种比较往往带来的是过于简约,甚至似是而非的答案。相反,作者抓住各时期帝国的主要特点和创新之处,借助历史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工具,在各章各有侧重地比较,力求呈现帝国的不同面向。比如第三章以帝国与宗教的各种关系作为主线,第五章以韦伯的“家产制统治”为核心来论述统治者的权力,第六章则比较了欧洲各殖民帝国早期扩张的各种策略。
纵向上看,作者对若干关键的帝国多处着墨,使其前后互相照应,让读者得以了解这些帝国的变化,或它们在倾覆之后的持久影响力。有些帝国绵延长久,其文化制度自然有连续性,但在不同时期也由于新的权力格局、新的技术观念,以及外来行动者(征服者)的闯入而产生新的变化。比如,《世界帝国史》一书涉及中国比较多的是第二、四、七章,既讨论了传统中华帝国文治武功的基本模式,又论及蒙元帝国以及后来清帝国所带来的内亚(Inner Asia)传统。一些帝国尽管延续的时间不算太长,却对后来的帝国影响深远,比如(西)罗马帝国对拜占庭帝国、早期伊斯兰帝国,以及欧洲加洛林帝国的持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蒙古帝国及其遗产给予了特别的重视(第四、五、七章)。蒙古帝国发源于欧亚大草原:那里诞生了诸多征服者,从公元五世纪让罗马帝国风声鹤唳的阿提拉,到十二至十五世纪蒙古诸帝国的统治者成吉思汗、忽必烈、帖木儿。蒙古帝国不但继承了欧亚大草原游牧帝国的特征,也从周边的诸文明和帝国中广泛吸收了宗教、技术、观念和统治术——从中国的火药到中东的伊斯兰教——并在其南征北战中将它们传播到整个欧亚大陆。统一的蒙古帝国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其身后的蒙古诸帝国却将这种蒙古模式的统治风格发扬光大,堪称欧亚大陆的枢纽。蒙古诸帝国与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中亚诸汗国都有很深的关联,可以说塑造了欧洲殖民帝国扩张之前整个亚欧大陆的政治版图。借用库珀之前著作中的一句话,在欧亚帝国史上,条条大路通罗马——或者通蒙古(“All roads lead to Rome—or to Mongolia”)。

作者最后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对当代世界影响至深的近现代西方帝国,用多个章节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其起源、演变、冲突、终结的长时段图卷。仅仅是所谓的漫长的十九世纪(the long 19th century, 1789-1914),作者就花了三章(八、十、十一)来讨论。但作者在这部分并没有拘泥于年代顺序,而是各章侧重于不同的主题,包括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和欧洲内部主权观念对帝国的冲击。这个阶段,不仅是欧洲殖民帝国的第二期和最高峰,也是民族主义观念和民族国家模式开始初显端倪的年代,不仅是欧洲工业革命和世界经济大分流的时期,更是各种政治革命层出不穷席卷全球之际。如前文所述,传统的历史叙事和历史社会学的主题词是民族主义、国家建设、社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帝国只是陪衬的绿叶,而今天选择以帝国为主线,并不意味着可以绕开这些主题,恰恰相反,帝国主题的加入使得讨论变得越发复杂而有趣——这从第八章的标题“革命年代的帝国、民族和公民权”就可以看出。作者借此拷问了很多已然是“神话”的命题:比如,法国革命带来的公民权仅仅适用于法国本土,还是涵盖整个法兰西帝国?美国革命之后的人民主权如何将奴隶和印第安人排除在外?共和体制为什么能和海外殖民并行不悖?民族构建又何以做到与帝国扩张齐头并进?总之,尽管线索纷乱,作者还是力图理出头绪,又不失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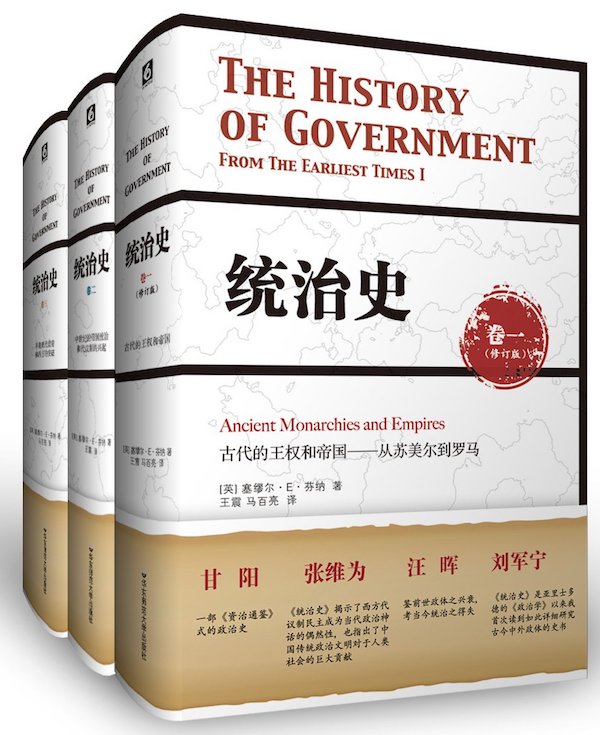
从《政府史》到《世界帝国史》,主题词从政府变成帝国,又体现了历史社会科学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另一个变化——帝国转向。在历史学里,投身这一运动的既有影响广泛的全球史、殖民史,亦有十九世纪美国帝国史和新清史这些旁支分流。2010年出版的《世界帝国史》可谓应时而生,对这波帝国研究运动做了一个中期总结。这种变化同样反映在历史社会学里: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的三、四卷(2012,2013)和一、二卷(1986,1993)的差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第一卷后半部分和第二卷尽管正涵盖欧洲帝国全球扩张的时代,关键词却是民族国家,帝国一词近乎阙如。相反,在第三卷里(1890-1945),“全球诸帝国”(Global Empires)的字眼包含在标题中;第四卷也用了两章来讨论二战后的美利坚帝国。不了解学术史的读者不免疑窦丛生:难道近代欧洲国家不是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反而是从民族国家到帝国?其实不然,只不过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帝国并非历史社会科学的宠儿,彼时民族主义和国家形成的研究则处于黄金时代;而到了曼写作三、四卷的时候,帝国研究正如日中天。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的概念如何塑造和限制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力,而新范式的出现带来的范式转移或者范式交替,则又能使得我们脱离思维窠臼而认识到历史的不同面相。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
客观地说,尽管帝国研究其兴也勃,但在历史社会科学以内,它尚无法与鼎盛时期的国家建设与民族主义研究相比,更没有生产出诸如蒂利、曼、沃勒斯坦、安德森兄弟的那些对整个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理论都有革命性影响的划时代作品。这部分源于帝国的复杂性而带来的比较、归纳、综合的难度,部分则是因为九十年代以来历史社会学者对经典历史社会学大理论、“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质疑和扬弃。新一波的历史社会学以小为美,以精细为美,长于事件分析、叙述和诠释,而不再热衷大尺度、长时段的结构性比较。笔者在这里无意对这一学术风格转向带来的后果作是非臧否,但不可否认,《世界帝国史》的可贵之处恰在于它综合了历史社会科学新旧两个看似对立的传统,视野开阔却又精细入微,广泛比较但不简单粗糙。当然,这本书的理论部分尚达不到曼和蒂利的代表作那般优雅,也不及芬纳独具一格的分析框架。所以,可以将此书视作帝国研究产生的重要作品的起点。
帝国应该活着,或者应该复活吗?这个开放的问题正在不同背景、语境下引发激烈争论。这不禁让笔者想起最近发生在美国学术界的一桩公案。去年9月,《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刊登了一篇题为“支持殖民主义的理由”(The Case for Colonialism)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学界轩然大波。作者Bruce Gilley(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不但说西方殖民主义有益、合理,而且提出应该在某些地区重新推行殖民治理模式,以消除贫困,实现发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三世界季刊》的创刊编辑之一正是大名鼎鼎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批判最深的《东方学》作者爱德华·萨义德。这种观点发表在这样一份期刊上,引发的反弹和批评可想而知。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这篇文章的标题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aill Ferguson)2004年出版的《巨人:美利坚帝国的兴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的第五章《支持自由帝国的理由》(The Case for Liberal Empire)形神兼似。在这本备受争议的书中,弗格森认为相比于去殖民地化运动后的失败国家,自由的霸权帝国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治理模式和公共物品。所以,美国应该大方承认自己是一个全球性帝国,勇于承担霸权性帝国的责任,就像当年的大英帝国一样,保护自由贸易,维护全球和平。《支持殖民主义的理由》一文对弗格森的观点几乎全盘照收,只是更加旗帜鲜明地主张恢复殖民统治。尽管在学术界民意汹汹的抗议之下,作者公开道歉,撤回稿件,但围绕着帝国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讨论不会随之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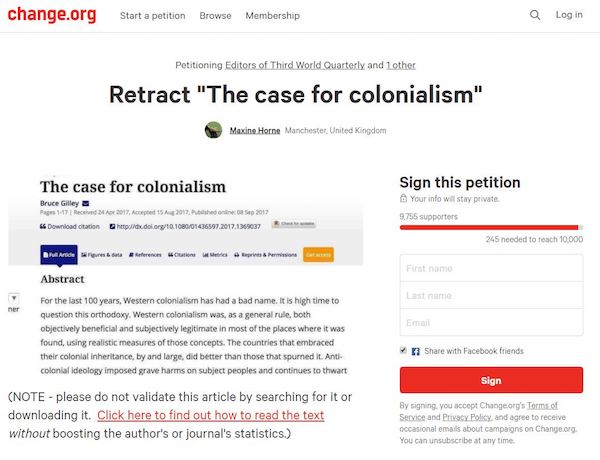

《巨人:美利坚帝国的兴衰》
帝国并非逝去的残垣断壁,而是实实在在地活在人间。不但过去的帝国还活在学术作品、大众文化和集体记忆中,帝国的器物、制度和观念还发挥着持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帝国从来没有真正死去,它在不断地被建构、解构和重构。二战后数十年的停滞——如果真的有过这样的停滞的话——相较于数千年帝国史,才是真正的过眼云烟。现在还远远不是说帝国“历史的终结”的时候:无论是作为实存还是话语的帝国,非但没有一去不返,可能才刚刚进入一个新时代。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