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怀念陆谷孙先生 | 开学季,来听听老复旦er的独家记忆
原创 吾目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十七年前,应复旦校庆出版策划人之邀,为校庆图书《我的阿拉丁神灯,在复旦》撰写其中有关复旦外文系的一篇。文成后交陆谷孙先生过目,先生回复“甚好”,并言因此文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鼓励我坚持阅读、继续写作。今陆师已仙逝数载,吾重改此文,只觉当时文字实在幼稚,难以卒读,当年竟敢斗胆付诸纸面,殊厚颜也;而十几年来,未遵师嘱,一事无成,实于心有愧,又无可奈何。惟望读者凭此旧文,再一览大师昔日风采,至于文中所载他事,不值一提,可忽略不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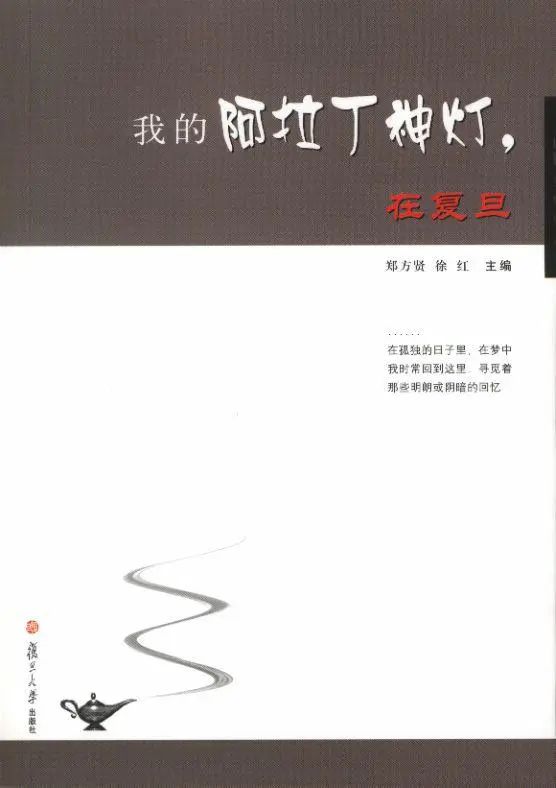
其实命运永远不会轻易地“捉弄”谁,能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固然很了不起,但在某些已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学会接受现实,尝试爱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并从中发掘出乐趣,这才是更有价值的。
“捉弄”
命运的
依稀记得汪国真先生曾说过:“喜欢文而终学理,或喜欢理而终学文,只是命运最初的捉弄,却非命运最终的捉弄。”同样,我想说的是,喜欢中文而终学外文,或喜欢外文而终学中文,也只是命运最初的捉弄,却非命运最终的捉弄。
和许多怀抱梦想、立志要考入复旦的莘莘学子不同,我进入复旦或许更多的是几分机缘,几分侥幸。

光华楼 复旦大学慕梁摄
说来好笑,在复旦来我就读的中学招保送生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复旦是在上海,对复旦唯一的直接印象还是来自“狮城舌战”中的那几位辩手。可能是当时古龙的书看多了,我总觉得所谓“江南第一学府”,就应该像其书中所写的某某山庄,在“烟雨江南”的某个小镇,某条乌衣巷中,有一座锈迹斑斑的青铜质大门,半虚掩地朝南开着……
由于我所就读的中学武汉外国语学校比较特殊,学生被保送的机会很多,尤其是去一些对口的外语学院,比如北外、上外和广外。然而,或许是我从高中开始就比较偏好文学尤其当时比较痴迷“五四”文学的缘故吧,我记得我当时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我高中时的偶像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所写的英国剑桥大学,另一个就是对于我来说很带有些神秘和传奇色彩的北大中文系。但前者对于我来说,实在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后者,对我来说也不大现实,因为一旦选择保送,我们保送生就不能选择自己的专业,而只能就读所规定的外语专业。也正因为此,当复旦来我们中学招保送生,我的班主任推荐了我时,我似乎并不是那么兴奋,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参加了笔试和面试。其实我当时的成绩也不怎么拔尖,也就中等偏上的样子,然而面试和笔试却都出乎意料地顺利通过了,我也就这样拿到了复旦的录取通知书。
✦
1996年9月,我和父母一起带着“烟花三月下扬州”一般的心情,像旅行团一样乘着“江申6号”轮船,花了整整两天两夜来到了这个现在我再熟悉不过、当时却充满了陌生感的城市——上海。
✦
✦
记得轮船驶近“十六铺”码头时,我第一次看到外滩,第一感觉不是上海多么多么繁华,而是“黄浦江怎么这么脏这么臭啊”!来到复旦后,看着那不大起眼的砖红色大门,我的心里总觉得它和“江南第一学府”的头衔不大相称,甚至后来还在给高中同学的信中戏称它“就像个农村公社的大门,甚至还有点像个公共厕所”。当然,这只是因为我当时的肤浅和对复旦的不了解所致,而在我已经在复旦学习、工作、生活过将近十年的今天,我却觉得正是这样的大门代表了复旦的那份不求虚奢、专注求实的精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那份失望却也是很真实的。
这些不太好的第一印象似乎已经暗示出了我对崭新大学生活的种种不适应。首先便是学习上的,虽然我是由外语学校保送到复旦外文系英语专业的,但来到复旦后我却发现自己在英语方面毫无优势可言,因为上海和沿海地区的同学学英语的起点比较早,大多从小学就已经开始学了,而在武汉却是初中才开始学。更糟糕的是,由于我中学时多是使用的原版教材,教学体系和方法与复旦的颇为不同,我从一开始就感到很不适应。然而,能进入复旦的学生谁没有一点觉得自己是根葱的盲目骄傲呢,叛逆的心理使自以为是的我坚持认为自己高中的教学方法比较“先进”,而复旦的则比较“落后”,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加之我当时盲目地自认为自己就是学中文的料子,学外文绝对只是一种命运的“捉弄”,因此还时常逃课去旁听中文系和其他文科院系的课程,结果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居然拿到了平生第一个英语不及格。
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甚至都准备接受自己沦为“差生”的事实,就这么混四年了事了。而学习上的巨大落差对生活也造成了很大影响,由于成绩不好,我似乎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缅怀过去的优秀上,似乎只有通过高中同学们在信中对我的称赞和鼓励,才能稍稍寻找到一些安慰和平衡。这样的结果便是我始终无法将生活的重心往大学里偏移,融入复旦的生活中,而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对往昔高中生活的追忆上,继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开始碰到在异地求学时的一个最大问题——“孤独”。这种孤独不是说我没有朋友,没处说话和交流,而是一种始终无法克服的不适应,尤其当周末寝室里上海的同学都回家了以后,这种孤独感更是如影随形,让人不由得烦躁。我甚至开始产生了能否让家里人让我转学回家的滑稽念头。
然而,就在这时,当时我的英语任课老师姜琴老师无疑察觉到了我的问题。她主动来找我谈话,告诉我不管我个人对复旦的教学体系有何种感觉和意见,但作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它被沿用至今肯定是有其道理的,这道理不论我是否真的能理解和体会,我都应该尝试着忘掉自己的从前,去接受它适应它。而所谓“术业有专攻”,如果我觉得自己对中文有兴趣,利用业余时间去旁听一些课程或讲座是可以的,而且学习中文本来也会对学习外语有帮助,但是不能舍本逐末,影响自己专业课的学习。
老师的一番话开导了我,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开始试着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按部就班地按照复旦的教学体系学习自己的专业课,四年下来,虽说也没有取得特别优秀的成绩,但自己感觉和以往相比在英语方面确实还是不知不觉地脱胎换骨了一般,无疑上了一个台阶,我想这或许正是复旦作为名校让我最有体悟的地方吧。更重要的是,这让我深刻地懂得了“态度决定一切”的道理。其实命运永远不会轻易地“捉弄”谁,能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固然很了不起,但在某些已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学会接受现实,尝试爱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并从中发掘出乐趣,这才是更有价值的。
做好中国人
学好外国语
“
听完你们练唱/我独自走在国年路上/冷风冷雨抽打着我的衣裳/心头却涌起一股热浪/学外语的人不能忘记根本/立身才能方正强刚……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外文系的同学记得这首诗,甚至包括这首诗的作者陆谷孙教授自己。这首诗是时任系主任的他在我们为“一二·九”歌会努力排练时临时口占的,但我却在听过一遍之后从此就把它深深印在了脑海,这也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陆老师“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的系训精神。
而到了大四,我们终于可以选修陆老师的英美散文课了。虽然听师兄师姐们说,陆老师的要求特别严格,考试的时候一个“spelling mistake”就会扣掉五分,而且临近毕业大家的学分也差不多修满了,但是谁也不舍得落下陆老师的课,而到了真正上课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还有好多其他院系的同学跑来旁听,害得我们选了课还不得不每次提前去占座。
点击上方书影,即可下单
陆老师上课旁征博引、纵横开阖自是不用我多说,更难得的是,陆老师教了那么多年英美散文,每一次上课都会给我们在讲义中重新补充许多与时俱进的新文章,不光让我们学习和了解英美散文的历史脉络,更让我们能去体会与发现其新的发展与走向。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陆老师上课时的风趣和幽默,他做系主任时要求外文系每一个任课老师每堂课至少让学生笑三次,而他在自己的课上更是不断地调动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笑声不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来复旦外文系读书如果没有上过陆老师的课简直就等于白来。
其实陆老师给我们上课时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虽然当时他已经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但是仍然有很多推不掉的社会活动,有时候还得去出差。有一次去北京出差,陆老师为了不耽误给我们上课,竟搭乘了一大早的飞机赶回来。陆老师心脏不大好,有一次课上到一半,突然显得十分吃力,细密的汗珠已经沁出了额头,我们当时都很紧张,有的同学想上前帮忙,陆老师却只是摆摆手,示意我们坐下先自己默读课文,自己走出了教室。过了一会儿,陆老师回来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又精神饱满地给我们上起课来,而细心的同学却发现陆老师这堂课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教室里走动,而是一手撑着讲台,另一只手一直捂在胸前讲完的课。这堂课,有很多同学是偷偷噙着泪水听完的,大师的崇高师德让我们终生难忘。
毕业后,由于工作业务上的关系,我得以有更多更亲密的机会接触陆老师,从中我也更懂得了什么叫作“要做文章先要学会做人”的道理。“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道理在现代社会说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记得毕业时,陆老师鼓励我们不要一味看重高薪,只想去外企做那看着华丽实际却要以丧失自己的自由为代价的“笼中的金丝雀”,而应该坚持自己的人文理想,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他更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们说,如果谁毕业了是去中学教书的,请和他联系,他要给他一笔奖金,而如果是去西部教书的,他更是要把那笔奖金double。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前不久拜读了陆老师新出的散文集《余墨集》,更是感觉点点余墨,一纸书香,沁人心脾,让我再次体会到“学好外国语”还只不过是表面,而“做好中国人”才是根本!
“一百本必读”
记得刚入学的时候,复旦正好在搞一个“一百本必读”的活动,分文理科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个书目,里面详细列出了建议我们阅读的一百本图书,并在图书馆阅览室里辟出了专门区域陈列这些书籍。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虽然我最后没能按照该书目所列读完所有书籍,但是我却受到启发,按照这一思路和自己的兴趣每学期给自己列出十五本必读书目。
我先从自己喜欢的文史哲方面各挑一本经典的“史”来读,大致地来个全方位的了解,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找具体的作品来读,这样对各部作品就既能做宏观的把握,又能做微观的分析,而且两者相辅相成,效果斐然。而且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也不喜欢因为专业的限制而只读英美作品,而是做到英美的作品尽量读原版,同时也不排斥翻译的其他各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读书时为了克服疲劳,我常常七八本不同类型的书在同一时间段进行阅读,这样可以时常换换脑子,用阅读来代替休息,节省了不少时间。就这样,四年下来,我也终于读完了我自己的“一百本必读”,而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这一百多本书所带给我的要远远胜过那些很多我没有拿到的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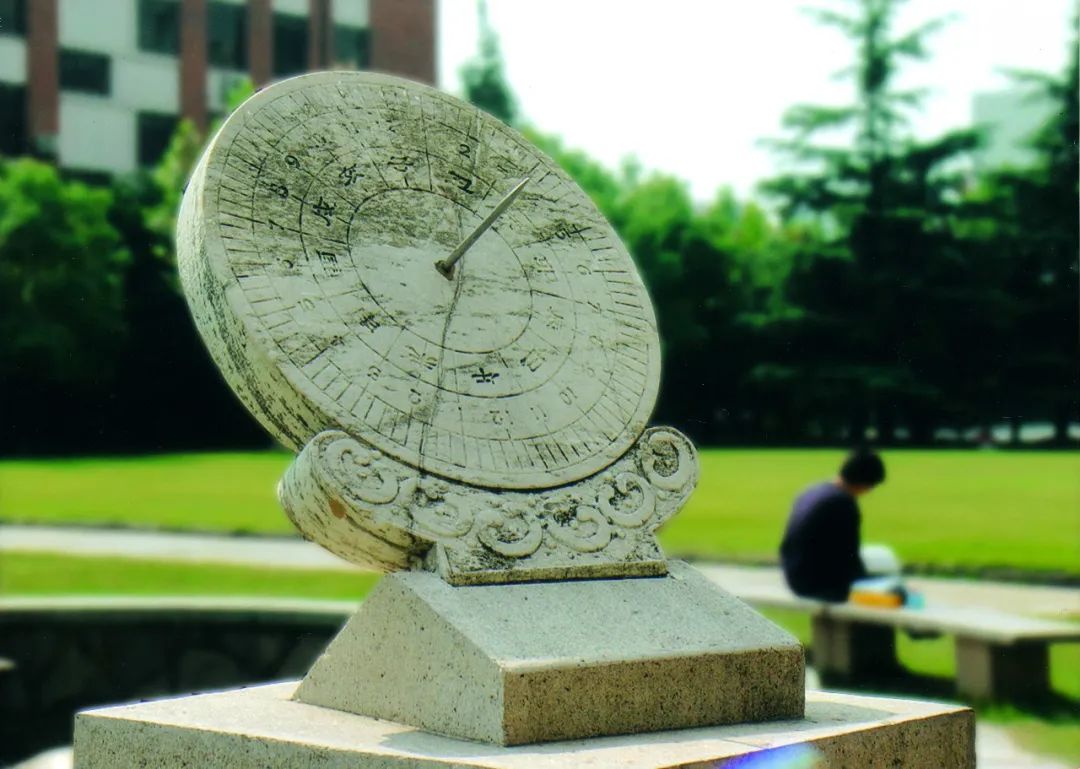
日晷 复旦大学李建军摄
比如读巴尔扎克的《幻灭》和司汤达的《红与黑》,让我虽没有经历那么多的人生起落,却仍然可以看清许多人生的真实;读《傅雷译文集》中的传记五种,让我从伟人和平凡人的生命历程中,悟到了许多人生真谛;读托尔斯泰的《复活》,让我真的感觉到灵魂受到洗涤,也仿佛经历了一次复活的历程;读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让我体会到真正的历史不是拥有话语权力者的记述,而是真正时间流里的一些不起眼的点滴变迁;而读卡夫卡、加缪、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则让我对现代人的存在产生了种种思考,印证自己的生活……而这些都是让我终身受益无穷的。
“白菜与国王”
也许是出于一种幸运吧,在我就读外文系的1996年,正好碰上了陆老师就任外文系系主任。虽然当时还不能选修陆老师的课,但一系列新的活动却仍然让我们受益良多,而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要属“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了。时至今日,我毕业已经差不多快整整五年了,但是看到外文学院要举办外文节的海报上,“白菜与国王”讲座的安排仍然历历在目,一种亲切感总是油然而生。
还记得我进复旦后听的第一场“白菜与国王”讲座就让我有缘见到了上高中时特别欣赏的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是我高中时难忘的文化启蒙读物,而有幸在当时亲眼见到书的作者,听他讲解,向他提问,与他交流,更是让我一下子爱上了复旦的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当时我便下定决心,决不漏过之后的每一场“白菜与国王”讲座。当然,“白菜与国王”绝不仅仅只是限定在文化这个小范围内,之后陈钢、俞丽拿、沈柔坚、黄蜀芹来过,叶扬、董鼎山、董乐山、冯亦代来过,复旦著名的“葛铁嘴”葛剑雄教授也来过……所请的这些主讲人既有音乐家、艺术家,又有诗人、作家、学者,涉猎范围之广、内容之博当真是切合了“从白菜到国王无所不包”的寓意。而这也正和陆谷孙老师一贯的理念“学外语的人不能只懂外语”是一致的,如今,“白菜与国王”讲座已作为外文系的一大优良传统被保留了下来,相信一代又一代外文人、复旦人都将从中获得养分,受益一生。
当然,除了“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复旦园里不容错过的讲座和学术活动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哲学系俞吾金、张汝伦等教授的讲座,中文系骆玉明、陈思和等教授的讲座都是不容错过的经典。当然,我所推荐的讲座基本上偏文,这或许是因为我是个典型的文科生吧,其实不论文科理科、专业性很强的还是普及性的,只要你多留心海报栏里的海报,肯定能找到符合你兴趣、适合你自己的讲座,而有时候能听到某位教授、高人、大师的一席话,当真是胜读十年书。



记得系刊《二十年华》也是在陆老师的大力支持下创办的,甚至连经费都是陆老师自掏的腰包,目的当然是为了给我们外文系的学生提供更多的练笔机会,而且中外文不限,因为在陆老师看来,多锻炼外文写作固然对提高外语学习能力很有好处,但巩固我们的中文基础也是不能偏废的。看看曾经的和如今的一些翻译大家,除了都十分精通外文外,他们哪一个不是中文也十分优秀,譬如钱锺书先生更是国学大师。
而我今天之所以能比较得心应手地从事编辑工作,很大程度上也许就得益于当时我能有幸担任《二十年华》的编委和主笔吧,至少它为我培养对文字的敏感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也教会了我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克服困难。虽然当时编的是这样一份连刊号也没有的系刊,但也绝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有的时候同学们交上来的稿件不符合要求,你就得花时间去和作者交流,告诉他你的想法和要求,启发他的思路,直至拿到你想要的稿件;有些时候稿件数量实在不够,我和其他编委便还得自己包办;当时由于经费有限,有时候排版工作也得我们身体力行,而在联系印刷、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我们也接触了社会,懂得了如何在这个商品社会里“据理力争”,不能让商家因为我们是学生就狠“宰”我们。
守望者
麦田里的
说起麦田剧社,上世纪90年代末在复旦读过书的人不知道的恐怕还不多。其实在它之前,复旦已经有两个剧社——复旦剧社和燕园剧社了。由于复旦剧社属于“官方”性质的,所以当时排的戏也不多;而燕园剧社虽然人才济济,但却一直“固执”地走着所谓“现代路线”,总是排一些不大让人“看得懂”的戏,所以在校园里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当时我们外文系的许多人其实也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燕园剧社,但由于一些理念上的分歧,加上正好当时系里要办外文节,希望大家自排自演一些中英文戏剧,于是在系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外文人自己的麦田剧社便应运而生了。
然而,剧社不同于许多其他社团,它的分工合作性太强,于是成立之初剧社内部便对到底排演什么风格的戏产生了分歧。然而,或许正是陆老师一贯强调包容、兼收并蓄的思想影响了我们,我们决定自由尝试不同风格的戏剧。
有了这样明确的大方向,剩下来的就是齐心协力的排戏、演出了。为了显得不是那么排外,我们也并没有拘泥于所有的戏都在系内挑选演员,而是大胆地在全校张贴海报,征召导演、演员,同时也成立了不同的小组分头负责宣传、剧务、舞美、灯光等。记得那时的演出一直是免费的,我们的经费很紧,为了不给系里造成太大负担,我们经常需要发动同学四处跑赞助,而在做道具、服装时也是能省就省,尽量节约。
记得有一次需要一些木料,我们就到周围的家具生产店门口去捡别人不要的边角料;还有一次做服装,是到一个工地上捡的一些大的包装袋,再拿回来洗干净;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要给一个男生做胡子,一位女生竟毅然剪下了自己留了几年的心爱的长发。像这样的点点滴滴简直不胜枚举,在不断碰到各种困难又不断地想办法解决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地体会到了“想象力”所带给我们的喜悦,与人合作的快乐,更重要的,是TEAM SPIRIT的可贵。
之所以写上面这两段,其实是想告诉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其实在复旦,类似《二十年华》这样的刊物和麦田剧社这样的社团还有很多。不要老是把自己锁在书本里,参加几个自己感兴趣、适合自己的社团,多参与一些社团的工作,多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多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还能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表面上被占用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却能在日后的求职、工作、人生中带给你许多意想不到的益处。提笔至此,已经洋洋洒洒几千言了。如果要对复旦的生活作一全面的介绍,想想哪怕几万言、几十万言也不一定能够真的做到,毕竟是整整四年的青春,怎么写也写不尽的,不如搁笔吧,只当是给后来人作一点窥豹一斑的介绍。
如果硬要对复旦生活作一总结的话,我觉得有一句话甚好,叫“‘疯狂’地学,‘疯狂’地玩,‘疯狂’地谈恋爱!”已经记不清这句话到底是出自哪里了,好像是从一位中文系的朋友那里听来的,据说是骆玉明教授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时的“聊发少年狂”,又模模糊糊有印象似乎是在听哲学系张汝伦教授的一次讲座时张先生的慷慨陈词,具体是谁,或许两位先生自己也只是一时的灵感,事后都不大记得了,但对于我,却变成了大学生活的座右铭,也是对我大学生活的一种归纳吧。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眨眼我来上海已经快十年了,而这在上海的十年也就是在复旦的十年。记得毕业时我本来是可以去《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但最终经过艰难的抉择我还是放弃了相对较高的收入,而选择了留在复旦。到底是什么促使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一直觉得能感受得很清楚,但却总有些说不明白。时至今日,我终于敢说或许正是“复旦人”这个骄傲的名字使然,毕竟,这里有我的青春,也有我的成长,更有我的梦想与未来!
本文来源:《我的阿拉丁神灯,在复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有删减
原标题:《怀念陆谷孙先生 | 开学季,来听听老复旦er的独家记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