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杨焄︱《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启人深思的陈寅恪“谬见”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的岁末,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等友人闲谈起唐玄宗和杨贵妃悲欢离合的往事,感叹唏嘘不已。受王质夫的鼓动,白居易提笔写下了《长恨歌》,随后陈鸿又撰有《长恨歌传》。在传世的白氏诗集中,《长恨歌》前就附有陈传。可惜前人在讽诵评赏之际,很少议及两者的关联。
陈寅恪在1947年发表《长恨歌笺证——元白诗笺证稿之一》(载《清华学报》第十四卷第一期),勾稽大量史料以阐发隐晦未彰的诗旨,并尝试藉此考察不同文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留意到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提起过唐代盛行的“温卷”风气,即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会预先将自己的诗文分数次投献给主考官,尤其是传奇小说一类的作品,“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从而达到提高声誉、确保及第的目的。他据此大胆推测,《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本属一体”,“《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之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通过考辨这个“小问题”,他还想进而揭示一个更重要的“大发现”,“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他顺带提及,此前用英文发表过一篇《韩愈与唐代小说》(载1936年《哈佛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其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恰好就在这一年,程会昌(程千帆)将这篇英文论文译出(载1947年《国文月刊》第五十七期),其中特别强调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并序》《毛颖传》等近于小说,“前者尤可云文备众体,盖同时史才、诗笔、议论俱见也”,确实可以和《长恨歌笺证》中的议论互相印证,足见陈寅恪得出这一结论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信口乱道。

不过这个新发现并未立即得到学界的认可,夏承焘在日记中就提到:“陈学恂处借来其友人戎女士在西南联大听陈寅恪讲授笔记,有说《琵琶行》《新乐府》《长恨歌》《连昌宫词》各章,考证有甚琐者,亦有甚可喜者。”(《天风阁学词日记》1949年3月4日条,《夏承焘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虽然语焉不详,但稍后就在《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载1949年《国文月刊》第七十八期,收入《夏承焘集》第八册《词学论札》)中做了详尽的论述。
他虽然充分肯定“陈氏著书,精于用思”,“兹篇以其隋唐制度专家之学绩,考此妇孺皆知之名歌,尤为生新可喜”,也补充了一些陈氏疏忽遗漏的资料以证成其说,但对白诗与陈传不可分离的推论则持有异议,“以为实有不可强通者”。在他看来,《长恨歌传》作于《长恨歌》之后,即便陈鸿不撰此文,“白歌亦已成为独立之体”;况且白居易在此之前早已进士及第,根本不需要“以此为温卷之用”;更重要的则是《云麓漫钞》所说的情况并不能得到普遍的验证,“似不应执赵氏一家之聊尔之言以绳唐代一切小说”。他由此得出结论,《长恨歌》“只是一篇故事诗而已,陈君必牵率以入小说之林,又强绳以赵彦卫温卷之体,求之过深,反成失实”。
文章脱稿之后,夏承焘曾与弟子陈广汉商讨过其中内容,然而在为这篇论文题写跋语时,陈广汉却认为《长恨歌》“恍惚迷离,不着议论,在白诗中实为别具风格”,如果用白居易所倡导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来加以衡量,似乎确有意犹未尽之处,“故歌成后,复使陈鸿传之”,两者“互有详略,歌多隐讳,传则直书”。他显然更接受陈寅恪的推断,并未信从老师的意见。

《长恨歌笺证》经过修订增删后收入《元白诗笺证稿》(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1950年)作为开篇第一章,陈寅恪在疏证诗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数句时补充了一则重要资料,并郑重声明:“此条失之眉睫,友朋中夏承焘先生首举以见告,甚感愧也。”而夏承焘在翻阅此书时则据此推测,陈氏“曾见予《读〈长恨歌〉》之文”(《天风阁学词日记》1951年4月14日条)。可知所谓“举以见告”并非当面告知,而是指那篇商榷文章。然而陈寅恪在采摭资料的同时并未接受夏氏的批评,依然坚持自己原先的推论,甚至在数年后发表的《论韩愈》(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中,又重申《元白诗笺证稿》中的意见,再次强调“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行之小说”。
个中缘由,其实不难推测,尽管夏承焘反对将《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合为一体,以附和赵彦卫的“温卷”之说,但态度却有些游移不定,陈广汉就提到“师固谓白诗不欲自言者,陈传代为点明矣。是亦歌、传不分离有助读者了解之一事也”。与此同时,夏承焘又充分肯定陈氏所言“元和古文与小说有关系之说,诚治文史者未有之妙谛”。而陈寅恪推断白诗和陈传本为一体,最终就是为了证明唐代古文兴起与小说创作关系密切,夏氏对此既然并无异议,足证大体已立,自然不必再纠缠于枝节末叶的琐屑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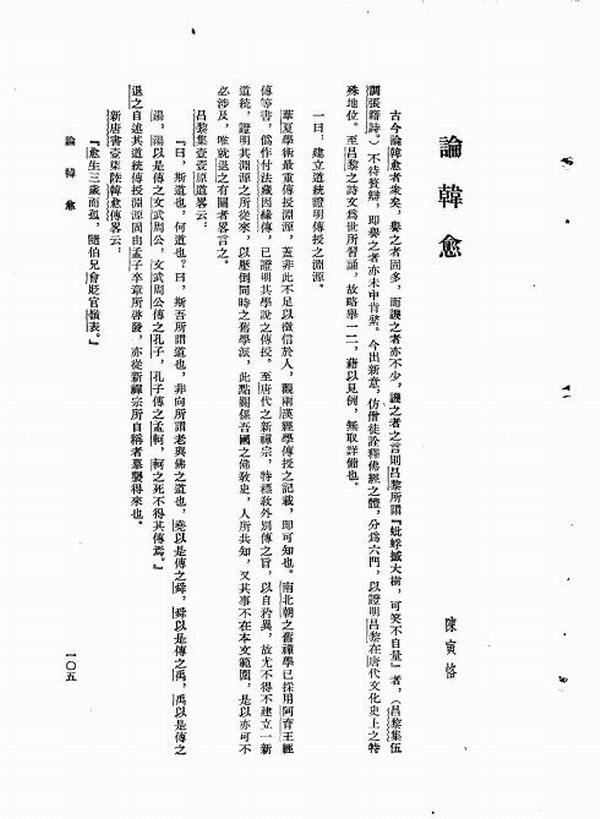
随后的事实也证明,有不少学者陆续接受陈寅恪的论断。
早年受业于陈寅恪的刘开荣曾撰有《唐代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47年),虽然为了因应时势的变化,后来做过大幅度删改,可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55年)中,仍然提到《长恨歌传》“完全用散文重述《长恨歌》之内容”,“到末了作者忽然板起面孔说出一篇甚么‘惩尤物窒乱阶’的迂腐教训来,实在是有些‘画蛇添足’,然而凡明瞭传奇小说产生背景及其与‘古文运动’及进士科举的密切关系者,疑惑自然便不攻而破了”(见该书第二章《传奇小说勃兴与古文运动、进士科举及佛教的关系》),显而易见受到陈寅恪立论的影响。
苏仲翔编注的《元白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在《长恨歌》后附有题解,称“此歌原与陈鸿《长恨歌传》并行。陈传原为补《长恨歌》之所未详”,“此正以‘史才’‘议论’补‘诗笔’的不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并明确交待参考过陈寅恪的论著。在稍后出版的《白居易传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中,苏仲翔又有引申发挥:“《长恨歌》既从一篇幅完整的小说(包括歌及传)分出别行,世人习诵,久已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它本身既无真正收结,亦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至如元稹的《连昌宫词》,虽然深受《长恨歌》的影响,但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的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一新体,即使史才、诗笔、议论诸体都能汇集融贯于一首诗中,自成一独立的整体。”稍作比对,就会发现这段文字其实直接迻录自《长恨歌笺证》。
周绍良在五十年代中期着手搜集相关材料,准备为鲁迅辑校的《唐宋传奇集》作笺注。其中一篇《〈〈长恨歌传〉笺证》(收入《唐传奇笺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颇多依傍《长恨歌笺证》,在引述陈寅恪所说的“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云云时,也肯定道“这样理解是不错的”。他后来又撰有《唐传奇简说》(收入《唐传奇笺证》),在介绍《长恨歌传》时,称《长恨歌》“可以看作这个传奇故事的附属部分”,也和陈寅恪的意见一脉相承。
程毅中的《唐诗与唐代小说》(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甚至认为“唐代文人把诗文结合,创造了传奇的一种体制。他们往往把诗序写成了传记体的小说,而且有时还由两个不同的作者分工合作”,所举出的例证就包括《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依然承袭着陈寅恪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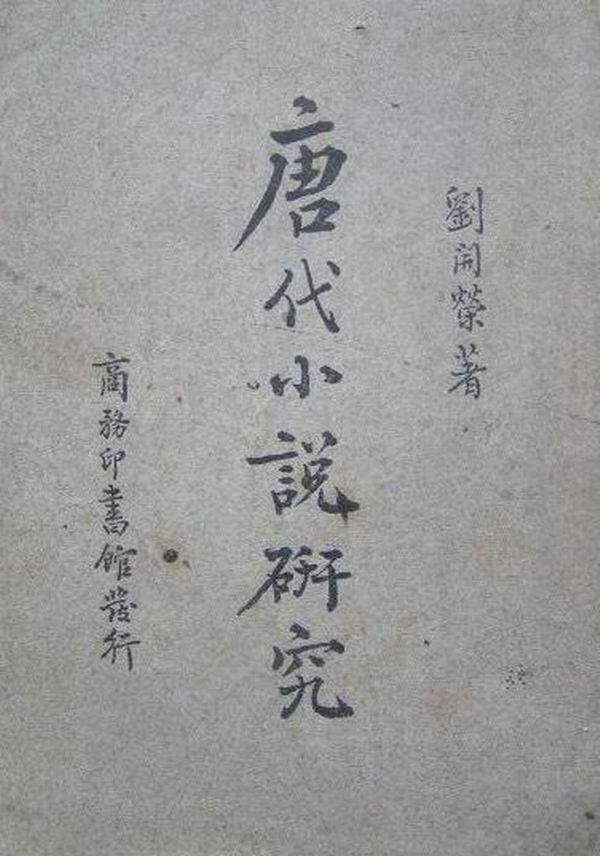
不过仍有学者对此说持不同看法,并继续予以商榷辩驳。
黄云眉在《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载《文史哲》1955年第八期,收入《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就有过针锋相对的批评。他在文章中指出,陈氏认为白居易、元稹、韩愈等人既是古文家,又是小说家,“古文与小说的关系,在一身二任的作者身上,便显得异常密切”,然而这个判断只是根据《云麓漫钞》的记载,“把这些诗歌传序套上呆板公式”,“唐代小说有它们一定的体制,但不会像陈先生所说是一种史才、诗笔、议论首尾搭配的综合物”。夏承焘对陈寅恪的意见还颇有些依违两可,黄云眉则完全不认同唐代古文与小说之间存有关联。只是此文涉及范围较广,并没有集矢于文学创作;又受到论题的限制,未能针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分合关系作集中研讨。
紧随其后,王运熙发表《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载1957年11月10日《光明日报》,收入《王运熙文集》第二卷《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完全赞同黄氏的意见,并做了进一步补充,认为“元、白与韩愈虽都作韵散合体的小说,但其风格迥不相同”,“文辞写得细腻、通俗化,内容多述情爱,是元、白诗文(包括《长恨歌》《莺莺传》在内)的特色,这种特色是为韩、柳古文派所反对的”,所以“古文运动不可能依靠试作传奇成功而兴起”。虽然也没有详细讨论白诗与陈传的关系,但通过辨析唐代小说与古文的风格差异,明确指出陈氏的推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否还能将这两篇作品合并在一起视作众体兼备的小说,也就令人疑窦丛生了。
吴庚舜在《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载《文学研究集刊》1964年第一期)中同样不同意陈寅恪的看法,强调所谓诗歌与小说两者韵散结合的方式“根本不是唐传奇的本来面貌”,更不能将不同作者用不同体裁写成的作品“生拉活扯硬拼在一起算作一个作品”。即使再退一步,姑且承认陈氏所说的《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本属一体”,可是将这样两人合作的作品投献出去,究竟能够“见谁的‘史才、诗笔、议论’呢?”陈氏的推论在逻辑上似乎也难以自圆其说。
罗联添的《〈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结构问题及其主题探讨》(载《中国史新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学生书局1985年;修订后改题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共同机构”问题及其主题探讨》,收入《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9年)则进一步推测陈氏立论偏颇的缘由,或许是受到白氏诗集中《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相连合刻的影响。他又根据流传于日本的《白氏长庆集》古抄本,判断宋代以后白集的编次、标题都存在讹误脱漏,“遂使歌成为传之附庸,进而容易产生歌、传一体的错觉”。
林文月在《〈长恨歌〉对〈长恨歌传〉的影响》(收入《山水与古典》,纯文学出版社1984年)中仔细考校过两篇作品的繁简异同,虽然并未提及陈寅恪,但也坚称“歌为歌,传为传,本不相关”。不过她居然认为白氏诗作中“竟无一言及陈鸿者”,由此怀疑两人并无交往,陈鸿只是选取《长恨歌》作为底本加以敷演而已,就不免有些矫枉过正了。林氏早年尽管研习过古典文学,但后来肆力于文学翻译和散文创作而无暇旁顾,此处所论就疏于检覈,显然并不知道白诗《早朝贺雪寄陈山人》中的“陈山人”就是陈鸿(参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元和五年庚寅”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未能恪守多闻阙疑的态度。


仔细寻绎种种来自不同角度的质疑辩难,可知陈寅恪判定《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并进而推测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小说创作密切相关,其实是没有充分根据的臆断。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推论徒劳无益而枉费精力,正是因为有了陈寅恪的“大胆假设”,才会引发后来众多学者的“小心求证”,并由此深入开掘、考索一系列相关问题。程千帆对早年翻译的《韩愈与唐代小说》就极为重视,不仅特意将其收入自己的论文集《闲堂文薮》(齐鲁出版社1984年),还在陈寅恪的启发下仔细追溯唐人行卷的详情。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他对陈氏的论说加以修正完善,认为陈氏指出的传奇小说在结构和内容上的特点,对读者而言其实大有裨益,只是不能以偏概全,“如果我们只说,在唐代传奇小说的某些作品中,出现过一篇之中兼备叙事、抒情、说理之体的情况,而这种情况的形成,则与进士们用它们来行卷,以便集中表现自己的多方面的文学才能有关,那就符合事实,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可被訾议的了”(见该书第八节《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其后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又在陈寅恪、程千帆等人的基础上做了周详细致的研讨,更能引导读者准确了解唐人行卷的风气及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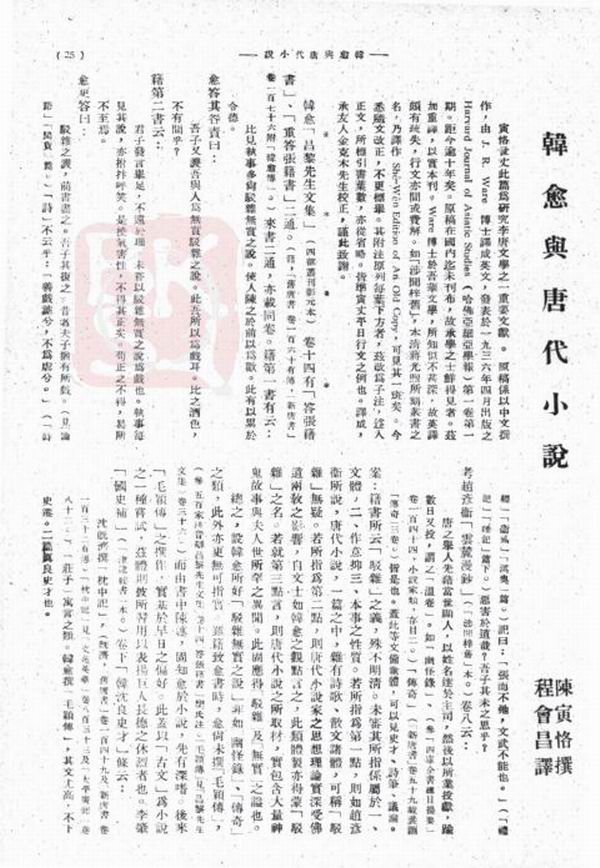

其实,如果加以必要的限定而不做过度的诠释,那么陈寅恪所揭示的《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内在关联毫无疑问是客观存在的,《元白诗笺证稿》所作的大量比勘互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即便是反对将此与古文运动牵强比附的学者,在这方面其实也并无异词。罗联添在《〈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结构问题及其主题探讨》中就认为:“歌、传合并读之,可相互参证,有助于了解歌,亦有助于了解传。”王运熙还与弟子杨明合作撰写《唐代诗歌与小说的关系》(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收入《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全面梳理过唐诗与唐传奇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将陈传与白诗列入“一篇小说与一篇诗歌叙述同一故事”的模式之中,指出这种情况“应是更多地受到当时盛行于城市中的讲唱文学变文的影响”,补充了先前未暇详述的内容。
学术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判定完是非对错就可以置之不理的,很多时候不断的“试错”和“证伪”也同样充满奇特的魅力,能够不断引人入胜。陈寅恪所做的推论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如此充满奇思妙想而不囿于常规的“谬见”,终究要比循规蹈矩却平庸无奇的“定见”更能启人深思。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