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在挪威教线上汉语这一年 | 三明治
原创 晴晴 三明治


"Dear Qing, Alberte came second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help."收到学生妈妈短信的时候,我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
Alberte是第一个非混血非华裔的学生,他在第二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全英大赛区得了第二名。这绝对算得上我职业转型后的亮点。
曾经,我是多么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呀。
我在上海一所民办高职院校工作了十二年。每每被叫“邱老师”的时候,总有些心虚,因为大学毕业入职后,我一直在行政岗位上工作,上课只是“蜻蜓点水”(为了职称评定时不要空白而上的)。但我一直有个三尺讲台的梦想。
移居挪威后,因为还处在语言学习阶段,又是小地方,没有特别合适的工作,想着自己汉语国际教育的专业,觉得或许可以试试看,重拾我的专业和此前一直未能实现的教师梦。而且,自己未来的孩子也会面临中文学习的问题,我不妨先在其他孩子身上实践下吧。
学语言的同时,我时不时地在网上浏览汉语教师的相关信息,在简历、复试、培训、线上答题、培训、复试、终面、试讲的严格筛选下,先后收到了K和L两家线上教育机构的录用通知,终于如愿以偿。
德国的姐弟俩Laila和Janus是我最初的两个学生。看到试听课的基本信息后,我迅速上网查了弟弟喜欢的pokemon,并结合课件内容,做了道具。正式上课前,衬衫、运动衫试了好几套;出门不抹口红的我,为了在镜头前显得更精神、年轻一些,擦了粉底涂了口红;提前开了电脑检查上课的系统,还在桌上摆满了玩偶、卡片和道具,以备不时之需。
“你们好,我是晴晴老师。”声音有一点点发颤,但强作镇定,“晴—晴—老—师。”放慢语速又说了一遍,还挥了挥手。
Laila和Janus是中德混血儿,姐姐Laila在上海出生且生活了好几年,弟弟Janus在家也常说汉语,于是在基本信息沟通后,我选了一首“问答歌”来上。
“我要画!”弟弟抢过画笔。
“晴晴老师,我知道我知道,海里浪花不结果。”姐姐举起手,兴奋地大喊。
......
上完课,和妈妈沟通后,退出教室,感觉自己浑身冒汗,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
当天,还没收到试课报告,妈妈就已联系课程顾问买了课。初战告捷,我在心里得意自夸了一番,毕竟我可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科班毕业呀!
趁热打铁,扣除必须要去语言学校的日子,我几乎开放了自己所有的空余时间。试听课接踵而来,美国的、新加坡的、荷兰的、希腊的......学生逐渐多了起来。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讲起那些个学生如数家珍。先生一边听着我眉飞色舞地讲我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学生们,一边少有严肃地说道:“你这样是不行的,至少一周要留两天完全休息的日子的呀!”
因为缺乏经验,又正在“蜜月期”,在开放可预约时间时,我压根就没想到要预留休息日,但看着月历上此起彼伏地标注着“周一9点峻峻”、“周二22点Aili”,“周三9点佳恩10点Thomas13点Linda15点美琪”......我仿佛欣赏一幅蒙德里安的作品,很是满足。
备课上课改作业成了生活的日常,学生是崭新的,课件是崭新的,连我自己似乎也是崭新的。
没过几月,K机构专门发了一篇关于我的公众号。既兴奋又心虚,自认为还是底气不足,于是特别怕有家长看到这篇推文来找我上试听课,可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果然荷兰的一个妈妈指名道姓要我上课。
试听课前几天,很是焦虑。线上中文教育机构很多,我猜想她找到我,一定是之前试课时遇到很多不理想的情况,但我这样一个没有自己孩子的新老师,并没有足够的经验来驾驭各种情况的孩子呀。感觉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审视的,善意的......“不能让人看笑话”是我的倔强,于是脑子时不时地在盘算这节课怎么上,备课时也预备了好几个课件和备选方案。
试听课时,因为妈妈本来是答应带学生去游乐场的,但因为上这节课,他们要晚出门,学生很抗拒。妈妈骗他不是上课,只是认识一个声音温柔的新姐姐,但儿子还是不愿露脸,于是妈妈非常抱歉地说,可能要下次了呢。我一边说没关系,一边不死心,拿出一个teddy熊,对着它讲起故事来。学生在门边躲闪着露出脑袋,于是我接着继续夸张地“演”,学生渐渐移步到电脑前,弱弱地回应了一句,又躲到桌子下面去了。
妈妈在边上给我竖起大拇指,然后我调大音量,播放狮子王片段,学生探出了脑袋,我立即然切换到课件,用手势和黑板的圈画功能,学生开始跟着我“按部就班”了......虽然最后这个孩子没有成为我的学生,但课后交流中,妈妈的认可让我特别有成就感,是那种“跳一跳摘到苹果”的快乐,仿佛我又打赢了自我挑战的一战。

初期的紧张之后,我开始享受给孩子们上课时纯粹的快乐。
“晴晴老师,我最喜欢小马了。”戴着一顶独角兽发饰的Anna扑闪着一双大眼睛,“你看你看,这是我的小马,它可乖了!”迫不及待地给我看她在马术俱乐部的照片,还不放心地问,“你看得清吗?”
“看得清看得清,这匹小马好像也很喜欢你呀!”
“那你能告诉晴晴老师,螃蟹是怎么走路的吗?”
Alice突然跳到身后的沙发上,双臂侧平举,双膝向外侧弯曲,左三步右三步,如横着走的螃蟹,活灵活现。
“哈哈哈!”我不顾教师仪态,大笑,真是太可爱了呀!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能见面呢?为什么她要把他们分开呀?为什么......”Malaike仍在打破沙锅问到底。
我每每被这样的童真无邪逗乐,被这种迫切要和你分享什么的一本正经的样子感染。孩子眼中的世界是彩虹色的,他们的“我想即我说”不掺杂成人世界因各种顾忌而形成的拐弯抹角,好就是好,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开心就是开心,这是我在高职院校的讲台上不曾体会到的。
“晴晴老师,马上中秋节了,我们推出了一个‘月球任务’的主题课件,想请您来上,不知您有兴趣吗?”
“好呀好呀!”我立即答应了。
浏览完课件,我不由一阵激动。以月球来信为轴,把嫦娥奔月、人类探月以及和“月”相关的歌曲和诗词都串起来了,这个构思也太棒了吧。我把授课对象分为低龄组和少年组,在网上搜了简繁体两版的神话故事视频和用乒乓涂黑来演示月相变化的视频,制作了中秋风俗习惯的ppt,查阅了人类和中国在探月过程中的成绩,最后还请教了教育专家,请他评点我的整个课程处理。
中秋节前夕,正式上课时,我自己感觉整节课行云流水,即使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课堂气氛的热烈。
我发现自己似乎更喜欢备课的部分。搜集信息,绞尽脑汁去想更好的呈现,过程中既有新知,又有被验证的收获。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对备课更上心了。
有的小朋友,会用动作演示一个东西的样子,于是我设计了“你演我猜”的游戏;有的小朋友课后总要和我玩九宫格,虽然每次都是我惨败,但受他的启发,开发了“汉字五子棋”和“大富翁”的游戏;有的小朋友,“春夏秋冬东南西北”总是混淆,我借鉴“找你妹”的游戏,把这些字用不同字体和颜色做了处理,用倒计时的方式让学生边找边记;有的小朋友汉字总是记不住,又不愿意写,于是我研发了“笔画/部件乐高”游戏和每天十分钟的作业纸,收效明显......
教学相长,说的就是这些吧。我在一次次尝试和探索中,感受到一股“心流”。

暑假到了,不少学生加了周课时,课表更“丰满”了,相应的,我自己的时间更少了。遇到三节课连堂的时候,激情抵不过疲惫,下了课,一句话都不想说。
一对一的课程,即使上过的课,因学生不一样,我备课时总会做些调整或补充。另一方面,还有自己没有上过的课需要花时间备课,学生中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我也想花时间做些研究和探索。但是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时间,也静不下心来去做这部分的工作。感觉自己被这些课困住了。
支离破碎的课表,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段让自己沉淀做研究。突增的课量,将每日除却三餐和睡觉,直接划分为上课和备课,日复一日中,疲乏感时不时袭来,觉得自己像一台上课机器,年中无休。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三尺讲台”吗?
“啊?你为什么还要额外做课件啊?”
“有时候是觉得这样能说得更清楚,但更多的时候,因为学生个体不同,作业中出现的问题不一样,总要课上有针对性地再强调操练下吧!”
“你只是兼职老师好嘛,这点课时费值得吗?我就是课前五分钟过下要上课的课件,如果遇到上过的,我点开就上了。你这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
同事在群里给我支招,诚然,我也是可以这样上,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是的,是我良心上过不去自己这道坎,但我好累啊。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教师是一个良心活,特别是面对低龄的孩子,他或许能感受到老师是不是喜欢他,但是分辨不出一堂课的好坏,或者对他们而言,上课上得开不开心就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晴晴老师,不想上这个,我们玩游戏吧?”小布央求道。
“那我们先玩个游戏,回来再继续,好吗?”
“不好!不要!”
“晴晴老师,我要听歌,就是上次那个有点难的歌。”Tatita突然说。
“那听一段,晴晴老师提问,答对了再继续好吗?”
“不,我要听!”
时不时遇到这些状况,也是让人头痛不已。我自己额外精心准备的课件,学生常常并不领情,“不要,不上这个”,相反的,那些给他们调剂用的短视频或游戏,他们可以每节课都要求重复,乐此不疲。到底是学生开心更重要,还是保证教学质量更重要?我的付出,意义在哪里呢?
我和我的这些孩子们“相爱相杀”着,尤其是,Chloe和她的妈妈深深刺痛了我。
第一节上完,Chloe凑到屏幕前,一张纸上扭扭捏捏地写着“我 ♥ Jane老师",瞬间被融化。于是我成了她的第二个中文老师,每周三节课,从level1上到level3。她的听力不错,习惯用词语或短语来回答问题,喜欢被鼓励,喜欢动画片,不愿意写字,于是我常常用她喜欢的小猪佩奇视频片段,锻炼她整句输出的能力,批改作业时也特意加上简笔画以表扬她汉字写得认真,希望她能再接再厉。
level 1升级到level 2那天,我给她写了一封信;level 2升级到level 3的那天,我送给她一幅卡通肖像画。就这样,我们一起上了近一百节课。
某一天,“嘟嘟,嘟嘟”手机提示音不断,一连串的课程取消通知,等我在系统一一核实后,发现Chloe不仅取消了当天之后的所有约课,而且妈妈还退出了企业微信群。好奇怪啊!这个太不正常了,毫无征兆。
我找了学管老师,才知道Chloe说她再也不想学中文了,妈妈一时生气,做了以上这些操作。可是为什么呢?明明学得好好的呀!
我又找学管老师,询问我可以做些什么,学管也说不清状况,只说安排了其他老师再试试。我又去看了近几次课程的回放,试图找到些蛛丝马迹,但无果。晚上躺在床上,脑海里都是这件事。翻过来,哎!睡不着,为什么突然就不愿意学了呢?翻过去,哎!睡不着,是不是我教得不好呢?
第二天一早,我给Chloe和她的妈妈分别写了一段文字,请学管老师转交,但再无下文。后来我看了新老师上课的回放,Chloe看着很喜欢的样子。课程结束,相似的一幕出现了。Chloe递上一张写着“我喜欢玮玮老师”的纸条,还用手比划出一个心的样子,妈妈在边上补充道:“这几个字昨晚练了很久。”我感觉自己被那么小的小孩“套路”了,只感慨自己怎么那么傻。
“老师,您上得很好的,Chloe很喜欢你。真的,不像之前那个老师,只会不断push她,让她说说说,很呆板.......”妈妈一脸讨好地说。
立马关了回放,愤怒,如鲠在喉,想到自己担心得睡不着觉,想到自己真心实意写的那些文字,只觉得一阵恶心。

Chloe事件的“蝴蝶效应”还在,我越来越困惑于教师的本分,每次上课都像赖床的孩子被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叫着起床,不情不愿拖拖拉拉地掐着开课前15秒进教室。是职业倦怠吗?可我才干了大半年。
除了刺痛老师的学生,还有只提出要求不提供支持、可能还让你违背良心的机构。
峻峻是我在L机构的另一个学生,来自美国,父母开餐馆,生意繁忙无暇顾及,平时都是奶奶照顾,奶奶不会说英语,因此,峻峻的汉语日常口语很不错。在他课时包快要用完的时候,学管老师找到我,希望可以和她一起努力,让峻峻妈妈续费。但我自己觉得,这个注重口语表达的版本不适合他,而之前我提出让他换一个版本试试,被公司拒绝了。如果再让峻峻妈妈续费,不是说峻峻学不到东西,而是他本可以学得更好,却被我们耽误了。
我一边“嗯嗯啊啊”地敷衍学管老师,一边很艺术地告诉峻峻妈妈什么才是更适合峻峻的。学管老师又给峻峻做了一张课程表现的奖状,并告诉我可以多试试这样的方式,孩子很喜欢。“表扬”不是这样做的,我被激怒了,于是我违反规定,私自加了妈妈的微信,课后直接语音坦言课程对峻峻的局限。
有时候,做个不听话的员工,真好,哈哈!
但我不能每次都这样做。Chloe和峻峻两件事在一个月里先后发生,我一边自我寻找着情绪出口,一边如坠云雾:L机构的这波操作显然是资本导向下的教育价值观,作为一个只是单纯地想上好每一节的老师,如何在这个中间找到平衡点呢?
或许,是时候做些改变了。L机构的薪资改革最终成了“导火线”。我递交了辞职报告。交接完手头的学生,顿时一阵轻松。
K机构的兼职仍在进行,但我有了时间做一些自我的探索——
我再次打开K的课件,试图研究其内在的逻辑和局限,找到华裔孩子学中文的最优版本和切实可行的方案;我回放自己的教学视频录像,一边做课堂反思,精进教学技能,一边找寻过程中自己真心享受的部分;我重新翻开了《现代汉语》,开始关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各类讲座和其他线上机构的公开资源……
我还突破自身的边界思维,联系了所在省区的图书馆,成功举办了一个中国新年小展和一个故事分享会,我期待用这种方式接触当地学习中文的潜在用户。
经过一番考察,源于对“双课制”的好奇,我应聘入职了Y机构,但严格控制可授课时间,却收获了意外惊喜。虽然一样是线上的教育培训机构,一样是兼职教师,但作为教师被重视的程度太不一样了。
“晴晴老师,我也正好在考虑桉桉的课程安排。他的试听课,我观摩了一下。课上让孩子开口说了不少话,但是从教学目标达成得如何这个角度,我感觉还是可以再想想的。比如,思考一下,经过这一节课之后,孩子做到了哪些,哪些没有做到,为什么?或者您先看看课程回放,然后我们再约个时间来讨论一下?”某节试听课后,开发这套教学课程的M老师给我留言。
“晴晴老师,这节课整体是没有问题的,看别人上课总是会有一堆意见,自己上时还不知道会如何,所以您别介意。”
“不会不会,我很喜欢这种方式。您是在帮助我更好地成长。我刚才看了回放,我自己感觉,问题在学生掌握的熟练度上,这个也是我自己比较困惑的点,口语课的标准到底是能说会说,还是流利地说......”
这些关于课程本身以及教学方法和技能的讨论,让我感觉,有集体的感觉真好!
“晴晴老师,跟家长沟通过了,家长对课程是满意的。我们也建议了弟弟的课更适合用YCT这套教材,因为弟弟更适合对外汉语教程,但姐姐用我们现在的启蒙课件和《中文》课件是可以的。家长对机构和老师都认可,但因为单亲妈妈带两个孩子,价格是主要因素。他们也试过L的课,报价比我们低很多,所以现在比较纠结,但我们也会根据家长的特殊情况商量是否做特殊处理,确定后,联系您。”
类似这些从学生个体出发,关于课程真心的推荐,不以卖课为唯一指标,也让我觉得我们在价值观上的相似。
“晴晴老师,我们想了解下现在的课件,您使用下来有什么问题,如果您还要做课后拓展,具体是哪些?因为我们现在并不能支付老师有竞争力的课酬,就不能过多在课堂之外要求老师有更多的付出了......我自己是老师出身,我知道备课量,所以希望尽可能地减少老师的负担,能让他们专注于课堂和教学本身就好。”
一个季度后的常规沟通中,M老师这样对我说道。这种对老师付出的认可和尊重,对待教育的严谨,都让我心生好感。我似乎有了归属感,也找到了坐标。
移居挪威,最大的改变是我终于有时间能相对抽离地进行自我探索。这一年的线上教学,算是自我探索的一部分。很幸运,它告诉我,自己是胜任“三尺讲台”的,也是真心喜欢的。但线上教学在课堂效果上终究是打了折扣的。师生互动方式单一,缺乏面对面的实践活动,学生之间无法互助和交流,学习氛围也不尽如人意。我给当地的高中写了封求职信,想毛遂自荐做一名线下的汉语老师。我想象着,美丽的挪威峡湾旁,一群少男少女,从“你好”开始,即将因为我而打开关于中国的一扇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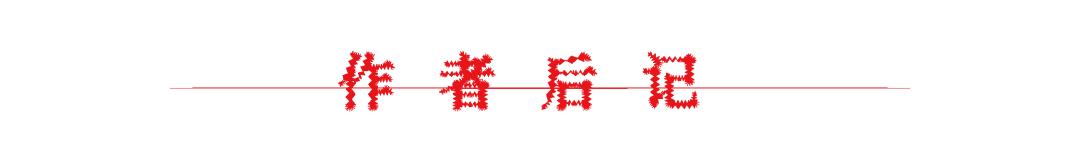
线上教学是我很想写的一个故事,经历的远比现在呈现的多。成稿不是我满意的,写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但完成的感觉很好。如“生命即叙事”,“写”的本身,是对自己的梳理和探索,我想这就是意义吧。我会继续写下去。
原标题:《我在挪威教线上汉语这一年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