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UABB侧记|城市冬泳:一头扎进这城里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这个属于南方的展览既搅动着一场关乎理想的志向,又始终克制在没有答案的发问里。实际上,众多城市及城市化问题,皆总以讨论开始,讨论结束。行动者更多的是在现实面前,破路而行的人民。本届双年展置身于一个拥有1700年历史的古城内,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因城市化演进而来的城中村。交杂的身份与混乱的秩序下,这个临时的庞然经验突然闯入城内的日常生活里。以此侧记,收集这人与城所变化的表情。
城墙已经老了,城还要继续下去。
新城与旧市
南方的冬天,一点都不冷。
就像这个城市永远的口号,永远热火朝天,永远奋发向上。


这种让人产生混淆感的变化充斥在整个南头古城内,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开幕后,那些截然不同的日常,出现在同一时空里,新的体验正在等待被习惯。
就在半年前,还是春天的时候,我们在古城内取景。租客、厂妹、舞狮队,与所有城中村一样,人物的背后是这个时代大多数的故事,他们从不孤独,他们属于某个集体,并相互怜悯。低廉、亲切、所需所想可以立刻动身,这是这里的好处。但比它们更快的,可能是这个城市更新的速度。
整个城变成了两个部分:正在改造的,与未改造的。
在2009年第三届深双上,策展人欧宁的展览叙事中,用“造城热”概括了在深圳肇始的新经济运动,房地产和服务业崛地而起。这种建造模式,也一路从自上而下的宏大的叙事规划,慢慢演变成加速的更新迭代。这个城市明明不是才刚建造完成吗,为何要如此着急寻找下一次高潮的领地。
一切都要够快。

本次深双的建筑改造以“起承转合聚敞隐”为叙事逻辑,比起垂直行进的购物城(shopping mall)地标,这里更像舒展开来的油布,可以一路通行。从城门开始,进入重现的“瓮城”,以武陵人的姿态穿过城门,进入川流之岛般的城中村,密集的楼房里隐藏了几栋改造后的建筑,修补、重建、再造、更新,以及合情合理的仪式感。
有新的土壤运进来了,它们成为了异形的风,吸引着好奇的目光。建筑由一种不涉及文字的实际行为(去做!),发展成一种知识框架和智力行为(去想!)。房子的本身承载了更多回声,包括思考与争论,质疑与探询。围合的城池早已四通八达,人流汹涌。丰盈的街市生活撞破了空间,也自成结界。城中村里万物万用的秘籍就此显影,横亘的衣叉、联排的遮阳伞、路中央的麻将桌、裹上塑料条驱赶苍蝇的电扇、溢满水的贝类……城中村内的街道就像城市的私生子,这是一个既有界也无边的地方,从零到零,被日常之物所占领,它又属于此间的人民。
“报德广场”原为水磨石的篮球场被围合成剧场的形式,两栋嵌入的建筑从顶部朝向广场逐级跌落,形成观众席,采用具有广东特色的定制陶砖。广场的美学源于中世纪的意大利,空间统一的热情被灌注了诸多艺术的徽章。而作为社区的广场,是生命力的漩涡地带,也是街道的磁铁,吸引着过客驻足、交谈、参与及想象。
两栋建筑内部一个作为书店,一个作为展厅而存在。冬日阳光普照的下午,不少人坐在二楼的展厅内,面朝着广场,晒着太阳,抛出的视野带来了新的风景,但落地玻璃终究少了一种亲密,在倒影之中,看见的更多,是自己。

另一个与时代相连的建筑改造,是位于展场的西北端的“大家乐舞台”,作为上世纪80年代普遍的建筑类型,在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承担着自娱自乐的展演空间,以满足在附近工厂内工人的生活与娱乐需求,是深圳早期打工文化的见证。即便万历工业区内的厂房在展览前仍有流水线在运行,上千人的宿舍就在舞台附近,对于手机盛行的年代里,社交并不差一面之缘,兴奋与热切,都可在无形的网络中穿行。大家乐舞台,反而成为老年棋牌围观的地方。
改造后以升降的反光银色织物为幕布系统,转换封闭与开敞的空间。在展览开幕前一晚,剧场内的同心圆才刚刚漆好,几个工人在调试帷幕的升降问题。深圳速度的效率依然适用于此,旷时矿日,变化就在分分秒秒之间。唯有那来不及散去的油漆味在展场萦绕多天,留下了“新鲜”的气味。
东门的市场,与往常一样,临近中午和傍晚,依旧是柴米油盐的交换地方。丈夫在打游戏、儿子在写作业、闲聊瞎逛,赶在节目开始前回家,好吃的包子依然卖一块钱一个。
倘若市井仍然能够依存,这座新城才召唤出野火与生风。
围观与微观
左顾右盼,成为了很多第一次来的人的惯性动作。照相机代替了瞳孔,拍下只等同于看过,不算是看到了。
本届深双的策展板块分为了三部分:世界南方、都市村庄、艺术造城。除了五栋主展馆外,介入式的展览方式直接以游击术占据城中村的不同角落,冲出了美术馆或博物馆的空间之后,接近、触摸、话语、若无其事与时好时坏的天气,持续而不确定的围观宛如频闪的曝光,形成了每个人独有的个体经验。
在张永和的信息亭旁,展期赶工的工人搭起了炉灶;尤纳·弗里德曼的“街道美术馆”,成为了儿童追逐躲藏的最佳场所;刘家琨的西村贝森大院模型的房间,经常能听到“不要碰小人”的惊呼……这些同框的“意外”,恰似一种偶然的反介入。展览的公共性,某种程度就是小灾小难的综合体,增添那些不合时宜的人物与事件,回到原始又混沌的状态里,才是让艺术发生有了一宗土壤。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街头上涌出了猎奇的围观,闲逛的老人问出了终极的问题,“小伙子,你开心吗?”小伙子回答,“今天太阳很好呀。”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指出,城市中有些看似乱糟糟的地方,其实背后都有一种隐藏的秩序,在维持着社区和城市的活力。“电视机组”、“拖鞋组”、“糖水组”、“理发店组”、“窗户组”,这些物件的触觉变成了一种蠕虫的视角,审查着重审南头古城乱糟糟的日常。作为一系列的工作坊成果,“Mapping南头古城-超级乱糟糟”呈现出了他们多个月以来守候式的调查报告,有些观点十分有趣,比如以拖鞋划分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的边界守则在城中村内完全被打破,电视机的作为活动分布表的功能而在村中各种角落出现,理发店内的乡音是心理学中的亲密。
这些从古城观察而来的“蛛丝马迹”,在展场之内得到放大的检阅。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抽象的关系被具象的物件、符号、身体所呈现,他们从私人经验中来,又从公共的展示中寻找新的理解。簇拥而成的拖鞋装置在灯光下,形成了高低起伏宛如天际线的倒影,最小的光源有最大的悬念。
微观作为一种痕迹并不会转身被人忘记,相反会犹如线索一般镶嵌在这些空间的经纬深处。展览是一种寄存目光的行为,以生活的痕迹作为标本,路上有捡不尽的意义。
场所与居所
住在城市里的人,几乎不可能经历得过一个“家宅”的建造过程。他们只会感受藏在一纸合同里的惊涛骇浪。城中村无论是城是村,最大的特征仍然是像贴于鱼腹内的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在狭小的单人房内纵横交错,在城市搏动的心脏中央此起彼伏。来客在本质上都是陌生的,短暂、变换、易逝、交错,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现代隐士,都在快速地更替着身份,也快速地更替着焦虑。
南头古城的建筑肌理作为构成记忆法则的证据,保留着十字街区的传统街道法则,也有极具时代记忆的工厂印记,见缝插针的自建楼组成了暗涌四起的面相。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空间及秩序成为了这个地方发酵的场所精神,多疑且变幻,丰富且混杂。
在本届双年展的介入方式中,在建筑空间维度上的店铺改造及升级,以街道生活为情境的艺术参与,都试图回应“城市即展场,展览即实践”的口号本身。怎么去理解这个场所里带来的平行体验,解决问题还是提出问题,秩序与混乱是现代性的根源。
“离开家并不意味着可以发现新鲜的东西,体验另一个时间或空间。生疏的事物往往邂逅于毗邻的街区,而熟悉的东西则出现在世界的尽头。”在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文化的困境》,每时每刻我们都在经历世界的位移。
对于以流动性著称的城中村而言,每一个房间都既旧又新,新世纪的游牧人民,正在从一个城中村辗转到另一个城中村里。以这些居所为展览,规划新的场所与情境,城中村嚼碎了干枯的事实法则,总以最大的弹性满足着上万人的憧憬。


位于春景街的“制造幸福” 由来自奥地利的林茨艺术学院空间的设计策略工作室,选取了南头古城内的一所废旧民宅。他们带着一系列的问题在开展前进入古城,翻新修整民宅的同时,“模拟”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购置了柴米盐油。布展的过程里,因为小灶需要摆在屋外头,偶然之间形成了截取人流的“路障”,大部分人在路过时都会探头扫视一番,企图窥视个中秘密。他们在观察城中村的日常特质,附近的村民邻居也在孜孜不倦地讨论他们的行径,“不是用来住的房子”,到底可以来用来干嘛?人与人之间的呼应,本来就可以靠问题而已行进。
开幕的当晚他们采买了本地的食材,在宅子内摆起长桌,邀请路过的居民参与这场西式“家宴”。居民大方地喝了一口汤,也掏出了口袋的槟榔邀请他们尝试。居所的情绪来自于居住者的想象,解决与发问,场所里栽植了不同的价值漂流。
在此之后,作为临时展厅的这个空间内仍然挂满了熟悉的城中村器物,同时有工作室留下的标识解说及速写记录,门口的相框内罗列了一系列的问题。场景已经消失,临时的“居所”已被拆解,这一系列被制造出来的“发生”穿过了生活的边际,成为了展览的本身。


建筑师属于最早加入城市空间的新规划、重组与转化的一群人。装饰性的改造的让“门面”受惠。比起庖丁解牛般的技法,更期待的是拥有永续的城市保鲜技术,将生机勃勃的城中村去除阴影,亮化起来。“功能”缩水的时候,往往要靠“形象“来补偿。在“世界|南方”的板块里,展出了亚非拉地区非正规的城市经验,所有规划都永远落后于贫民窟的自发生长,越精准,越失控。

说到底,从标签到氛围,从居所到场所,缝合出一个城市命脉的,是人与城之间无法停止的博弈。
参加与遗忘
观众掏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手机会收到一张电子门票,进入展场。这道虚拟的关卡不难,有时候有小猫小狗会偷跑进来,他们反而不需要领一张门票。
主展馆的空间曾经是个工厂,24小时流水运转,早晚两班工人维系着上面不断复制的成衣制品。展览只开放三个月,每天8小时的观看时间,周一闭馆,最后这里仍然会清空。墙面保留了众多痕迹,新的展前和标识,也有过去收信的地址与语句。墙上的风景吸收了叙事证据,每个空间都有平行的故事。


展览策划(Curatorial)的概念从一开始便是与所谓的“浪漫参与”无关的,因为它是由外或由上而下的决策;与此说策展人的工作是决定要展什么,不如说他们是要决定不展什么。


“图纸无法做决定,你只有站在现场进行决策。”
即便已经94岁,尤纳·弗里德曼还是坚持站在草坪上指挥着环环相扣的建筑元素,这是属于他经典的空间链结构(space-chain)。在这个结构之上的“空中城市”也应运而生,定义建筑的原材料是“虚空”,是“虚空之外包覆着表面使我们得以感知虚空,体量服从于不断变化的需求。”
与其说是建筑观点,尤纳 的创作更像是一次又一次西西弗的偏执前行。他的大部分构想都无法从纸张中剥离,无论是从上世纪到现代,依然走在未来的前面。乌托邦式的奇想,质疑、抵抗、逃亡、移动、上天下地的天空与街头,一直在印证“无秩序才是秩序”的抗争。
这一次尤纳在深双落地作品,被称为“街道美术馆”。设置在南门公园的草坪上,在空间链结构的基础上,利用从居民手中收集的物件,作为美术馆内的“展品”。共制而成的这个“建筑”最后在草坪的一角,成了小朋友穿行的小型迷宫。空间如果是自由的,参与将不必分类。
在刘庆元的壁画后面,一墙之隔是南头城小学,下课时走廊会围满了观望的学生,而在壁画前拍照的人也会将这群表情挤进相框。放学时,从北门进入展场的他们只是为了更便捷的回家,放大的惊奇在日复一日的围观里也逐渐演化成普通的习惯。不过仍然会在他们结伴而行的讨论里,听到“这个我看过,你进去过吗?”这样的话题。
工作日的展场,大部分时间都是空荡荡的,最多的观众反而是场内的工作人员:安保、清洁工、志愿者。他们有时会驻足在作品前,反复地观看着,试图找寻那些可以理解的语言。这些不自然的参与者,由直觉引领着他们的目光。


个体的经验如此珍贵,每个参加者有其自己的理解与想象,一个展览所能带来的,快速的热情与遗忘,恰恰变成了这个城市的日常对话。
一座城,有它的前身与后世。
在诸岛的面前,浪是公平的。
参考文献
欧宁:南方以南:空间、地缘、历史与双年展 — 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站全纪录 【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
(德)马库斯. 米:参与的恶梦 【M】,翁子健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法)侯瀚如:在中间地带 【M】,翁笑雨、李如一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
唐克扬:纽约变形记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德)马库斯. 米:参与的恶梦 【M】,翁子健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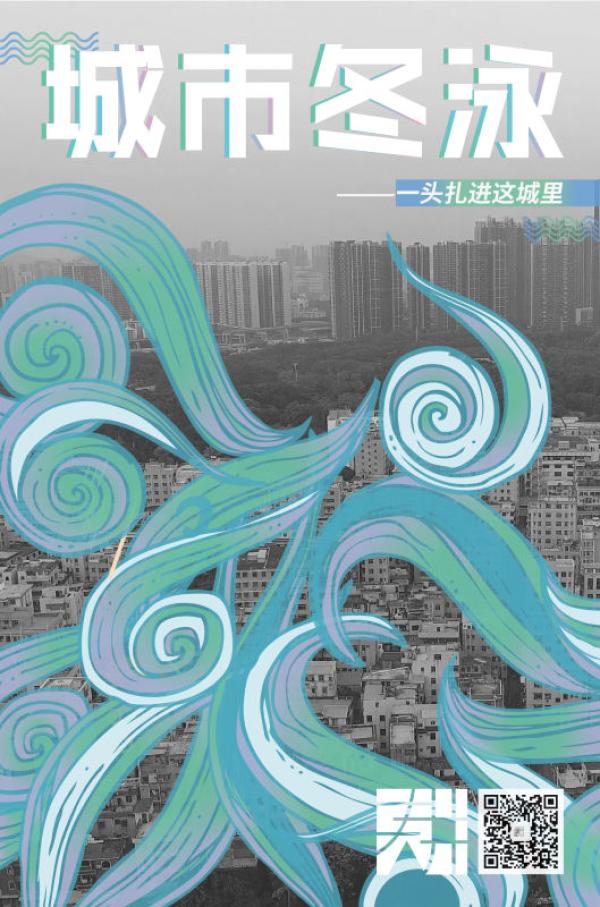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