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威廉•福克纳:那眼神确实不是针对他来的,像是仇恨整个人类 | 纯粹新书
原创 威廉•福克纳 纯粹Pura
野棕榈
作者: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斯钦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 2022-07
《野棕榈》是现代主义文学大师•意识流小说开山鼻祖之一,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长篇力作。
福克纳以音乐复调对位的手法,打通了音乐与文学之间的通道,在两个故事——《野棕榈》《老人河》的交替讲述中,构建起相辅相成、宏大深远、丰厚隽永的地理与时空的对位关系。整部小说像巴赫的复调音乐,获得了超越于两个文本之上的回声缭绕般的和谐美感,爆发出宏大深沉的能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纯粹君

威廉·福克纳(1897.9.25-1962.7.6)
野棕榈
Ⅰ
文 / 威廉·福克纳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有点不容分说的意思,却不莽撞。医生下楼,手电筒发出的光在暗褐色的楼梯上晃了几下后,停留在一楼大厅里那个棕色的木头柜子上。这是一座靠近海边的小屋,虽然小,但是也有两层,小屋里只有油灯可以照明——确切地说只有一盏油灯,晚饭后被医生的妻子拿到楼上去了。医生拥有三处房产:这座海边小屋和隔壁那幢屋子都是他的财产。不仅这两处屋子,他在离这四英里远的村子里还有一间更好的屋子,屋里装了电灯,墙也批得平平整整。从楼梯上下来的他只披了一件夜间穿的薄衫,而不是睡衣,这种和他身份不相称的简朴衣着,和他从来只抽烟袋而不抽雪茄,甚至从来都不愿意学着去抽雪茄是一个道理。他也抽雪茄,但大多时候是在星期天出诊时接过来病人递给他的雪茄,至于他自己掏钱买的雪茄,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一周最多抽三根—今年四十八岁的他,从十六七岁起就记下了(并且深信不疑)父亲常常叮嘱他的一句话:雪茄和睡衣是有钱人才会用的东西。
时间刚过午夜。即便窗户关得严严实实,门也上了锁,风很难进来,但医生还是感觉到了海风那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气味。他熟悉这种气味,不仅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出生——不是这所房子,而是位于离这里不远的镇子里的另一处房子——而且在这个靠海的州度过了大半辈子。这大半辈子包括他在州立大学医学院待的四年,他在那里完成学业,然后又在他一点都不喜欢的新奥尔良市做了两年的实习医生(年轻时他就一副憨相,身材微胖,手长得像女人,厚而柔软,总之看上去不像医生。即便已经在城市里度过了六年整的学习生涯,面上仍旧是一副从小地方出来的模样。打量他的那些同窗时,眼神里常常流露出诧异的没见过世面的表情。在他看来,他这些穿着棉布夹克,身材像麻秆儿,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同窗们和那些护士一样,虽然长相不出众,脸孔也各有千秋,但每个人的脸上几乎都带着一股不近人情同时又自以为是的神情。这股子神情是他们的招牌,像是身上常年挂着一个类似花环的东西)后,以不好不坏实际是中等有点儿偏下的成绩毕了业回到家乡,一年内便遵照父亲的遗愿和一个早早为他选好的姑娘结了婚。四年后父亲的房子也归了他,连带还有那间诊所,诊所在他手里虽没有做得风生水起,但也说不上萧条败落。又过了十年,他用积攒下来的钱买了这两套互相挨着的海边小屋,一套供他们两口子夏天度假用,另外一套则出租给观光游客或者来海边聚会、野餐、钓鱼的人。就是结婚,夫妇俩也没有度过蜜月,只是在结婚当晚去了趟新奥尔良,在新奥尔良的酒店里只住了两个晚上便匆匆返回。他和妻子同床共枕了二十三年,可至今没有诞下一男半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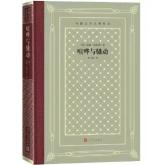
喧哗与骚动
作者:[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李文俊 译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07
虽然屋子里没有风,但医生还是判断出了大概的时间,因为那罐紧贴墙皮在冷灶上靠墙放置的秋葵汤散发出了馊味,汤肯定已经凉了——那是医生妻子早晨特地熬好,准备送给刚租下他们房子的邻居的。那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四天前搬到他们旁边的那间屋子里住下来,这两口子很可能并不知道住在隔壁的医生夫妇既是邻居也是房东。那女人黑色头发,高颧骨,下巴宽而大(刚开始让他想到“乖戾”这个词,后来觉得不如说是让人害怕),皮肤很薄,脸色憔悴,眼珠是黄色的,看上去诡异而倔强。女人穿一件旧毛衣和浅色牛仔裤,脚上趿拉一双帆布鞋,面朝大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张看上去很新但廉价的沙滩椅上,一坐就是一天,但从来不见她抱本书看或者做点其他什么。无须考虑那女人的皮肤和呆滞的眼神,医生(拥有博士学位,是正经八百的医生)已经意识到了这女人的健康出了问题——那是熬过疼痛和恐惧后的病人惯有的呆滞气色,不过那呆滞里似乎残存着一丝生气,仿佛残存的这点气息是留着倾听或者看着她身体里的某个器官如何逐渐衰弱下去,也许是一个渗血却无法修补的心脏?还有那个穿着无袖汗衫和脏兮兮卡其布裤子的年轻男人,脸上同样也是一副呆滞的表情。医生常常看见他光着脚,手里拎着用皮带扎起来的木头沿着海滩走回来,头上连帽子也不戴。要知道在这个地方,就算是年轻人也抗不住暴烈的阳光。男人经过屋前时,女人从来都是一动不动,连头也不转一下,很可能连眼珠都不带动一下。

《野棕榈》展示图
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医生对自己说。那两个人住进来的第一天,他曾经躲在那道隔在两座院子间的夹竹桃篱笆墙后面暗暗地打量过那女人,当时他就看出她不是心脏的毛病。对医生来说,他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并非是要为一个隐蔽、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找到答案,而是坚信他自己与揭示真相的答案之间只隔了一层面纱,就像在他和那尚有一丝生气的女人之间隔着夹竹桃篱笆墙一样。即使揭示真相的答案就在面纱后面,也让人雾里看花,难以辨认真相,更不敢妄下结论。医生并不认为自己这样的行为是在偷听或者窥探,就算是那样,他心里想的也是:我还有时间搞明白那女人究竟在倾听她身体里的哪个器官;反正他们已经付了两个星期的租金(作为一名经验丰富阅病人无数的医生,他觉得根本不需要几个星期,而是几天就可以搞清楚这件事)。他甚至想,那女人显然需要救助,这么看来他们碰上他这个做医生的房东算是走运,不过他又想到那两个人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是他们的房东,所以也无从谈起他们知道他是医生的事实。

海边的棕榈
帮着他出租房子的地产经纪人给他打电话时这样介绍这一男一女。“女人穿着裤子”,地产经纪人说,“我的意思是,不是女人穿的那种松松垮垮的裤子,而是男士裤,所以,有些地方对她来说尺寸小了点,男人肯定喜欢看她这么穿,可女人们受不了,除非她们给自己也穿这么一件。我觉得玛莎小姐不会喜欢她这副打扮的。”
“只要他们能按时付房租就行。”
“这个你不用担心!”地产经纪人说,“我看人很准的,不然也不会在这行做这么久。我一上来就和他们讲明租金必须提前付,那男人说没问题,问我房租多少,口气很大。身上穿条脏裤子,大衣底下只穿了一件衬衣的人在我面前装得那个样,好像他是范德比尔特似的。他从裤兜口袋里掏出一沓钱递给我,里面就两张十块的票子。我抽出其中的一张十美元还给他,对他说如果他们直接租下这房子,不要添家具,房租就能便宜点。结果他直接就说:‘ 没问题,没问题,我租了,多少钱?’我本来还想提提价,但一想到你和我说过,不愿意再给房客买家具我就没有说什么。我看这人就是想找一处能让他们马上安顿下来的地儿,四面有墙、墙上有门就行。女人一直待在出租车里等着男人,她身上的那条裤子对她来说有的地方确实显得过于窄巴了。”电话里的声音打住了。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嗡嗡声,医生心里突然有点得意,语气立时苛刻了一些:
“那他们到底要不要家具?那屋子里可啥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床垫是——”
“不要不要,他们不要家具。我告诉他们房子里只有床和炉灶,他们自己还带了把帆布椅,对折后可以放在出租车里的那种。我看这事儿差不多能就定下来了,他们不会再提出什么要求了。”和刚才一样,医生暗自得意,他心里对自己笑了。
押沙龙,押沙龙
作者: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李文俊 译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5
“那么,”医生说,“是什么?什么事情让你犹豫?”其实医生隐约猜到对方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是觉得玛莎小姐也许不会同意租给他们房子,倒不是因为那女人穿了一条那样的裤子,而是这两个人不是夫妻。哦,男人和我说他们是已婚人士,看女人的样子的确像结过婚的,他应该没有撒谎,也许他自己也是结过婚的,问题是,他们两个不是夫妻,那女人不是那男人的妻子。一个男人是不是结过婚,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女人,哪怕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或者随便是在哪里碰到的,莫比尔大街还是新奥尔良大街,对我来说都一样,我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不是——”
那一对男女当天下午就搬了进去。那间屋子,名义上叫作度假屋,其实相当简陋,屋里的床无论弹簧还是床垫都已旧得不能再旧。炉灶上只有一口平底锅,因为常年用来煎鱼,锅底上糊了厚厚的一层。与房间里唯一一把咖啡壶相配的是几把不配套的铁汤匙和刀叉以及裂着口子的杯子、碟子,喝水的器皿不过是几个原本装果酱和果冻的瓶子。再有就是那把沙滩椅,女人在上面一坐就是一天,眺望着对面的大海—海面上波光粼粼,晃来晃去的棕榈树叶子彼此击打发出干涩刺耳的声音——等着男人从海边回来,手里拎着从海边拾回来的木柴,走进厨房。两天前,那辆定期光顾他们这里的牛奶车曾经来过一趟,医生的妻子出去买牛奶时看见那男人手里拎着一条面包和一个鼓鼓囊囊的纸袋从位于海滩边的那间小杂货店(店主是葡萄牙人,原先也是个打鱼的)的方向返回来。医生的妻子告诉医生说,后来她看见那男人坐在厨房后门的台阶上(手忙脚乱地)收拾鱼,把阳台搞得乱七八糟。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尖酸刻薄,表情怒不可遏,好像她抓住了什么人的把柄似的——这就是他的妻子,一个虽然不很胖(至少没有医生那么臃肿)但已经谈不上有任何曲线的女人。十年前她的身材就开始走形,连头发和面色乃至眼睛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后者的变化不似身材变化那么明显——现在的她常年穿着一件家居服,灰突突的颜色像是专门为了和她灰突突的五官的颜色搭配而选的。“他把阳台弄得乱七八糟!”医生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厨房外面搞得那么乱,灶台上也干净不到哪儿去!”
“也许是那女人做饭呢。”医生委婉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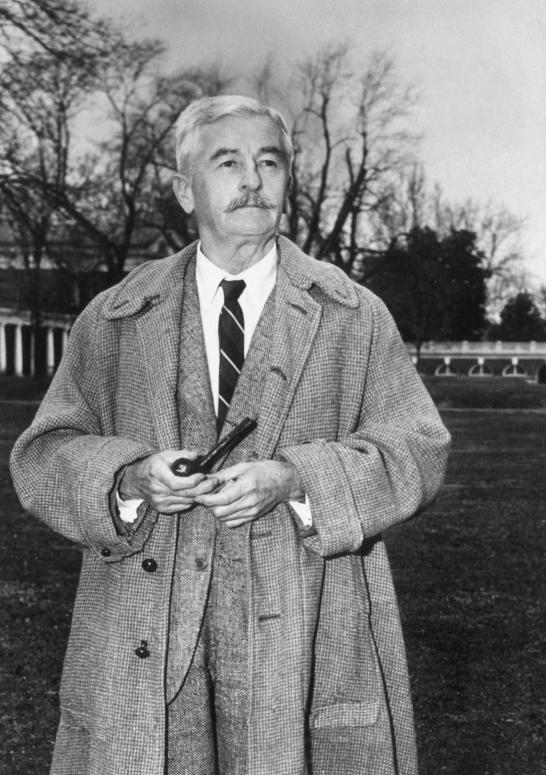
威廉•福克纳
“在哪儿做?怎么做?成天坐在院子里能做什么饭?你见他什么时候把锅灶给她端出去过?”其实医生知道妻子不是因为那女人不做饭而愤愤不平,她没有把真实原因说出来。两个人都知道,她最终也不肯说出“他们不是两口子”那句话,原因是不管他们中的谁先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医生一定是要赶走那一男一女的。两个人都不肯说这句话也许是因为内心的顾虑:如果赶走这两个人的话,首先从良心上说他们要退还租金给对方。面对这种状况,医生的使命感战胜了他作为一名乡下新教教徒(接受过浸信会洗礼)的道德感;对于医生老婆来说,也许是其他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或许医生也有)战胜了她身上的新教教徒的道德观。这也是医生的看法,原因是今天一大早他就被老婆唤醒,太阳刚刚升起,她身上裹着那件如同裹尸布一样的显不出任何曲线的棉布睡衣,灰突突的头发用卷发纸扎住站在窗户边上,示意他看窗外那个刚从海边回来,手里还拎了一捆捡回来的木头(用皮带扎得紧紧的)的男人。后来医生出门了,等他中午回到家时,看见妻子已经熬好了一大锅秋葵粥,分量多得足够十二个人吃饱肚子。医生可以想见她熬粥时一定神情严肃,带着一股会过日子的撒玛利亚妇女行善事的劲头,就好像她必须要熬这锅粥。哪怕心里不愿意也要委屈自己认真严肃地熬好这锅粥,哪怕这粥最后落个剩下的结果,不屈不挠地在炉子上待它个十天八天,一遍又一遍地被加热,直到两个从小生在海边长在海边喜欢吃金枪鱼、鲑鱼以及沙丁鱼(它们被离这里有三千多英里远的油脂厂屠宰,然后经过防腐处理被制成罐头)罐头而不是秋葵粥的人彻底消灭它。

威廉•福克纳的故乡密西西比河
医生亲自送粥过去——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的他手里端着一个盛粥的大碗(碗口上盖了一块平平整整、连一道褶子都没有的亚麻手巾,亚麻手巾看上去崭新挺括,还没下过水),挺着矮墩墩的身子笨拙地挤过两院之间那道由夹竹桃树组成的篱笆墙。医生这个笨笨的带着慈善意义的行为似乎表明他正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上帝给他的一个任务,而他之所以执行这任务不是出于对上帝的忠诚和对被施舍人的怜悯,而是出于责任和义务——他小心地放下碗,好像碗里盛的不是粥而是硝酸甘油之类的药汁儿。女人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甚至没有挪窝儿,只有眼珠动了动,像猫的眼睛。表面上看医生似乎只是一个面带憨笑且不修边幅的矮胖男人,但在这副面具下面,那双只有医生才会有的敏锐的眼睛警醒异常,什么都逃不过这样的一双眼睛。它们打量着那女人,严肃地、大胆地打量那女人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那是一张病入膏肓的脸,消瘦憔悴。事情清楚了,医生振作起来,却看见女人正用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盯着自己。他长这么大从没遇见过这样的眼神,里面像是酝酿了深仇大恨,但并没有针对性,性质反倒像是一个人因为心里高兴所以即兴朝一棵树和一根电线杆瞟过去的那种眼神。他(医生)不是给自己开脱,那眼神确实不是针对他来的,像是仇恨整个人类。医生想,噢,不是的,不是的,稍等一下,——那层纱即将被撕破,推理的齿轮即将咬合——妻子也许注意到了这女人的无名指上有戴过结婚戒指的印痕,但作为一名医生,他的观察自然更细致一些。
“这不是汤,是秋葵粥,”医生说,“我妻子熬的。她——我们——”女人没有任何从医生手里接过粥的表示,身子还是一动不动,看着医生皱巴巴的衣服弯下腰,小心地放下盛着秋葵粥的碗,还有托盘。
“谢谢,”女人说,“哈里,拿进屋子里吧。”说完便不再看医生,嘴里却又说了一句:“谢谢您妻子。”
福克纳作品精选系列(共6册)
作者: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蓝仁哲等 译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3
手电筒的光在前面晃着。医生下楼,一楼客厅充满了一股子秋葵粥的味道,门那边敲门声还在响着。医生知道敲门的人肯定是那个叫哈里的男人,他的这个推断不是因为预感,而是因为这四天来他一直在想着那女人的样子——医生现在的形象颇像国民喜剧演员,睡眼惺忪的他从散发着一股子霉味儿的床上(上面还躺着他那从没生过一男半女的妻子)爬起来,头脑里闪着隔壁那个陌生女人的眼神,一种没有针对性但是仇恨满满让人困惑的眼神。医生心里又涌起一种紧迫感,他想去探索那面纱后的真相,想揭开面纱触摸到真相,哪怕摸到后依旧不十分明晰,看到后还是不十分确定的真相。穿着一双老式拖鞋的他在楼梯上停了一会儿,脑子闪过一个念头:知道了,知道了,她是恨所有的男人,恨他们对她所做的事情,或者说是她因为相信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事情而恨他们。
敲门声再一次响了起来。敲门人应该是从门缝底下看到了手电筒的光,于是等了一会儿,看没人开门才不得不以陌生人的身份再一次怯怯地敲响了门板以寻求帮助。医生继续向门口敲门声传来的地方走去,但不是因为要去回应那再一次响起来的不请自来的敲门声,而是因为内心认为那敲门声正好应了这四天以来一直困扰着他,搅乱他的心神,让他无法不去想的一些问题;也许是本能让刚才陷入沉思的他重新向门口走去,也许是他的身体相信前去开门是为了揭开那层把他和近在咫尺的真相隔开的面纱,总之医生没有任何防备地打开了门:一个人的身影出现在手电筒的光里,是那个叫作哈里的男人。他还是像医生往常见到他时的装扮,脏兮兮的帆布裤子,无袖衫。黑漆漆的夜色里回响着强劲的风声,中间夹杂着躲在暗处的棕榈叶子相互击打的声音。医生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衣站在门口,不动声色地听着对方礼节性地说着这个时间还来打扰的话以及拜访的目的——借用一下电话,脑子里却俨然一个胜利者般地想。“不用,”他说,“你不需要打电话求助,我本人就是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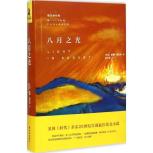
八月之光
作者: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蓝仁哲 译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03
“哦,”来人说,“您可以马上出诊吗?”
“可以,不过我需要穿件衣服。病人是哪里的毛病?这样我看一下自己应该带点什么。”
男人的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不决的神色,医生注意到了,但并没有在意,在过去的行医生涯中他没少见过这样的表情:求助的人即使面对具备技能和专业知识而且收费不菲的医生或者律师这样的人群时也妄图掩盖真相时的表情。。“她在流血,”男人说,“您去一趟的收费是——”
医生没有理会男人的问话,心里对自己说,“好的。”医生说,“你先等一下,要不你进来等吧,一分钟,一分钟我就能准备好。”
“我在这里等您。”男人说。医生不再坚持,转身重新回到楼上。当他踢踢踏踏地跑进卧室时,看到已经睡下的妻子这会儿又坐了起来,身子斜倚在床头上,默不作声地看着自己。医生急匆匆地穿着衣服,放在床边小桌上的灯把他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息。灯光把穿着高领灰色睡衣的医生妻子的影子投射在墙上,一张没有光泽的脸顶着一头用烫发纸束紧的灰色头发,影子像是蛇发女妖。在医生眼里,穿在妻子身上的每件衣服都有一种庄重的铁灰色,代表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任何人无法战胜的道德感,而这种道德感在这个社会无处不在。“嗯,”医生说,“说是流血。也许是肺出血。为啥我以前就——”
“我看多半他是用刀砍了他女人,要不就是给了她一枪。”医生妻子冷冷地说,语气里明显带着嘲讽的意味。“有一次我走近了看那女人的眼睛,光看眼神的话,我看她才是那个敢拿刀动枪的人。”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作者: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李文俊 陶洁等 译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03
“不要乱讲!”医生斥责妻子道。他把肩膀往里缩了缩,把两条背带套在身上。“就知道胡说八道!”他像是在自言自语,“都是些傻子,带着女人来这么个地方,去哪儿不行,来到海边上,密西西比河河口的海边儿上——需要我给你吹灭油?”
“吹了吧,不会那么快的,等那俩人把出诊的钱付给你,我看且要等上一会儿呢。”医生吹熄了油灯,在手电筒的光里走下楼,帽子和黑色医药包放在大厅的桌子上。那个叫哈里的男人仍然站在门口,只是这次他没有倚着门框。
“给您这个。”他说。
“什么?”医生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男人伸过来的手,低头看过去,那是一张钞票。他也只有这十五美元了,医生想。“不用,过后再说钱的事,我们得快点。”医生一溜小跑冲在前面,手电筒的光在地上跳来跳去。叫哈里的男人大步跟在他后面,院子有遮挡,风势还稍微弱些,等他们刚从那道被当作两个院子之间的分界线的夹竹桃篱笆穿过去,立刻被迎面而来的强劲的海风和风掠过棕榈树叶发出的唰唰声以及很久没有修剪过的盐草发出的嘶嘶声围了个正着。从隔壁屋子里透出来一丝微弱的灯光。“吐血了?嗯?”他问。夜色很浓,风击打着被夜色吞没的野棕榈树,强劲而持续,虽然看不见海,但是听得到海的声音——那是海浪冲刷海岬和松林发出的声音,声音不高,但持久而强劲。“吐血了吗?”
“什么?”男人说,“吐血?”
“没吐血?”医生说,“这么说只是咳嗽时有点血?就是说咳嗽时带点血丝,嗯?”

童年福克纳(中)
“咳血?”对方的语气显然不像在反问,也肯定不是认为自己的话可笑,因为他们正在说到的事情绝非可笑之事。医生犹豫了一下,表面上他没有停下脚步,那两条常年久坐的腿依然保持着一溜小跑的动作,跟在手电筒光的后面向透着微弱灯光的隔壁屋子跑过去。但在医生的心里,作为一个受过洗礼的乡下人,他确实犹豫了,不是对什么东西感到震惊而引发的那种犹豫,而是因为失望引起的犹豫以及失望后的某种惊诧:我需要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天真得像是生活在鸡笼里的小鸡?那层纱正在消失,一点点地消融,最后烟消云散,可是他现在却不想看到面纱后面的真相了。他知道自己之所以不再想看到真相是因为不敢,他不想在以后的生活中不得安宁,可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他听到自己在问那男人话,虽然都是些他不想问的问题,答案也是他不想听到的答案。
“你刚才说她在流血,是哪里流血?”
“女人还有什么地方会流血?”男人恼怒地嚷道,“我不是医生。如果我是医生,我还用花五美元找你?”
医生仿佛并没有听到他的话。“啊,”他说,“明白了。也对。”医生不再往前走了。他似乎并没意识到自己停住了脚步,风呼呼地吹着。“等下,”他说,“你等等。”男人站住了,两个人都站住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强劲的夹杂着棕榈树叶撞击声的海风吹得两人都有点站立。
“我可以付你钱,”男人说,“五块够吗?如果不够的话,能否给我介绍一个愿意出诊的医生,或者让我借一下你的?”
“等等,”医生说。,他想:你们不是夫妻,可是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这些呢?医生并没有说出他心里所想,只是说:“你们没有?你们不是……你是做什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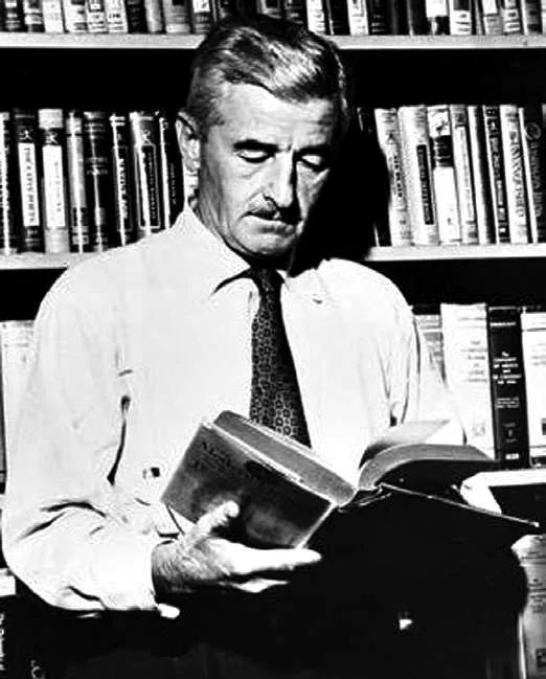
威廉•福克纳
男人似乎快要给风吹得站不住了,因为个子高,他其实是自上而下地看着医生,他的脸上明显表现出克制不住的不耐烦的神色。那座小房子隐没在黑乎乎的夜色里,从里面透出的灯光与其说是从窗户或者门里发散出来的,不如说像是一小绺颜色暗淡且透着悲凉色彩的布条,只不过这是一小绺在风里岿然不动的布条。“什么?”来人说,“我是一名画家。你问的是这个吗?”
“画家?可是这里没有工地,经济这么差,没有工程,九年以前这里还不错。你的意思是你手里没有任何工作邀约或者合同就跑来了?”
“我会画画,”男人说,“我以为我来这儿能找到工作……好了吗?我能借一下电话吗?”
“你会画画。”医生尽量用平淡的语气掩盖他内心的讶异——他不知道的是三十分钟以后这种讶异会变为愤慨和失望,甚至以后的几天他会在这种愤慨和绝望的情绪中摇摆不定。“不说这些了,这会儿她可能还在流血,走吧。”两个人继续向那间屋子走去。医生第一个进屋,他之所以在那一瞬间抢先进到屋子里是因为他觉得只要那女人在屋里,两人之间最有权利进到屋子里的人应该是自己,不是因为他是客人,也不是因为他是房东,而是因为他是一名医生。风声被隔在了外头。叫哈里的男人在身后关上门,门把那压过来的黑乎乎没有重量但又强劲无比的风隔在外面。医生马上闻到屋里有一股冷秋葵粥的馊味。他甚至知道那锅粥在屋子里的什么位置,它被放在厨房的冷灶上,原样未动,里面的粥还是那么多,没有人吃过,他对这间屋子的厨房很熟悉——灶台破旧,有数的几个可以做饭的家什和几把不配套的刀子、叉子、勺子,喝水的器皿不过是曾经贴着俗气标签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草莓酱或者腌黄瓜的瓶子。作为屋主,他为建造它出过力——风从单薄的墙壁(墙与墙之间是叠加搭建的,而不是像他住的那间屋子,墙板之间是榫槽结合的,接口处的复合板在潮湿的海风的风化下已经开始扭曲变形,像是春光乍泄的破丝袜或者裤子)吹进来,像是幽灵在喃喃自语。这房子已经被出租了三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他(不是他妻子)一直对租客的行为佯装看不见,只要这帮有男有女的租客的总数是奇数即可;或者露宿的男女本是陌生人却声称他们是夫妻,他和妻子都是一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态度。正因为如此,这种愤慨的情绪只能让明天乃至以后的他感到怅然若失。

喧哗与骚动
作者:[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方柏林 译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06
从房间的门缝里泻出一星昏黄的灯光。其实不用借助灯光医生也知道女人在哪个房间,他知道那张破床,妻子曾说过即使对方是一个黑人仆人,她也不会叫她躺在那上面睡觉。医生正要进入房间,突然听见自己身后那个叫哈里的男人光脚踩在地板上的动静。他想,我其实并没有多少权利进到这间卧室里,想到这儿他突然想笑。医生停住了脚步,对方也停住了:医生感觉好像有一双眼睛正在一动不动地盯视着自己,仿佛两个人同时停下脚步是在礼让一个影子,让那个最有权利对这件事义愤填膺但此时却不在场的丈夫的影子先进到卧室里。这时从屋子里传来女人的声音——像是酒瓶碰在玻璃杯上的声音,两个人这才不再犹豫。
“等我一分钟。”叫哈里的男人说道,随即快走几步先走进那个房间。医生没有跟进去,他看着那张沙滩椅,上面挂着女人那条褪色的牛仔裤——该大的地方却偏偏很小的牛仔裤。屋子里传来男人光脚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好像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说着什么,听得出他很紧张,但他的声音一直不高,不仅不高,还很温柔。医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女人的脸上没有痛苦和害怕的神情,那个男人显然在承担这些,就像医生看见他时,他手上总是拎着那捆用来烧火的木柴并且用这木柴为女人生火做饭一样。“别,夏洛特,”男人说,“别下来,你不能这样,回到床上躺着。”
“为什么不行?”是女人的声音,“凭什么不行?”医生听见两个人在纠缠。“让我走,该死的坏蛋,”(医生相信自己听见那女人好像说的是“拉特”,那应该是人或者物的名字)“你答应了,拉特,我就这么一个请求,你答应了。因为,听着,拉特——”女人的声音突然变得神秘起来,“不是他的原因,你明白的,不是那个笨蛋,不是韦伯。我欺骗了他,就像我欺骗你一样。孩子是另外一个人的,我的屁股和那些人的肚子一样可以做证,反正谁知道婊子做的那些事呢——”医生现在听到的是两双光脚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像是光脚的人在跳舞,舞步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然后不跳了,女人的声音恢复了先前那样,不再诡异。?医生想,为什么不害怕?“天哪,又开始痛了。哈里!哈里!你答应的。”
“我在这儿。没事的,回到床上躺下。”
“给我喝点那东西。”
“不行,我说过了,不能再喝。我也告诉过你为什么不能喝。疼得厉害吗?”
“我不知道,上帝。我不知道,给我杯酒,哈里。也许一会儿就流出来了。”
“不会的,现在不会了。太晚了。医生来了。他会帮你的。我给你穿上衣服,让医生进来。”
“我就那一件睡衣,会给血弄脏的。”
“没关系,衣服就是用来穿的,很快就会好的,穿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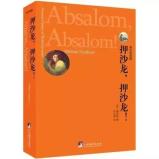
押沙龙,押沙龙
作者: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李文俊 译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05
“可是为什么要请医生呢?干吗要花那五美元?哦,你这个傻瓜——不要,不要走得太快,又疼了,慢点,我疼。疼得厉害,哦,不行了——”女人说话的声音像在笑;音量很小,听上去干巴巴的,又像是干呕或者咳嗽时发出的声音。“就是那儿,那儿疼。像是掷骰子,一会儿七点一会儿十一点。一直说话的话也许会好点儿——”他(医生)听见那两个人的脚在地板上蹭来蹭去的声音,还有弹簧床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女人一直在笑,声音很低,但里面有一种不认输的绝望,让医生想起今天中午给她送秋葵粥时她斜睨过来的眼神。医生站在阳台上,手里抓着他那个看上去又皱又旧的黑色出诊包,眼睛还是盯着那张沙滩椅,椅子上堆了一大堆衣服,那条褪色的牛仔裤也在其中。很快,那个叫哈里的男人从屋里冲出来,从那堆衣服里拿了一件睡衣后重新消失了。医生看着椅子,是的,他想,这时那个叫哈里的男人再一次出现在。
“你可以进来了。”他对医生说。
(未完待续……)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原因为"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他一生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与12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15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的故事都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其主要脉络是这个县杰弗生镇及其郊区的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若干个家族的几代人的故事,时间从1800年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系中共6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在各个长篇、短篇小说中穿插交替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 他以长篇和中短篇小说见长,他同时也是一名出版诗人和编剧家。大多数福克纳的作品背景被设定为他的故乡密西西比河流域,同时他也被认为最重要的南部作家之一。与马克·吐温、罗伯特·潘·沃伦齐名。他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福克纳从1957年起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驻校作家,直到1962年去世。
原标题:《威廉•福克纳:那眼神确实不是针对他来的,像是仇恨整个人类 | 纯粹新书》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