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项静:从博物到非虚构:自然生态写作的一条路径 | 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专栏
原创 项静 文学报
兴安(作家、评论家)
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专栏

“中国当代的自然文学,尤其是生态文学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论据和方法舶来品居多,自主者鲜少。所以,研究自然文学或者生态文学,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也应该根植于真实的个体经验和国家经验,从而真正建构和完善中国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
讨论还要继续,还有诸多高论将陆续推出,欢迎更多的评论家、作家以及热心读者参加到这场讨论中来。”


从博物到非虚构:自然生态写作的一条路径
文 / 项静(青年评论家)
在生态和自然的写作之中,固然博物、科学和实践性的方面能够让我们更容易辨认出它们的身影,我们还应该在其中看到国家、族裔、文明、政治、经济、信仰、阶级、性别、趣味和人性等等与今日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自然写作、生态写作是近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引起讨论的重要话题,议论的兴起有诸多理由,全球疫情下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态的重新思考,长期以来笼罩全球的生态危机在文学中的反应,或许还有对以人类为中心叙事的日渐疲态。具体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我比较认可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一书中的判断,“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唯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在文以载道占据极大优势的社会环境中,以自然为取向的文学往往不是作家们的首要选择,尤其在危机重重的近现代历史发展中,鲜少看到自然万物显赫的存在。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在生活中抽取出的中国人观山玩水、看云鉴石、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的欢愉和世情,由于关于中国生活艺术的写作初衷是介绍给西方社会,自然多了一层滤镜,但生活本身确有这些组成部分。万事万物有时候还是一种标明姿态的写作策略,比如周作人的《草木虫鱼》立在刚勇与空洞之间,“我在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便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在博物和趣味的方向上,中国当代青年写作者非常自然地承接了“与万物荣辱与共”的面向,比如盛文强的《渔具列传》《岛屿之书》既有地方生活的记录,又有海洋动物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考察;沈念的《大湖消息》记录了作家多次去往东洞庭湖湿地、长江集成孤岛的见闻与思考,描述了候鸟、鱼类、麋鹿、江豚等生物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遭际,呈现洞庭湖区人与物的复杂纠葛,向人们描画大湖的过往与新貌;在豆瓣上成长起来的作家邓安庆《永隔一江水》、沈书枝《八九十支花》等作品,他们对树木花草,晨露夕阳与其间的人物付出同等的情感,人事与风景、动物、天气同体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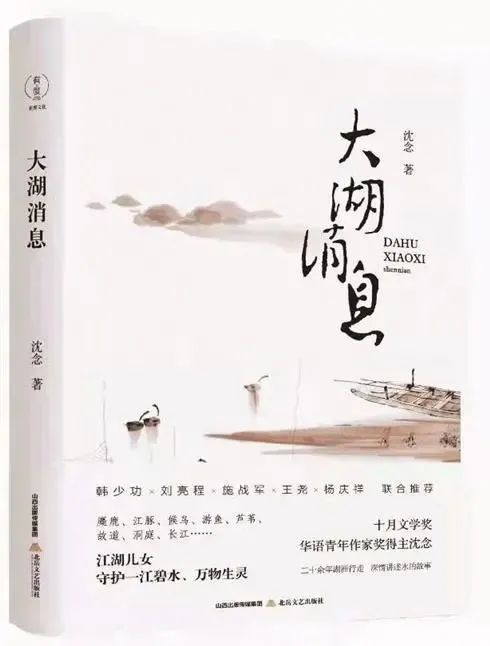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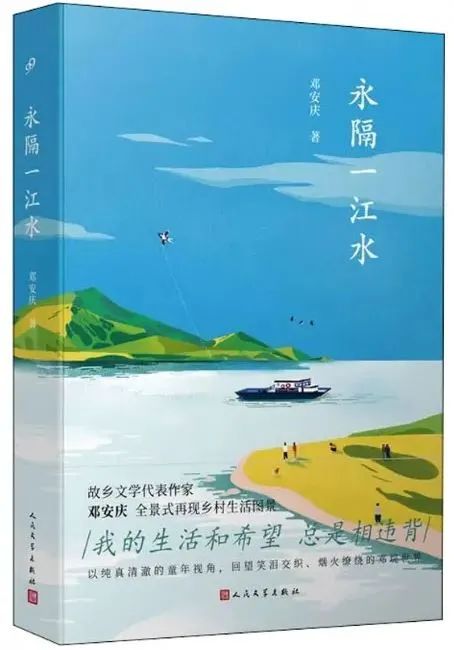

博物有时候就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地方风物,微小的事物和日常的乐趣,发现日常的存在和肌理,去抵挡空洞和不确定性,构筑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承平日久和物质丰裕的时代,生活的艺术和自然博物取向的写作的确有上升的趋势,精神生活和审美的问题越来越进入写作者的视野。文化与生态关系密切,韩少功在《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中把本地的生态、地理看作文化的成因与动力,“当我们看到很多文化创造者坚持多样性和原生性,用独特来对抗复制潮流,用深度来对抗快餐泡沫,他们总是会把目光更多的投向自己的土地、自己特有的生态与生活、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资源。一些被都市从自然生态中连根拔起的人,似乎正在重新伸展出寻找水土的根须。”韩少功的《山南水北》、阿来的《成都物候记》可以看作这种生态观的体现,突破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城乡分野,在自然世界中借助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自然生态和民间传统智慧构筑和想象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我们看到图书出版市场诸多关乎自然生态的非虚构作品翻译进来,比如译林出版社的天际线丛书《云彩收集者手册》《杂草的故事》《明亮的 泥土:颜料发明史》《鸟类的天赋》《水的密码》《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望向星空深处》《鸟鸣时节:英国鸟类年记》,图书品牌以“天际线”为名,是天空与大地、自然与文明的交汇,取其广阔、辽远之意,表达人类望远而知新的渴望。这些书均以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某一个侧面为切入点,凭借广博的视角和生动的叙述,在看似平凡的事物背后钩沉丰富的历史,找到自然世界与人类文明各个层面的纽带。商务印书馆的“自然文库”旨在复兴博物学的传统,追溯人类对自然也包括对自身的认识历程,通过创作者的求知与实践,激发都市人重拾对有灵万物的信仰和谦卑,《寻鲸记》《寻找金丝雀树》《鲜花帝国》《看不见等等森林》《流浪猫战争》等等以及后续的《寻蜂记》《寻蚁记》,以其丰富的题材和广阔的生态关注,不断冲击和提高着我们对自然生态的认知和理解。在科学认知和实践行动的参照系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此类样本较为稀缺,与万物荣辱与共不仅仅是写作对象的问题,山水、动物、植物、地域这些单就写作对象而言,我们的文学中并不缺少,反而有极其丰富的表达传统,比如发达的山水诗和景物自然书写,缺少的是系统与自觉性,自然山水的写作不是寄寓个人情怀和简单的方向转移,而是重视自然生态本身,自然山水不是以点缀、环境、背景、工具出现,而是被表达的主体。比如胡冬林的《山林笔记》,作为一本原生态生活记录,呈现了作家2007年5月入住长白山区至2012年10月的观察和思考。胡东林在2008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愈发明确了来林区的想法:确立自己今后的事业与方向;将终生喜好与理想融洽地结合;创造中国文坛前所未有的自然文学作品。”由此可见,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此类写作仍属凤毛麟角。《山林笔记》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游记散文,而是侧重对当地植物、动物等生态环境的记录和严谨科学的考察,间杂个人的生活起居,与猎人、山民、亲朋好友的交往,书中涉及到的鸟类190种、哺乳动物40种、节肢动物门昆虫纲52种,后期出版的时候附有作者拍摄的动物、植物、菌类的大量照片等,更直观地展示了作家所挚爱的山林生态。在《山林笔记》中万物存在与自我的存在合为一体,《文艺报》记者李晓晨记录过胡东林在山林中经历的重要“事件”,2007年,胡冬林发现一处距长白山保护区仅300米的山火,及时报警避免了山火蔓延;2008年,他举报当地主管部门在保护区砍伐树木、兴建别墅,带记者调查走访20多天;2012年,他发现国家濒危动物极北小鲵的栖息地,建议有关部门采取保护措施,他举报盗猎分子猎杀黑熊,配合公安机关迅速破案……胡冬林也把这些故事变成文字、照片。写作本身改变了写作者的生存状态,与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拉开了距离,他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山林,并作为一个行动者加入到对山林的保护中去。非虚构写作特别强调的“在场感”和“行动性”,都可以在胡冬林的作品中感受到,写作对象不仅仅是审美对象,还是科学研究对象,是写作者的共存对象,在思想、情感和行动上与之融为一体。

在“森林书桌”前写作的作家胡冬林
在文学领域谈论生态写作,经常追溯到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其发轫之初建立在对启蒙现代性和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反拨,并构造了一个基本认知框架,胡志红在《生态文学精讲》中概括为矫正社会主流发展范式、唤醒普遍沉睡的人类生态艺术、建构生态文明、推动社会生态变革。而生态文学主要内涵也有一个大致范围,描写非人类自然生态及物种之间的关系、探究人之肉身和精神对自然生态的依存并反应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纠葛,深挖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开展对启蒙现代性和工业文明的全面、深刻的批判、反思、纠偏及抗拒,探寻走出生态危机的文化路径,以重拾人与自然生态间本然一体共生的关系和永续何写。每一个时代和社会中的生态写作各有差异,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框架和思想认知上看大同小异,并且已经刻入生态文学写作的骨髓,并无殊异新鲜之事。
在固有的意义上打转,容易让生态文学偏狭化为休闲愉快和复归自然的代名词。生态写作公认的重要作家梭罗,苇岸认为人们谈论梭罗大多时候把他描述为一个倡导并身体力行返归自然的作家,其实这对梭罗可能是种误读,或者说不够准确和全面。梭罗的本质主要的不在于对返归自然的倡导,而在其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梭罗不是我们熟悉的陶渊明式的隐士,也不是机械地不囿于某个职业和岗位,而是整体地表达写作者对世界的态度:是否为了一个“目的”或者“目标”,而漠视或者牺牲其他。梭罗在自己特立独行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和著述之外,对美国当时的奴隶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拒绝为存在奴隶制度的政府缴纳人头税,组织营救南方奴隶抵达加拿大,帮助被捕的废奴主义的领袖,同情印第安人等。大部分人把两个梭罗孤立起来看待,固然可以塑造出一个更易被传播和接受的生态主义作家形象,但实际上是缩减了生态写作和一个作家的复杂性。

生态写作从来不应该等同于简单的山水意识、诗意生趣、和谐相处的同义反复和现代泛神论,生态自然写作如何深入是当下中国自然生态写作需要回应的问题。在生态与写作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会议非常值得回顾,1999年10月由海南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与生态”研讨会,国内关注生态问题的作家学者韩少功、张炜、李锐、苏童、叶兆言、乌热尔图、李陀、黄平、王晓明、陈思和、王鸿生、耿占春等人参加,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讨论了一系列问题。李少君根据发言人的观点和临近思路,整理出《南山纪要》,其基本观点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对中国和全球带来巨大的破坏,环境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从性质上说环境—生态问题涉及到对自然资源如何占有、如何利用和如何分配的问题而这种占有、利用和分配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下发生和展开的。对这些社会领域和社会过程的关注、反思、批评是人文—社会科学者、作家—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传统的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山水自然之爱,对动物的尊重等等人文主义视角已经不足以面对当下的问题,一些自然生态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带来更有力量和深度的关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新兴科学的视角,让生态问题更加立体。《南山纪要》的结尾发出呼吁,超越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思想定势,从人类/自然,市场/政府,社会/国家,现代/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增长/贫困,发展/环境等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和媒体流行话语,正在妨碍人们对历史和现实作出真切而准确的诊断。从这个问题上看,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固然还以熟悉的方式表达着相关内容,但面对新的形势都有捉襟见肘之感,需要混和的文体和表达方式的突破,也需要写作者的实践行动和认知框架的革新。
兴安在《自然写作:一种文学与生存的建设性选择》一文中重申“自然写作”开放性的特质,可以在不断地扩大写作范围和主题中获得新的可能,与此相应,“自然写作”理应是一个“跨文体”的写作,它不应拘泥于一种文体,也不应该纠结于体裁是散文或者小说,它应该包含文学的所有样式。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纯文学的诟病也恰恰来自于,日渐失去问题意识,失去发现问题和回应现实的能力,一个有效的文学话题,或者一种有效的写作,应该是可以容纳更多社会共情和核心关切的写作,在生态和自然的写作之中,固然博物、科学和实践性的方面能够让我们更容易辨认出它们的身影,我们还应该在其中看到国家、族裔、文明、政治、经济、信仰、阶级、性别、趣味和人性等等与今日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而在文体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问题意识带来的变化,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墨菲《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天地》以“自然取向”的文学指代这个庞杂的文类,并宣称其为“国际性的多元文化运动”,在这个多元化的运动中,非虚构写作在其中显示了重要价值。生态写作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都是与环境生态相关的非虚构作品,在其中我们看到了生态环境“事件”(DDT的滥用导致环境失衡,过分关注经济导致的环境失序),事件对社会生活产生的改变,从作家们的视角还原出问题的产生,写作者带领我们去追根溯源,不停留在“诉苦”与哀悼的情绪类型中,而是抽丝剥茧地找到与更大事物的关联,引起世人警惕,甚至带来社会政策和认知的改变。自然生态写作在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环境生态问题上,基本都是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呈现的,在这些写作实践中,写作是一种思考和改变世界的方式。

工作中的蕾切尔·卡森
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说,这是一个专家当道的时代,这些人出于无知或者偏狭,总是只盯着自己的专业领域,看不到背后反映出的整体问题。这也是一个工业化生产的时代,只要产品能赚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不会有人质疑。公众看到了杀虫剂所致的灾难性后果而提出抗议,却只收获一些半真半假的安慰。我们需要戳穿虚伪的承诺,剥去那层糖衣,正视难以下咽的苦果。承担害虫防控风险的群体是人民大众,所以只有大众才有权决定自己是否还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做决定的前提是完全掌握事实。自然生态写作是多种多样的,也吁求着新的突破,但非虚构写作对真实的诉求,强烈的问题意识,田野调查的方法,会对未来中国的自然生态写作提供深度支持。
原标题:《项静:从博物到非虚构:自然生态写作的一条路径 | 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专栏》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