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正在消失|随机与匿名
视觉艺术的历史,是观念、技艺和物质互动的历史。观念是指社会观念,不一定指艺术家特有的观念。大多数时候,艺术家没有什么独特观念。在欧洲,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为社会提供观念冲击,这种现象出现得很晚,可能和摄影的发明和普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艺术从其他社会场域分化出来,不会早于1840年代。
逻辑是这样的:摄影发明后,制作图像的门槛突然变低了,图像的物质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制作图像的传统技艺随之贬值,原来以制作图像为生的人群发生了分化。观念的重要性渐渐超过技艺。艺术的定义、艺术家的身份意识和艺术史这门学问,差不多都是这时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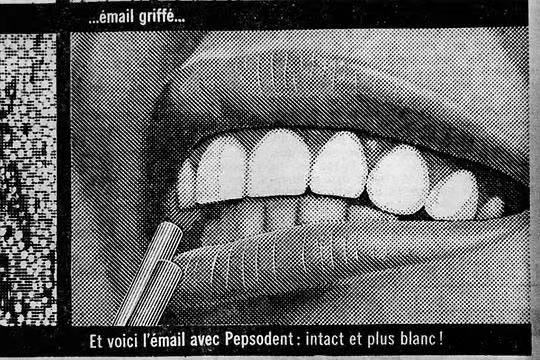
现代艺术发生学与摄影发明史之间的联系,当然无法坐实。谁也不能构建一套实证主义历史叙事,证明现代人对艺术的理解与摄影的出现有排他的因果关系。但摄影出现后,传统视觉艺术的确朝着远离技艺而倾向观念和社会解释的方向演化。到了工业时代,视觉艺术的技艺部分,就被匿名的设计者/摄影师和批量生产的流水线/照相馆取代了。艺术家的工作,变成通过命名和介入,把商品场域和艺术场域连接起来。杜尚如此示范这个过程:他去商店买了一只小便池,签名后送去参加艺术展览。艺术的历史于是借着这个小便池发生了不可逆的转折。
一旦艺术变成展演观念的过程,就有了流动性。观念在交流中不断变化,找不到固定起点,也永远不会终结。艺术品不再囿于作为展品、收藏品和财产存在的物(things),还可以是打破场域和身份界限进行观念交流的过程(events)。作为中间人,艺术家必须了解不同场域的人在观念和行事方式上的差异,而不再以精通某种技艺为前提,也毋需以手艺人自居(当然其人可以精通技艺并且以手艺人自居)。艺术范围内的一切都媒介化了。展演观念的过程中用到的物与技术,在场与不在场的人,不管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都是媒介。身体也不例外。
形式从前以技艺为前提,也就是贡布里希所说,艺术新风源自传统,归于传统,个人只是在传统中传承并改进技艺。身体是技艺的载体,也就是传统的媒介。但作为技艺,操作相机的流程与方式是标准化的,标准曝光效果可以提前度量并制成表格,正如一张照片在商品或意识形态语境中所处的位置,也常常是标准化的。

巴黎,1971年10月,中平卓马
技艺,也就是具身性,在摄影中的发展,被光学机械和化学反应的客观性所抑制,也使得摄影的风格发展特别依赖光学系统和感光器材的设计。光学系统从大型座机到小型便携相机再到有自动曝光功能的电子相机,感光器材从湿版到干版到胶卷,再到半导体感光器件,都会引起观看方式、拍摄方式和照片风格巨变。摄影文化往往随之转型。
与标准化的曝光技术相应,商业摄影、新闻摄影和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社会纪实摄影,效果非常容易预测。因为它们都有相对固定甚至是标准化的图式。这些图式构成了摄影的主流传统。成为职业或专业摄影师,就是个人被纳入这个主流传统的过程。PROVOKE时期,中平卓马反对的正是“个人被纳入传统的过程”。中平起初觉得,独特的图像源于独特个性对世界的反应,从形式或者说风格入手,疏离甚至反抗传统和主流的图式,是可能的:
……图像首先是世界在个体身上的一种函数式的反应。不管怎么样,那里就是世界-个体这种直接的对应,所设想的是世界就是世界、个体就是个体这种明确而不可动摇的关系。那么所谓艺术就是这种关系的个体性反映的外化或表现。正是这种反映在各个作家身上的微妙偏差,保证了艺术家的个性。不仅仅是在艺术领域里,甚至在生活领域中,个性曾经都是一种如此受到尊重和被神圣化的东西。(《为什么,是植物图鉴》,123页)
在现代艺术中,个性是否真正可靠?“二战”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回到法兰克福大学,重建文化研究所,将战争期间在美国体验到的发达商品社会的经验变成理论叙事,其要旨是,主流文化会通过吸收边缘文化的特征,来抑制其叛逆的内涵。在出版PROVOKE的过程中,中平卓马亲身体会到,此理论一步步被发生在日本社会的事实所验证。结果,PROVOKE的摄影风格变成一个新的商品种类。作家/艺术家的独特性,不过是梦幻泡影。所谓风格,随时可能被复制,并在此复制中被转变成毫无个性的商业包装。在此意义上,森山大道和筱山纪信一样,变成了完全可预期的商业摄影师。
中平熟知艺术史。个人风格消失在可复制商品的洪流中,是杜尚这代艺术家最早身临的情境。立体主义想通过强化个人风格的方式,来对抗这股可复制洪流,而达达主义和杜尚选择顺流而下。不是消融于其间,而是将复制这个社会事实置于艺术观念中心,通过对复制品和复制/消费过程的凝视,将复制品和复制过程转变为艺术。

1971年10月,中平拍摄的展览现场照片(然后又加入了当天的展览)
经过相当复杂的考虑,1971年10月,中平赴法国参加巴黎青年双年展,作品名称“循环——场所、日期、事件(Circulation: Place, Date, Events)。分配给中平的展位是一堵4米高、15米宽的墙。从当年10月10日起,他每天外出拍照,晚上回到暗房冲洗底片,扩印成照片,不等照片干燥,就贴在墙上进行展示。一周时间里,中平每天制作200张照片,不但贴满自己的展位,还扩展到展场其他空间,直到10月18日退出双年展为止。
很难知道中平拍照和制作照片的细节,但通过当时的文章和事后回忆,可知与PROVOKE时期的思考和摄影实践完全不同。
……如何从作为制度的艺术展览、作为制度的艺术,以及作为制度的艺术家中摆脱出来,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唯一问题,只要我们不考虑从中摆脱出来,那么所有的表现肯定就只是普通的构思、普通的时尚,而且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被还原为一种商品。
……如果是把我在日本拍摄完成的照片送去巴黎,这种做法我是比较反感的。把摄影塞入个人作品这种小框架中,想要在作品中涂抹上自己的那些若有若无的主张、“思想”,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我拒绝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念以作品这种形式来外化……

1971年10月,中平拍摄的展览现场照片(然后又加入了当天的展览)
在中平的设想中,在巴黎每一天拍摄的照片,都是无我的:
……我要将隐藏在一张照片背后的我个人的意义彻底擦拭干净。到那个时候为止,我的照片抛弃了“我的”这个所有格,拒绝让照片成为个人独占的作品,尽管是一堵从我身上穿过的东西,但应该是无限地接近现实。
那是一种进行当中、不断被覆盖的、“仅限一天的现实性”,包括可以转化为照片因此是可见的现实,也包括无法通过媒介再现的看不见的现实:
大概,我所谓的表现,并不是展示、堆积的照片之山,而是包含了拍摄照片、显像、赶到郊外的会场(正好赶上巴黎地铁罢工,就乘坐的士,有时候甚至要靠搭便车才好不容易去到会场)进行展示等所有这些基本上就是近乎徒劳的行为。按照某种看法,这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的无偿性、无目的性极其相似。
总之,中平想要复制而不是再现世界:不是为了通过照片及其视觉风格来呈现作为主体的拍摄者对世界的认知,而是让世界如其所是地随机显影在一种无意志的媒介上。
将自己变成现实的复印机,随机地制作一种去作者、无标识的图像。只有随机性,才可能消除摄影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即拍摄者为主体、世界为客体的二元论,而只有匿名性,才能防止摄影被制度和商业的逻辑吸纳。在中平的摄影生涯中,巴黎时期只有七天。这七天时间里,作为理论家的中平将自己的逻辑推演到极致,而作为摄影师的中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自己的逻辑做出反馈。他第一次感到知与行可以互洽。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