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评展|柏林双年展:讨论危机,“搏斗”议题
近期,第12届柏林双年展“仍然存在!”(Still Present!)正在展出。这是一场不带幽默感的严肃的展览,其目的是抚平“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积累的所有创伤”。展览冒着概念超载的风险,讨论了当下所存在的各种危机。双年展在与议题“搏斗”的同时,也在与自身“搏斗”。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柏林学习后于1843年写道,要想象一个新世界,你首先要严格地解构旧世界,“对一切现存事物的无情批评”。
这一批判精神弥漫在今年的柏林双年展(Berlin Biennale)上。本届双年展在柏林的五家博物馆展开,策展人是法国-阿尔及利亚籍跨学科艺术家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处理,你都会立即看到与战争及殖民主义遗产作斗争的艺术作品,有关于种族、性别、阶级,还有关于生态破坏、虚假信息及社会问题的。
从KW当代艺术中心开始,你会看到一个墙壁大小的装置,里面有20世纪80年代住在巴黎的葡萄牙及土耳其工人的照片和视频采访。该作品由女权主义艺术家尼尔·亚特(Nil Yalter)创作,名为《背井离乡是一件艰难的工作(Exile is a Hard Job)》。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作品《Air Conditioning》
在当代艺术博物馆(Hamburger Bahnhof museum)的第一个展厅中,沿着四面墙的水平带展示着连续的关于云的图像。这不是一张照片,而是由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根据以色列在黎巴嫩领空上的15年监视飞行数据制作的合成图像。
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边的德国艺术研究院( Akademie der Künste),你会进入一个空间,里面挂满了摩西(Moses März )的巨幅绘画作品。这些作品描绘了政治网络和思想史,其中主题包括了激进的生态、被掠夺的艺术品归还问题、德国的黑人政治和反种族主义。
今年的柏林双年展“仍然存在!”(Still Present!)是一场严肃的展览,将持续到9月18日。虽然本届双年展也包含优雅的瞬间和一些令人感动的片段,但大多时候,它并无幽默感。在参展的69名艺术家和团体中,有这个圈子里的老手,也有不少新人。这并非是一个“全球南方”展览,展厅虽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欧洲艺术家作品,但依然包括了不少来自越南、印度和阿拉伯语国家的艺术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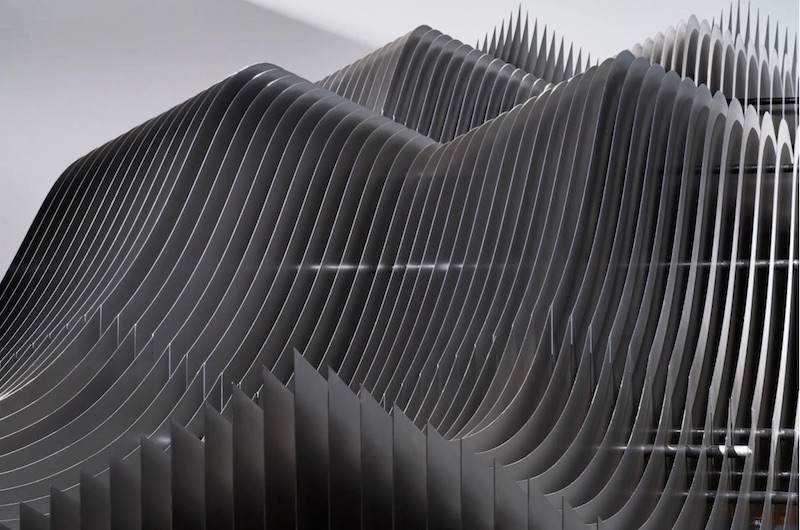
越南艺术家Dao Chau Hai作品《Ballad of the East Sea》
这是一场强有力的展览,而非令人愉悦的展览。双年展在与议题“搏斗”的同时,也在与自身“搏斗”。阿提亚的策展声明指出,今天“大量的、庞大的、巨大的展览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物质过剩”,并问道:“那为什么还要再办一个展览呢?”
阿提亚得出的答案是,艺术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算法强制的社会监控中收回来。这是一个过渡点,在艺术家的引领下,旧的被抛弃,新的被接纳。
这种观展经历可能会让人觉得无情。屏幕上有大量的纪录片和调查性质的艺术。开创性的数据和视频研究机构Forensic Architecture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展示作品包括一个大型装置,回顾了该机构多年来的一些重大调查,另一个装置是关于俄罗斯在基辅的一次空袭(虽然做得很及时,但不是很有启发意义),以及与该机构相关的研究人员的多个项目。苏珊·舒普利(Susan Schuppli)的视频展示了加拿大警察对原住民的暴行和美国边境人员对移民的虐待;伊玛尼·杰奎琳·布朗(Imani Jacqueline Brown)在一个更能唤起人们回忆的多媒体装置中,展现了路易斯安那州被污染的湿地,描绘了那里的危害,并提出修复建议。

伊玛尼·杰奎琳·布朗(Imani Jacqueline Brown)多媒体装置《地球的尽头还剩下什么?》
著名学者阿瑞拉·阿祖莱(Ariella Azoulay)在KW当代艺术中心中展示了一篇文章,探讨了二战后的视觉记录如何避免涉及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的强奸。但是,她的项目只是展墙上的一张小纸,再加上一个不允许观众拿起浏览的相关书籍表格,使得这一重要话题的展示是令人沮丧的。

阿瑞拉·阿祖莱作品
在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区中间,有一件作品显得怪异又令人厌恶,破坏了整个展览的平衡。法国艺术家让-雅克·勒贝尔(Jean-Jacques Lebel)的作品《可溶毒药》是一个房间大小的迷宫装置,隔板上布满了美国士兵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待俘虏时拍下的照片。作为艺术作品,它是淫秽的,但又是有效的。至少在这些事件的展示中重新点燃了人们的愤怒。
《可溶毒药》是本届柏林双年展中最令人震惊的作品,它曾在2018年巴黎联合展览中展出。此外,勒贝尔在此次双年展中还有另一件作品,创作时间比这件早了半个世纪。创作于1960年的《大型集体反法西斯主义的油画(Large Collective anti - fascist Painting)》是他与另外五名欧洲艺术家共同创作的,以回应阿尔及利亚活动家德贾米拉·波巴查(Djamila Boupacha)被法国士兵虐待的事件,该事件后来成为一项公益活动。这是一幅略花哨的作品,有着独特的暴力风格。

让-雅克·勒贝尔(Jean-Jacques Lebel)作品《可溶毒药》

勒贝尔参与绘制的《大型集体反法西斯主义的油画(Large Collective anti - fascist Painting)》
除了能告诉人们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艺术中的某种欧洲与男性模式是如何在真实政治斗争中形成,勒贝尔的两件作品之间的历史界线可能是本届双年展最不具成效的载体。在《可溶毒药》的外侧,有一个警告标志,提示道,这幅作品描绘了激烈的暴力,但没有说明主题。它的指示是“经历过种族创伤或虐待”的人不应该进入这里。
幸运的是,这个双年展在多地处运作。虽然展览总体上与阿提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也得到了一个由五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组成的策展团队的支持。在安娜·特谢拉·平托(Ana Teixeira Pinto)、杜襄林(Đỗ Tường Linh)、玛丽亚·海琳娜·佩雷拉(Marie Helene Pereira)、诺姆·塞加尔(Noam Segal),以及拉沙·萨尔提(Rasha Salti)的共同努力下,她们打开了诗意的空间。

萨米·巴洛吉(Sammy Baloji)设计的装置作品
在西部的汉莎街区,那里的展览在采用环境导向的同时保留了社会和帝国历史的活力。萨米·巴洛吉(Sammy Baloji)设计的是一个令人感动的装置,包括了一个小温室热带植物(贸易商曾经把这种植物标本运到欧洲);还有展现的是一名比利时军队的刚果老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俘虏,并被迫参加了他们的民族志录音。不远处,特米塔约·奥贡比伊(Temitayo Ogunbiyi)的精美画作描绘了尼日利亚菜中的秋葵、水叶和其他蔬菜。

巴塞尔·阿巴斯(Basel Abbas)和鲁安·阿布-拉赫梅(Ruanne Abou-Rahme)作品《Oh Shining Star Testify》
巴塞尔·阿巴斯(Basel Abbas)和鲁安·阿布-拉赫梅(Ruanne Abou-Rahme)在三个大屏幕上创作的装置作品《Oh Shining Star Testify》充满了诗意和戏剧性,投射的图像被堆叠的木板分割,形成一种舞台布景。该作品使用了一段监控录像,一名14岁巴勒斯坦男孩在穿过隔离墙采摘一棵可食用的植物时,被以色列士兵杀害了。一些镜头、配乐和简明的文字,让这件作品具有古典的悲剧力量。

阮龙梅(Mai Nguyen-Long)的作品《呕吐的女孩(Vomit Girl)》系列雕塑,展现的是越南战争的历史创伤
法国的艺术团体PEROU则直指荒谬,将警察镇压和清理巴黎郊区一个吉卜赛人营地的视频文件与批准这些行动的市政命令放在一起,呈现出官僚的想象力与人民的利益是完全脱节的。
双年展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欣赏。就单个项目而言,阮龙梅(Mai Nguyen-Long)的作品《呕吐的女孩(Vomit Girl)》和《标本(sample)》雕塑系列讲述的是越南“橙剂”爆炸后的故事,艺术风格徘徊在俏皮与恐怖之间。莫妮卡·德·米兰达(Mónica de Miranda)在安哥拉宽扎河的红树林中拍摄了一部影片,郁郁葱葱,巧妙地将母系知识、内战和生态联系在一起。德内特·皮姆马克西·维达·阿拉奇奇格(Deneth Piumakshi Veda Arachchige)将欧洲博物馆里的斯里兰卡土著居民的照片、岛上的景观和艺术家自身相联系,以民族志的展示和自我雕塑的形式,呈现出摄影、雕塑、视频、文字等相结合的系列作品。

莫妮卡·德·米兰达拍摄的影片
马约里·查里(Mayuri Chari)用牛粪雕刻的外阴和在布料上缝制的作品则更直白。在印度教对纯洁的痴迷中,这一作品解决了印度对女性身体的羞辱。查里和另外两人——普拉巴卡尔·坎布尔(Prabhakar Kamble和比伦·亚达夫(Birender Yadav),他们来自印度种姓制度中最低的社群,他们的作品直指前线,带着一种物质上的紧迫感,展现的粪便、扫帚、骨灰盒、建筑工地的粗凉鞋等物品比任何政治宣言都要清晰。

马约里·查里(Mayuri Chari)作品

德内特·皮姆马克西·维达·阿拉奇奇格(Deneth Piumakshi Veda Arachchige)的作品
柏林双年展是自信而坚定的,从展览花名册和策展团队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广泛而又一致的全球愿景。当然,结果是五花八门的,人们必须研究这些延伸出来的作品表达,并试图理解这些碰撞。
展览的矛盾反映了阿提亚在展览文本和他过去的项目中大量引用的“去殖民”概念。这个词从学术界浮现出来,在艺术界流传了十年左右。“去殖民”起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他们认为整个现代世界的建设——实际上自1492年以来,世界受到了殖民主义、种族、等级等方面的污染。
传统意义上的去殖民化是一个关于政治的、领土的项目,对现代性没有内在的不满。而今天的“去殖民化实践”是关于改变知识体系的,一个更加模糊的、可能永无止境的项目。这次双年展是“去殖民战略”的集合。阿提亚写道,这项任务是抚平“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积累的所有创伤”。
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这些永久化的伤害,包括双年展和博物馆在内的每个机构都需要去殖民化。这届柏林双年展也难以避免这种倾向——表现出极重的自身独特的概念。即便如此,双年展在多个方面都巧妙地呈现出自由的创作之态。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作者系艺术评论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