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忧郁的解剖》到新经验主义:18世纪显微镜下的鸦片
【编者按】
在人类寻求短暂解脱的过程中,鸦片有着特殊的“魔力”。每天,它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慰藉,确保医疗护理体系的正常运转;同时,它也让很多人产生了毒瘾,加剧了人类社会最恶劣的堕落和剥削现象。从古至今,鸦片以合法或非法商品的形式遍布全球。在《天堂之奶:一部鸦片全球史》一书中文化历史学家露西·英格里斯描述了这一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当今美国、从罂粟乳汁到海洛因、从吗啡到人工合成鸦片的鸦片全球史。成瘾、贸易、犯罪、战争、文学、医学,尤其是金钱——一部鸦片史,半部是金钱对人性的嘲讽,半部是肉体与精神的悲歌。本文摘编自该书,澎湃新闻经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在“金酒热”持续的那些年里,社会不仅对醉酒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而且对人类情感的态度总体都发生了改变。在17世纪,被认为与身体感官有关的东西,越来越多地意味着对整个世界的感知。1621年,牛津大学的学者罗伯特·伯顿(1577—1640)写出了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探讨精神健康问题的著作。在那个年代,《忧郁的解剖——它是什么:忧郁症的种类、成因、症状、征兆以及几种治疗方法》一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一直颇有影响力。伯顿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但是他使用了化名),在书中写道,“我在写忧郁的问题,由于忙于写作,我躲过了忧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能比懒散更容易导致忧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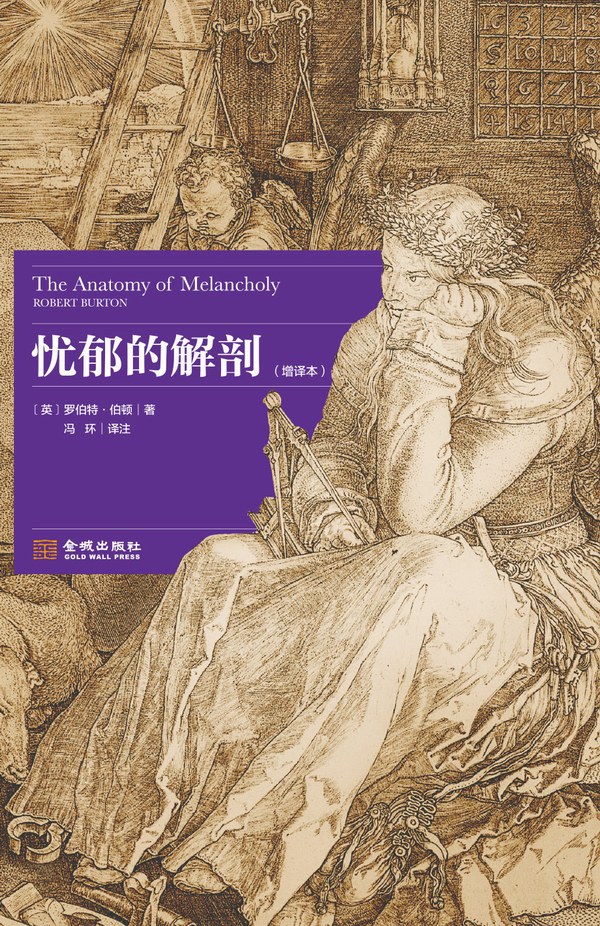
这本书涉猎广泛,既是一部医学教科书,又是一部哲学专著,其中涉及了现代心理健康最关心的问题。他对失眠及其伴生问题的探讨“始终充满了关怀、恐惧和悲伤”,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论述不断地被许多作家引用着。伯顿坚信,失眠患者必须 “立即得到帮助,要尽一切办法获得睡眠,有时候睡眠就足够治愈患者了,而无须服用其他任何药物”。为了帮助失眠患者入睡,他推荐了“罂粟”的基本成分,以及“曼德拉草、天仙子和大麻籽”,或者他称之为“鸦片制剂”的更复杂的药物。接着,他针对各种问题做了说明,比如如何服用这些调制的药物,应当吃哪些食物,甚至应当以怎样的姿势躺在床上,他推荐的睡姿“或许能让世上最忧郁的人入睡”。伯顿的这部著作十分冗长,里面不乏重复性的内容,但是对于现在被称为临床抑郁症的精神状态,书中收录了足够多的敏锐观点,因此对于接下来两个世纪的读者和作家来说,在有关精神健康问题的专著中,这部著作始终是最有影响力的。通过伯顿提供的各种复杂的治疗方法也不难看出,即使在他写作的那个年代,许多人仍然在几乎不间断地自行用药,乡下的穷人用煮熟的大麻籽治疗失眠,绅士们在家里将水蛭和鸦片敷在耳朵后。伯顿的这部著作含蓄地表明,精神健康、精神痛苦和鸦片制剂的使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在启蒙运动刚刚开始的18世纪,《忧郁的解剖》成了这类绅士的标准读物。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天赋的一个英国人,他一生都在与抑郁症以及酗酒问题作斗争,他曾说,《忧郁的解剖》“是唯一一本曾促使他比希望的时间提早两个小时起床的书”。
在约翰逊拜读伯顿这部著作的时候,欧洲已经发生了巨变。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被重新划定,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正在日渐衰落,萨非王朝也结束了。持续不断、毫无结果的战争耗尽了这几个帝国的资源,摧毁了它们的边境地区。欧洲与伊朗、埃及和叙利亚的贸易往来正在逐渐减少,与伊斯坦布尔和巴尔干地区的贸易往来则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在英国,虽然白色的埃及底比斯鸦片仍然属于上品,但是主要的鸦片供应方已经变成了土耳其,而不再是波斯。来自土耳其的鸦片“呈扁平状或者蛋糕状,外面裹着树叶,里面通常是一小包一小包的(酸模叶)。这种鸦片有一股浓烈的特殊气味,味道比较苦涩,令人作呕,长时间咀嚼还会产生一点辛辣的味道。它的颜色呈红棕色或浅黄褐色”。土耳其的鸦片甚至中国的茶叶、也门的咖啡等基本生活用品,随处都能买到,成了许多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到了18世纪中叶,不仅消费生活变得复杂了,精神生活也具有了一种新的重要价值。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这样的哲学家都在针对宽容和公民权利的问题著书立说,他们的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科学已经坚定地走向了以经验为依托的理性主义。1753年,杰出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将鸦片罂粟划进了罂粟属和罂粟种,并用一根别针在一个罂粟果上数出了超过32000粒种子。林奈发明的分类方法现在被称为“双名命名法”,这种分类方法在18世纪下半叶对自然科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迫使各学科的科学家们以一种相似的模式对自己的研究进行系统整理,这种模式远胜于他们以前使用的各种个人方法和一些古怪的方法。

罂粟
通过古老的手册、药剂师的店铺——也越来越多地通过鸦片酊、止痛药和多弗粉——鸦片几乎在每个家庭里都占据了一席之地。政府一心扑在蒸馏酒和“金酒热”带来的灾难上,这就意味着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药品界的这种可靠的备用品。进入一个出版和小册子盛行的时代后,社会上终于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在整个18世纪,一系列有关鸦片的著作问世了,这表明医学界对鸦片的态度有所改变了。其中很多作品都是在爱丁堡大学工作或者在那里接受过教育的人撰写的,在18世纪后半叶,这所大学培养出了全世界最杰出的一批医学学者。
不过,在此之前威尔士医生约翰·琼斯首先写了一篇论文,并被收录在了 《鸦片揭示的秘密》(1700)中。琼斯针对鸦片产生的效果提出的见解清晰而准确,并且表明罂粟种植在当时已经扩大到了多大范围。他偏爱埃及鸦片是因为这种药片靠近赤道,他认为那里更热,所以鸦片的效力和质量都胜过英格兰和德国“生产”的。就连“地中海边上的朗格多克(原法国南部一省)”出产的鸦片,都比英格兰和德国的更强效。他针对长期服用鸦片会产生的效果——“在老酒鬼身上看得到的”所有症状——所发表的观点,表明了滥用鸦片制剂存在的各种危险,但是他丝毫没有道德评判的意味,对鸦片的总体看法也是积极的。对于鸦片对感官产生作用的过程,他首先观察到了一种穿越的感觉,也就是一种离开平凡世界的梦幻般的感觉,这种感觉和毒品对人的精神产生的效果非常接近:“因此,在一定距离,别针落入一口铜锅的声响,听上去就像枪炮、铃铛之类的声音,在空谷里比在平原上更清晰、更悠远。”
与琼斯等作家针对鸦片提出的有用而古怪的建议相反,在“金酒热”过后出现的文章和专著开始对鸦片存在的危险提出警告。1742年,也就是多弗逝世的那一年,爱丁堡的植物学和药物学教授查尔斯·奥尔斯顿发表了《有关鸦片的论文》,这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对鸦片进行的药理学研究,其中一些研究是奥尔斯顿用自己种植的罂粟进行的。奥尔斯顿确信,鸦片能直接对神经产生作用,而不是通过“稀释”血液产生作用。不过,直到一个世纪后,他的这一观点才得到证实。
1753年,同样在爱丁堡大学工作的全科医生乔治·杨(1692— 1757)发表了一篇关于鸦片制剂的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警告:“每个人都知道大剂量的鸦片酊会致人死亡,所以我无须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但是,很少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慢性毒药,可事实的确如此。”奇怪的是,杨反对给极度疼痛的患者服用鸦片制剂,如肾结石患者,病人会对他的这种观点心存感激,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他在文中也通情达理地表示,患者的确需要服用适量的鸦片制剂,而且他还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大量试验。在当时,他对孕妇和儿童进行的研究也是最清晰的。对于孕妇的晨吐现象,他摒弃了体液观点,认为这种现象是“子宫出现的某种变化造成的,现在我们还无法解释这种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似乎对整个神经系统产生了影响”。他建议产妇在分娩时使用鸦片酊,不过他建议用量必须控制在减轻疼痛但是不会对母体产生抑制作用的范围内。对于处在断奶阶段的婴儿,他也建议服用少量鸦片,但不能“将其当作一种解药,被他们慈爱的母亲和各种果冻蜜饯一起喂给他们”。
1763年,伦敦东南部格林尼治医院的药剂师约翰·阿韦斯特出版了一本论述“鸦片作为一种毒药的作用效果”的小册子。鸦片作为一种毒药显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古代到中央刑事法院的记录,人们都曾使用鸦片,后来又使用鸦片酊来麻醉或毒害他们的受害者。但是,阿韦斯特在开篇就指出:“先生们,我之所以写下这篇论文是受到了一种欲望的诱惑,这种欲望要求我对一个迄今为止尚未得到重视,最多只能说有过一些模模糊糊研究的问题发表一些见解。”
无疑,这位药剂师认为,鸦片“最初是用来驱散心灵的焦虑、痛苦和不安的,这种用途看起来和欧洲人极其需要的致醉性饮料产生的效果没什么不同”。他断言鸦片在英国“没有得到普遍使用”,也不应该得到普遍使用,人们一旦熟悉了这种药物,就会失去 “阻止他们体验这种药物的巨大效力所必需的恐惧和谨慎,因为这种药物具有很多特性,如果人人都对其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会习惯使用这种药物,就会对它产生大量需求,甚至超过土耳其人对它的需求,事实必然会证明了解这种药物将给整个社会造成不幸的结果”。接下来,他介绍了一些治愈过量服药的患者的案例,他的描述表明鸦片制剂的滥用现象比他最初指出的更为普遍,泻药和催吐药中都含有鸦片成分,在帮助病人保持清醒和维持活动能力的时候,也会用到鸦片制剂。在给一个18个月大的用药过量的女婴进行治疗后,阿韦斯特还对托儿所提出了告诫,因为托儿所通常会让孩子们服用含有罂粟成分的糖浆,例如“戈弗雷氏露酒,这种制剂含有鸦片,它的使用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研制者的初衷绝对不包括这样的用途”。在18世纪末的时候,戈弗雷氏露酒已经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专利药之一,并且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药剂师
阿韦斯特这本充满警示故事、朴实无华的著作,显示出伦敦的医务工作者对鸦片制剂服用过量的情况非常了解。直到最近,我们的医疗工作者针对服药过量的治疗方法与阿韦斯特那个时代仍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本书很有价值,尽管其中包含的实践知识不无瑕疵,但是它显然是个人经验的结晶,表述方式也非常实用和严谨。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知识分子视野的拓宽,这种经验主义的精神在18世纪下半叶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爱丁堡大学工作的约翰·利(1755—1796)是一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医生。1785年,利针对鸦片的问题写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他借这篇论文向乔治·华盛顿表示了致敬。这篇论文获得了爱丁堡大学颁发的“哈维奖”,在次年发表后受到了广泛好评。在谈及鸦片模糊不清的起源问题时,利指出:“对于这种宝贵的药物及其价值最初是如何被发现的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作家向世界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许多人都依靠自己的想象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结果却只是提出了一堆五花八门的徒劳的猜想来填补这个自古以来一直令人神往的空白。”利在志愿者、动物和自己的身上进行了许多实验。
爱丁堡大学在这段时期里对欧洲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尽管其中一部分影响不像约翰·利的经验主义研究那么以事实为依托。与利同时代的约翰·布朗博士提出了一套被称为“布朗氏保健法”的理论,这套理论的核心因素是刺激———所有疾病都是过度刺激或者刺激不足造成的。处于兴奋状态的人需要服用催吐剂和泻药,无精打采的人需要鸦片和丰盛的食物。“布朗氏保健法”几乎就是彻头彻尾的江湖骗术,但是在德国和意大利极受欢迎,其影响力持续了数十年,不过这个谎言最终还是被戳穿了。
在爱尔兰的利莫瑞克大学工作的爱尔兰医生塞缪尔·克朗普曾是约翰·利在爱丁堡大学的同学,他对鸦片有着理智的看法。他在1793年出版的著作《鸦片的性质和特性研究》的开篇写道:“有一点似乎很奇怪,与这种非凡的药物有关的每一种情况几乎都受到了争议……然而,最新的经验似乎已经明确了它的生产和配制方法,从而消除了这些方面存在的一切差异。”
约翰·利和塞缪尔·克朗普都是富有天赋的作家及科学家,他们关于鸦片制剂的著作是所有先驱著作中最准确、最实用的。1786年利回到美国,他在婚后成了一位著名的———即使算不上杰出的话———彩票经理,最终他在40岁那年就去世了。克朗普则在29岁的时候突然离世,生前他凭借着关于爱尔兰就业和经济问题的著作,获得了爱尔兰皇家学院颁发的奖项。科学界的这种重大损失对爱丁堡大学和利莫瑞克大学的狗、兔子、青蛙来说,不啻为一种解脱。

《天堂之奶:一部鸦片全球史》,[英]露西·英格里斯著,徐海幈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