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讲座│张大春:不写“西方”小说,打造“笔记”神品
作为当世最卓越的华文作家之一,每本张大春作品的引进出版都几乎可以引起轰动。“春、夏、秋、冬”系列是张大春的著名系列笔记体小说,张大春在系列小说第一部《春灯公子》中化身说书人,“希冀带领读者重返古代中国热闹的说书现场与幽邃的故事秘林”。台湾INK(印刻文学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早在2005年便推出了繁体中文版,在大陆无数书迷的殷殷期盼中,简体中文版终于引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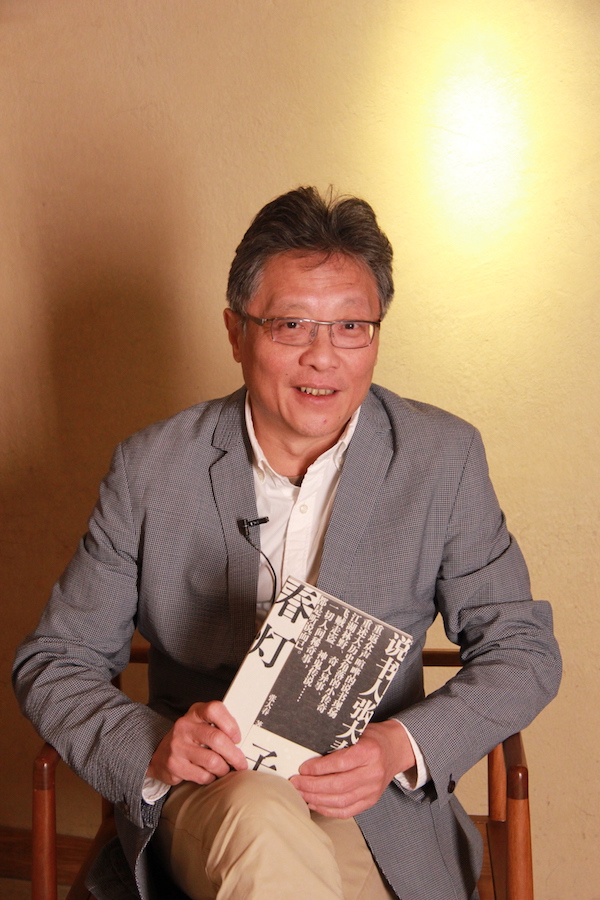
出品方华文天下图书公司近日接连举办了两场《春灯公子》新书发布与读者交流会,自少女时代就已经引起瞩目、现今已成长为大陆严肃文学代表性作家的张悦然担任了首场活动的嘉宾。现场气氛热闹非常,有“老顽童”之称的张大春自述其平生趣事时,更引发了在场观众不计其数的笑声,他可谓在小说之外的现实中也身体力行地践行了自己“说书人”的使命。

《春灯公子》复活的中国笔记传统
张大春享誉文坛多年,更是台湾文化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创作花样繁多,小说、诗词、京剧,乃至文学评论、历史评论、书籍导读、文章写作指南等等可谓无不手到擒来,并且样样精彩纷呈。与一些风格一成不变的作家不同,他几乎从不重复自己,每部作品更是都有独一无二的鲜明特点,梁文道因此赞誉他是“华文小说家里头装备全面、技法多变的高手——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样样精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他更得到了个无比形象的绰号——“兵器库”。
兵器库里花样繁多的兵器却苦了读者,他作品中左宜右有的技法和浩瀚磅礴的海量知识既容易令普通读者望而却步,也往往会让铁杆粉们爱恨交加、头疼不已。交流会甫一开场,就有读者把张大春与另外两位同样以“炫学”、“炫技”闻名的作家艾柯和京极夏彦相提并论,并迫不及待地提问张大春写作时是否考虑过读者会有阅读难度的问题。张大春笑言自己必须正面回答的话,“我从不考虑读者会不会觉得我的书难读”,顾文豪也打趣道这关乎张大春的书能不能卖得动,是他的夫人才该考虑的问题。

让张大春有足够的本事如此这般“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是他无比丰厚的古典文化修养。他自幼读书无数,从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成绩是第一名,他不但每天都“以古典诗为早晚课”,书法造诣更是非凡,除了“日复一日地读帖、写字”,在此次读者见面会中,他甚至给所有提问的读者都赠送了自己亲笔题写的福字或春联。张大春着重提及了中国传统典籍对自己的滋养,而他每每在床头翻阅的则是广文书局出版的《笔记丛编》,这近百册的历代笔记连句读都没有。
恰如顾文豪一再强调的,《春灯公子》正与这中国传统笔记小说有着本质性的关联。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提出了“史统散而小说兴”的重要命题,亦即中国的小说是源于史书的旁支,《儒林外史》里面的人物是走马灯式的,人物可以突然出现,也可以突然消失。这与西方小说中常见的连贯性人物描写和因果性故事逻辑截然不同,但这种故事的非逻辑性和叙述的松散性不但恰是张大春的创作手法,更是他一直坚持认为的“中国传统书场的叙事特质”的体现。
“立题品”的“品”更鲜明地暗示了张大春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接续——春灯公子在一年一度的春灯会上大宴江湖人物,每年的宴会则是由宾客逐个化身说书人,说一段令人咋舌称奇的故事,春灯公子则为这些故事以诗、词“立题品”——全书即由这二十段斗怪争奇的故事和实由张大春自作的二十首“题品诗”组成。

此书所有章节也都以“某某品”命名,比如《艺能品》、《聪明品》、《练达品》等等,仅有最末章《春灯宴罢》例外。但春灯公子在此章中给予了自己“炫奇品”的评价,当有暗指是书本身即为这第二十品“炫奇品”的含义。“品”的概念是中国文学独有的,它不仅表明了一种分类,也是一种价值观的指向,清代、民国编撰的笔记就是分门别类的,《清稗类钞》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在顾文豪看来,这种形式本身对应着的就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价值观,但西方小说的观念传入中国之后,传统的价值观就没有了。随着这种价值观的消失,这种“分门别类”的形式也就随之消亡了,但《春灯公子》令人惊喜地复兴了这种传统。

小说家为什么一定要是说书人?
《春灯公子》的编排体例也格外与众不同,很少有小说敢于像这本书一样在开首时即印上整整十九首古诗,而且是每首都排一整页,连续十九页竟全是古诗,仅有代表“炫奇品”的诗因张大春巧妙安排的结构而放在了全书最后。这种既不合时宜又容易吓跑读者的体例着实令人吃惊,当有读者问及如此编排的原因时,张大春的回答更是展现了 “老顽童”本色:“都是我好不容易一首一首写出来的,我舍不得放后面呀”!
其实在古代的书场里有所谓的定场诗,当说书人念起定场诗时,观众就应该准备安静下来听说书人讲故事了。但如果观众仍在吵闹,说书人就要先用一段小故事做引子,用一些讨喜的话把观众的注意力马上吸引过来,这就叫做“得胜头回”。张大春也希望放在前面的十九首自作诗可以起到“定场”和“得胜”的作用,让读者由他精心设计的古典诗词“陷阱”陷入到后面自己精心编织的故事中去。
张大春念兹在兹的,不是“小说”,而是“故事”。《列子·汤问》是超逸绝尘的千古名篇,汤以世上之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问革,面对这无解之问,革则以万般不可思议的神话传说与无数诙诡奇谲的海外之物相对。张大春的目光没有聚焦在《汤问》篇中有何莫测高深的道家思想,而是“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知道那些飘渺无迹的人、事、地、物之存在呢”?

革回答的其实便是那些“在流传途中历经不同的讲者、穿越不同的语境、透过现实的刺激和打磨,就会像历史、新闻、谣诼及所谓街谈巷议之类的本文一样,产生变化”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流传需要的是“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张大春由此点明了在他心目中“何为小说家,小说家何为”:“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尤其生于现代,经常自诩为创造之人,殊不知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夷坚、伯益、大禹。一旦听到了、看到了可喜可愕之迹,就急忙转述于他人,此市井之常情,一切都是听说而已。”这也正是他认为自己系列笔记小说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民间。”
说者,亦即说书人,便是张大春眼中小说家,也就是他自己的天命。他对古代说书人体现出的这种使命般的神往,与他对中国笔记传统的自觉接续一样,均可谓其来有自。《小说稗类》的写作时间较《春灯公子》更早,这部充满了睿智的著作全面体现了他对中西文学与小说理论的洞见,不但是论说中国传统笔记与西方现代小说关系的文论名著,更是他缘何这般理解故事与小说的关系和鼓吹说书人的隐秘钥匙。

中国古典之中的笔记何啻千万,笔记中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笔记之琳琅满目、巨细靡遗,连百科全书一词皆不足以名状,可谓一套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生活总志”。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他又不太赞成小说家直接“取用”传统笔记中的故事。
原来在他看来,“更多的笔记唯有在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时候才能见神采;它既不应被垂扁拉长变成一个短篇小说,也不该被前呼后拥变成一个长篇小说的填充物……真正的中国小说早已埋骨于说话人的书场和仿说话人而写定的章回以及汗牛充犊的笔记之中”。在他悟出这层道理时,说书人其实就已经在他脑海中登场,春灯宴则是他首次在纸上为说书人创造出的书场,所以《春灯公子》才得以成为“传统书场松散的叙述特质”的笔记体小说。
张悦然则用了一个神妙非常的比喻说明了笔记与小说的这种关系。她说故事是笔记里面干瘪的种子,“这种子冻在了过去的时代,冻在了过去的江湖里面”。而张大春则对笔记小说中的故事种子做了解冻,他让种子复活,让它们长成树,开出花:“这是很奇妙和难以置信的事情,我觉得这些故事本身不是一个扩写,这个故事的魂魄让人疑惑是属于原来笔记作者呢,还是属于大春老师呢?”
显然,她的答案是“这是他们共同的演绎”。
随手出神品,哪怕你说它不像小说!
“春、夏、秋、冬”系列笔记体小说并非没有借鉴西方的地方。早在1990年代中期,台湾便引进出版了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编写的意大利民间故事选《意大利童话》,而 “春、夏、秋、冬”系列创作的直接契机正是张大春对卡尔维诺的阅读。张大春不但意欲效仿《意大利童话》“用现代小说的叙述模式讲述民族传统民间故事”的形式,更明言自己铺陈故事的方法借鉴了薄伽丘的《十日谈》。

但两个传统如何在一个作品中碰面,对张大春而言才是“更重要的召唤和迷人的使命”。他要利用一些不为现代人所知的议论、资料、文献和夸张的形式,使自己的作品看起来像一种考证和学术工作,使笔记体小说可以负载原本在小说中不会使用语言,使不太像故事的故事可以呈现出一种民间传奇的感觉。由此,简陋而直白的笔记就被张大春找到了一种更为迷人曲折的叙述模式,他强调“这大概才是我做这四本书的根本动机”。
他从来都是西方“小说”观念和理论的反对者:“今世吾人所称的短篇小说也罢,长篇小说也好,原非本国固有……论体制,论理念,论类型,论结构,论布局,论技术,皆由移植而来”。与主流西方小说,哪怕是最前卫实验新奇变怪的西方小说比,旧时代中国作家的笔记都全然不同,但时下所谓的现代中国小说作品,在张大春看来“绝大多数只是用汉字凑成的西方小说”。汪曾祺却是少有的例外。张大春认为汪曾祺的作品中“非但不曾取用笔记,甚至在打造笔记,他用字精省,点到则止”,所有的现代小说理论对他都不适用,但也唯有汪曾祺是那“极少数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写作中国小说的小说家,一位深得笔记之妙的小说家”。
显然,张大春对自己的希冀也是与汪曾祺一样深得笔记之妙的小说家。这样的笔记体小说才称得上是中国小说,“随手出神品,哪怕你说它不像小说”!

最令读者们激动的,则是张大春公布的自己作品新的引进、出版计划。“春、夏、秋、冬”系列中的“夏”与“秋”分别为《战夏阳》和《一叶秋》,华文天下将马上陆续引进,“冬”还未完成,暂定名为《岛国之冬》,但这本书不会在近日出版,这是因为张大春还有很多旧作并未完成。
他拟以百万字篇幅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以及大唐盛世兴衰的系列作品《大唐李白》目前已经出版了三部,写作计划则一共有五部。张大春更准备为被广泛称誉为“《鹿鼎记》之后最好的武侠小说”的《城邦暴力团》写前传和后传,目前也已经写就了数十万字。
张大春对于时下的应试语文教学时的八股应试作文非常不满,去年在台湾出版、今年大陆已经引进的《文章自在》即是他试图扭转这种不良风气的评论文章首次结集。而最早在明年年初,同一写作初衷的《见字如来》就会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