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钱一栋评《刺猬的正义》︱德沃金的“终身大事”
刺猬和狐狸
“狐狸知道许多事情,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这是古希腊诗人阿基洛库斯(Archilochus)的一句诗。以赛亚·伯林在其名篇《刺猬与狐狸》中化用这两个形象来比喻两类思想家:刺猬型思想家试图找出可以解释万事万物的一元真理,狐狸型思想家则认为人事纷繁复杂,不可强求绝对真理。
在现代社会,当狐狸很容易博得掌声,做刺猬则要面对一系列知识困境,还会被认为有封闭、专断的潜在危险。德沃金就是一只执拗的刺猬,他的晚年名作《刺猬的正义》系统论证了他思索终身的那件大事:“价值统一性”(the unity of value)。

“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德沃金和罗尔斯
为了理解价值统一性命题的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扯远一点,谈谈德沃金与另一位大哲约翰·罗尔斯之间的复杂关系。
德沃金和罗尔斯立场相近,在政治光谱上,他们都属于强调平等的自由主义左翼,与持自由放任立场的哈耶克、诺齐克,以及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激进左派相对立。但在罗尔斯转向“政治自由主义”后,他们相似的立场背后有了极为不同的辩护路径:在价值多元主义问题上,两人产生了根本分歧。
需要说明的是,价值多元主义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标签。价值多元主义不仅主张存在多种价值,而且强调不同价值间不可通约、无法比较、相互冲突。如果我们进一步区分所谓的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观,那么这一标签将变得更为复杂。但借助对伯林、韦伯等人的大体把握,在不那么学究气的语境中,我们还是能自明地使用这一概念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从物质财富分配转变成了道德文化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罗尔斯从《正义论》的“整全性立场”退却到了《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之中。罗尔斯自己交代,他之所以对《正义论》作出修正,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多元主义的挑战:《正义论》构想的宪政民主社会必然是一个非同质的多元社会,存在多种而非一种道德观念、生活理想;而《正义论》的良序社会稳定性论证,以康德式道德学说占主导地位的同质社会为前提,简单讲就是社会稳定有赖于道德整合,因此《正义论》自相矛盾。《政治自由主义》的写作正是为了化解这一矛盾,使《正义论》前后融贯。罗尔斯后期理论的基本特点在于,它不再依附于某种道德哲学,而选择把政治哲学从道德哲学中切割出来,提出一套自立的(self-standing)、亦即纯粹政治的正义观,并希望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康德主义者、功利主义者都能基于各自的理由接受他的正义观,以此来克服多元主义的挑战。

《政治自由主义》
德沃金的理论发展也和价值多元主义有关,但他与罗尔斯在同一挑战面前分道扬镳。罗尔斯将多元主义视作需要回避的困难,德沃金则将其理解为有待纠正的错误。那么,以伯林为代表的价值多元主义错在何处呢?
伯林转行得失考
自分析哲学兴起以来,许多原本以“XX是什么”的提问形态得到处理的问题,被转换成了概念问题,比如罗素认为,正确的伦理学问题不是“什么是‘正义’”,而是“我们如何使用‘正义’这个概念”。
伯林出自日常语言学派,后来转行从事观念史研究。这一“观念史转向”并不意味着伯林的工作失去了哲学色彩。按伯纳德·威廉斯的说法,伯林是从一种遗忘历史的哲学,转向了一种关注历史的哲学。就此而言,伯林的观念史研究依然是一种关注概念的哲学研究,并且基于概念的历史维度,相比于坐在书桌前凭空思索词汇定义、考察概念用法,这还是一种更优越的研究方式。只有通过历史考察,了解先辈们如何使用自由等概念,我们才能理解这些概念的力量(force)。

但德沃金认为,历史研究只能告诉我们过去的人大致如何理解这些概念,却无法说明这种理解是不是最好的理解。古代人的自由关注的是公民从劳作中摆脱出来,投身于城邦政治;现代人的自由则强调不受政府打扰,过自己的小日子。历史研究可以通过分析特定概念的源与流、主流与“反潮流”,使我们敏感于这些概念在不同历史脉络中的具体用法,更好地理解不同时代人的具体言说,但也仅此而已。历史研究无法告诉我们“何种自由观才是最好的自由观”,在这类问题上,历史并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
德沃金认为,有些哲学家之所以强调概念研究必须带有浓厚的历史色彩,而不能进行相对超脱的概念建构,可能是因为他们将所有概念都理解成了“判准性概念”(criterial concepts),亦即认为人们在使用概念时遵循着同样的规则,如果违背这些规则,就只是在无意义地自言自语。这些哲学家大概认为,历史研究可以揭示自由等概念长久以来始终包含的属性,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属性就是概念的本质属性,因此借助历史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些概念的使用规则。可见,这种历史研究恰恰预设了一种非历史的概念观。

伯纳德·威廉斯
当然,许多概念确实存在共享的使用规则。普通人未必能明确意识到这些规则,因此需要由对日常语言敏锐异常,或精通观念史的哲学家来澄清概念,帮助我们摆脱无谓的争论。比如,如果当你说“菜”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与肉类相对的蔬菜,我想到的则是用来下饭的副食品,那么我们对“猪肉是不是菜”的争论就是虚假且愚蠢的,因为我们使用的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争论头发少于多少根才算秃头也是无聊透顶的,因为“秃头”这个概念的使用规则并不精确,说一个秃得不那么明显的人是或不是秃头都没问题,因为这种情况落入到了这一概念的边缘地带。围棋是不是体育、自拍是不是艺术、阿森纳算不算豪门、《上海书评》算不算学术刊物……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无可无不可的边缘争议。
在这些问题上,澄清共享的语义规则确实可以使我们穿透语言迷雾,聚焦实质争议。但德沃金认为,并非所有概念都是判准性概念。价值概念属于另一类概念,德沃金称之为“解释性概念”(interpretive concepts)。区分这两类概念是德沃金反击价值多元主义的关键步骤,德沃金认为,伯林之所以得出价值冲突的结论,与他忽视价值概念的解释性特征有关。
“文学是什么”:解释性概念与实践传统
所谓解释性概念,是指我们对概念的使用规则未达成一致意见,且没有决定性的检验方法来判断谁的理解正确,但依然共享的概念。我们且以正义为例,来说明解释性概念的特点。
我们可以给出“正义”这一概念的使用规则吗?罗尔斯认为,虽然我们在具体的正义观念上存在分歧,但在高度抽象的层面,我们有着基本的共识:正义就是不任意分配人们的基本权利义务,以恰当方式规范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但德沃金认为,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就无法作此理解。
因此,我们在正义这一概念上并没有共享的规则,甚至无法给出一个最抽象的概念性说明作为具体争论的共识平台。区分概念的边缘与核心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正是在正义概念的中心地带发生分歧。那么,这种争论愚蠢吗?自然不愚蠢。几千年来,哲学家、政治家、普通民众用正义这一概念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争论。争论者其实是在询问,我们用正义这一概念去评判的那些实践有何种本旨(point),对实践中人提出了什么要求。
类似地,当我们讨论的不是歌词算不算文学,而是《水浒传》算不算文学时,文学就变成了一个解释性概念,因为此时我们不是在文学这一概念的边缘地带进行细枝末节的讨论,而是在探讨文学的核心特质,在辩论“宣扬暴力” 的小说是不是违背了文学所承载的价值这样的“本质性”问题。

德沃金最关注的法律也是一个解释性概念。熟知各种法条的法律人依然在讨论“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似乎“法律是什么”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法律的规定不是法律文本白纸黑字都交代清楚了的。只有将“法律”理解为解释性概念,这种争论才能得到最好的说明,否则我们只能说,法律人太傻,在争论这些伪问题;或者法律人太虚伪,想用法律论证来包装自己的政治信念、道德立场。(参见Ronald Dworkin, Justice for Hedgeho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63-164.)
诸如此类的争论既不罕见,也不怪异。如果我们认为一切概念都是判准性概念,那么这些争论的正当性就很可疑了。不过,当理论与日常现象冲突时,问题往往出在理论一方。
既然我们在使用解释性概念并没有共享的规则,那么如何确定我们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呢?会不会出现我说bank(河岸)、你说bank(银行)的情况?德沃金认为,即使不存在共享的规则,甚至无法给出一个粗略的概念性说明,我们也可以针对同一对象进行真实的讨论。“我们之所以共享这些概念,是因为我们共享社会实践和经验,而这些概念在这些社会实践和经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Dworkin, 2011, p. 6.)
我们对“法律是什么”缺乏共识,但我们共同拥有法律这样一种实践,这足以使我们对法律是什么获得粗略的共识:我们都了解,法律与法院、法律文本、法官的活动有关。虽然我们在“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分歧颇多,但我们都同意诗经楚辞、李杜苏辛、四大名著是典范性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对“文学是什么”的争论就是围绕这些典范作品展开的。如果一种文学理论不能将这些典范作品囊括进文学的范畴中来,无法讲出它们的价值,那么这种理论就是失败的。当然,典范并非不可颠覆。一种激进的文学理论也许会把《水浒传》逐出文学名录,这种理论很可能是荒谬的,但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它乍看荒诞,但听完它的整个解释后,我们确实发现它对文学传统作出了更有吸引力的阐述。例如,强调文学应该表现阶级斗争的理论将主张阶级调和的小说贬得一文不值,转而抬高宣扬造反有理的作品。在这类文学观式微后,认为文学应该表现真实人性、侧重抒情的新理论出现了,于是,沈从文、张爱玲被拔高,鲁迅、茅盾开始遭受质疑。
因此,此类解释的对象是特定实践、某类传统,比如文学、艺术、政治、法律。实践传统是一代代人创造出来的,承载了特定的价值。在此意义上,德沃金的解释理论是一种实践解释学。解释性概念引导我们去反思,运用这些概念的实践具有何种目的,要实现哪些价值,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些价值。这些实践所承载的价值对回答“文学是什么”这类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此时我们不是在对文学现象作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而是通过诉诸自己对文学价值的某种信念,来建构最好的文学观念。
也许会有人说,这不是在探讨“文学是什么”,而是在构想“文学应该是什么”。但德沃金强调,虽然我们在回答文学是什么时必须诉诸自己的价值信念,可它依然是一种解释,而非纯粹的创造。因为,整个文学传统、典范性文学作品制约着我们,我们的解释必须使文学传统呈现为最佳形态,而非面壁虚构一种文学观。
因此,在“法律是什么”“文学是什么”这类问题上,共识与分歧并存。分歧的出现使争论成为可能,共识的存在则确保我们争论的是同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任何分歧,那只能说明这些实践传统还非常朴素、稚拙,或者已经僵化了;如果不再有足够共识,则表明这些实践传统已陷入混乱、濒于崩溃了。
简言之,在某种实践究竟要实现什么价值这一问题上,我们产生了真实的分歧,这种分歧是价值分歧。浪漫主义者认为文学是作者天才的流露;文以载道者坚持文学必须传播正确的道德观念。他们发展出了各自的理论,试图证明自己的文学观可以对典范性文学作品、对文学传统作出最富吸引力的解读。什么样的解读才有吸引力?这取决于我们的价值信念。因此,如果价值有真理,则解释有真理。那么,该怎样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呢?如何在价值问题上找寻真理?我们应该把权威词典上的定义视作对特定价值的正确解读吗?还是必须像自然科学那样去发现价值的本质属性、深层结构?
“终身大事”:价值统一性
自休谟提出事实价值两分法后,价值领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据麦金太尔考察,在目的论传统中,事实这一概念本就含有评价属性。(参见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 77.)但现代自然科学兴起后,事实被建构成了一个与价值相对立的概念。根据某种流行的偏见,只有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问题才谈得上真理,因此,只有事实真理,价值判断没有真假、无关对错,只反映了不同的主观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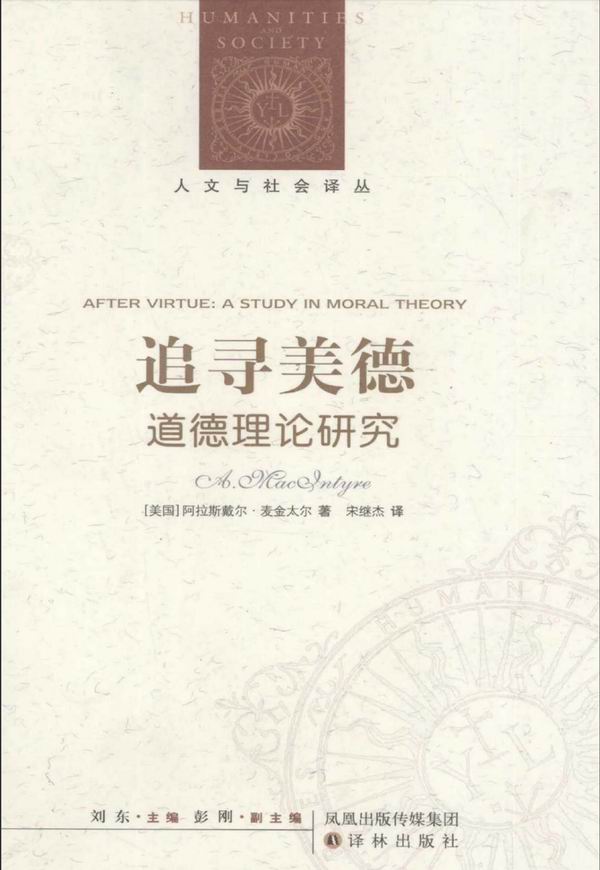
由此,出现了种种价值怀疑论,德沃金将它们细分为外部怀疑论和内部怀疑论。外部怀疑论是实在论的变体。和实在论一样,外部怀疑论也认为,只有客观存在的价值实体才能证实我们的价值信念。但在现代自然科学塑造的世界图景中,价值实体显然是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我们甚至无法设想它,更不要说发现它了,因此,怀疑论似乎不可避免。可以看出,外部怀疑论并不分析一阶的价值信念,它试图站在价值领域外的某个阿基米德支点上,对整个价值领域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然后根据某种形而上学观点否定价值真理的可能性。内部怀疑主义则是一阶的,它坚持一些实质性价值信念,根据这些信念来怀疑其他信念。
德沃金认为,休谟定律并不意味着怀疑论。休谟定律强调的是价值领域的独立性,即不能用事实性说明来为价值信念辩护,而要让事实的归事实,价值的归价值。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证成价值信念呢?我们不能用自由来证成自由,用平等来为平等辩护,这只是一种无力的循环论证。必须援引其他价值来为特定价值辩护,同时这一价值也为其他价值提供支持,最终,不同价值彼此融贯、结为一体。德沃金承认,这同样是一种循环论证,但循环的半径足够大。(Dworkin , 2011, pp. 99-100.)
举例来说,每个人对自由和平等都有某种前反思的理解,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自由观与平等观之间存在冲突。比如,如果我们认为自由意味着做什么都可以,平等则要求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那么,平等就与自由冲突了。可为什么要这样理解自由呢?自由没有分子结构式的客观本质,从我们对自由概念的使用中也总结不出一个无争议的语义规则,它是一个解释性概念,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提出一种更好的自由观。
我们前反思的价值信念是粗糙且不系统的。在反思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经历某种“价值惊奇”:发现自己最初理解的自由原来会与许多善好事物冲突。这一发现使我们放弃了原有的自由信念,转而构建一种更富吸引力的自由观,以更准确地表达自己深思熟虑的信念。因此,为价值信念辩护就是一个在诸价值间建构融贯秩序的过程,当发现诸价值构成了融贯的整体,且这一整体表达出了自己真诚相信的信念时,我们就可以负责任地说,自己获得了价值真理。
德沃金强调,这种真理是客观真理。他所谓的客观当然不是“价值信念符合价值事实”这种符合论意义上的客观,而只是对真理的一种强调:这确实是真理,是不偏不倚的个人所持有的信念,而非主观偏好的表达,更不是在诉诸某种形而上学立场。

结语或开端
德沃金一生著作宏富,《刺猬的正义》是他的集大成之作。此书囊括了德沃金在其他作品中处理过的所有主题,并将这些分属于价值理论、解释理论、伦理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的论题纳入了融贯的整体阐述之中。可以说,德沃金一生都在写作此书,之前那些作品都是这本书的局部习作、长篇注释,以前那些令人费解的观点也终于在这个融贯整体中变得清晰且富有说服力了。对尚未读过德沃金的读者来说,这本收官大作也许是进入德翁思想体系的最佳入门读物。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